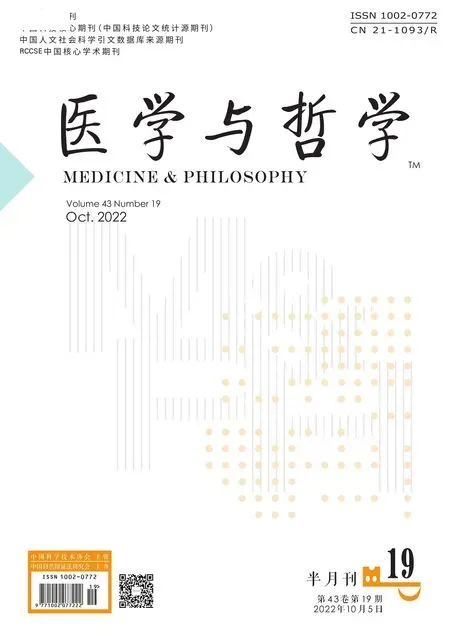生物道德增强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
叶岸滔
1 生物道德增强中人格同一性问题的提出
人格同一性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人独特的、区别于他人的属性。一个人拥有的任何持久的特征都可以成为识别其身份的一部分,拥有越多这样的特征,就越有助于突显一个人的独特性,从而有助于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帕克(Parker Crutchfield)等[5]引用不少经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揭示一个人的道德特征对于这个人的身份识别至关重要,他们认为人格同一性可以是个人的道德特征构成,当一个人的道德特征发生根本变化时,他的身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帕克解释,道德特征被广泛地理解为包括道德信仰、态度、动机、性格或情绪等,道德增强其实就是通过生物手段操纵一个人的道德特征。经过道德增强之后,这个人就失去了他的基本道德特征,有了一套区别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特征,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法比亚诺(Joao Fabiano)[6]也认为,人的身份与道德品质特征联系密切且直观。在实践中,人们也倾向于把道德行为与个体的身份联系起来,因此道德感是构成一个人身份的核心方面。从根本上增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最终可能导致构成一个人身份的特征被彻底毁灭。马西莫(Massimo Reichlin)[7]认为道德进步的传统方式和生物技术方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道德增强可能会对道德主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为道德增强会严重破坏主体自由,改变我们的身份和道德人格。因此从这些观点可以预见,道德增强的方式会影响到人格同一性,这种增强方式虽然不会改变人的外表,但会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可能改变个体体验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导致个人身份剧烈的变化,甚至无法被识别。然而,也有不少道德增强支持者则认为,道德增强很少会带来人格同一性的改变,自主性也难以受到影响[8]。道格拉斯等就认为道德增强不太可能影响人格同一性。他们强调,道德增强不太可能影响人的记忆或心理连续性,因此个体在使用道德增强前后依然为同一个人[9]。道德增强是否会对人格同一造成影响,让人们面临和经历自我同一性的重大转变?道德增强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能否进行辩护或在何种程度上能获得辩护等,都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一些学者也指出,不管道德增强的讨论如何,我们需要在道德增强中对人格同一性和所有与人格同一性相关的人类特征进行适当考虑和相应的关注,以免我们创造出不属于自己的存在[6]。
2 生物道德增强中人格同一性的论证与分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格同一性的研究很多,切入点大多集中于两方面,即数字同一和叙事同一。数字同一讨论的是道德主体在时间变化中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主要为道德主体在经历变化后而继续存在提供标准和辩护,如身体标准,心理标准等。叙事同一讨论的是个体的自我概念,角色认同等,涉及如何通过一些核心和突出的特征来定义自己的问题[10]。考虑到生物道德增强的特殊性,其人格同一性问题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证与分析。
2.1 生物道德增强中的身体同一性问题
身体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因其具有直观的特性,往往被我们视为表达和确定自我存在的优先标准。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变化,性格、处世态度和原则等都会随着阅历的发展而不同,但是主体始终依然是自己,这是一般人从身体直观的角度对人格同一性的基本感知。我们是否可以从身体关系来判断一个人在道德增强后是否保持人格同一?
通常从身体关系来判断人格同一性的标准可以表述为:如果P1是一个在T1时间里的人,并且P2存在于任何其他时间,当且仅当P2的生物有机体是P1的生物有机体的连续,则P1=P2,即P1和P2为同一人[11]。按照这种标准,从表面上看,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实现道德上的增强并没有造成身体上的剧烈和根本的物理变化,一个不道德的人变得有道德和一个有道德的人变得更加有道德,依然属于同一个生物有机体,从外在的观察上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两者前后之间继续存在着物理的连续性。因而,有观点会认为,从身体关系出发,道德增强并不会干扰个体人格的同一。
然而,这种观点至少有两个问题没有梳理清楚。第一,身体标准有严格和宽泛的区分,主张道德增强不会干扰个体人格同一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严格的身体标准的理论主张。严格的身体标准会认为,身体应该要完全同一。这种标准强调,哪怕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都不能视为身体的连续和同一。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尽管道德增强从表面上看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外表,但会潜在地影响一个人的神经功能以及意识和行为的发生机制等,这种影响可能包含一些不可逆的大脑生理结构的改变或者某种激素水平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道德增强实际上破坏了人的身体连续性,从而导致人格同一性的中断。第二,即便遵循一种宽泛的身体标准,承认身体会有一定程度的物理变化,承认这些生命的必然变化并不影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连续性,如细胞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等,身体标准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双胞胎问题和脑移植问题。两个双胞胎身体结构完全一样,我们不可能会认为两个双胞胎会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习惯等都可以不一样。脑移植问题也一样,如果将大脑A 移植到个体B 上,那么拥有大脑A 的个体B 还是之前的那个人吗?在道德增强中,尽管一个人的身体外表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内心世界却可以发生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外表不变就是同一个人,就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因此,身体的标准过于宽泛,身体的同一并不意味着人格的同一,仅从外在观察角度来判断人格同一性问题过于简单和轻率。
2.2 生物道德增强中的心理同一性问题
心理特征对人的持续存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完全失去了心理特征的人,他可能就没有了存在意义和条件。因而相比较身体的连续性而言,心理的连续性更具有吸引力。人格同一性的心理标准一般是这样表述的:P1在T1时间里跟P2在T2时间里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P1是P2唯一的心理连续[12]300。于是,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具有心理联系,仅当今天的我具有昨天的我的心理特征。
在心理连续性中,被讨论很多的是洛克关于记忆的连续性。这是因为正是记忆使我们绝大多数人意识到自己在时间向度中的连续存在。洛克[13]310认为,同一性就只在于意识,而意识又借助于记忆。一个人的意识在回忆过去的思想和行动时,它追忆到多远的程度,人格同一性就达到多远程度。一个过去的或将来的存在物是某个人,当且仅当这个人能想起那时的经历。因此,不论什么主体,只要能意识到现在的和过去的各种行动,它就是同一的人格。洛克甚至认为,一个人醒时和睡时可以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人在醒时可能并不记得在睡时的所作所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两个双胞胎因为外貌相似而就根据这个人的行动来惩罚另外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并没有延伸到对方的行动或意识之中,他们是具有两个不同人格的人[13]318。因此从洛克的观点看,道德增强应该不会影响到人格的同一性,原因在于人的记忆不会因为道德增强而断裂,先前的行动并没有影响到后续记忆的连续,我不会完全忘记道德增强前那一部分生活,也不会忘掉之前所做的行动和所产生的意识。一个人变得更加有道德,并不会忘记他不道德时所经历的事情。因此,一个道德增强后的人依然具备连续的人格,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道德增强并不会干预一个人的人格认同。
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记忆作为判断人格同一性的标准,洛克的人格认同标准依然具有缺陷。休谟就认为记忆不是一种可靠的标准,因为我们难以完全记得过去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记得每个具体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由于完全忘记了某个时间的事件而认为,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不是同一人格[14]292-293。例如,A 在年轻时作为一个学生做过某件事情,在中年的时候成为了律师的他依然记得这件事,但到了老年之后,尽管他还记得当律师的经历,但却将年轻时的许多记忆包括这件事忘记了。如果按照洛克的观点,我们只能认为中年律师和年轻学生都是A,老年人和中年律师也都是A,但老年人和年轻学生就不是A 了,因为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记忆连续性已经断裂了[15]。这显然是违反直觉的,不管A 记不记得之前的某段经历,A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历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人而不可能是两个人,这里不能简单地以记忆的丢失来抹杀掉A 在不同时间向度中的连续性。另外,记忆作为判断人格同一的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从洛克的标准看,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记得过去的经历,某些人也有可能为了逃避道德和法律责任而主动或故意忘记某段经历,这种情况会让我们增加判断的难度。因此单凭记忆作为判断人格是否同一在道德增强中并不可取。
因此对于休谟而言,他在洛克的基础上提出将“自我”归结为各种知觉的集合,认为同一性之所以能形成,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知觉的接续和重现。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人,就是在任何时候,这个人总是能碰到某个特殊的知觉。当一个人的知觉在一个时期内丢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觉察不到自己,也就是一种不存在了[14]282。在休谟看来,因果关系是构成人格同一性的关键。因果关系把各种不同的知觉联系起来,A 意识会被B 意识所替代,接着引进第三种意识C,之后B 意识又被C 意识驱逐,以此类推,不管一个人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他的各部分仍然被因果关系所联系着。正是因为因果联系才使得“自我”能在时间流中持续存在[14]292。从休谟以上的观点看来,如果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来获得道德上的增强,也是可以遵循这种因果关系的,因为道德增强使用者是用一种道德的意识替代一种不道德的意识,这与人通过道德教育等方式提升道德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实现道德上的增强不会中断这种因果联系,那么生物道德增强同样不会,人的各部分依然被这种因果关系所联系,自我依然能够持续存在。
根据《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辽宁省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县(市、区)共有52个,分布于13个市,除2010年汛前已建设完成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凤城市3个试点县(市),剩余的49个县(市、区)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2010年度安排12个县(市、区)的建设任务,2011年度安排27个县(市、区)的建设任务,2012年度安排10个县(市、区)的建设任务。目前2010、2011年度的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并投入试运行。2012年度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施工过程中,并将于2012年年底前完成建设工作。
休谟的观点中还认为,一个物体的任何重大部分的变化会消灭它的同一性,因此在连续的相关对象中,渐进式的改变可能更容易保持同一性。这就要求各部分的变化不要太突然,也不要很彻底[14]289。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增强人的道德,给道德心理和道德特征所带来的是彻底的还是渐进的变化?道德增强的支持者并没有明确地说明道德增强会带来突变还是渐变。但从其特点来看,道德增强可能会两者兼有。首先,如果使用的是外科手术式的深度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来干预人的道德,那么使用者在干预前和干预后性格、心理等可能会产生显著的差别,是一种完全而非零碎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会中断人的心理延续性。因此,在这种间断下这个人不再显得跟之前那么同一,所以构成不完全的同一性,是一种间断的进程。其次,如果相对于使用的是药物方式干预的道德增强来说,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渐进式的改变,而且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大多是可逆的,也就是停止服用药物之后就可能失去效果而恢复原状,有些人为了维持道德增强效果需要不断地服用药物以保持体内的某种化合物的水平。因此这种逐渐而又非彻底的变化对于人的同一性来说影响比较小。但是即便是一种渐进式的道德增强,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不会威胁人格同一。因为判断某个对象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是否依然同一,不能仅依照这种外部因素作用的大小,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它们和某个对象之间彼此的比例,不能用绝对的标准加以衡量。例如,对于一个湖水,如果加上或减少一杯水,并不足以使这个湖发生异样。但是对于某种化学试剂而言,增减那么几毫升物质,就可能完全改变它的化学功效,使它与之前完全不一样。对于个体而言,改变或遗忘一两种记忆或意识或许并不会影响到自我的认同,但当作为区别一个人的重要标志的心理、性格等被去除或改变一部分的话,都有可能会让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造成明显区别,陷入一种“我是谁”的自我辨识的模糊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道德增强反而会造成人格同一的困扰。
然而,如果用帕菲特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来看,道德增强却能保持一个人的人格同一性。帕菲特的观点认为,人格同一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质的同一,另一种是量的同一[12]293。质的同一是有关事物的相似或者人类物种之间的相似度,量的同一描述的是一个实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作为同样的实体存在。量的同一对于个人同一性概念来说是关键,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其量的同一[12]291。一个过去的人或将来的人要成为现在的我,就必须在量上与我保持同一,但是在质的方面却不必完全一样。这种关系为通过改变而持续存在的某些特别的种类提供标准。例如,一朵花可以生长,改变颜色甚至枯萎,但这朵花依然是这朵花。一辆汽车在使用中可以不断磨损或者不断更换零件,但依然是同一辆车。而相反的是,即使某个人和现在的我在质的方面保持同一,也不能保证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例如一对双胞胎在质的方面可以是同一,但我们不会认为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按照这种观点,道德增强不会干扰人格的同一。因为这些使用了道德增强技术的人,跟未使用道德增强技术之前的人实际上是同一人,他们在量的方面是保持同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某些质的方面,如在道德心理方面。一个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事件后,道德心理也会发生改变,可能从一个悲观的人变得乐观,从胆小变得勇敢,从自私变得无私,但我们并不会轻易地认为这样的人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物医学技术所带来的效果其实也是类似的,况且道德增强带来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上的改变只是一种局部的、单一的,而不是一种全方位的或整体的改变。既然传统生活经历的改变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同一,道德增强同样也不会改变人格同一性。
另外,帕菲特对人格同一性的理解重在心理联系,认为一个人的心理能联系在一起就能保证其同一性。因此,帕菲特强调,判断前后不同时间段的两个人是否有连续性,重要的是关系R。如果未来有一个人与现在的我有关系R,而且没有不同的人与我有关系R,这个人就将会是我[12]373-374。如果两个人的心理联系已经很微弱了,这表示现在的这个人和过去的这个人的行为已经具有非常大的改变,我们可以判断这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人已经几乎接近于不是同一个人了。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改变会不会造成自己心理连续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一个人身份的丢失?目前看来并不会。首先,一个人变得更加有勇敢、善良、正义和无私等,并不会失去他之前胆怯、狠毒、邪恶和自私时候的心理连续性,这并没有涉及到人格同一的改变。同样道理,从效果上看,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实现道德上的增强跟传统方式的道德增强是一致的,既然传统的道德增强方式不会隔断个体前后时间的心理联系,生物道德增强同样也不会,道德增强后的这个人依然具有之前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其次,帕菲特强调的是,只有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之间的联系性已经变得相当微弱,我们才会认为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人格[12]299-300,这种情况下不管事实究竟是谁引起的过错,我们都应当从道德责任上不给予追究。这也可以为激进的道德增强方式如DBS 等提供一定程度的辩护,因为即使这些激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心理的连续性,但只要能保持大部分连续性,我们也能认为这个人依然保持着人格的同一。因此,从帕菲特的观点看,认为道德增强会造成人格同一性改变的担心是多余的。
2.3 生物道德增强中的叙事同一性问题
心理连续性似乎能解决道德增强的人格同一性问题,但是对于复杂的道德增强而言,只从心理连续性角度讨论人格同一性问题依然欠缺说服力。叙事同一理论认为,人类的生命故事一般以时间为标准来组织,自我可以通过生命故事予以表现。通过自我的叙事,人类可以在时间向度中直观地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容易理解个人生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人类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可读。利科认为,自我的概念其实离不开叙事,我们谈论的个人,行动依赖的施动者,都是有历史的,而且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16]170。通过叙述故事或讲述事件,真实的叙事对我们进入真实世界有帮助,可以开启自我认识,找到自身的位置并把自我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叙事认同突出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体可以通过叙事来整合、内化他们的生活经历,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因此,人格同一性可以从叙事身份的角度予以理解,叙事正是通过建构叙事故事的同一性,构成了人物的同一性。
如果从叙事角度看,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增强人的道德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叙述认同。这是因为:第一,道德增强会干扰人的真实性。道德增强后的个体可能通过对自我真实性的否定从而内在地对人格同一性造成困难。一方面,这种自我真实性的否定意味着使用者产生了对自我感到陌生和失去了控制的忧虑。一个人通过生物医学方式突然变得更加有道德,或者在某些涉及道德的行动中更具有操控力和支配力,这样的改变跟他们增强之前的状态可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都会觉察到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他之前所拥有和存在的东西[17]。这种差异性可以让一个人在适应自己的心理和功能的改变上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全新的自我画面,对此会产生一种真实性的质疑。特别是剧烈地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很可能会带来人的极端心理的改变从而切断一个人的真实性。有些人会产生是工具或药物控制了自己思想的错觉,从而使个人远离自我真实性,造成叙事认同上的困难。另一方面,这种对真实性的否定也会带来自我异化的担忧。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感到陌生,得到认可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真实状态,而是我们的伪装,自我的一致性,最终结果可能就是一个伪自我,连自己都无法知道我是谁。真实性的生活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相比拥有一种愉悦的生活但是却会对自身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和误解而言,拥有一种更真实的自我但相对更少愉悦的生活可能是更多人的追求[18]。许多人已经感觉到道德增强会提升人们在关于自我真实性方面的特别关注。在一个关于生物道德增强的公众态度的调查研究中,认为最不愿意经历道德增强的原因就是对于自我真实性的忧虑,担心在道德上过多地干预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自我[19]。
第二,道德增强还可能会造成性格的中断从而模糊一个人的叙事认同。这意味着道德增强的这些改变并没有与个人的行动、经验、信仰、价值、梦想和性格特征相一致[20],而这些正是组成一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成分。利科认为,自我在时间中存在一种恒定模式,即性格上的持续[16]177。一个人的性格一生中会不断经历变化,如果这些变化都是自然结果或自然反应,即使经历了这些变化之后,性格仍然具有连续性。但是,如果是由非正常的介入而产生的这些极端变化,例如,DBS 对大脑结构的改变或外科手术切断两个脑半球的联系等,性格可能就不具有连续性。利科特别强调性格是一个人的独特符号,是辨认一个人是同一个人的标志,并且把性格置入个人同一性的叙述化之路[16]148。性格的连续性可以确保量的同一和质的同一,并最终保持人格在时间变动过程中的不变性。而性格的中断,带来的后果就是叙事认同的混乱。道德增强带来的性格和心理改变可能会非常深刻,一个精神变态者变成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爱心,温暖向上的人,一个具有暴力倾向和脾气暴躁的人变成一个温柔和容易相处的人,一个自私的人变得非常无私,一个爱说谎的人变得充满诚实的思想,或者一个对周围不感兴趣,失去了活力和动力的人变成有目标追求,充满活力的人[20]等,这些性格上的改变或中断也最终会让一个人远离自我的真实性,从而脱离叙事同一。因此,由这些讨论来看,道德增强会干扰一个人的叙事同一,道德增强后的人与之前的人并不会是同一个人。
3 生物道德增强中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可能回应
上述从叙事认同的角度来讨论道德增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的推断其实还不够全面、客观,并且这种人格同一性判断的进路依然也无法回应道德增强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困境。如果我们能从获得性认同角度出发,从个体所处的社会角度或道德地位考虑道德增强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可能更加合理客观。人格同一性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叙事同一理论就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其重点放在了主体的传记性特征上,强调人格同一性只在密切而持续的实践交往中产生并维持。我们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认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自我并建构自我的概念,最终在实践中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就叙事性的自我概念而言,它通常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我”是作为一个叙事的主体,具有独特的意义,所叙事的历史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人的,也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判断现在的“我”是不是过去的“我”。另一方面,我不仅自己能够解释,而且还总是被别人要求能够给出一种解释,也就是可以从他人角度来判断是否同一[21]。因此,之前的讨论更多的是从“自我”的主体角度考虑“我是谁”的问题,而忽略了从他者的客体角度思考“你是谁”的问题[22]。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通过他人角度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同一个人有其合理之处。特别是在脑科学的时代里,我们的身体、容貌甚至部分脑结构也许很容易被侵犯、改变甚至更换,而个性上真正极端的改变又会产生其他的问题,自己和周围人都需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个体。因而传统的同一性标准可能很难判断这个人的心理本质部分是如何延续和同一的,而来自他人的评价和承认对我们人格的连续性判断就很重要,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社会上总是扮演多个角色,角色呈现了我们的过去、本性和特征等。尽管我们扮演的角色可以随着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但自我与它的社会的、历史的角色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恒定性。这种角色的恒定性是自我长期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因此,道德增强也可以保持这种角色的恒定性。例如,A 是一个多种族地区法庭的法官,他是在一个种族偏见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最近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和法律的思考会被种族偏见的动机所影响,于是他服用了一种药物可以帮助减少这样的偏见。从道德增强的定义来说,这样的药物能够减少他的偏见动机,A 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道德增强。现在A 在服用了某种药物之后获得更好的动机,并且确实有相关的道德行动,但是A 现在是否已经成为了另一个人呢?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考虑,药物确实在消除A 的偏见动机上有效,但我们并不能认为A 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因为一个新的获得增强的A 尽管带着更少的种族偏见,但在周围人眼里,他可能仍然是一个性别歧视者,一个在球场上的恶霸,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或伴侣,喜欢去欺骗人和不诚实等。这就是说,他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少的种族偏见,但也不会改变周围人对于他在性格和行为习惯上的总体看法[23],他的社会角色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种角色的恒定性其实也反映了个体社会关系的持续和传承。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格并不是仅限于个体的,而是需要人与人的互动,我们需要其他人的陪伴和支持,我们生活在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关系之中。我们的人格本身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人与人互动的基础之上,从本质上说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周围人的关系而存在。利科在叙事认同理论中也强调,人的个性的形成除了需要习惯,另一个就是获得性的认同[16]181。而这种获得性的认同,使得他者与自我共同走进了人格同一性的构成之中。我们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承认,能有助于真实地认识自己,将他人外在的评价转化为自我的内在化。在亚当 · 斯密看来,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通过他人的眼神、表情、感情等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也需要将他人的反应和判断作为参照物。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而无法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实际上会因缺乏他人的评价而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或行为是否合适,从而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24]。自我的认同不仅来自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25]。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认可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取决于他们认可的我们是什么样子,个人完全可以通过他人所谓的评估来认识到自己。因此这种来自他人的评价和承认对自我的认同有重要意义。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了解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只有通过他人的评价和承认,我们才会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不管是社会角色的恒定性还是伦理关系的持续性,道德增强都不会轻易地改变一个人的人格认同。
但是,考虑从伦理关系的传递去判断人格同一性问题,并不是仅仅要求依靠他人和周围关系来判断,从而忽略了个体在人格同一性判断上的主体地位[22]。社会关系的判断是一种互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处事风格,不会任由外界将某个角色强加于自己,而是用自己的风格对社会角色加以诠释,并从中找到自己与他人交往时的一贯性。自我必须在诸如家庭、邻里、同事等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它在这些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去发现它的道德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必须接受这些共同体形式的特殊性在道德上的各种限制。而且有时候,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通常又是有冲突的,我们需要辩证对待。例如,肥胖可能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大多数人认为她很瘦[26]。另外,通过社会关系判断人格同一也有局限性,准确性就是其中之一。首先,一个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交圈里,对于这些有交集的社交圈而言,判断他是否为同一人或判断其真实的人格可能会较为容易,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太多交集的社会成员来说,以这种方式去辨认一个人的真实人格就较为困难,而且容易造成误解。其次,有些人可能故意隐藏自己真实的人格。例如,某个在周围人看起来是个优秀的法律学生,也可能同时是一个连环杀手。某个看起来很真诚的人,也可能是一个伪君子等。还有一些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事件之后行为表现产生了变化,从无神论者变为虔诚的信徒,或者从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周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但实际上他依然是同一个人,人格同一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4 结语
当前,生物道德增强问题在国内外生命伦理学领域持续引发广泛的讨论。相对于安全、公平、自主性等比较普遍而且容易理解的伦理问题而言,道德增强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则显得相对复杂和困难。首先,道德增强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改变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本身极具争议性和特殊性。其次,任何一种同一性观点和理论都具有困惑和悖论,这让道德增强在人格同一性方面的论证缺乏足够的和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人格同一性的讨论对道德增强来说依然具有重要和迫切的意义。一方面,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性格或行为或许会引起的潜在的身份改变,从而带来人的真实性问题困扰,因此如何避免自我真实性的丢失将成为道德增强具体应用中的难题和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这种身份的改变很有可能会涉及道德责任的问题,因此也必须确定相关的道德和法律的责任主体。而更为重要的是,人格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更加有助于我们对道德增强及其技术做出合理、客观的道德评价。目前而言道德增强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依然面临很大的争议,因此更需要我们对人格同一性问题继续进行理解和分析,在同一性的领域寻找更多的建设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