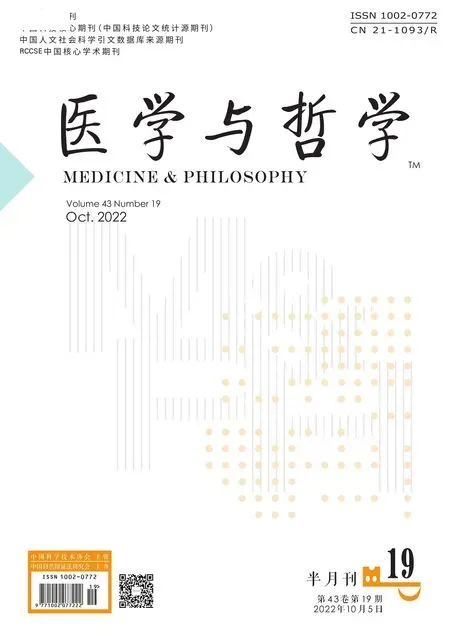预防还是增强?*
——人类增强与预防医学之辨析
王荣虎
2018 年11 月26 日,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团队宣称,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上敲掉了CCR5 基因,并成功诞生了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由于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的重要门户,所以这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对艾滋病病毒HIV 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基因编辑婴儿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舆论风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立即表态并迅速介入调查,科学界和哲学界也都纷纷表示谴责。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严重违反了相关技术规范和伦理规范,造成了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本文不打算讨论基因编辑婴儿违反技术规范和伦理规范问题,但是假如敲掉CCR5 基因确实可以获得对HIV病毒的免疫能力,那么它显然将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联系起来,一方面,“在贺建奎看来,他利用CRISPR 技术编辑了双胞胎女孩的基因组,是为了保护她们免受艾滋病毒感染,属于预防性基因编辑”[1]。另一方面,敲掉CCR5 基因似乎超出保持健康之所需,并且使得受体在抵抗HIV 病毒方面获得优势,“这明显不是基因治疗,而是意图进行基因增强的实验”[2]。那么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是否确实存在某些重合以致消除了两者之间的界线?本文在对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详细分析之后指出,尽管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在社会接受程度、分配制度和公平性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
1 预防医学的概念、潜力与“O-M-P”模型
疾病是人类生命历程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它们使我们的生物体在功能上出现衰退,进而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死亡。长期以来,人们试图通过膳食选择、调整作息和体育锻炼等方式来延缓甚至阻止这种功能衰退以维持我们当下的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拥有了更加精确有效的措施来防止疾病带来的损失,这些措施被称为预防医学干预。预防医学因其低成本高收益而在现代医学当中显得尤为重要,以至于许多国家将预防医学纳入公共医疗的范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预防医学可能面临一些革命性的变革,例如,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使得基因医学在预防医学领域的潜力不容小觑,加之人们普遍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医师的角色定位在过去几十年里由患者的治疗者转变为通过预防措施保证健康的推动者”[3],所以,预防医学在未来将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但什么是预防医学?
为预防疾病而采取的干预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但正如约翰 · 保罗(John Paul)[4]所说,预防医学是在医学上没有互补学科的一个奇怪领域,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被称作“治疗医学”,所以“预防医学”一直没有一个合法的定义。尽管在概念上没有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合法定义,但在实践上治疗与预防确实存在明显的界线:治疗的对象是“实然疾病”,而预防的对象是“潜在疾病”。人们也基于治疗与预防的区别来解释甚至定义预防医学。保罗[4]认为预防医学是“为了防止健康的人生病,或者为了防止病人的病情恶化而做出的努力”。克拉克[5]认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对大多数人而言,健康就是无疾病。预防医学的真正目标就是实现这种无疾病。”而约瑟夫 · 斯托克斯(Joseph Stokes)等[6]39-40则将预防医学进一步划分为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临床医学预防:“初级预防是所有旨在降低疾病发生风险的干预;二级预防是任何旨在检测无症状且可救治的疾病或减少疾病复发风险的干预;临床医学预防是对患有公认疾病或限制性疾病的个人的所有护理干预。”正如克拉克[5]65所说:“初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之间通常有一个区别,“初级预防用于防止疾病的发生,二级预防是疾病或者其并发症在疾病发作之后的任何点上被停止(halted)或被防止(averted)。”显然,预防医学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但任何旨在“守护”健康的提前干预都可能被认为是预防医学干预。
正如克拉克[5]所说,根据预防医学相关的定义,“显然预防医学基于知道疾病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个体是如何从正常状态进入疾病状态的。因此,预防医学需要知道新的事实以及已知事实的有效应用,这两者都是流行病(epidemiology)过程”。因此,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人类将拥有一个关于潜在疾病的“知识库”。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基因组为向导的预防干预将会在预防医学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基因咨询”和“家族史评估” 将以纯商业的方式运作,前者“以帮助人们理解和适应在医学、心理和家族方面,基因对疾病的影响过程”[7],后者目前属于基因医学前沿,“它可识别个体患家族常见疾病的风险,如心血管疾病、癌症、II-型糖尿病以及精神疾病等”[7],正如奥丹尼尔[7]所说,在充足的临床信息和沟通之下,依据基因组评估可采取改变生活方式和定向筛查等方式干预潜在疾病,“因此,从个人的角度,以基因组为导向的预防医学对促进广泛多样的人群健康和医疗提供了非常大的潜力”。然而,还有比基因咨询与家族史评估更具争议的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是指对试管内的受精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检测[8],从而了解胚胎的基因状况;而基因编辑技术可对基因检测中发现的严重基因缺陷进行修改,从而纠正“上帝的失误”。关于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讨论持续不断,一些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它们为预防医学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疫苗接种还是基于基因组分析的预防干预,实质上是以相对明确的潜在疾病为对象,通过对人类生物体抵抗疾病之能力进行提升或增强,从而阻止疾病产生的既得利益损失。例如,接种新冠疫苗以新冠病毒为对象,通过提升受体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从而减少甚至阻止该病毒在身体、经济和社交等方面所产生的利益损失。因此,预防医学是以潜在疾病为对象,以增强人体对抗疾病的能力为方法,以阻止疾病产生的既得利益损失为最终目的,现将其记为“对象-方法-目的”(objectmeans-purpose,O-M-P)模型。然而,贺建奎团队所进行的基因编辑也能够以此模型为自己辩护-在人类胚胎上敲掉CCR5 基因是以潜在艾滋病为对象,以获得对HIV 病毒的免疫能力为方法,以阻止艾滋病产生的利益损失为最终目的。既然贺建奎可以争辩说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是预防医学干预,但为何被指责为人类增强?
2 人类增强的“进取型”“保守型”与“O-M-P”模型
“人类增强”是一个新兴概念,但它却有着古老的历史。事实上,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增强史,从能 人(homo habilis)到 直 立 人(homo erectus)、再 到 智 人(homo sapiens),人类在学习制造工具和掌控火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安全、饮食、健康和智力状况,从而增强了人类物种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直至今日,我们仍然通过学习、体育训练、膳食选择和自我反省等方式进行着自我改进,正如特纳(Turner)[9]8所说:“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是一个长期自我改进的计划。”尽管人类有着古老的自我增强史,但人类增强却是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之下的一个新兴概念。
近年来,随着生物医学、纳米技术、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类自我改进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们企图借助于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来改进人类的生物体、运动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甚至道德等,进而希望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现有能力,于是伦理学家提出了“人类增强”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人类增强?特纳(Turner)[9]8认为人类增强是人类自我改进的新手段:“当我们讨论人类增强的新技术伦理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样的论点:毕竟,我们总是试图通过传统手段实现这些目标;新的手段也是寻求相同的目标,但它们更快或更有效地实现目标。”这种看法更侧重于“技术手段”。在央斯特(Eric T. Juengst)和佩莱格里诺(Edmund D. Pellegrino)看来,人类增强是那些超越了医学上恢复或维持健康之所需的干预,央斯特说:“增强术语一般用于生物伦理学范畴,以表征旨在改善人类形态或功能的措施超越了维持健康或恢复健康之所需。” [10] 佩莱格里诺认为,“增强”一词具有 “增加”“强化”“提升”或“放大”之意,而这些语词具有“超越当下状态”的涵义,因此“人类增强意味着一种超越传统医学目的的干预措施”[11]5。这是一种易于接受的观点,它强调了干预的直接结果。从统计学的角度,克里斯托弗 · 博 斯(Christopher Boorse)和 诺 曼 · 丹 尼 尔 斯(Norman Daniels)认为疾病是低于物种特有(species-typical)正常功能的统计学定义水平之下的生理或心理状态,而增强则是对人类生物体或心理状态的改变,将物种的特有正常功能增加到超越统计学定义的水平[11]5。上述解释更多是一种宏观的解释,从具体功能的角度来看,对人类任何机体功能的改进都是增强,例如,道格拉斯 · 恩格尔巴特(Douglas C. Engelbart)将人类智力增强定义为:“‘增强人类智力’的意思是提高一个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增加他的理解来满足特殊需求,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11]6根据这个思路,对人类听力和视力的改进都算作人类增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解释的着眼点不在于干预本身,而是它带给人们的福利,意即“如果对人类生物体或心理状态的改变致使其在相关环境中享有美好生活的机会增加,那么这个干预就是人类增强”[11]7。
综合上述理解,人类增强是以人类的某种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为对象,通过新技术改善或增加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从而获得额外的收益。例如,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可调节携带氧气的红细胞数量进而可改善耐力,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可改善特定的肌肉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可 改 善 血 管 进 而 为 肌 肉 组 织 提 供更多氧气和养分,从基因上改善运动员的促红细胞生成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以增加他们的运动能力,从而在比赛中获得额外收益[11]275。因此,人类增强具有与预防医学一样的“O-M-P”模型。
然而,“O-M-P”模型对人类增强来说并不只有上述这一种情况。考虑:随着衰老,人类机体在视力、听力、记忆、外表和运动方面都会出现衰退现象,甚至在抵抗疾病的能力方面也会出现衰退现象,如果特定的增强技术用于对抗这种衰退,那么这种增强虽然也以人类的某种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为对象,但并不是增加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而是为了让其保持曾经的最佳状态,进而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例如,延年益寿(lifespan extension)作为一种人类增强,它有望通过限制热量摄入、服用生长激素、端粒酶激活、干细胞移植等手段“永葆青春”[11]339-340,从而避免因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既得利益的损失。
因此,人类增强存在“进取型”和“保守型”,它们都以“人类的某种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为对象,但是进取型人类增强试图“改善或增强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从而“获得额外的收益”,而保守型人类增强试图“维持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的最佳状态”,从而“避免自然衰退所产生的既得利益损失”。
根据博斯和丹尼尔斯等人的定义,疾病是低于物种特有正常功能的统计学定义水平之下的生理或心理状态[11]5。因此在“O-M-P”这一模型下,预防医学也是以“人类的某种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为对象。进而可见,预防医学、进取型人类增强和保守型人类增强都有着相同的对象-人类的某种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并且预防医学与进取型人类增强有着相同的方法-改善或增强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同时与保守型人类增强有着相同的方法和目的-维持这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的最佳状态,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因此,贺建奎团队所进行的基因编辑处于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重叠区域:增强人体对抗HIV 病毒的能力,从而阻止艾滋病产生的利益损失。
3 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之间的进一步交错
如上所述,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在“对象-方法-目的”这一模型下存在一定的重合,这使得像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这样的行为游走于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边缘,而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在诉求、技术、概念、形而上学等方面的相互交错进一步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
从增进人类福祉的角度,人类增强亦可声称与预防医学诉求一致。疾病和衰老是生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预防医学意图减少甚至避免生病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显然,很多疾病与我们生物体的有限性相关,例如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老年)疾病,人类增强倡导者希望通过根治老年疾病从而使人们拥有更长和更高质量的生命,即“延年益寿”(lifespan extension)。盖亚 · 拜瑞泽蒂(Gaia Barazzetti)说:“实际上,通过临床上的对照实验,对于那些与年龄相关的致命疾病,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以及治疗方法在预期寿命的增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针对老年人进行干预和预防的老年医学的进步,可能导致老年人过早死亡的发生率进一步降低。”[11]336换言之,保守型人类增强似乎并不那么“令人反感”。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现代科学技术既促进了预防医学的发展,也为人类增强提供了可能。随着基因组检测、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互动发展,人们对人类生物体和疾病将会有更深的认识,从而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预防潜在的疾病。以基因科学为例,如奥丹尼尔[7]所说,基因医学将有极大的潜力:“基因组医学最新的工具是基因组风险检测或整体基因组分析,这项技术自2007 年以来已经直接面向消费者。不久之后,消费者在2009 年可获得整体基因组的测序。目前只是处于初期,在不久的将来,基因组测序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它的影响并不完全为人所知,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以基因组为主导的预防医学将会针对潜在疾病提供更丰富、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干预。然而,基因科学的成果同样也可能用于人类增强:贺建奎团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另外,科学实验证明修改基因可增强大鼠和小鼠的记忆[12],增加脑生长因子的数量和信号转导蛋白腺苷酸环化酶的数量可以改进记忆[13-14],进而为人类从基因上进行认知增强提供了可能;科学家也发现人类基因当中有一些特定等位基因与改善耐力相关,这就给为了运动目的而进行的基因修改和基因筛选提供了可能,如海德 · 海斯玛(Hidde Haisma)所说,“早期的基因筛查可能会表明特定儿童发展成为顶级运动员的最大潜力,并且可以设计特定的训练计划。另一方面,运动员的基因筛查可用于选择特定的训练方法以增强或改善其基因倾向”[11]260。因此,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可能使用同样的技术。
从概念上来说,健康、疾病、正常功能以及幸福等是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共同的核心概念。据上文所述,预防医学是为了防止“疾病”实现“健康”;人类增强被看作是与“疾病”相对立的、增加物种特有正常功能超过统计学定义水平,或超越医学上恢复或维持健康之所需的干预。然而正如保罗 · 沃佩(Paul R. Wolpe)[15]所说:“任何排他的(exclusive)增强定义最终必定会失败,部分原因是像疾病,常态和健康等这样的概念显然是受文化和历史约束的,从而也是价值协商的结果。”詹姆斯 · 坎顿(James Canton)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影响文化、智力、记忆力、机体效能(physical performance)、甚至寿命的人类增强在未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文化将根据其社会和政治价值来定义人类效能(performance)。”[11]4换言之,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疾病、健康、正常功能和幸福的理解和期望不同。以健康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没有疾病,而且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的完整状态。威利(Wylie) [16]将健康描述为“一个生物体对其环境完美的、持续的调整”,而塔尔科特 ·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7]将健康定义为“履行有价值的社会角色的能力”,它不仅强调功能能力,而且将健康概念与个人信仰和价值观联系起来。例如,对钢琴手来说,手指的细微损伤会被视为健康受损,而声带的细微损伤则不被视为健康受损,但歌唱家则相反。斯托克斯(Joseph Stokes)等[6]认为,健康是“以解剖学上的完整性为核心特征的状态;个体有能力履行其重视的家庭责任、工作责任和群体角色;有能力应对来自生理、生物和社会的压力;具有幸福感;没有疾病,也没有过早死亡的风险”。显然,斯托克斯等人对健康的定义涵盖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强调个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幸福感以及应对压力的能力。然而,当“健康”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时,它也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明确,因为价值观、社会认同和幸福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如尼尔森(Lisbeth Witthøfft Nielsen)所说:“以前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类行为或人类生活‘自然’条件可能逐渐被视为一种人们可以选择不必忍受的疾病或病症。”[11]25-26然而,健康、疾病、正常功能和幸福是理解和定义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当人们对“健康、正常功能和幸福”期望较高时,一个干预可能被辩护为预防医学,但当人们对“健康、正常功能和幸福”期望值较低时,该干预则被指责为人类增强[18]。
从形而上学层面,预防医学与临床治疗不同,临床治疗的对象是实际上已经发生的疾病,而预防医学的对象是潜在未发生的疾病,进而是某种可能性。接种疫苗X 靶向的对象是疾病Y,但接种者并不必然会成为Y 病患者。假如接种者Z 不可能成为Y 病患者(不存在患有该病的因果链条),那么给Z 接种X 时所靶向的对象(即Y 病)是否“真实存在”?正如“购买保险”与“获得理赔” 通过“购买合同”建立了一种人为因果链条,预防医学也人为地设定了“干预”与“疾病”之间的因果链条,但这种因果链条可能不会实际发生,最多是一种潜在对象。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潜在对象是非现实的存在对象,“与非现存物中,有些为潜在,但它们既然不是完全实现的存在,便不能算作存在”[19]。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对象必定会实现,如果某一对象(潜在疾病)最终并没有成为现实,那么就不能证明它是潜在对象,甚至不能证明它是存在的。因此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预防医学的对象不具有“治疗医学”之对象的实在性,从而具有“超越治疗”的嫌疑,进而为人类增强留有可辩护的余地。
4 社会接受程度、分配制度与公平性
在绝大多数人的粗略印象中,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然而,对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它们在“对象-方法-目的”这一模型下有某些重合,而且在历史、技术、概念和形而上学方面两者也相互交错,这使得人们对其“粗略印象”产生怀疑。但事实上,这种粗略印象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由于模糊的认知,公众对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整体接受程度存在巨大的反差。正如文章第一和第二部分所示,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都没有相对明确的概念,但预防医学属于更为熟悉的“医学领域”,且人们普遍相信“预防胜于治疗,言下之意是,任何可能的损失都大于用既得利益的偿还”[20]。因此人们对其具有强烈的好感。相比之下,人类增强作为一个新兴概念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例如,以哈贝马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们认为人类增强背后是人定胜天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导致潜在的风险、亵渎了人类的尊严等[1,8,21],进而易于塑造公众对人类增强的整体排斥感。事实上,目前公众对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在态度上巨大反差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继而,公众对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整体态度缔造了不同的分配制度。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都将预防医学纳入公共医疗,因此当某一疾病有效且可靠的预防措施被研制出来之后,几乎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该技术带来的福利,意即预防医学实行相对平均的分配制度。例如,在我国几乎所有人都可接种针对各种病毒性疾病的疫苗,而且国家为0 岁~6 岁儿童免费提供乙肝、卡介苗等十余种疫苗;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ovel coronavirus 或SARACoV-2)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后,我国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全民免费接种。然而,人类增强的技术是稀缺资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享有通过增强技术来改善或提高自身的能力”[22]。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信息、也有很多人支付不起高昂的增强费用。例如,近来一些研究发现,士的宁、营养素、激素、胆碱能激动剂、吡拉西坦家族和巩固增强剂等药物有助于长期记忆,进而为认知增强提供了可能。因此,“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智力增强(intelligence enhancement),我们的孩子将比其他人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不公平将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加剧”[21]。换言之,人类增强完全实行市场分配制度,其直接结果是资源分配不公平。
分配制度所产生的不公平是可以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而减少甚至消除的,但人类增强对公平的固有破坏性是它与预防医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正如夏皮罗(Michael H. Shapiro)[23]所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具体能力、健康、外表、个性和文化偏好的行为倾向都是影响社会政治地位、收入和财富、表扬、择偶机会和奖励等生活回报分配的关键变量。”预防医学与进取型人类增强都试图改善或增强这些变量,但预防医学改善或增强这些变量之目的在于维持健康从而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并不会产生新的不公平;而人类增强“通过技术上的改变来增强这些分配标准。那些已经能够获得大量资源的人可能会大幅增加其对资源的吸引力,可能处于一个自我加速的循环中,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吸引到被增强的人身上”[23]。因此人类增强严重破坏了公平原则。当然,保守型人类增强同预防医学一样也是试图维持人类某些功能、形态、特征或能力的最佳状态避免既得利益损失,但保守型人类增强这一方法和目的违背了自然规律,反而扩大了个体之间的公平性。在人类生命历程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疾病和衰老,而且它们往往结伴而行以致最终导致死亡,这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当人类增强试图对抗这一自然法则时,表面上避免的是既得利益的损失,但事实上相对于其他个体来说是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例如,在视力、听力、记忆、运动甚至外表方面“永葆青春”的增强对于其他个体来说就是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从而扩大了个体之间的不公平。
正义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而“正义的概念又以复杂的方式与其他基本价值观相联系,包括公平、自治和平等”[23]。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认为,正义要求所有公民享有平等自由,并且要保证在不平等方面对每个人有利,而且机会(地位与官职)应对所有人开放[18]。事实上,“‘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罗尔斯对传统契约理论精华的一个概括”[24],它表明正义应该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就此而言,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在分配制度和固有性质上的差异表明了预防医学在机会和结果上都是公平的,而人类增强既不机会公平也不结果公平。
五 结语
以往从医学角度对人类增强的讨论更多是聚焦于“治疗与增强”,但“预防与增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密切:它们在对象、方法和目的上存在某些重合,并且在历史、技术、概念和形而上学方面也相互交错,以至于在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灰色地带”,例如各种保健理念和保健品,甚至基因编辑等。然而,无论人类增强与预防医学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但当前社会对它们的接受程度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而社会接受程度的不同又进而导致不同的分配制度,与分配制度导致的不公平相比,人类增强对公平的固有破坏性是它与预防医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正如夏皮罗所说:“增强资源的分配通过改变分配要求的标准来改变规则;这种反馈可能远比教育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反馈更令人震惊。”[23]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且价值追求多元化时代,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之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