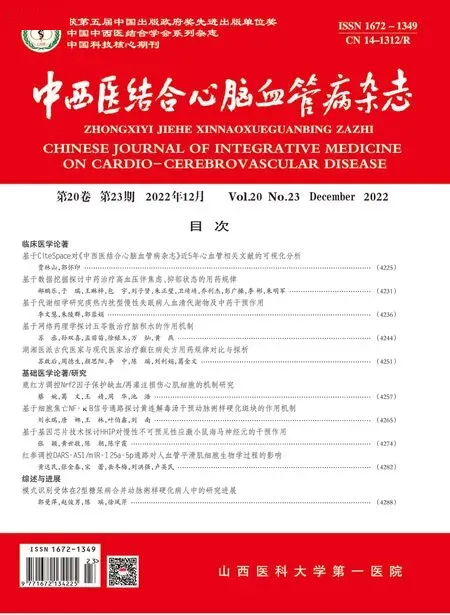模式识别受体在2型糖尿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病人中的研究进展
郭曼萍,赵俊男,陈 瑶,徐凤芹
近年来,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等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1]。与健康者比较,T2DM病人更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也是造成我国人民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2]。这两种疾病之间的协同作用是通过无菌炎症来实现的,而无菌炎症又被称为代谢性炎症[3]。代谢性炎症通过直接促进动脉脂质沉积和诱导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4];其还通过增加冠心病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血脂异常、糖尿病和高血压)间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5]。糖尿病病人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易感性在内的多种因素及高脂饮食、久坐、慢性应激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1]。尽管炎症与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早在19世纪就已被发现,但介导这些炎症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
先天免疫系统是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同样也是糖尿病病人动脉粥样硬化中炎症反应的一线始发者。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包括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s,NLRs)、Rig-1样受体(Rig-1 like receptors,RLRs)和C-type凝集素样受体(C-type lectin like receptor,CLRs),其作为先天性免疫的主要武器库,用于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s),激活免疫系统,导致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干扰素(interferon,IFN)-γ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分泌增加[6]。其中,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IL-6和TNF-α等可作为冠心病的预测标志物。研究显示,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RAGE)可与多种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相互作用导致促炎反应与氧化应激,是参与炎症和衰老的一种重要的PRRs[7]。本研究对PRRs在糖尿病并发动脉粥样硬化中引起代谢性炎症的作用进行综述。
1 PRRs在糖尿病并发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1.1 TLRs TLRs是1型跨膜结构域糖蛋白,在特异性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及非免疫细胞(如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上表达[8]。研究表明,人类有10个TLR基因(TLR1-TLR10),小鼠有12个TLR基因(TLR1-TLR9,TLR11-TLR13)[8]。TLRs识别病毒和细菌产物(即PAMPs)以及真菌和宿主衍生的内源性分子(即DAMPs),最终导致炎症[9]。TLRs的激活导致促炎性细胞因子(如TNF-α和IL-6)的分泌增加,这些因子可诱导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导致T2DM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10]。
TLRs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可在局部血管细胞和招募的免疫细胞上表达[11],TLRs缺乏有助于基质降解[12],并且能够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主动脉内侧破坏发生率[13]。TLR2的激活可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去分化、迁移和增殖表型[14]。TLR4缺乏改善了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DLR)缺乏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指数[15]。在内质体TLRs中,已观察到TLR3可促进内皮细胞[16]和造血免疫细胞[17]致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的进程。此外,TLR3在调节巨噬细胞MMP-2和MMP-9活性方面、在介导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性方面均发挥着关键作用[13]。TLR7与TLR9作为血管重塑和泡沫细胞积聚的一种介质[18-20],研究显示,高胆固醇饮食的LDLR-/-小鼠主动脉中存在强烈的自噬、TLR9表达和炎症信号[21]。
TLR2/TLR6及其相关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巨噬细胞的活化,并产生IL-1和IL-6等促炎性细胞因子加重胰岛炎症[22]。T2DM病人的巨噬细胞可上调TLR2[23]。与体重正常的T2DM病人相比,肥胖的T2DM病人体内TLR2表达水平更高[24]。游离脂肪酸和高糖水平上调了TLR2和TLR6的表达,从而导致单核细胞活性增加、超氧化物产生增加,超氧化物以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B,NF-κB)依赖的方式释放[25]。游离脂肪酸在通过TLR2诱导胰腺β细胞炎症中也发挥重要作用[26]。另一项研究表明,TLR2不仅在T2DM病人的免疫细胞上比在健康人的免疫细胞上有更高的表达,而且TLR2配体(包括透明质酸、热休克蛋白和内毒素)的水平也更高[27]。使用TLR2反义寡核苷酸(ASON)抑制TLR2可导致喂饲高脂饲料的小鼠肌肉和白色脂肪组织中胰岛素敏感性和信号传导的恢复[28]。T2DM期间产生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诱导巨噬细胞中TLR2的表达[29]。Wang等[30]研究发现,TLR3及其相关的信号分子如TIR结构域诱导干扰素-β(TIR-domain-containing adapter-inducing interferon-β,TRIF)可以抑制β细胞的生长,可能与TLR3通过调节细胞周期蛋白D的降解以泛素/蛋白酶体依赖的方式抑制胰腺β细胞的增殖有关。Sepehri等[31]研究发现,T2DM可以独立于性别、血糖浓度和体质指数(BMI)增加TLR4的表达。TLR4基因缺失小鼠可拮抗饮食诱导的IR[32],提示TLR4与T2DM的关系密切。
1.2 NLRs NLRs作为信号转导型PRRs,分布于细胞浆中。在NLRs家族成员中,NOD1和NOD2识别导致MAPK和NF-κB信号激活细菌肽聚糖,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转录上调[33]。NLRP是NLRs的最大亚科,NLRP3炎性小体包括传感器分子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 like protein,ASC)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aspase-1)[34]。NLRP3炎性小体的组装和Caspase-1的激活可将pro-IL-1β和pro-IL-18切割成生物活性形式,然后将IL-1β和IL-18从细胞中分泌出来[35]。这两种细胞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和T2DM病人中均升高,并且每种细胞因子都可能潜在地改变IR和T2DM的进展。
研究证明,ox-LDL和胆固醇晶体能激活NLRP3炎性小体和Caspase-1,诱导巨噬细胞热休克,导致IL-1β和IL-18的释放增加,进一步诱导局部和全身炎症级联反应,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脆弱和破裂[36]。NLRP3等炎症信号通路的相关成分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高表达,而在健康肠系膜动脉中表达较弱[37]。研究表明,急性冠脉综合征病人的NLRP3浓度明显升高,NLRP3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呈正相关;通过全球急性冠脉事件登记(Global Registry of Acute Coronary Events,GRACE)评分和心肌梗死溶栓(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风险评分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基线NLRP3浓度是预测心脏不良事件的有效指标[38]。Abderrazak等[39]研究发现,NLRP3基因敲除降低了喂饲高脂饮食的ApoE-/-小鼠整个主动脉和主动脉窦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
研究表明,内源性和外源性刺激因子可以在T2DM期间控制和诱导NLRP3炎症活化[40-41]。胰岛β细胞分泌的胰岛淀粉样多肽(islet amyloid polypeptide,IAPP)从溶酶体释放到T2DM病人胰腺β细胞的胞浆中,导致NLRP3炎症活化[40]。临床研究表明,IL-1β与脂肪细胞炎症和IR有关[41]。高血糖可导致T2DM病人单核细胞NLRP3的上调和IL-1β的分泌增加[42]。Lee等[43]也报道了T2DM中NLRP3及其下游分子的上调。T2DM病人炎症脂肪组织中NLRP3表达增加[44],促炎性他汀类药物氟伐他汀通过上调NLRP3诱导脂肪组织炎症和IR[45]。Vandanmagsar等[46]研究表明,在动物体内消除NLRP3可保护慢性肥胖引起的胰腺损伤;NLRP3在小鼠体内的消除可以抑制肥胖引起的脂肪库和肝脏炎症反应的激活;当炎症途径被消除时,慢性肥胖NLRP3和ASC基因敲除小鼠的胰岛素水平高于野生型小鼠;此外,NLRP3消除导致脂肪组织中IL-18表达减少,这与组织中效应T细胞数量减少有关。其他研究表明,通过消融NLRP3炎性小体,饮食诱导肥胖小鼠脂肪组织中活性IL-1β的表达降低[40]。重要的是,NLRP3炎性小体的消除可保护胰岛β细胞,减少其因炎症引起的细胞死亡和胰岛大小的显著增加[41]。
1.3 RLRs RNA解旋酶家族的RLRs有3个成员,分别是维甲酸诱导基因-1(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1,RIG-1)、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elanoma differentiation associated 5,MDA5)和遗传生理学实验室2(laboratory of genetics and physiology 2,LGP2),这些受体特异性识别病毒RNA并激活免疫系统,激活后,RIG-I和MDA5被招募到位于线粒体外膜上的干扰素β启动刺激因子1(IFN-β promoter stimulator 1,IPS-1)适配器上;IPS-1通过TRAF3-TANK-NAP1复合物招募TBK1-IKKε-DDX3复合物,同时激活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3和IRF7;IPS-1还通过IKK与FADD-RIP-1-TRAF6激活NF-κB形成复合物;活化的IRFs和NF-κB依次激活1型IFN和促炎细胞因子;以独立于IPS-1的方式,RLRs促进炎性小体的组装和pro-IL-1β和pro-IL-18细胞因子的加工[47]。与TLRs一样,RIG-1也可抑制胰腺β细胞增殖,表明其在代谢调节中的作用[48]。在代谢过剩的情况下,RIG-1诱导Src/STAT3信号传导受阻,从而阻止胰岛β细胞进入G1期[48]。LGP2是这个家族的第3个成员,作为RIG-1和MDM5的负调节因子,抑制炎症[49]。LGP2诱导的RIG-1和MDM5负调控是否有利于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尚不清楚。
1.4 CLRs CLRs是钙依赖的聚糖结合蛋白,共享一个独特的碳水化合物识别域[50],包括1型(DEC205和巨噬细胞甘露糖受体)和2型(Dectin-1、Dectin-2、Mincle、DC-SIGN和DNGR-1)膜蛋白及可溶性受体(甘露糖结合凝集素)[51]。一般来说,CLRs识别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修饰细菌和真菌细胞壁并激活免疫系统[51]。然而,在T2DM等致病性条件下,同样的受体极有可能识别修饰的宿主聚糖,并且不适当地激活免疫系统,导致炎症。与TLRs、NLRs和RLRs不同,CLRs不激活IRFs并诱导1型IFN分泌,其通过NF-κB、AP-1和NF-AT激活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51]。研究报道,在肥胖条件下,脂肪组织中的M1巨噬细胞会诱导Mincle,表明其在肥胖诱导的炎症中发挥作用[52]。其他CLRs在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代谢性炎症中的作用尚待进一步阐明。
1.5 RAGE RAGE是来自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一种45 kDa跨膜受体,基因名为Ager[53]。可溶性RAGE(soluble RAGE,sRAGE)分为内源性分泌型RAGE(endogenous secretory RAGE,esRAGE)及裂解RAGE(cleaved RAGE,cRAGE),RAGE具有结合蛋白质和脂质的非酶糖化和氧化修饰剂的能力,即高级糖基化终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AGE)[54]。AGE不仅是高血糖和促炎/促氧化状态的生物标志物,通过与RAGE的相互作用,AGE/RAGE轴在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中心作用[55]。
RAGE表达的原始来源除内皮细胞外,主要来源于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分布于ox-LDL和硝基酪氨酸的磷脂产物区域[56]。大量研究表明,RAGE在人类非糖尿病和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均有表达,但在糖尿病中表达更高,并与病变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标记物共同定位[57]。将糖尿病、西方饮食喂养的LDLR-/-供体小鼠主动脉弓移植到糖尿病Ager-/-中,发现与野生型糖尿病受体小鼠相比,移植主动脉弓可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消退;在消退的糖尿病斑块中,Ager的缺失降低了巨噬细胞中IRF7的表达;IRF7在巨噬细胞中调节胆固醇代谢和炎症,靶向RAGE和IRF7可能有助于糖尿病血管修复[58]。Bu等[59]在1型糖尿病(T1DM)状态下缺失Ager或不缺失Ager的非糖尿病和糖尿病ApoE-/-小鼠的主动脉上进行Affymetrix基因表达阵列的研究发现,平滑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信号通路的Rho相关激酶1(Rho-associated kinase 1,ROCK1)分支存在显著的RAGE依赖性调节,提示RAGE通过调节ROCK1信号通路加速糖尿病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骨髓移植研究也揭示了髓系Ager在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关键作用[60]。在巨噬细胞中,RAGE配体与RAGE相互作用显著减弱胆固醇向载脂蛋白A1和HDL的流出,并通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反应启动子元件下调胆固醇转运体ATP结合盒转运体(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ABC)A1和ABCG1的水平[61]。在非糖尿病性动脉粥样硬化兔病变血管中,RAGE在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中的强烈表达,可能导致斑块的炎症、血栓形成和细胞外基质降解,进而导致斑块不稳定,这表明RAGE可能是治疗糖尿病和非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新靶点[62]。
sRAGE已经在人类受试者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测试RAGE通路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研究发现,sRAGE血清水平升高与心血管疾病病人的进一步不良事件有关[63]。研究表明,非糖尿病男性血浆sRAGE水平与冠心病或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反相关的横断面关联[64]。低水平的sRAGE能预测糖尿病和非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死亡率[65]。Di等[66]研究表明,糖尿病前期病人的esRAGE水平显著降低,炎症标志物水平显著升高,这些改变与心血管疾病的早期标志物有关。后续研究发现,高葡萄糖负荷1 h后的受试者中,esRAGE与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HbA1c)和高敏感性CRP相关,年龄、HbA1c和esRAGE是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标志物内膜-中膜厚度的决定因素,而esRAGE配体(S100A12)和收缩压是脉搏波速度的决定因素[67]。
2 小 结
代谢和免疫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免疫介质(如细胞因子)决定了新陈代谢的变化,正常的代谢也有利于有效免疫反应的进行。因此,免疫代谢领域的迅速发展为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提供了理论基础。代谢性炎症被假设是由长期营养过剩引起的,PRRs现在已经成为感知营养过剩和引发代谢性炎症的主要传感器。尽管代谢性炎症似乎是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但并非所有的炎症都是相同的,而且每种代谢性疾病似乎都有一种独特的炎症特征细胞因子和炎症细胞。与血清细胞因子分析相比,观察实际分泌这些细胞因子的免疫细胞的研究是有限的。最后,只有在动物模型和临床试验中测试抗这些细胞因子的单克隆抗体的治疗效用时,这些研究才会有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