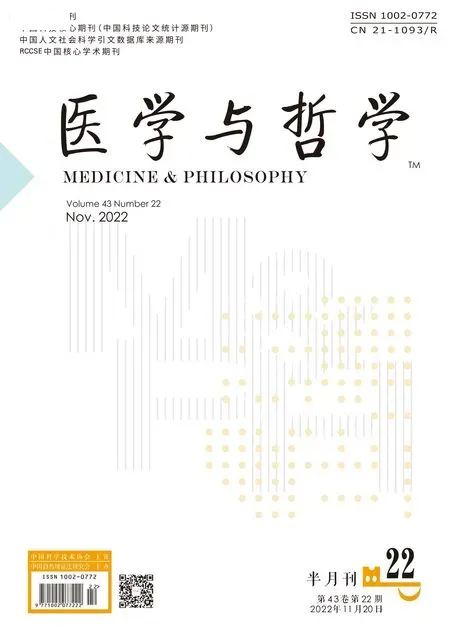从科学革命的视角看《中医内科学》教材的结构性范式*
郭逸文 付广威 桑希生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将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的思路总结为:以病机为核心、病证结合的思路[1]10-12。这是对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十五”规划《中医内科学》的继承。这两部颇受整个中医学界认可的《中医内科学》教材都强调了中医内科思维中“辨证与辨病相结合”[2]的特征。然而,不论是哪一个版本的《中医内科学》教材,在疾病各论当中对“辨证”的强调远大于“辨病”。这种偏袒蔓延到整个中医学实践之中,甚至有以单一的“辨证论治”替代“病证结合”的趋势。张效霞[3]在《回归中医 · 辨证论治厘正》一书中进行了充分的考证,他指出:“近40 多年来,传统中医学中‘证’字的内涵一再被任意扩大,乃至完全改变,其目的均在于使‘辨证论治’能够表达中医学的基本规律与特点,然而这一勉为其难的作法不仅同传统中医学固有的概念和特点相抵触,而且违背了语言学的规律。”《中医内科学》教材的疾病各论作为中医内科学乃至中医学的理论主体,却由于结构上对单一的“辨证”之偏袒,几乎葬送中医内科疾病的论治特色。这警示着学者:一个深层次的变动亟待出现,对于中医内科学教材各论部分的逻辑解构或可为这场深层次变动的排头兵。
这种深层次之变动的必要性并非危言耸听,早在20世纪后半叶,科技哲学家托马斯 · 库恩就预言了一种存在于每个学科当中的“科学革命”-当一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诸多教材体系所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一种如同社会革命般的狂风暴雨注定到来。20 世纪90 年代,潘卫星在《反光:中医学方法论分析》一书中借用库恩的理论分析过中医学的一般范式,但对于中医内科学的临床范式,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1 库恩科技哲学思想的引入
1.1 “范式”概念的引入
托马斯 · 库恩是20 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哲学家之一,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科学学派的理论之变革有着极强的解释力。首先需要对“范式”及其相关概念有一个基础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库恩[4]本人也曾经在21 个不同的意义层面上使用“范式”一词。因此,这里介绍的是最为学者所公认的“范式”定义,即学术共同体从某个经典范例中所引申出的研究规范。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 玛斯特曼将之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内涵:最根本的部分是形而上学范式或世界观范式,这部分较为稳定,因为具体科学往往是构建在某一个世界观之上,而很少能够动摇整个世界观;最关键的部分是结构性范式,这是一个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本质特征;最后是社会学范式或价值观范式,这是学术共同体为了维护研究的合理性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价值共识[5]24。
潘卫星[5]24对中医学的各层次范式进行过分析,他认为:中医学的形而上学范式是一种天人相应的有机自然观;中医学的社会学范式是一种“实用理性”的价值标准;而中医学的结构性范式是以“气-阴阳-五行”来构建的理论系统。他对于中医学的形而上学范式和价值观范式之分析,基本道出了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但是,以“气-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结构性范式,仅仅能体现传统中医生理学的结构性特点。对于中医学的临床范式之分析,在该书中是缺如的。因此,本文尝试将库恩的理论引入到对中医内科学结构性的分析当中,以完成潘卫星在《反光:中医学方法论分析》一书里未能完成的任务。
1.2 “科学革命”概念的引入
范式的本质是被学术共同体视作经典的范例,故范例相较于范式的各种规定性来说,更具有优先性。当某个范例被学术共同体奉为经典之后,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就会模仿该范例。这个过程包括对范例的提问方式之效仿,以及对范例研究手段的模仿。并且,研究成果也会尽量被构建成类似于范例的体系结构。在对范例的模仿过程中,经典范例所包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被学术共同体内化。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得学者们相信自己的提问方式、研究手段和理论结构是无限接近于真理的。因此,科学共同体能够集中资源去解决科学实践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个稳定的阶段被库恩称作“常规科学”,而源自于经典范例的对于研究对象、手段、理论结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规定性,则被库恩统称为“范式”。
当科学实践的环境发生历史的变化时,旧范式不能够满足科学实践的需要。于是,常规科学活动中频繁地出现范式所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学者们对旧范式的信任开始出现动摇。为了应对“反常”,部分科学家试图提出新的范式。于是,学术共同体逐渐瓦解,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最终,某一个新范式全面地取代了旧范式的地位。库恩将这一过程命名为“科学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是因为新旧范式之间难以从逻辑上直接产生联系,故具有库恩所谓的“不可通约性”。因此,范式之转变有着类似于社会革命的断层性特征。
库恩并没有对这种导致“科学革命”的“反常”之来源做过多的解释。但是,这却是具体科学在面对反常时不得不关心的话题。所有的具体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科学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故可以认为:常规科学活动中的“反常”来自于实践环境的变迁。以中医学为例,疾病谱的变迁是“科学革命”的客观动力。正如范行准[6]在《中国医学史略》中指出:新病鼠疫的出现是导致金元时代的中医理论之剧变的重要原因。
2 中医内科学教材的结构性范式的指认与分析
2.1 以证素为核心的病机语言体系及其弊端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及变化的内在机制。病机是一种过程,故唯有通过一种特有的术语体系方可把握病机。正如研究电影的学者把描述叙事过程的术语体系称作“电影语言”[7]一样,我们亦可把描述病机的术语体系称作“病机语言”。
当今中医内科学的病机语言,基本上是对朱文锋提出的“证素辨证学”的实践。朱文锋[8]认为诸种辨证方法之间有其共通的本质,即:“任何复杂的证,都是由病位、病性等辨证要素的排列组合而构成。”因此,可以通过病位和病性两个维度来解构相关的要素,从而重构一种“辨证统一体系”。朱文锋[9]260在《证素辨证学》中分别总结出了20 个病位证素和53 个病性证素,并经过软件排列组合出了637 个证候(即症状)和150 个常见证。进而,朱文锋通过“证候辨常见证量表”规定了证与证候的对应关系。
《中医内科学》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来描述疾病的病机与治疗。诸种疾病的分型论治中:凡是涉及“倦怠乏力”的证候,则会有“脾”“气虚”两个证素出现;凡是涉及“抑郁恼怒”的证候,则会有“肝”“气滞”两个证素出现;凡是涉及“腰膝酸痛”的证候,则会有“肾”“阴虚/阳虚”两个证素出现,等等。简而言之,虽然《中医内科学》教材强调要以病机为核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1]10-11。但是,其所设想的临床模式并没有能够深入到本质层面去思考病机,而仅仅是在现象层面上给症状群贴标签并进行排列组合。
这种病机语言虽然有利于实现中医诊治标准化与客观化,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弊端,即忽视了对于疾病规律的把握。因为,这种“证候-证素-证-方剂”的模式架空了疾病的地位,从而使得“证”处于独立于“病”而存在的状态。这种结构无法为“从疾病规律中把握证的预后转归”预留出逻辑的位置,故学习者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孤立地从“证”的方面把握临床诊治;二是彻底地抛弃中医内科学教材,而走向个人的临床经验。因此,以证素为核心的病机语言体系试图从本质层面上去分析病机却走向了现象层面的排列组合、试图使中医学客观化却推动着学者拥抱了主观化的个体经验。
2.2 以二分法为特征的分析逻辑体系及其弊端
纵观整部《中医内科学》的辨证原则部分,不难发现:其中出现最多的是诸如“虚实”“轻重”“气血”“阴阳”“内伤外感”“寒热”等具有二分法特征的对立统一概念。
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是中医学在两千多年前的实践中就已经形成的思维。范行准[6]在《中国医学史略》中论述过:扁鹊的时代,医家就已经能够对诸如气血、寒热、缓急、邪正、内外、虚实等概念进行区别与运用,故可以在看到表证的时候联系到里证的方面、看到热证的时候联系到寒证的方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是将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综合起来分析,而《中医内科学》则将这些对立统一的双方割裂开来看待。正如范行准的论述中所强调的,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由兼有虚实、阴阳等两个方面的复杂病机所构成,故对立统一概念的指认要求综合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情况以指导用药。但是,《中医内科学》却要求将两方面区别成两种证型以论治,如将水肿根据虚实分为阴水、阳水。而实际上任何一种水肿都是虚实兼有的,故张仲景在治疗水气病时所用之方,皆既可以找到针对实病机的药物,也可以找到针对虚病机的药物。
因此,以二分法为特征的分析逻辑体系有两个方面的弊端:其一,并没有能体现出古人对于诸种对立统一概念的综合把握;其二,仅仅看到了临床病理要素的对立性,而强行割裂了临床疾病的统一性。
不过,二分法的思维有一个间接的可取之处,这就在于从多个维度把握复杂病机。正是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二分概念都是宏观的,故教材中几乎每一次以二分概念去分析病机的时候,都动用了许多组二项对立的范畴。这就潜在地形成了一种以多维度来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多维度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被二分法所割裂的中医整体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放纵二分法继续篡改古人的本意。
3 《中医内科学》结构性范式亟待科学革命的征兆
3.1 致命反常的出现
上文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体系所教育出的医生的临床感受之再现,以及对《中医内科学》内在结构性范式之不自洽性与局限性的指认。由此可以宏观地感受到《中医内科学》的结构性范式所面临的“反常”。不过,这只是山雨欲来之时的满楼风,旧有范式还面临着更加致命的“反常”。
肿瘤成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之一,不同的肿瘤在现象层面的“证候”各异,但都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0]:阻塞症状(如呼吸困难、吞咽困难等)、压迫症状(如声音嘶哑、排尿困难等)、组织破坏(如咯血、便血等)、病理性分泌物(如黏液血便、乳腺溢液等)、疼痛、溃疡。这些症状在早期往往难以被意识到与肿瘤的关联。若仅仅通过以证素为核心的病机语言体系去判断,常会发生误诊。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证素为核心的病机语言体系没有疾病意识参与对预后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症状极容易被关联上“痰”“瘀”等证素。而痰瘀仅仅是部分肿瘤病理过程中的一个继发表现,肿瘤的核心病机应当是形质层面的“恶肉”[11]。
从恶性肿瘤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当下《中医内科学》的结构性范式在面对复杂疾病时的处理能力不足,这种反常迫使患者走向民间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命反常危及的亦是主流《中医内科学》的命运,即一个努力使中医学规范化、客观化的学术共同体之命运。
3.2 世界观和价值观范式的潜在变革
阻碍《中医内科学》结构性范式彻底变革的,还有部分来自世界观和价值观范式的因素,即一种对于“大道至简”之世界观和“智者察同、愚者差异”之价值观[5]28-33的追求。正是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学者追求共性的内容、排斥特殊性的部分,故朱文锋[9]50,52试图将各种临床思维抽象为辨证统一体系,并在构建通用证素的尝试中将具有阶段演变特征和程度递进特征的内容还原为孤立的要素,如将卫气营血的阶段演变还原为“风寒、风热”两个证素、将程度不同的郁结滞病机还原为一个证素“滞”。
然而,《黄帝内经》之所以强调“智者察同、愚者差异”的价值观以及一种“大道至简”的世界观,实则是迫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无奈让步: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若着重于“察异”则会导致“愚者不足”的状态,唯有“察同”方可“智者有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完全能够满足于对特殊性的考察,故唯有放弃简单化、程式化的证素病机语言与二分法的分析逻辑,在一种更加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感的多维视角上革新《中医内科学》的结构性范式,方可真正“为古人继绝学”。
4 具有多维度与层次感的疾病分析模式设想
基于上述的分析,由于中医的临床实践需要综合二分法的两个方面去发现问题,重构后的《中医内科学》体系不妨参考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对水肿、黄疸等疾病的分析逻辑,即:抓住疾病的病因、综合二分法的双方并从层次的视角去探讨病因在人体的阶段性演变。张仲景提出“脏腑经络”层次体系以及由叶天士提出并经桑希生发挥的“气血水精”层次体系[12],应当从辨证统一体系的还原论下复苏。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医内科学》结构性范式中潜在的多维度视角应当在科学革命中被保留,并且还需要在理论重构的过程中被明确提出。正如付广威等[13]从多维度的视角重构体质生理学一样,由于病理与生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医病机体系及其分析逻辑亦应当是包含多个维度的综合体系,如气血水精维度、脏腑经络维度、五志七情维度、六气维度等。
5 结语
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出发,《中医内科学》的结构性范式的确存在着诸多的内在问题,并且其已经面临着“致命反常”,故一场科学革命势在必行。这并不是要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在一种实践与历史的视角上,使得《中医内科学》更加符合中医临床的要求,进而守住主流中医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
除此以外,由于西医内科学在对复杂疾病(如前文所举例的肿瘤病)的处理上有着极其缜密的思维和深入的认知,故《中医内科学》不妨抛开“中西”意识形态的成见,勇敢地走向西医内科学。这关键的一步,既能够推动中医学理论的复杂化,又能够促进西医学理论的个体化。并且,这一步还将在医学领域率先践行李泽厚[14]提出的“西体中用”之设想,或可能开辟整个现代医学体系之范式革命的“六尺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