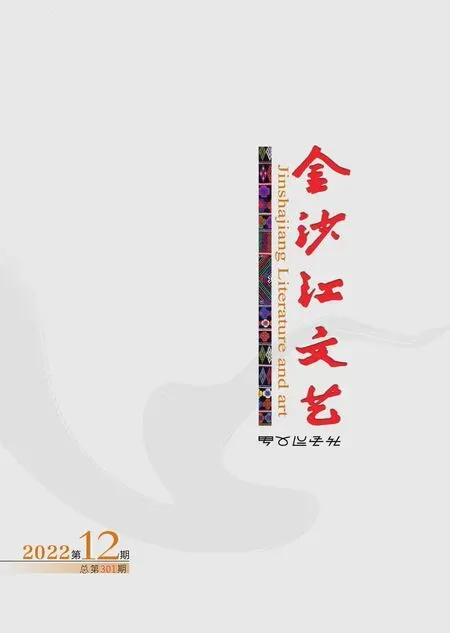两个老人(外一篇)
◎杨 轶(彝族)
我原带着一些嗔怪去迎接爸爸妈妈,怪他们在我期末考前一天约我的老师见面,耽误我复习的时间。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同他们打电话的语气都不是特别好,虽然不是发脾气,但总是在言语间怪他们耽误了我。
但心中的埋怨在看到他们从火车站走出来的那一刻瞬间消失了。
两个人,一人手里提着两大盒东西,沉甸甸的东西把两人的腰都坠弯了。他们从远处走过来,驼着背,在人群中像从很小很小的县城里来到大城市的人一样,眼神畏怯但满含期冀。我在心里觉得他们好笑又可爱:哈,好像两个老人。
妈妈穿了一件新衣服,但还是永远丢不掉的教师气质,打眼看过去就能看出是一位语文老师。爸爸,朝我走来时,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霎时充满心酸。每一次见他,都觉得他比上一次我们相见更老了一些。他怎会老得这么快,明明才半年的时间,明明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就老了这么多。甚至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突然宕机,他老到离我而去时,我该如何面对,好像马上要窒息,连想象都让我难以呼吸。
妈妈走过来问我冷吗,我说不冷。爸爸走过来,看了我的眼睛,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一起打车到老师家附近的地方吃午饭。我没有表现得特别开心,其实我有些畏惧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我总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才能和他们相处得亲近一些。
偌大的城市,我们三人提着一堆东西,真真像外地进城毫无归属感的三个人。穿梭在四周散步、闲逛的当地人群中,我们不属于这座城市,像复制粘贴进这个世界的一样。
随意走进了一家小吃店,我们在那里简单地吃了午饭。饭间,我帮妈妈拿下了一根白头发。其实,我不敢跟他们多说什么,我不想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老了,但事实是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同以前不一样了。
爸爸手上的皱纹变得很多,眼角和额头也多了很多皱纹,皮肤更黑了,还要半摘下眼镜,架在鼻梁上,用电视里老人的姿势看手机。妈妈弓着腰,拿着号码牌,坐在门口等我们的午饭,带着一丝丝不知所措和茫然的神情。我又一次觉得他们像从很小很小的县城里来到这里的人,但不是觉得他们丢我的脸,也不是嫌弃他们,就是莫名地觉得他们像两个质朴的老人带着一点畏惧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不敢贸然行动的样子。我又一次在心里想:好像两个老人。
爸爸和我说他们带了牟定和双柏的特产,还有两瓶酒,还特地给我搜了那两瓶酒的价格,很贵,我就随意扫了一眼,完全没有在意。再说,爸妈从小都没有克扣过我什么,我从来没有为钱这件事觉得烦恼过什么,我没有在意,继续吃着我的东西。
见了老师后,我们一起去了翠湖公园,爸爸想和牌坊留影,让妈妈给他拍照。我在后面看着他们,我眼里的画面是一对退休的夫妻相扶来到公园散步,妈妈还蹲下给爸爸拍照,爸爸悠悠地走过来摆姿势。我又一次在心里想:两个老人。
后来我们去找了姐姐,姐姐在肯德基打工。爸妈说正好给室友带点吃的东西,他们给我买了很多很多,让我带回宿舍。
匆匆地就要离别了,我和姐姐目送着他们离开。妈妈驼着背,背着一个包,催促着走在后面的爸爸,脚步左右左右地摇摆,轻快又不轻快。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又和姐姐说:他们真的好像两个老人。
回到宿舍和室友分享完东西,觉得自己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姐姐也对我好,边吃东西边沉浸在幸福中。正巧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外卖被偷了,虽然只是二十几块的东西,本来没什么,但越想越生气,为什么有这么过分的人,那也是我的妈妈给我的钱。自己的奶奶是一年只花几百块钱的都要留给我五十块钱的人。”
我一瞬间怔住了,一股心酸涌上鼻腔。突然想到爸妈为了我拿了这么多东西来昆明,但爸爸只吃了一碗汤圆一碗粥,妈妈连22块的米线都觉得贵,没点。甚至我都没想起来把吃的东西分给他们一点,就让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走了,然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动于衷。
眼泪止不住地就往下流,我们本也就是普通家庭,又加上早年爸爸生病,看病花了很多很多钱。爸爸妈妈在这些经历中早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甚至妈妈的睡衣都快穿了七年了。
从前租很小的房子住、穿了多年的睡衣、不愿吃更贵的东西……每一件事,和他们提着的那些东西、他们给我买的吃食放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刺眼,叫我心里难受。
打电话给他们,妈妈说她在看风景,爸爸在高铁上抱着手睡着了。我又在心里笑他们:真像两个老人。
写下文字的这一刻,我觉得“像两个老人”,不是“像”,是我侵蚀着他们的生命,我长大一岁,他们就变老一岁;不是“像”,是为我操心一年,他们就变老一年;不是“像”,生命怎可能静止,它会毫不留情地在人的身上留下年岁的痕迹,毫不留情地倒计时,毫不留情地攫取着人与人能在一起的时光。不是“像”,他们就是在肉眼可见地变老。
像两个老人……不是“像”。
看见风筝飞起来
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甚至都忘了,连爸爸妈妈怎么离开家去的北京也都忘了。爷爷和奶奶从老家出来,在我们出租的小屋里,天天照顾我和姐姐。房子很小,连沙发都是用房东留下的,棕色的,很破旧。刚搬进来的第一天,妈妈带我去买了沙发巾铺上时,我在心里默默开心,我们家也有和其他人家一样带着浅色花纹的沙发了。
我和姐姐各有一张书桌,我的在爸爸妈妈和我的卧室里,其实那不算书桌,是妈妈的梳妆台、爸爸的工作台、我的书桌。姐姐的书桌小小地夹在阳台中间,阳台是外露的,只有铁栏杆,下雨的时候姐姐只能把所有书本收起来。那张书桌被雨淋、被太阳晒,但十年来,它一如刚买来时坚固,同人的意志一样。
从小到大,我最怕蜘蛛,可家里的卫生间因为狭窄潮湿,会有很多体型叫我害怕的黑色蜘蛛,它们经常爬在水瓢下、外露的水管后面,黑色的躯体像眼睛一样觊觎着我,每次洗澡我都不敢闭眼睛,洗多长时间我就盯着它看多长时间,我怕稍不留意它就会靠近我。
今年暑假,路过那里时,我进小区从外面看了那个家。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绿漆扁平栏杆的窗子还没有掉色,玻璃都快掉光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奶奶一起睡在床上,奶奶睡着了,我透过那扇窗子抬头看窗外的星星,想爸爸妈妈。
因为一个病魔,我们所有人挤在那个房子里,住了十年。
爸爸、妈妈和叔叔是我全部人生中最伟大的人。得知病情后,爸爸在十分钟之内冷静下来,小县城里的医生在那个年代能有多大的远见,他们告诉爸爸妈妈,就等待生命的流散吧。妈妈一个人躲进房间里哭泣,而爸爸自始至终没有落一滴泪。在之后的时间里,爸爸四处打听消息,到处买报纸看相关的信息。半个月后,他瞒着所有人坐火车去了四川华西医院,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不是奔赴美丽的风景……我不敢切身去想象他只身一人坐在火车上的场景,心在此时此刻是会痛到流血的。他去找华西医院的一位专家问这个病是否有别的医治办法,他不甘被命运摆布。医生说要到北京做骨髓移植,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但越被折磨,越应该反抗不是吗,用生命反抗。
中间的记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为何,为何?
时间来到手术成功的时候,还需在北京留下观察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我到底是怎么坐上飞机的,只记得妈妈的好朋友任阿姨坐在我旁边。那时我七岁,第一次坐飞机,奶奶用彩色头绳给我绑了很好看的头发,任阿姨是学美术的,她用飞机座位后面的纸垃圾袋画下了绑着彩色头绳的我。
然后我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和叔叔三个人住的房子竟然比家里的房子更大,有一台只有七个频道的电视机,笨重地躺在架子上。爸爸住的房子是向阳的,被套床单全是干净的白色,上面还有红色的小花,我多么喜欢那样漂亮的被子,多么喜欢那些小花。每当有了阳光,那间房子就像天使住的房间一样,洁白光亮。
妈妈把爸爸照顾得很好,经常出门买活虾给爸爸煮粥,虾肉在砧板上被剁得很细很细,粥熟了真的很香,可我从来没有吃过虾,我悄悄跑去问叔叔,虾是什么味道,叔叔说他和妈妈也没有吃过。
至今我还记得叔叔给我们做的发面饼,因为发酵饼有了酒的味道,小时候不懂呀,以为叔叔在里面放了酒,妈妈、叔叔和我一起坐在桌子上吃饼。暖黄的灯光照着我们,我倒在妈妈怀里看着叔叔说:“叔叔你真坏,让我们喝酒,我都醉啦。”边说边摇晃着脑袋,我们三个人都仰天大笑。爸爸在天使住的房间里也和我们一起笑,因为他还不能接触细菌过多的环境,他基本没出过那间屋子。但看着他们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叔叔给爸爸捐了骨髓,他在生理上承受的痛苦不比爸爸少,我感激他,把他当作我的父亲一般感激。
北京天黑得很早,我和妈妈很早也就睡下了。床铺是行军床放在过道上铺的,我睡在靠墙的一面,躺在床上,正正对着有一块厨房墙壁延伸出来的板子,我需要小心才不会碰到板子。我问妈妈,为什么北京天黑得这么早,妈妈和我解释时差,我自然是听不懂的。妈妈睡着了,我悄悄用手指在板子上画着时钟的样子,想这是为什么呢。
爸爸不能吃油腻的食物,所以我们的饭菜是分开做的。有一次妈妈做了很好吃的鸡翅,我端着饭碗站在爸爸的房门外,一边吃鸡腿一边看着吃青菜和粥的他,呆呆地站着,我也记不起自己在想些什么。妈妈和我说,想看爸爸就进去,可以站远一点,我端着碗站在与爸爸最远距离的墙角,和爸爸成斜线对视。他的头发都被剃光了,脸很白,但看起来很精神,其实在这之前,我真的快要忘记他的样子了。他看着我笑,和我说:“鸡翅好香哦,再在我面前吃我都快馋坏了!”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他可能也许久没有这样好好看过我了。
在快要离开北京的前几天,妈妈带我去了天安门。夜晚天安门的上空飞着多少京剧里的脸谱风筝。那么多人在放风筝,我抬头驻足,真的很美,风筝上洒了金粉,在夜空里闪闪发光。我在心里想:大城市里幸福的人应该不会经历苦难吧。
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脸谱风筝,我们一起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