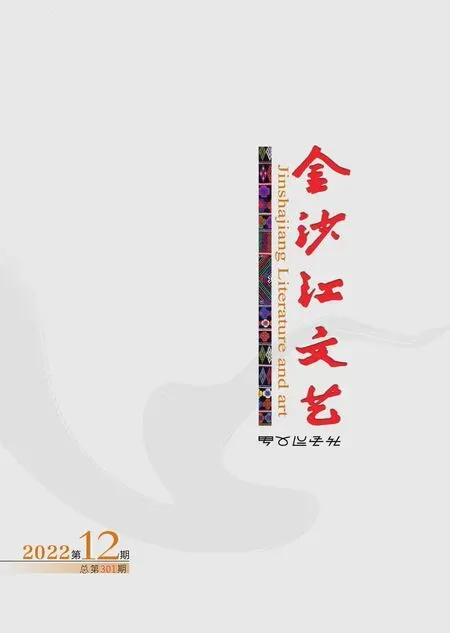潮州巴黎
◎邢若琳(山东)
(一)
高三那会儿,安况睡我下铺。我那时候点灯熬油学到半夜,上进啊,跟现在不一样。有天夜里起来上厕所,见他光着上身,瘦得皮包骨,趴在窗台上,翻看什么纸张。细长的指间烟雾升腾,汩汩融进夜色里。那时我觉得抽烟是只有况子这样的“二流子”才干的事,瞎拽,有屁意义。如今的我,没有烟一天都活不下去。我愣了半天,头一回觉着,他抽烟的样子挺好看。那也是他头一回跟我讲,他叔叔的故事。
他说他有个叔叔,叫安勇。72年生,比他爸小两岁。他从没见过这个叔叔,只能从街坊四邻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人的一生。若不是偶然发现安勇亲笔写的日记,他都不相信,真有这么个传奇般的人物。神经兮兮,听起来都笑人。
“高考完,我就去找他。我真很想知道,他最后,最后到底找到安妮没有。”况子吐出一口缠绵的烟圈,将手中一沓泛黄的纸递给我。
(二)
仔细想来,那个十八岁的夜晚,离现在已有十年。都说这十年是最好的时候,年轻人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我举着T大的录取通知书,骑着单车冲出东坪县城,我还没明白孔老夫子这一套纯属扯淡。后来我恍然发觉,那时候坚信不疑的事,与现在全都惊人地相反。我从没以为我会一直记得况子,没以为他给我的那几张破纸还留着,就像没以为自己会回到这个当初拼了命也想离开的地方,结婚生子。十年,我忘了高中时追过的姑娘到底是长发还是短发,忘了父亲喝醉时甩在我脸上的巴掌是怎样刻骨铭心的疼痛,忘了当初离开东坪时信口说着的那些豪情万丈的鬼话。但是我记得况子给我讲的、他叔叔“安勇”的故事。奇怪吧,我这么个从小到大按部就班的好学生,怎么会对这么古怪又离奇的故事感兴趣,着魔似的,魂牵梦绕这么多年。
“他有个表妹,叫安妮。他俩从小就好,但近亲结婚违法,你造吧。”况子吐字不清,口头禅“你知道吧”听起来像“你造吧”。我心里发笑,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拽一点生涩的台湾腔,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只是东坪县城一个最不起眼的小混混。我接过他手里七零八落的纸张,目光所至,满是泼泼洒洒的钢笔字,随意写就,但苍劲有力。夜凉如水,况子额上留得很长的头发被风刮到脑后,剩下这张记忆中永不褪色的面孔。香烟呛进鼻腔,浓烈而清冽。
“这都是你叔叔写的?”
“嗯。”
(三)
2000.3.30
小安病了。两岁的孩子,烧得脸通红,手一摸都烫人。开始还哭,后来连哭的力气也没有,蜷缩在被子里睡着了。我给她吃了退烧药,在台灯下看着她很长很长的眼睫毛。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安妮就在旁边,小安要是我和安妮的孩子,就好了。
退烧药起作用了,小安额头上起了大滴汗珠,背上更多,被褥洇湿了一大片。我终于松了口气,出了汗就降温了,她能舒服一些,我想。我去壁橱里拿新被褥,秀珠正酣睡,她都不知道小安身体不舒服。她跟她那个卖金银首饰的老爹一样,除了打算盘什么都不会。潮州是个好地方,但是人心冷漠。
半个月前,那个东北来的家伙把五百条皮裤的钱付清了,还是北方人讲义气,说什么是什么。其实钱不是问题,两年以前我就已经准备好去巴黎的路费,还想着雇个翻译,到处打听打听。巴黎一共能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安妮不难找,肯定不难。
但是现在都没用了,因为有了小安。秀珠本来不想这么快要孩子,潮州人没有北方那样“多子多福”的观念。我更不想,我准备动身去巴黎。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就像安妮就在国际机场等我一样。但是一下子没用了,小安来了。
秀珠在店里忙,连跟了她爹一辈子的那个管家都不放心。她说不行就打掉,我说别,是条命啊。
我不后悔生了小安,可我觉得命运在捉弄我。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这十年就像是一个个应接不暇的错误。千玺年,说什么世纪之交、时来运转,这不扯淡吗?今天和明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有时候我想,人也不能活得太悲观了。就算有了小安,也不要紧。不过就是再晚个三五年,我还可以带着小安一起去巴黎。安妮会喜欢她的,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关于未来啊、教育啊,什么的。就算三五年还是去不了,那再等十年可以了吧?十年,如果你一直想做一件事,怎么会做不到呢?巴黎又不是火星,还能一辈子到不了不成?等到小安长成了大姑娘,再去也不迟。
我一开始就不该来潮州的。
去巴黎吧,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四)
“他本来跟安妮好,但是安妮去巴黎了。他去了潮州,批发裤子。娶了个叫秀珠的女人,生了小安。是这意思吧?”我翻过一页,饶有趣味地抬头看况子。他把细长的身子探出窗外,吐出一口烟,不耐烦似的:“往下看行。”
“别吸了,进去说。阳台这么黑,字儿又小,眼都瞎了。”我拍拍况子的后背,这小子真他妈瘦啊,肩胛骨突着,咯得我手疼。
“不想看算了,耽误你考清华。”况子眯缝着眼,舌头抵着上膛,发出“嘎嘎”的怪声。我笑,我俩就是这样,一个奋发向上,一个吊儿郎当。外人看来,从头到脚没一点相似之处,却搁一块儿厮混了三年。
况子这人了解了以后其实挺有意思的,他知道很多别人打死也不知道的事,比方说他这个什么安勇叔叔。我没跟他说过,我从来没像别人说的那样“看不起”他,打心眼里没有。是他自己,心情不好就发飙,拍个图片一排喝空了的酒瓶子。电话里骂,说什么没人管他,哪个妹妹又对不住他了。当年他说这些我觉着很笑人,他分明很享受这种状态,港台片里的古惑仔不是潮流就是偶像。如今十年过去,我不知为何开始觉得,当他说自己很难过的时候,也可能是真的不好过。
“别闹,还真挺有意思。你讲讲。”我踮脚进屋,把床上的台灯提进来。
(五)
1998.5.28
1992年夏天吧,大概是,最后一回见安妮。当时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一年,管吃管住还发工资,回家都是大包小包地带。安妮比我小一岁,刚高考完,在家等成绩。我衷心地盼着她考好,别来当女兵,训练苦啊。我还记着当时坐的绿皮火车是T字打头的,说是条件好,死贵。上车以后才知道被坑了,闷罐一样的车厢里人挤人,前面一大队赤膊的农民工大声嚷嚷着什么。没有风,汗珠子从脸上一串串地淌,纸都擦不跌。我忍不住高声问乘务员:“这破车咋这么贵啊?”那女的瞥我一眼:“空调车。”“那咋这么热啊?”“还没安呢。”
我刚想骂,忽然被刚上来的一对母女挡住了视线。那女孩儿也就十七八岁,一手提一个大包袱,脸上挂着汗珠,白嫩水灵。我不由得笑起来,她长得挺俊俏,但跟安妮比,还差得远。安妮现在干啥哩?她知道我回来,烧饭没有?那些年我爹在海上当渔民,不着家。娘开门市部,忙得自己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我天天往三姨家跑,就是她蒸的那些馍酥肉香的花卷子把我喂大的。三姨很稀罕男孩,但是怀不上,年过四十只有安妮一个姑娘。我娘常开玩笑说,把小勇送给你家当儿子,安妮换给俺。三姨光笑,说你可别反悔。后来懂事了我才知道,三姨那时对我有多好。上初中的半大小子,顿顿来家吃,任谁不烦?三姨却像是比我娘还疼我,可劲儿往我碗里盛肉,还给我洗衣裳,干净、软乎。
那时候小啊,有的是劲,三姨家的体力活都是我干的。三姨说:“安妮没个兄弟姊妹,孤单得很。你就把她当亲妹妹,照应着点。”
是啊,她是我妹妹啊。我陪她玩布娃娃,给她擦眼泪,在三姨发火的时候拉着她往我家跑。替她背锅,逗她笑,一起趴在老李家后院偷葡萄被逮住的时候说是我的主意。我陪她上学放学,给她讲题,逮住那个给她递情书的小子,一拳揍得他鼻子冒血。从小到大,我无数次提醒自己,要好好保护安妮,因为她是我妹妹啊。
她也只是我妹妹啊。
(六)
2003.1.06
部队四年,潮州八年。十多年下来,彷徨无措有时,左右逢源有时,但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提起过安妮。侃大山的时候没有,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没有,跟秀珠刚开始还能聊到一块的时候也没有。潮州人会做生意,就在于明白这个理儿。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定是一回事。
安妮走后,我再没回过家乡。回去干啥呢?难受。我跟我爹说,娘反正没了,来潮州跟我住呗,好吃好喝伺候您。我爹腰虽然弓了,口气硬得很,说打死不跟那个南蛮子媳妇一块儿过,瞧不上。在海上打了一辈子鱼,老了反倒恋家。也不知道当初是谁雄才大略,可劲儿劝我下广东。
“时代变了,勇。当兵有啥好?早不时兴了。你五叔家那一对小子,没上几天学,跟着两个南方来拉货的到处跑,不知倒腾啥,没两年就发了。”我刚退伍那会儿,恰逢禁渔期。我爹一到晚上搬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嗓子眼儿咳咳咔咔,张三李四咋着咋着。我心想,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又不憨不傻,咋就干不了?去。
我娘当时就不愿意,拼死拼活地反对。我离家的前一晚,我娘攥着我的手,哭得眼都肿了。说我爹净看见人家发财,不晓得人家受罪。就算挣几个钱就活得舒坦了?赔了咋办。还有,千万别跟那些南蛮子走得太近,尖嘴猴腮、鬼精鬼精的,坑得你找不着北。
我当时心里还笑,我娘一直也算是个识大体的人,怎么会对我南下潮州这件事这么抵触。如今再回想她那晚说过的话,竟句句应验。又想她年轻时操劳过度,体弱多病,离世前一刻还在牵挂着这个远在潮州的儿子,不由心如刀绞。
我真不该来潮州的。
去巴黎吧,安妮在等我。
(七)
“不是,疯了吧这人。安妮就算还在巴黎,也早就结婚生子了,怎么可能在等他?”我翻看着这些泛黄发皱的纸张,想要再寻出点蛛丝马迹。“这日记残缺不全,中间甚至隔了有七年。而且这只写了潮州,后来呢?巴黎才是重头戏。你还有没有?”
况子抽一口烟,定睛看我,语气半死不活:“没了。就这些。说了这事儿很邪乎,当真啊?”我笑了,拍拍他陡峭的肩峰,说话慢下来:“不是那意思。就是单纯好奇,这个人最后怎么样了。很明显,他脑子有病,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找不利索。”
况子扭过头,将烟头在窗台上捻灭。“咋着有病?”
“二三十的人,天天想着上法国找个女的,魂不守舍想了十年。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他垂下脑袋,很久没再说话。
“睡吧,明天还得上课。”我熄灭了台灯,刚想回屋,却听见他撕纸的声音。
“干吗!你不要我要。”我猛地拽住安况的手臂,抢过已被他撕裂一半的纸张。
“不是说脑子有病么?”他没好气地吼。
“那也不能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叔叔很珍贵的东西。”我使劲将揉皱的纸张展平,拎回床上,在枕头底下压好。“先放我这儿,毕业的时候还你,省得你哪天喝醉了又给撕了。”我在灯下早已看得眼疼,倒头便睡。况子依然站在阳台,月光将他清瘦的背影斜斜拉伸。我不知道他又站了多久,只听到一声轻微的“谢谢”。
(八)
2003.5.30
吵架,天天吵架。祖宗八辈儿的骂,然后就是摔东西。秀珠跟她老爹一个模子刻出来,平时慢声细气、眼珠子溜儿转,鸡毛掸子的小事实际都给你攒着,惹恼了就骂不绝口。也怨我,一点就着。都不敢想,那时候在部队,战友们都愿意和我拉呱,山东人就是厚道,他们说。可是来了潮州,一切就都变了。做生意的,厚道挣谁的钱?
散了吧!汕头裁缝、大连批发商,从南到北没一个好人。上个月我瞅准的那个卡其色,在隔壁店里卖成了“红门”,看着都眼馋。当时差点就拿下来了,干这行许多年,眼光总还有。结果秀珠嫌贵,怕亏本儿。现在好,悔断了肠子,钱还是进人家腰包。
能不怨她吗?就会瞎叫唤,没一个大心眼儿。但我不当家,她老爹是大拿。东南沿海这一片,但凡做服装的,没一个不认识老明。我刚从家乡出来的时候,血气方刚一身闯劲,碰钉子、吃亏。跟秀珠结婚以后,这些破事儿都没了。在家坐着、数钱。
潮州拥有一切,又什么都没有。
(九)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回东坪。
本科毕业,读研,进了家互联网公司,拼死拼活。凌晨两点,特浓咖啡喝到反胃。有天我妈来电话,说今天老糊涂了,以为我还在家,包了我爱吃的花边饺子。我挤在人潮汹涌的地铁中,如鲠在喉。
当初骑着单车冲出东坪县城的小男孩,不知何时起,再没摇旗呐喊的热情。
决定回家乡考公务员的那天晚上,我在狭窄老旧的出租屋内收拾行李。逼仄的空间本就拥堵,又堆满凌乱不堪的杂物,心烦意乱。掀起堆在角落的旧被单,一时间灰尘呛鼻,我才发觉这个屋里除了那个常在手边咖啡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得到过清洁。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它们就静静地待在那里。静默、蒙尘、生根、发芽。无人记起、无人挪动。
这屋子是时候有个女人了,我想。
被单底下有几本小说,旧得起了毛边儿,同样一层灰。蓝色封皮的一本,王小波的,里头有张照片,露出一半的人像。大红T恤、牛仔裤、黝黑的皮肤。手插在兜里,笑得灿然。
那是最年轻的况子。
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十)
2010.4.17
三姨葬礼,大人小孩站一屋,脸孔陌生。除了当年做邻居的友庆叔,没一个人和我搭腔。
“回来了,勇?”
“替我爹娘,来赔个不是。”我看着灵堂上被花圈拥簇的黑白相片,想到那些年吃过的馍酥肉香的花卷子,眼泪止不住地冒。我去潮州没两年,我娘和三姨因为分房子闹恼了,两家再不来往。忘了是哪年过年,我带秀珠回家,想着一块儿看看三姨。我娘挡在门口,说我要敢去,她就敢死。
我问友庆叔,安妮去了法国以后,回来过没。他说没见,就是你三姨两口子,去看过两趟。
“那丫头从小就跟你三姨不亲,看不出来?她是抱来的,性子怯,就跟你能玩到一块儿。这么些年,我一直不明白,你为啥上广东了,没和她一起去那什么法国。”
我问我爹,知道这事儿不?他说知道啊,街坊四邻哪有不知道的。以后别再提他们家,堵得慌。
原来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十一)
高考放榜,我考上T大,一下成了县里的红人。我爸摆了二十大桌,喝得眉开眼笑,说儿子比老子强,这回可算是光宗耀祖。我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儿去况子家找他,心想今儿个得彻底跟他去酒吧浪一回。结果他家大门锁着,有只野猫趴在草窝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第二天再去,他母亲开的门,朱唇粉面,有几分姿色。屋子里烟雾缭绕,赤膊的男人围桌而坐,弥漫着打麻将的吆喝声。女人说,况子没考上大学,去南方打工了。
我猛然发现,高中时勾肩搭背玩儿了三年的人,竟连个电话号码都没留下。
从此以后况子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关心。
可是他那晚给我的几页日记,依然压在我的枕头底下。平平整整,没有一丝皱褶。
(十二)
2010.6.01
这些年挣下的钱,我单独存在一张卡里,七位数。姓刘的翻译今天到了,一起吃了饭。这小伙子很机灵,巴黎留学回来的,法语说得溜。
潮州的最后一夜,闷热欲雨。
巴黎很远,也很近。
(十三)
再看到况子叔叔的日记,我已在县交通局工作了两年。娶了条件相似的明慧为妻,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大年初一,带着妻女回父母家。来了许多亲戚,一屋子吵吵嚷嚷,热闹得很。母亲照例包了花边饺子,小时候的味道,一点没变。父亲喝得满脸通红,兴致勃勃地总结往事,说咱们家几个后生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你瞧老五家刚子,别看上学不中用,如今日子过得最红火。我们家阿亮,当个公家人,虽说不算有大出息,也还凑合。
一个远房的堂兄起身给我敬酒,神情激动:“你就是阿亮啊?早就听说二叔家出了个高才生。你咋回东坪了呢?也不再闯闯。咱这地方小,真是屈才。”
我尴尬地笑笑,碰杯喝酒,突然想到前几天在书柜里找到的,安勇的日记。那些随意写就的钢笔字,我一气读完,好似回到那个浸透香烟的夜里,做一场十年一觉的美梦。况子的脸、况子的脊背、况子点烟的神态,还有他那不可名状的愤怒和沉默,就全都想起来。
况子说他就是个废人,我说别呀,人要有点儿追求。比方说你那个安勇叔叔,哪怕天天想着去巴黎,也算有个盼头不是。
安勇说他不喜欢潮州,打死都不喜欢。至于批了几条皮裤、挣多少钱,其实都无所谓的。潮州的空气令人绝望,绝望到窒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去巴黎找安妮,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些无聊的看客,凭什么说人家不对?我当时真傻啊,说安勇“脑子有病”。十年下来,发现是自己无知。
我不也不喜欢东坪。
(十四)
我再拿着日记去安况家的时候,还是他母亲开的门。她老了,眼角绽开皱纹,蜡黄的脸上沟壑纵横,再无年轻时的姿容。我说我是安况的高中同学,这是他叔叔的日记,当时放在我这儿,忘了给他。
女人很震惊,连忙请我进屋。看完几页,她面色凝重,说我肯定是搞错了。这些东西要么是哪本书上的,要么是安况写的小说,反正不是真的。她说安况没出息,念书念不好,净整些没用的。十八岁离家以后,再也没来信,要么出事儿了,要么是不想见她。
“我这样的人,哪能培养出你一样的好学生。不怨况子。”女人说。
我鼻子一酸,把我的电话写在纸上,告诉她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
临走之前,女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感觉面熟,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是啊,阿姨。我以前来过的,高考完那会儿,来找况子。”我声音哽咽,匆忙下楼。我怕她看见我脸上的泪,也会回头难过好久。
我们已然各自过了十年。
(十五)
后来我想,况子母亲说的,也不一定对。
她都没提到况子的父亲,又怎么证明,他有没有叔叔呢?还是说,其实她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愿对我这个外人讲。不论怎样,有关安勇叔叔的故事,到这儿就算是没了下文。我的日子一切照常,今天和明天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我开始喜欢上安勇的日记,一遍遍看,越看越有味儿。
如果这是十八岁的况子写出来的,他还真算是个人物。不过不像啊,他当年就烫个头发泡个妞,哪还能搞得了文学。有天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看那浓白的烟雾一汩汩融进黑夜,被瞬间吞噬,突然觉着,安勇的故事,我也能继续往下写。
那个姓刘的翻译,是个骗子,卷了他所有的钱,跑了。他就一个人晃悠在巴黎的大街上,逮个人就问,见着安妮了没?见着安妮了没?人家骂他一句,他不理会,继续问下一个。他想啊,巴黎一共能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安妮不难找,肯定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