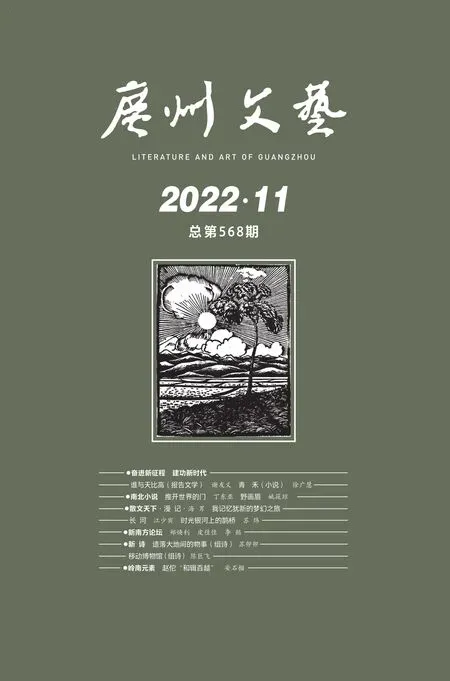从岭南画派到新南方写作
皮佳佳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一位革命者写下“黄花岗上旗溅血,赤子心中气贯虹”,立志为战友复仇。6个月后,清朝派来镇压革命的铁腕将军凤山被炸死在广州南关仓前街。革命胜利,这位革命者却悄然转身,重新拿起了画笔。他希望这片土地创造出新的革命烈焰,在艺术的天空如杲日升空,“高举艺术革命之大纛,从广东发难起来!” 他是高剑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
20世纪初,广东人康有为率先喊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随后陈独秀、吕澂、鲁迅等大家高声疾呼,开启了一场“美术革命”,以求焕新艺术面貌,改良国民精神。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三杰”创立“折衷派”,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道路,强调艺术大众化,希望在中西绘画融合中寻找国画新道路,这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最早提出中西结合的画派。后来折衷派被称为岭南画派,成为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大画派之一。此后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等再传薪火,以强烈的时代关怀和创新意识,在传统笔墨与借鉴融贯上更进一步,形成了具备岭南特色并影响深远的画学流派,这是岭南文化史上的金声玉振。
对于前人的探索,后人有赞许,也有反思,诚然,在融贯中西的同时,不应忽视中西艺术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差异。然而,就当时国画颓势而言,变革在所难免。文人画本是抒写性情、旁通诗意的艺术,清末画者却将本身力求突破窠臼的文人画拉入窠臼,将前代文人画家的胸中逸气变成程式化笔墨。在变革的大潮中,即使坚持国画传统者如黄宾虹,也认为当时所谓文人画多为庸俗之作。只是黄宾虹并不赞同以西画改革国画,主张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处,在复古中寻找创新的力量。即使路径各异,他们都带着使命去寻找国画的前路。
朱万章说:“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现在的绘画环境已与高剑父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提出的折衷中西的理念在今天已经成为任何一种绘画所认可的共识,在技法方面的改良已与今天的状况完全不同。因此,作为开创之初的岭南画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画派,虽然经过二代、三代甚至四代的延续,但其文化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因此,有人提出‘岭南画派已经终结’是可以理解的,但高剑父所提倡的革新精神则永远不会终结。”
作为艺术家,面对时代,他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正如高奇峰之言:“画学不是一件死物,而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每一时代自有每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
而作为写作者,站在同样的土地上,我们又该如何作答?这并不是老生常谈。写作者心里一定有关于时代的共振和焦虑。江山风雨外有万不得已者,这是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应答。我们要回答什么?从前辈画者那里,我们能得到启发,高剑父曾说,“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亦可算是艺术革命策源地”。倏忽百年已过,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的梦想策源地。山海之间,一幅新的千里江山图正缓缓展开。与“岭南画派”一样,我们有着很多疑问,如何创新,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同时,“新南方写作”也是从地域概念出发,寻找新时代经验在文字中的流淌,寻找纷繁现象背后的恒久精神。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次历史性跳跃,从农业时代直接跳入工业时代。这种幅度与力度,也许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用动词和形容词准确概括,“南方”作为这次奇迹的代名词,就这么粗糙、仓促地参与一场如同炼金般的奇迹,冲刺完成本应百年的过程,又在后工业时代急速转弯,在新的领域继续奔跑。这个过程粗粝,却十分完整,从前现代到后现代,就这么并置叠加在大湾区,这是“时间的空间化”。这一完整的时间空间化,在全国来说应当是独特的,也是属于大湾区写作者的独有体验。
大湾区城市群落里,工厂与稻田,高楼和城中村,各种元素杂糅,并列着原始与现代的冲击。正是这种张力,如未成形的陶泥,蕴含原始生命力的无限可能。我曾走进东莞一家工厂,厂房简陋,走进门去,如同破壁进入另一个次元——从《星球大战》《蜘蛛侠》到《变形金刚》《阿凡达》,各种英雄玩偶站立,恍若梦的丛林。厂外有一片荔枝,正是五月,果农忙着采摘红荔,他们并不知道,那些陈列在全世界最高档商场的潮玩,就来自这里。穿拖鞋的老板说,刚刚帮航天部门造出了月球车的模型。对此地的写作者来说,这些并不是外在观察对象,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写作者,也是生活者、创造者,不过让心澄净,等生活的泉慢慢涌出。
同时,大湾区作为一种整体地域概念,不仅探索新的城市生活样态,也在人的层面寻找整体文化联结。立足大湾区的写作应当去寻找这种联结性,文学不应该成为某种装饰品,而要成为地域生活面对世界的价值坐标。
现代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在另一个层面带来了现代性难题。科技改变了生活,又让人逐渐成为格中之物。神性本体让位给了理性主体,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张扬。现代主义替代了宗教之高悬,填补人类心灵空白,那些固有的、共有的价值体系也逐渐消解,人更多强调个体价值,或者从个体去寻找价值,而肉身的可腐朽必然导致价值的无限虚无。即使后现代再进一步,认为现代性也是一种建构,要将这理性主体也进行消解,并没有根本触及价值虚无的问题。
对那种盘桓在现代性难题里走不出去的写作,我保持怀疑,曾经那是经典,然而,现在是否还要延续以个体面对世界的荒诞书写和价值虚空,实在应该思量。把一切崇高拉平,最后也只是交出“无意义”三个字。人类逃不开这些问题,如果生活永远建立在虚空之上,如同只有黑夜而没有白天,那文学也就成了为写作而写作、为虚无而虚无。作为文学工作者,要敢于直面人类命运,要在坍塌之后勇于支撑,思考如何重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大湾区给了这样一种契机,让后现代原子化的个人,在新的空间重新拼贴。这里是曾经的南方,世代生活的人们赓续他们的传统;这也是新的南方,带着各自生活记忆的人们,将新与旧重新编织出另一个维度的通道,让身体与精神聚合进新的游牧之地。这次新旧融合,将在何种程度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之前没有答案。文学离不开一次次回望故乡,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旅行途中的停留。我们重新出发和停留,让故乡不仅仅属于血缘,而是以志趣和心灵为联结的新栖息地。安迪·克拉克说,“心灵在哪里止步,世界在哪里开始”。是的,皮肤并不一定是人的界限,心灵并不是困在头脑里的工具包,心灵可以延展至世界,甚至创造世界。心灵柔光下的城市,不是人的对立面,也不会畏惧被科技吞噬,而把科技视为心灵延展出的银翼。以此为旨归形成的城市,肯定不是赛博朋克里的末日残阳,而是无噱头元宇宙的现实降临。
梅洛庞蒂指出,无穷多的个体与世界达成一个“生命本原的契约”。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作为整体生命的第一个应答者。我们以身体嵌入世界,见证人在时间中的显现,把握世界的身心统一。如同我写下第一个字,我的心灵已经连通了百年前的画者,并将与无数心灵交相辉映,共同指向世界的永恒。在以心灵为旨归的梦想策源地,我们可以去探索属于人类未来的生活,让文学重新建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大湾区的文学是面向未来的。
从岭南画派到新南方写作,我们寻找属于未来的文学,我们也不忘记回头,聆听来自百年前的声音。过去并不只是过去,不是摆放在博物馆的藏品,几千年来的蚝壳、红土、谷粒、绢帛,连同这片土地上曾有的足迹、光影、怀想、诚心,都层积于整体时间褶皱,仿佛已消失的乐音,却以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奏涌现。时间从不会断裂,一如生命的眼,凝望古今。每次俯身向前,都来自我们一次次回望后的勇气。这勇气才能让我们将地理称谓定义为一种精神脊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