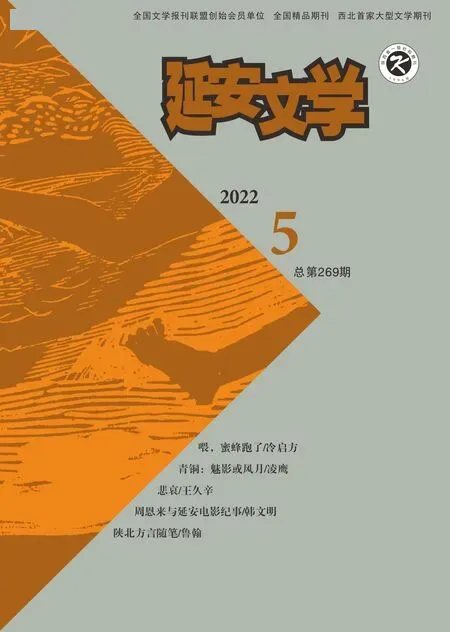野草赋(外二篇)
惠 雁
草,没有不野的。受人豢养,修剪的草已经是草中的另类,有草之形貌,而无草的精神。
草,是时光的手痕,时光之手轻轻过处,草极自然地生发了,湿润处葳蕤而生,干渴处紧贴地皮执着存活。草,就这样绿了江南,装点了塞北。在更辽阔的荒原上人迹少至处,草漫漫而生,成就了百兽角逐的疆场,演绎生命欢与痛的舞台。
一叶草冒出地缝,大地睁开了绿色的眼眸;千叶草从大地上冒出来,大地青丝万缕,青春勃发;衰草铺道,大地又苍桑又丰美。
草最为适意的归所,是村童天真的手,集百草为肴摆家家;是乡女的手指送它到猪舍牛栏;还有那云朵一样的羊群移过,草荒凉的心油然生动如诗。
草是没有权利选择或谈论归所的,这一年一生死的贫贱生命,感春而生,知冷而衰,在山野荒原离离而生,青青而漫,不争不怨不怒不感伤。
草啊,一定深怕寂寞!这敏感于寂寞的生灵,不可遏制的脚步追赶着时光,驱散荒凉,漫过了庭园,覆盖了古道。草想填补大地每一处的寂寞与空白,还是草心里本蓄积着万千的相思,相思疯一样地长。
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草,是大地神经内部的万千思绪,丝丝缕缕,点点处处,总于无端处、无端时随意生发。
也许,草缺乏擎天的志向,缺少花开富贵的憧憬。草只将惊天的风雨化作一次次顽强的倒伏与挣扎,将万千细小的花朵铺满山涯。草,只在低处生生不息,紧贴着地皮护一片水土。
擎天揽月,志与天齐,那是人类的梦想。草,在低处,自自然然立于地,一回生,一回死,这就足够了。
草,于节气里生发干枯,于秋光里粒粒结籽,于大地深处埋下一段根系。草平静而悠然地说:能有一番生,就是美好;看看那万物的有生,看看那繁华与寂寞,就是美好;生命是一场经历,有觉就是收获。
草,低低依附大地,在低处感知生命,在低处体验天光地气,在低处仰望万物,在僻处自生自长,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越!
大地上的野草,这识春秋的贫贱之物,这知炎凉的生灵,也想开出一朵小小的花!草啊,心怀着那么多的梦想,那么多的重任,要不然它不会有那么深长绵延的根,它不会在野火浴身之后,年年知春而发!
草,是那植物世界里的芸芸众生,不在庙堂,在山野。就像人类中的万万民众。
对 草
春天从何处睁开眼睛?从点点的草星儿。
春天才要起程,但草色已经遥遥知意,一星儿鹅黄,一芽儿新绿,点染氤氲出一片朦胧春色来。
转眼之间,这隐隐草色就可定睛细看,但见一片青青之色全然去了娇黄。就像穷困人家的孩子,并没有真正的童年的,会走会跑就自然感知并适应了生存的艰难。
野草,总是欣欣然生长着。
楼下原是有一片花园,花不发,后来又种了草。所种草也日渐稀疏。但这一片园却从未荒疏,另有数种野草地挤满了花园,甚至是参差披拂、杂草竞发。
一种极小的蕨类草,叶子密密实实地铺在地上,紧贴着干瘦的地皮,它总是不计卑微地生长着。最繁盛的要数蒲公英草,早春发叶,未及春分时便开出一朵金黄的小菊花来,那黄菊花衬在一地绿叶之上,鲜艳灿烂。接着,一朵朵蒲公英仿佛胆子大起来,争相绽放。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蒲公英都在开花,密密的叶支持着繁盛的花开,一茬开败了,结起了白色空灵的花苞,风吹即飘,这时又一茬花已经开了。
我每每经过花园,不经意间就对这一园的蒲公英看了又看。看它在烈日下萎靡了,太阳斜时又欣欣然而开;看它不以短暂而悲伤,不以烈日阴雨为愁困,前仆后继,煞有介事坚持一园花开。
来来回回对着这一园花开,我不禁从心里笑道:你这微介之物,还兴兴头头地开个什么劲呀?
这一笑,心里立刻一惊!仿佛草会在起伏的身姿里白眼反问我:你一天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前无车队,后无凤辇,中无陪伴,未见风光,犯得上如此汲汲营营,忧己忧人忧百岁?
来来往往,缓缓走过,我便不敢再笑那草了!仿佛一起嘲笑的念头,就是一种大不敬。这冒犯里会牵扯起心深处的痛。
心,在一次一次面对草时低下来,与草面面相对!
一次还乡,走上儿时常去的那一面山坡,惊讶地看到,这在过去种满了洋芋、麦子的整个山坡,全然间变成了草的“盛会”。蒲公英、打碗碗花、牵牛花等等各色野花铺满了夕阳里的那一面山坡。心一时被那一坡花开抓得紧紧的,想流泪的感觉。如此盛大,如此繁密,如此绚烂地绽放,在这无人到访,更无人打理的一坡弃田里!
这灿烂而放的野花,这密密相挨而生的草啊,在这只有朝光与月辉的山川大地上。
草,生长在大群牛羊的嘴与四蹄下。辽阔的草原上,壮观的食草和食肉动物群在反复迁徙,然而草总是不可灭绝,生与死,低贱与尊贵,在草这里只是倒伏重生之间的一个微笑。
草,在生命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个空间里顽强生长,自然生长。
山花无言,草更无言。
那无言的姿态里,仿佛在宣示着一种庄严与坦然:我就这样活着,不思量任何追问。
悬崖上的一棵草,那姿态多么像是一位得道高僧,在不可汲雨水的险处依旧花开,绿叶铮然,依旧自在地活,自然地活,有兴头地活,给自己活,活出生命的欢悦。
大地上的野草,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总能将重复的游戏玩出兴头。对此简单的游戏乐此不疲,对于生时的乐趣孜孜不倦。
我目睹了草的自在生长,不惧荣枯的那一种洒脱。我见过幼儿甜美的笑,吃饱了,睡足了,他会睁开亮晶晶的眼睛欣喜地看着一切寻常,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会有那么多的妙语赞叹。一颗恬美的童心里,天然与眼里万物透着禅的会意与欢喜。
大自然,就是人类的故乡。童心里,有人类精神的家园。散淡无求或少求,就是天然,就会有幸福。
在宇宙眼里,地球尚且只一微介,何况地球上那出人头地,权贵加身者。
对草,活得多么安然。
草说:这微风里的叶摇,这清晨里的花开,这冬日里的枯萎,是我们的生生世世。我们草族身在低处,漫漫而生。
静静地活着,在来来往往的人海里,活得像一棵草,一棵在背山陡坡上的草。无人来采,也无风来喧,自在地体会一回生命的过程就足够了。
这平常,贫贱,寂寞的生活,其实满含欢欣,多么有滋有味,还想过上千年万年。
活着就是无边的美好。
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在这大千世界里找到一种对应,哪怕这对应只是一地漫漫而生的草,你就不至于孤独,你就会感知到生时的无边美好。
车水马龙的大桥上,有老农背着一捆秋草过来了。那一捆黄蒿草几乎横扫半个桥宽。
从车窗里望出去,我惊讶黄蒿草竟然可以长这么高,那草几乎已经是一棵树的高度了。如果老农不砍掉这与树比肩的草,来年它会不会旧体还魂,长成一棵树?明知道草便是一岁一枯荣,我还是这样的念想。
颀草被砍,那一颗梦想成为树的草心草魂呀!
一岁一枯荣,岁岁心青青。
我的心,一时连通在那一棵草根上,不由得泪涔涔。我还在想,那大地上的千叶草,几劫几世才会完成修练,幻化形状,开口对我说法!
那长在大地上的草啊,活在我渐渐会意的俗心里。
面对大草原,一生辽阔而悲壮地活着,
面对一畦草,天天欣欣然地活着,
面对一棵草,执着而安适地活着。
青青坡上草
一番轻暖又一阵冷雨阴风之后,春天的暖意,终于稳定些了。公园里那绚烂的花儿已开至极,有的已经谢了,这各色的花被养护起来,引人观赏,看久了便也俗了。
荒坡上,弃园里,有那青青的草长起来了,转眼之间就已婷婷地出于地表,没膝长,一茎香,细弱、秀美。草在风中轻轻挥动枝叶,如伶俐的小女儿披拂柔软的长发,飘举青青的衣裙。知道她们在风中的美丽么,《诗经·卫风·硕人》中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鲜嫩柔美的草,只有美人的素手堪比。大片或密或疏的软草随风或徐或急抖动绿色的波浪,似无数的柔荑之手在起舞。你可以说草是在风里挣扎、彷徨,不胜娇弱、悲凉,也可以说她是在演习最美的舞蹈。疾风扫过,即使一次次地扑倒于地、贴伏于泥,风暂歇,草又优雅尊贵地起立,根依旧未作一点动摇,绝不有半点的颓丧之意。草将疾风当作舞蹈的灵感,最是辽阔壮丽的舞台。
谁人会在意草间的一朵花开呢?在五月的暖香里,草间的花还是矜持地、悄无声息地开出了一朵两朵、千朵万朵。鲜黄的向着太阳,淡黄的,也在青草间衬托出了难以描摹的清新,还有那一簇簇洁白、淡粉、浅紫的花也在绿叶间开得烂漫。即使无人观赏,也无须他人前来命名,那小小的草花自开自妍。这是她们这一个轮回里的美丽,不负天恩,不负已心,从从容容开了一朵淡淡的花,小太阳似地擎着。
青青坡上草,无须嫁与如意郎,枝叶沐天露,心事托与风,开一朵淡黄黄的花,结一篷小小的籽,来年春天,再生一群青青的草娃娃。
青青的草娃娃,还送草香于我心。疾风过处,又有一处青青草园为我生。
只要能够感受地气、天光,种子就会发芽、开花。
只要能够内心有所坚持,生命必将如花绽放。
生命的园林中,没有荒坡废园。心灵的天地里,没有被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