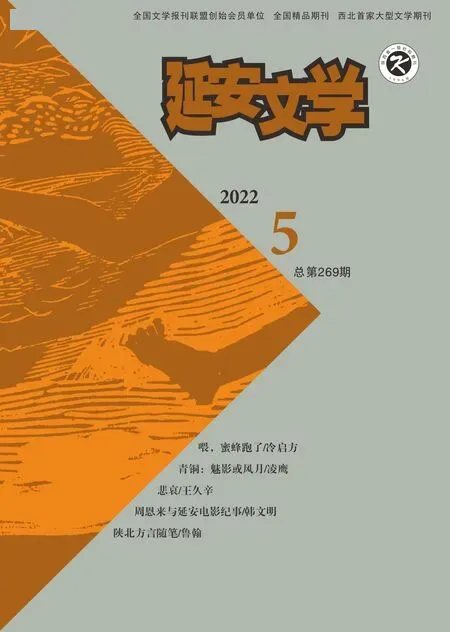鸭绿江边那座水泥平台
王延昌
我和班级里的几个同学是属于比较淘的那一类学生,但不是坏学生,淘学生和坏学生是有本质区别的。淘学生不被孤立,不被歧视,还非常奇怪地很有“人缘”,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还很有些号召力。被认为是坏学生就不同了,不仅被同学孤立和歧视,老师也不待见。其实坏学生在全学校也没几个。
我、赵宇、徐正锋、孙建军都属于淘的学生,我们几个关系又非常要好,人以群分嘛。你想想,四五个淘学生形成了团伙,形成了一股势力,也确实让老师颇伤脑筋。无论谁搞个恶作剧,还是捉弄一下哪个老师哪个同学,都相互策应,彼此支持。有些男生就很羡慕我们的团伙氛围,也以能参与我们的恶作剧,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为荣为豪。仿佛这样才有了气派,才有了“棍儿”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小团伙从来就不缺乏追随者。我们下课了就去教室后面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大谈一些显然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谈论的话题,说些不着调的话,并不时会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来。都极力装出那么一副很成熟很老练的样子,都让自己显出一种很有故事很有经历的样子来。
我们去鸭绿江洗澡时,会无遮无拦地站成一圈,比试我们那个年龄段所特有的正在破土冒头的某些青春期特征,以此来证明自己更成熟更像个男人了,也更有资格谈论关于异性的话题和可以去找个女同学处对象了。
如果谁还仍然是个毛发无有的光溜溜的泥鳅身,就会遭到嘲笑,被奚落成还是个“小屁孩儿”。于是,就都为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长势着急着,暗暗地使着劲,恨不得自己一夜之间就跨入到成人行列。徐正锋就很有经验地告诉大家一个快速催生和助长的方法,每晚要用生姜在那里擦,一边说还一边在裤裆那里比划着,说一星期就见效,半个月就全长出来了。过了好多天,我都忘了这事了,个子最小的还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温建伟很火气地对我说,“徐正锋这个鳖犊子太他妈的坏了,我天天晚上用姜蹭,半夜起来撒尿还蹭一遍,根本没用,这地方都火辣辣地疼了。昨天,我妈还嘟囔说咱家这姜怎么没怎么用就少了呢。”然后他问我擦没擦生姜,我就随口说也擦了,可能是没有坚持天天擦,所以不见效果。
后来长大了,我们这批同学大部分都在矿上工作了,也就经常在一起聚会。我就提起这事,大家全笑翻了,唯独温建伟笑得像哭似的。末了,他用筷子指点着笑歪了脸的徐正锋,全班就数你最坏!
说徐正锋最坏当然是句玩笑话,但徐正锋是我们班级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我们这些男生搞对象最早的一个,也是最早上班最早结婚的一个。初三还没念完,他的父亲就在矿工职业病普查中办理成了二期矽肺,按当时规定,二期矽肺病职工适龄儿女可以直接入矿上班。徐正锋转眼就成为了一名机修学徒工,早早地上班挣工资了。
徐正锋搞对象最早,就和我们班的付秀丽。那时候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把学生之间早恋一律叫搞对象,在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把“搞”字强调的很重。我觉得这个“搞”字用得很传神,在美好的异性情感前加上这个字,美好的情感一下子就不美好了,一下子就被踩在脚下了,一下子就被吐上口水了,这种美妙的情感活动一下子就给人一种偷偷摸摸、捅捅咕咕的感觉了。真为大人们对汉字的智慧运用和组合而产生出来的这种神奇效果叫绝。
徐正锋、付秀丽分别在男生和女生堆里都是个子最高和体型最大的,但学习也是全班最差的。他俩就理所当然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并且还是同桌。那时老狼的《同桌的你》还没出现,徐正锋也没有把付秀丽的长发盘起,但却在桌子底下经常摩摩挲挲地搞小动作。这个奇观,我们班级的许多男同学都亲眼所见。特别是下午上课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趴在课桌上恹恹欲睡,他俩就借机搞起了小动作。我们只要弯腰装作捡掉在地上的笔呀本的什么的,就会偶尔看到这一奇观。时间长了,他们在同学面前也就不避讳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了,仿佛他们就是天生一对似的。我们甚至会在徐正锋面前戏称付秀丽为“嫂夫人”,徐正锋就很满意,表现出很大哥的样子来。付秀丽是个性格温柔但不内向的人,长大后也是那样,怎么拿她开玩笑,她也不恼,就知道笑。因为皮肤很白,一笑时脸上会快速地红起来,哎呀叫一声,在拍打你一下的同时,会嗔怪地喊一声你的名字,但一定是在你的名字前加一个“死”字。比如,哎呀,你个死赵宇!
徐正锋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中,结婚是最早的,但“嫂夫人”却不是付秀丽。这个也很正常,中学时期就早早搞上对象,然后又双双走进婚姻殿堂的同学夫妻,好像也不多见。
在中学那几年里,徐正锋和我的关系比较好,一直到我也入矿上班后,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可以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彼此之间没有那种成人间的小心和提防。这里还有个原因是他上班早,工资挣得比我多,花钱比我宽绰,我是刚上班的学徒工,学徒期间工资不多。
那是他要结婚的前夕,我们俩在矿区的小酒馆里喝了许多酒。他喝得舌头都有些不会打弯了,但是眼神格外亮,直勾勾的盯着你。他将半杯白酒又灌进嘴里,然后逼我也把那半杯白酒干掉,一字一字语气很重地说,我要结婚了。我说我知道。他对象也在矿上工作,比他小好几岁。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最后没有找付秀丽,我要是想找她,她就能跟我。我说这我信,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找她结婚。他告诉我,其实他在心里一直都很喜欢付秀丽,毕竟是他搞的第一个对象,她什么都好,但就是最重要的一样她没有,就是她没有正式工作。他说他父母是双职工,日子过得就宽绰富裕。他那三个叔就是单职工,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吃得不好穿得不好,遇到用钱的时候总是东挪西借的。他很少去这些叔叔家里玩,因为他们生活那么拮据,你去了是给他们添麻烦。他又说,你说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图个享受么,我上班第一天,我父母就和我交代了,将来找对象一定要在有正式工作的人里找,住家过日子一人挣钱和俩人挣钱那是绝对不一样的。没有工作的你考虑也不要考虑,也别给我们往家领。
这都是父母的生活经验呀,我不能不当事呀。说着,他继续大口喝酒,喝完还使劲地摇着头,很痛苦的样子。
我在班级里,是个小个子,长得也不起眼。这样一种情况,我的青春期就注定是缺项的。我曾偷偷地同时喜欢过本班级和其它班级的,甚至还有高中部的不止一个的漂亮女生。其实除了本班级的女生,别的女生我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只是远远地看着人家而已。说来可怜,在整个中学时期,从未察觉到有哪个女生对我有好感。所以,我只能可怜巴巴地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找点快乐和满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班后的几年里。
清楚地记得是我上班不久以后,有一次,我和徐正锋在小酒馆喝酒,看他喝兴奋了,什么也不在话下了。我就问他你搞对象到底都搞到了什么程度。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用我们这地方的话说,虽然没吃到过猪肉,那看看猪跑还不行么。
他使劲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喝下了一杯酒。就很够意思地告诉我,就在中学毕业后第二年夏天的某个晚上,他们的对象搞到了我想知道的那种程度。我陡然兴奋起来,脑中开始闪现出一些画面。我当时特别想知道他们那个“第一现场”在哪里,是一种什么环境。他说就在江边的水泥台子上,我脑中的画面就一下子切换到了江边的那座水泥平台上。那是个废弃的水泵站,上面的水泥平台能容纳几十人,有台阶可以上去,就在沿江公路的下方,矿上的通勤车上下班一定要经过那个废弃水泵站。矿上的人再熟悉不过了,都叫它水泥台子,是个很好的钓鱼台,当然也是年轻人搞对象的好去处。临江,碧水悠悠,江风习习,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异国风情,令人遐想。他俩选的这个地点居然是这么浪漫的地方,并且是我天天上下班都能看到的地方,还是他们的第一次,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我的想象力瞬间就活跃起来,就有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感,就好像他们就在我眼皮底下一样,但那画面却是模糊、凌乱、支离破碎的。接着他对这篇特别记叙文的其它要素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我就觉得徐正锋真够朋友,这事情都对我讲。
他还以过来人的姿态向我传授经验,他说我告诉你啊,等你搞对象的时候要是想那什么的话,那必须得按步骤来,简单说就是三个步骤六个字,谁都离不开这几步。我就特好奇,在心里琢磨着,这搞对象还得有步骤啊?说完,他把一支烟拿在手里,笑眯眯地看着我,在桌上一下一下地蹾着,富有得很,得意得很。我就赶紧按着打火机,让打火机燃着火苗,等着给他点烟。按他的说法,搞对象的六字方针是一亲二摸三……
那天听他说了那些事,给我撩拨的热血沸腾,大有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之势。我不时地插话问他,尤其问一些细节,你怎么知道她是第一次,你怎么向她提出的要求,她都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反抗,那次之后她再见到你的时候有没有不好意思,我甚至问到了你们是不是把衣服铺在了水泥台子上等等等等。
他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令我意想不到但同时经他一点拨又是让我霎时有了窥到真相后的那种恍然大悟。我就一下下地做挠头状,笑得意意思思的,在恍然大悟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没经过没经验”而惭愧着。
自从我们俩那次喝酒后,每次上下班坐通勤车经过那座废弃在悠悠江水边的水泥平台时,我都会抑制不住地想象在我们中学毕业后第二年那个夏日的夜晚,徐正锋和付秀丽就在这个水泥平台上的种种样子,脱下的衣服就铺在平台上。这个属于徐正锋和付秀丽的水泥平台给了我太多的想象和冲动,它刺激着我身体里的荷尔蒙激素旺盛地分泌着。我就常想,那个属于我的女孩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我也能和她在这水泥平台上像徐正锋和付秀丽一样也那么搞搞对象呢?也把衣服铺在平台上……
这个我每天都要经过的废弃在鸭绿江边的水泥平台,它承载了我在那个时期对爱情以及性的所有向往和渴望。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符号,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寂寞而热烈的青春岁月里。
非常有意思,在我们这班同学里,徐正锋除了学习不是第一(但也是倒数第一),在其它方面他总是与第一有缘。徐正锋是我们这班学生中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离婚的。两口子因为什么离婚,我们不知道,他不说,我们也不便多问。离婚后,那比他小好几岁的前嫂子很快就和她当年的一个同学结婚了。
很快地,就听同学们说,付秀丽和她的丈夫总吵架,还上纲上线地要离婚。我们都觉得这似乎不是巧合,于是都怀揣着一种既定结果的期待,甚至希望付秀丽快些离婚得了。
这期间,我也结婚了。我和徐正锋还时常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他告诉我,现在这样子也挺好的,先不着急,儿子由爸妈带着。还不无得意地说,放心吧,我自由着呢快活着呢。我心领神会,就问,付秀丽是吧?他就笑了。
大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徐正锋又结婚了,但付秀丽却没有离婚。徐正锋找了一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做服装生意的女人,也是离婚的,这女人在商场有两个摊位,还雇了个人给她打工。可知这第二任嫂夫人绝对是个搂钱的耙。知道这个消息,我竟没有感到意外,我想起了那次喝酒他和我说的话。在爱情与物质两者前,徐正锋选择了后者。不过,我这么认识问题也不对,首先爱情与物质并不是对立的,其次爱情这东西是两个人的世界(没有爱情了,就是世界上的两个人),有与没有爱情别人怎么能知道。再其次,两个都是离过婚的人,还爱情个啥呀,也就是搭伴过日子得了。
在生活面前,你得允许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徐正锋的再婚,仍然没有选择付秀丽,但你不能说他有罪,付秀丽不是没离婚么?但据我所知,只要徐正锋有这个意思,付秀丽就会毅然决然地和她丈夫离婚。这是徐正锋亲口和我说的,这个,我信。
徐正锋的再婚,是大张旗鼓地操办了一下。在本地的同学们全部都来了,当然也不能缺付秀丽,她打扮的还挺招展的,似乎是有意的。我们这些没有离开矿区的同学联系的特别紧密,经常在一起聚会,聚会就是聚餐喝酒,嘻嘻哈哈,胡说八道的,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那些禁忌了。也许这和矿区的特殊风情有关系,我们矿山有近百年的历史,伪满时期就已经建矿,矿藏遭到小日本的疯狂掠夺。一代代矿山人将乐观豁达、粗犷豪放、海量喝酒的性情传承了下来。用有的男同学的话来说,你说咱们都还装什么装呀,再过几年都快成干巴茄子,快使劲得瑟吧,就你身上那几根鸟毛,不得瑟也快掉光了。轰的一下,让你笑出了眼泪来。笑过,就端起酒杯往桌子上一蹾,过个电,来吧,走一个。
徐正锋和付秀丽之间的关系,我们同学之间不但都知道,而且还经常拿他们开玩笑,但这些玩笑只是在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开,在其它场合,我们绝口不提,大家都知道怎样戏谑和保护他们俩。他们也不在乎,在中学时期不就不避讳了么,我们也早就认可他们了。所以,每次同学聚会,无论是他们俩谁先到,坐下后,他(她)旁边的那个座位一定是没人去坐的,大家会很自动地留出那个位子让他们坐在一起。等那一位来了之后,就不谦让地直奔那个预留位子坐下来。有时候位子靠里时,还要费一番挪椅子、起立、收腹的周折,大家也从没有嫌麻烦过。
那天的天气还真不错。婚礼是在职工饭店办的,地方挺宽敞的,大厅能摆开好几十桌,里面还有单间。典完礼后(二婚还典什么礼,到点就开喝得了),我们这些同学就去了专门给我们准备的一个大单间,单间摆了两张桌,全上了酒菜。十五六个同学分两桌坐有些稀松,坐一桌就有些挤,但大家都想坐在一起,图个热闹,要个气氛。就都把椅子换成塑料凳,挤挤挨挨坐了满满一大桌子,反正菜是两桌的菜,不够从那桌端过来就是。妥了,那就喝吧,造吧,二婚不也是婚么。
男女同学围坐一大桌子,果然热热闹闹的。当然这次付秀丽旁边没有预留空位子,新郎官今天忙着呢,就不能和我们一起热闹了。都倒上了酒,还没等喝,刘洪涛就开始打趣付秀丽,说付秀丽你今天应该是我们这些同学里最高兴的一位,你要多喝点酒才对呀。付秀丽使劲地白了一眼刘洪涛,一脸嗔怪,我凭什么就得多喝?刘洪涛煞有介事地回头看看其实是关着的门,一脸坏笑地冲着付秀丽说,你今天必须要多喝,为什么呢?因为徐正锋今天终于结婚了,他结婚了,咱不就—轻—松—了—么。刘洪涛将“轻松”两个字说得宛转悠扬,赋予了某些色彩,同学们的脸上都开始呈现出了要大笑前的神色。付秀丽的脸腾地红起来,隔空拍了一下刘洪涛,嗔骂一句,哎呀你个死刘洪涛!
边吃边喝中,新郎新娘来敬酒了,徐正锋看看那空的一桌,就明白我们是图热闹才挤在一起的,就说,挤一桌可以,但是酒菜都是给你们准备的,随便造,你们不吃不就剩了么。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两桌的人当然要吃两桌的菜了,吃不了我们兜着走,我们打包。他说,对,吃不了,就打包,别浪费。晚上咱们换个地方再整一桌,我们俩口子陪大家好生喝喝。这也是我们同学多年形成的惯例,逢哪个同学家里有喜事聚会时,除了白天捧场的酒席,晚上这个同学一定还要再安排一桌好生喝喝的。
因为晚上还要好生喝喝,大部分同学就留了酒量,菜吃得自然就不多,另一桌上的海鲜、青菜、凉菜、豆腐都被我们端过来吃了。清蒸鸡、红烧鱼,还有几个肉菜我们都没动。临走时,有同学就看着这几个没动过的菜说,这还真没吃了,看来真要兜着走了。就又有人嚷说,刚才是谁说的吃不了兜着走来着?刘洪涛这时凑过来俯身看着那被蒸过被烧过的样子很归顺很可怜的鸡和鱼,翻了翻眼皮,缓缓抬起头来,抬眼将目光稳稳罩住了付秀丽,又慢慢地翻了翻眼皮,像是在翻弄他最恰当的鬼点子,慢慢悠悠地来了几句打油诗:当年正锋吃不好,属你秀丽对他好。我看今天这鸡鱼,咱就顺手打个包。付秀丽的脸就又腾地红起来,就又隔空拍了一下刘洪涛,就又嗔骂,哎呀你个死刘洪涛!
有人隔在付秀丽和刘洪涛之间,说,付秀丽你打包吧,谁也没动。付秀丽夸张着表情说,不打!又有人说,打包吧,还都是硬菜呢。付秀丽继续夸张着表情说,不打!有女同学说,秀丽,不打包,真白瞎了,一点都没动,回家热热吃多好。付秀丽的表情就忸怩了一下,嘟囔着说道,不打,谁爱打谁打!又有女同学说,秀丽,打了吧,好好的鸡鱼,那就和你订做的菜一样,就你家离这近,咱不打白不打。付秀丽有些嫌麻烦的样子说,还打么?这时孙建军拿了个迎风而立的形象振臂一挥高叫道,对,秀丽呀,打,咱不打他的咱打谁的,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打了也白打,打,给我狠狠地打!大家轰的一声又是一阵大笑。这时,陈爱枝已经把方便袋拿来了。付秀丽突然收敛了笑容,一脸坚定地说,那就打!
几个女同学就帮忙把那冷却后已失去食欲感的鸡鱼和几个肉菜往方便袋里倒着。付秀丽一派很理直气壮,很当家作主的气势,一边狠巴巴地往方便袋里倒着菜,一边扫视着刚被吃过的那一桌说,那个水煮虾和牛排也可以打包。
付秀丽的两手各拎着三四个沉甸甸的方便袋,白花花地在身体两侧悠荡着。和我走在后面的刘洪涛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手指暗示性地按了我一下,用眼神很有内容地指引我看付秀丽,冲我很有意味地一笑。
他笑什么呢?他想到了什么?我们想的会一样么?以往无论是同学还是同学之间有什么事情,刘洪涛总是愿意和我说说,交流交流。这次,我们却奇怪地谁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最后,我还是说说那座废弃的水泥平台吧。其实,就是因为当年徐正锋酒后告诉了我那个水泥平台是他们的“第一现场”,而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朋友,正处在对于爱情有着近乎于疯狂的想象和向往的阶段之中。我想,每个正在年轻着和曾经年轻过的人,都会正在经历和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所以,那座水泥平台对于那个时期的我来说,似乎就成为了爱情的象征。也正是这座水泥平台让美好的爱情在我的想象中变得具体和清晰起来,这犹如许多人在面对遗迹、遗物凭吊古人或感慨往事时而产生的那种遥远而真实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座水泥平台还沉默在鸭绿江边,在有的年份因雨水过多江水暴涨会把它淹没。淤积的泥沙也快要与它平齐了,四周茂盛着杂草。就那么安静着,寂寞着,似乎没有人会在意它。
其实,后来,我也没有把我的女朋友约到那里具有朝圣意义地搞过对象,但在当时,我确实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许下宏愿,我一定要把我的女朋友约到那个水泥平台上,也在夏风阵阵的夜晚,把衣服铺在上面……有时候,真实会无情地击碎你梦中的东西,却不会发出惊魂的脆响。倒是在一个休息日,我和妻子领着儿子顺着沿江路散步,当看到那座水泥平台时,大概四五岁的孩子觉得临水的那个平台平展展的会是个好玩的地方,就指着要上去玩儿。在平台上,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徐正锋和付秀丽,也想到了当年我的那个隐秘的令我着迷的但却没有实现的想法,就无声地笑了。妻子看了我一眼,大概看出我的笑里有些内容,就歪着头研究着我,问,你笑什么呢。我看着妻子突然想说点什么,但还是摇摇头说没笑什么,随即,我却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现在,我上下班坐通勤车还是要走沿江路,还是要经过那座水泥平台。偶尔地,我会看着那个四周杂草的水泥平台,突然地想起徐正锋和付秀丽来,但却再也没有了当年那些衣服铺在平台上的种种画面的想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前却会浮现出付秀丽那次在徐正锋婚宴上狠巴巴地打包的样子,和她两手各拎着的那三四个沉甸甸的方便袋白花花地在身体两侧悠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