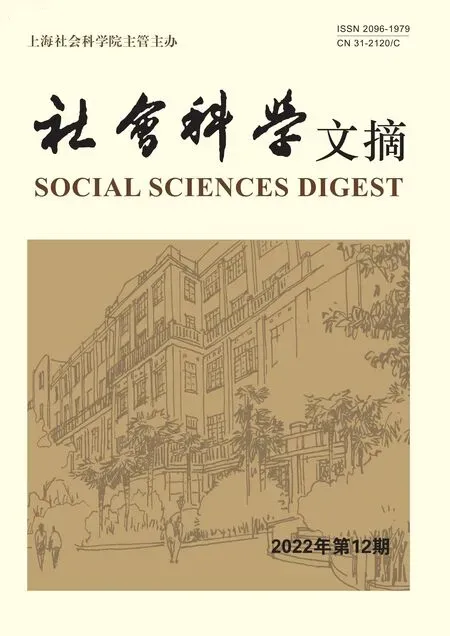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一体多面”: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文/周黎安
引言
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概括。比如费孝通先生就指出,皇权统治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止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而乡村社会是“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士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形成皇权与绅权的“双轨政治”。温铁军也提出,中国晚清以前的政治是“皇权不下县”,概括起来就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以萧公权、瞿同祖为代表的学者则明确否认了中国传统乡村在中央集权之下享有自治的说法。也有学者提出国家与社会相互调适、密切互动的观点以及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理论概括。
上述学术争论主要围绕着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程度而形成不同的判断。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从资源汲取和动员的国家能力视角提供了新的理论概括。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专制性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弱”的治理形态,中央朝廷看似高度集权,拥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基础性权力不足,难以渗透至社会基层继而大规模汲取资源,例如税赋占可征用的经济资源比例就很低。与曼的理论概括相对照,黄宗智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分析概念,强调中华帝制治理形态一方面是皇帝专制权力的集中性和绝对性,所有官员均由皇帝任命;但另一方面,皇权在基层治理上是高度简约的,利用准官员和非正式制度治理社会,区别于现代国家的官僚政府依靠正式化的公文系统、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例如在司法领域,传统中国除了官方正式的司法判决之外,广泛依赖半官半民的非正式调解制度。“集权的简约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曼所强调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之间的巨大张力,指出看似“基础性权力弱”的表征——如“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依靠准官员和士绅治理——其实是王朝国家借助庞大的准官员队伍,以低成本、广覆盖的方式统治如此庞大的疆域。
关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方式,傅衣凌曾深刻揭示出中华帝制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奇妙结合。一方面是中央政权的高度集权和王权的绝对强制性,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如多元的财产所有形态(官田、族田、民田)、多元的司法权(如官方律例与法庭审判、宗族裁决审判、民间调解,以及政府的律例与民间族规、惯例并存,法庭裁决与民间调解、宗族裁决并存)。而且,用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社会传统社会奇妙地统一着,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描述,可谓众说纷纭。“士绅自治”“官民合作”应该各自有其所适用的治理领域或特定历史时期,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特征在这些不同治理领域(或历史时期)的大致分布呢?对于大致相似的国家治理形态(例如王权与基层社会看似松散的关系),学者赋予了很不相同的解释(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轨政治”,“专制性权力强”与“基础性权力软”的组合,以及国家治理的一元性与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这些相关联却旨趣各异的理论概括呢?傅衣凌关于中华一元性与多样性的概括非常具有洞察力,尤其放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之下,更彰显中华帝制国家治理形态的鲜明特色。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华帝制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如傅衣凌所述的中华深层结构的稳定性、统一性与表层结构的多样性、适变性又是如何连结起来的?其内在的驱动力量和治理逻辑是什么?
本文尝试运用行政发包制理论对中华帝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相比如上概述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笔者曾经提出的行政发包制理论蕴含了一个对于中华帝制国家治理的解释性框架。它不仅通过“行政内包”的视角理解从朝廷到州县官的行政发包链条和具体形式,揭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的运作特征,而且还从“行政外包”的视角透视国家与社会的连结部分,解释行政外包的重要特征与内在机理,探索官民互动的诸种形式,包括国家组织边界的伸缩(如从“官吏一体”到“官吏分流”)。该理论借鉴了威廉姆森的交易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如科层制、市场关系或两者混合形式)与经济交易的具体特征(如交易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王朝国家的视角看,在不同的治理领域,如资源汲取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性公共产品供应、民间内部秩序维护,国家—社会互动关系面临不同程度和范围的统治风险,政府处理这些关系也涉及不同规模的行政治理成本。王朝政权面临的预算约束使得政府有动机在统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节约行政治理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约束越紧张,政府节约行政治理成本的动机就越强烈。为此,政府迫于预算压力将一系列公共事务“外包”给社会团体和个人,具体的行政外包形式则依据公共事务和治理领域的特征而相机变化,国家—社会关系呈现“一体多面”、丰富多变的治理形态。
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一个分析框架
在统治风险高的公共事务领域,如国防、征税、社会稳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水利工程,政府倾向于直接参与,完全委托民间提供这些服务容易面临多方协调的困难,也可能发生社会承包方打着官方名义恃强欺弱、过度搜刮老百姓而引发社会动荡。对于这一类事务,政府直接供应无疑耗资巨大(如建立行政机构、雇佣政府人员、组建职业化军队等),但相比潜在的统治风险而言,这些成本付出也是值得的。即使在统治风险高、国家直接介入程度高的治理领域,国家也会有降低治理成本的动机,寻求更加有效的官民组合方式。例如钱粮上缴和社会治安属于州县官两大政绩考核指标,尤其是钱粮上缴每年都有硬性上缴任务。为了完成这些基本任务,我们看到的是王权对乡村社会的强控制,编户齐民、里甲制、鱼鳞册等统治工具深入每家每户,乡民之间的血缘关系和自然聚落关系被国家设定的“里甲制”“什伍制”“保甲制”进行了人为的切割与组合,进而在自然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上嵌入了反映国家意志的印记。这最接近于秦晖提出的“吏民社会”的情形。从这一个侧面看,王权用自己的意志“塑造”了民间结构与秩序,通过乡里制深入乡村汲取税源,派发徭役,支撑朝廷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县以下的乡村行政建制则依情况而变,例如秦汉时期盛行的乡官制到唐宋之后就变成了职役制。乡官作为国家正式官吏,享受国家正式薪俸,履行政府职责,属于典型的“行政内包”;而职役(如里正)一方面是官方任命,承担政府指定的公共职责,但同时又是农民身份,花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为政府“勾摄公事”,属于典型的“行政外包”,可以称之为“准官员”。
在统治风险总体不高的领域,如区域性的公共产品提供(道路、水利、救助),国家就会寻求更加开放、多样和灵活的“行政外包”方式,以减少国家的行政和财政负担。但即便在这样的场合,国家并非“撒手不管”,而是仍然保留行政的相机控制权,犹如一只隐性之手,视情况随时准备干预,民间社会只有在不威胁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此时国家不干预)才能享受“自主性”。另外,视政府财力情况,官府仍然选择程度不同地参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个治理领域最接近于文献所强调的“官民合作”的情形。在水利、赈灾方面,当国家财力充裕的时候,政府会直接组织动员,主要以“官办”形式兴修工程和提供救灾设施,保证社会免受水患、灾荒的困扰;但如果财力紧张,则更可能外包给民间力量,政府只是负责引导和监管。
民间内部秩序的维护与管理,如三老、乡约、宗族、商人会馆等,主要涉及村庄内部的礼仪教化、民间组织的日常管理。因为局限于一个相对更小的群体范围(如同俱乐部产品一样),单一村落或宗族的失序对于国家来说威胁不大。从州县官的角度看,一个县所面临的村庄聚落、宗族数量之多,远超县衙门的监管能力,因此只能委托(外包)给这些民间组织自我管理,采取“官督民办”的治理模式。这是最接近于费孝通等学者所强调的“士绅自治”的领域了,但我们很难将这种“自我管理”看做是“士绅自治”状态。原因很简单,且不论三老、乡约(约正)本身就是官方授权、且享有半官半民的身份,即使宗族和会馆的内部管理也只是一种政府相机控制下的自主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外包”的概念特别适合分析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和“一元化”权力使得王朝政权面临“无限治理责任”,所有涉及政权稳定的事物都是政府关心的事务,王朝国家以相机控制权为基础,向官僚体制之外、满足一定“资质”条件的社会团体(个人)外包政府事务,赋予后者“半官方”身份,并给予必要的引导、监督和奖惩。在此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的治理特征决定了“行政性”机制与“外包”机制之间的组合配置,塑造相应的治理模式特征,由此形成了国家治理所呈现的“一体多面”的总体格局。
本文的贡献
借助行政发包制理论及本文的拓展分析,我们也可以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华帝制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些理论概括进行重新评价。例如曼关于“专制性权力强”与“基础性权力弱”的概括只是注意到了在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行政”与“外包”两个极端情形: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行政”这一端是等级权力、强力控制等特征,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包”这一端,尤其在涉及民间内部秩序,是民间自主管理的特征。而中华帝制的国家治理最奇妙的地方恰恰是联结和整合“行政”与“外包”的丰富多变的治理机制,忽略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联结整合机制显然无法真正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再例如,西方历史学家经常感叹于中国王朝政权仅仅依靠一支规模很小的官僚队伍治理了一个如此幅员广阔的疆域。有学者把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德国做比较,发现中国官民比所反映的政府规模之小是惊人的,简直就是一个悖论。这些西方学者显然只聚焦于中国正式的官僚体制以及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直接渗透,而明显忽略了正式官吏系统之外庞大的准官员队伍以及由此推动的形式多样的“行政外包”和官民互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突破了传统上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有助于引导人们关注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且反映中国传统治理奥秘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但是,“第三领域”以及“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更接近一种特征描述,并未给出关于官民互动的内在机理的系统分析。例如在赋役、司法判决、道路水利和宗族管理等不同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显然不同,乡村治理的简约程度和具体形态亦有显著差异,集权与简约治理的连结与互动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目前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当中描述性、概括性的理论偏多,而真正提供解释性的分析理论偏少。本文旨在提供一种解析性理论,揭示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互动关系的内在治理逻辑和运行特征,剖析中华帝制国家治理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
本文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国家权力与社会团体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特征。目前考察国家—社会关系的文献深受西方国家建构理论的影响,倾向于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力与可渗透性作为分析的焦点,经常将国家权力的强弱与社会团体的自主与否置于二元对立或零和博弈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关于国家权力的传统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术界关于中华帝制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本文提出的“行政外包”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关于国家权力的另一种解析视角,强调国家权力在支配和强制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意义;这类似于科斯提出,区别于以契约为中心的市场,企业通过行政权力的协调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按照这个观点,国家与社会关系所涉及的国家行政控制与基层社会自主管理如同一个权威组织(王朝国家)内部的“行政管理”过程,国家与社会的权力配置旨在节约行政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而非以追求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和直接控制为目标。这对应着在中华帝制的“大一统”结构内部,一元化和中心化的王朝政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外包”给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或个人,并施加一定的行政性约束和相机性控制。国家权力的控制与社会团体的自主性在各个治理领域的不同搭配组合不是以国家支配力、控制力或渗透性的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节约稀缺的国家治理资源,更加有效地实现王朝政权的治理目标。在一些官民利益冲突明显的领域(如赋役和治安)国家控制相对严格;但在更多的官民利益兼容的领域,如区域性公共产品(如道路、水利、抚恤、乡勇)和民间内部秩序维护(如乡约、宗族、会馆)领域,国家的相机性控制与民间自主管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