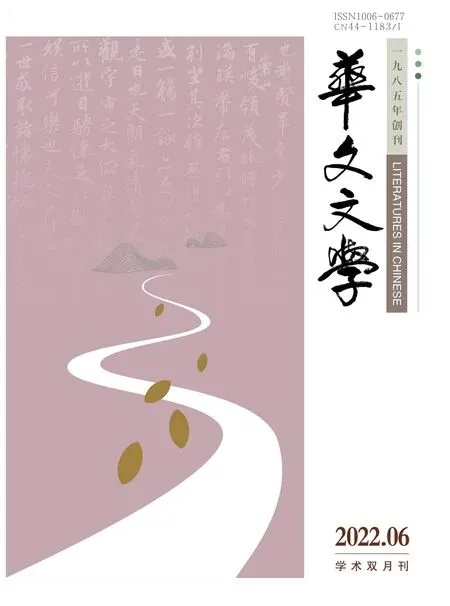关于跨过“门槛”以后的想象
——细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①
[韩]李宝暻
一、绪论
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的《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创作的第二篇小说。这篇小说极短,大约2000 多字,也许与其叫做短篇小说,不如叫做一个小品。然而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在回忆其老师的文章时说,“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②,鲁迅自己曾经将其译成日文,而且孙伏园认为如果有译者要翻译他的作品,他会首先推荐《孔乙己》。中国文学史家杨义就此说,“这就难怪作者怀着舐犊之爱,把《孔乙己》列为《呐喊》中最喜欢的一篇了”,而评价为采用第一人称的鲁迅的12 篇小说当中“具有最精粹面又完整的艺术格局的”作品。③
日本学者也对《孔乙己》给予高度评价。比如,藤井省三试图从《孔乙己》读到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1919)的影响,而说《孔乙己》与《药》“实际上是作为作家的鲁迅的初露头角的作品”④,丸眉常喜也说,在将“文学革命的实绩”显示于世的作品当中,“我以为第二篇《孔乙己》的成功,对于肩负着‘先锋’重任的鲁迅来说,无形中给予他以自信”⑤。这些批评意味着,《孔乙己》不但是鲁迅的创作生平中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作品,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有得到广泛的肯定。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对《孔乙己》的批评可以参考李宗刚的文章。1950 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只是将其提及为鲁迅的小说当中一个,未视为重要的讨论对象。这是与当时文学史家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农民有关。像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对《孔乙己》的评价进入1980 年代后才开始有所变化。王瑶在1982 年重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突出作为“一个人”的孔乙己形象的“可悲可怜”的一面。李宗刚对此说“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开始了其漫长的‘原罪’历程”。到了二十世纪末,就《孔乙己》再度有了新的解释,比如1998 年钱理群等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修订本以所谓“被看/看”的模式解读。文学史家们以自己的文革体验折射而突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也背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子”的孔乙己形象,与此同时淡化孔乙己与科举制度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摆脱启蒙主义而从自身的“现代性的体验”来读解《孔乙己》。⑥
总之,对《孔乙己》的认真的读解可以说进入1980 年后才开始的,从对深受孔孟之道的毒害而不适应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变为对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背负痛苦命运的认同。然而,虽然这解释上有所变化,孔乙己在“吃人”伦理和“看客”的嘲笑中的“失败”和“没落”这框架却几乎没有变化。这也许是跟《孔乙己》的最后发言,即“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⑦有关。可是,笔者从叙述者“我”的发言中觉得有种无可奈何的不释然,“我”所说的这“的确”能不能如实地相信?如同“大约”这副词透露什么,让读者毫无犹豫地相信“我”的发言,觉得有些不足。
二、天真的少年叙述者
按照孙伏园和周作人的观点,《孔乙己》是以鲁迅故乡的酒店和出入其酒店的人家为原型的小说,咸亨酒店由鲁迅的远亲秀才经营,而孔乙己的原型是从写手赚酒钱的叫做孟夫子的人和屡遭科举落第的其酒店老板的哥哥来的。⑧
鲁迅虽然向孙伏园说孟夫子的行迹跟孔乙己相似,他发表《孔乙己》时,其篇末写了如下的附记: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⑨
《孔乙己》发表在1919 年4 月《新青年》第6卷第4 号,上文附在小说的末尾。鲁迅批判当时的小说家将小说当作攻击某人的用具,而要求就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不可等同于现实社会里的某人。众所周知,这附记针对以文言短篇小说《荆生》嘲笑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家的林纾。丸眉常喜从这附记读到鲁迅对“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⑩的“影射小说”的批判。[11]鲁迅也说小说里“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12]
丸尾常喜所说的鲁迅要通过《孔乙己》批判传统文化的解读,笔者也十分同意,可是他为了突出鲁迅对影射小说或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却淡化与“文白论争”的关联,这一点值得再考虑,因为《孔乙己》跟“文白论争”的关联也仍然重要。内室长衫顾客与柜台外面的短衣顾客之间的完全的隔绝,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的孤独无助和下落不明,这些切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语言状况而预告文言的命运。因为如此,从《孔乙己》读到“文白论争”的学者们关注孔乙己的失败与没落。如同鲁迅所说的“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13],这反讽当中显得孔乙己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
可是,小说《孔乙己》为什么不告诉读者离去咸亨酒店后的孔乙己在哪里?读者只是从叙述者“我”所说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14]预料孔乙己的“以后”。料定孔乙己的“以后”之前,首先要探讨围绕孔乙己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来说,《孔乙己》是对空间下功夫的小说,不是时间。所以研究《孔乙己》的空间布局的文章比较多。[15]《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众所周知,“咸亨”是从《易经·坤卦》的“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来的。咸亨酒店假设为包容万物而畅行无阻的空间。以曲尺形柜台为中心,里面有小伙计“我”和掌柜,外面有靠着柜台站着喝酒的短衣零工,深渊的内室有吃酒菜的长衫贵客。酒店是十分反映中国人的语言状况的空间。站在外面喝酒的只说白话的短衣零工和在内室吃菜喝酒的自如运用古文的长衫贵客之间的隔绝,以及不同程度地中介于他们之间的“我”和掌柜,虽然这些人之间不会有真诚和隐秘的对话,就因为如此,反讽的是他们之间却没有纠葛与矛盾。咸亨酒店是古文世界与白话世界被和谐地分离的空间。所以,可以说《孔乙己》的附记是对影射小说的批判,与其同时,通过以召唤影射小说这鬼祟批判林纾,从而积极参与“文白论争”的。
张法在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以四合院说明中国人对空间的思维。按照他的说法,在我们感觉到的范围内,宇宙整体的和谐以一种空间的和谐显现,其特点是内向性、等级性和自足性。其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不对外开窗(内向性),其院内的布置全按贵贱、老幼、主仆的等级关系设计为一和谐的整体(等级性),等级和谐是依乎天理的,在封闭的等级和谐格式中能深感自足(自足性)。一句话,四合院的布置体现“一个容纳万有的和谐观,一个把时间空间化的和谐观,一个对立而又不相抗的和谐观”。[16]咸亨酒店是一个完美地体验四合院的和谐的空间。这里有内室长衫贵客、柜台外面的短衣零工、还有小伙计“我”和掌柜。他们各自都占有自己的位置,而不会贪图或觊觎别人的位置。所以咸亨酒店的时间永远地空间化了,决无时间的积累。就因为如此,“我”“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17]
孔乙己是唯一的不适合这和谐空间的,有一点生疏、不自然和奇异。就这孔乙己的身份,“我”就介绍如下: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18]
站着喝酒的人一般穿着短衣,其中只有孔乙己倒穿着长衫,而且身体健壮,满口“之乎者也”。可是他不能进入内室而不自然地夹在站着喝酒的零工中。读者就这缘故能从其皱纹间的伤痕、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和又脏又破的衣服推测到。人们没有注意他的姓名,而只是从描红纸上的第一个句子给他取绰号。就像《阿Q 正传》叙述者为了让读者相信这故事的真实性,详细地解释“阿Q”这名字,结果,反而招致了对叙述者的角色的限制,[19]《孔乙己》的读者也开始怀疑叙述者“我”的角色必定有限制的。关于主人公的名字或行迹,叙述者“我”倒没有把握。笔者认为这一点就是解释《孔乙己》的一个重要线索,因为暗示着“我”说明孔乙己的生平具有先天性的限制。
读者对“我”所说的故事感觉不可靠,这里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我”负责“温酒的一种无聊的职务”的原因,解释如下: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威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20]
“我”最初看孔乙己是12 岁在咸亨酒店当伙计的时候。“我”是太傻,伺候不了顾客,因为托荐人的福,幸亏免得解雇,只管“温酒”。如果不是太天真的读者,谁也不会原原本本地相信“太傻”的少年所说的有关孔乙己的故事。当然,这小说是成人的“我”回顾20 多年前的故事,可是,我们要注意“我”所说的故事是在12 岁少年的眼光下展开的。王金胜说《孔乙己》的“我”是一个“天真的叙述者。”[21]天真的叙述者是让读者怀疑对其说法该信任到什么程度,一句话,他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22]《孔乙己》是被“不可靠的叙述者”和“天真的叙述者”的“我”叙述的。所以读解《孔乙己》时,就“我”的叙述,与其如实地接受,不如怀疑叙述者,他也许是一个陷于混乱之中,或自欺欺人,或做错判断甚至恶意判断。读者怀疑“我”的叙述的时候,孔乙己的“现在”和“以后”就显现为意外。
三、和谐空间的裂缝者“孔乙己”
进入孔乙己的“以后”之前,首先看看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角色。按照“我”的回忆,无聊而和谐的咸亨酒店也有了裂缝的时候,就是孔乙己的出现。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23]
之所以“我”还记得20 多年前的孔乙己,是因为在这“教人活泼不得”的咸亨酒店,只有孔乙己出现,“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己的出现是让这酒店的永远的无聊一下子破坏的瞬间,咸亨酒店是从等级的、封闭的和自足的空间变为具有可能性破坏其秩序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就是说成为会导致顾客之间的对话的空间。虽然如此,站着喝酒的人却只是以伤痕或偷东西等闲话嘲弄孔乙己,而孔乙己忙着以“之乎者也”的辩解对付,不消说内室的贵客不会认知孔乙己的出现。
“我”借用顾客所说的科举落第,而且“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解释孔乙己,与其同时,附加如下: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24]
叙述者“我”的真实体验是孔乙己从不拖欠,定然还清的人。依“我”看,孔乙己的品行“比别人都好”,与人家所说不同。这蕴含着人家所说的有关孔乙己的传闻会与事实有一定的距离。值得注目的是“我”还记得的孔乙己的另一个面目。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25]
避开嘲弄自己的顾客,孔乙己“只好”向孩子说话并分给他们茴香豆吃。而且他向“我”说“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要教写字。[26]他的这些行为却都被不理睬,“我”拒绝他的指导,孩子们要连剩下的若干茴香豆也都拿去。就孔乙己向孩子们包括小伙子的对话,丸尾常喜说“鲜明地显示出孔乙己心中潜在地‘善良’和‘善意’”[27]。
在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孔乙己的视线从不向着内室的长衫贵客或遵守在已定的秩序中的位置的短衣零工,他注视的却是12 岁的小伙计和孩子们。孔乙己一般解释为不能介入长衫贵客或短衣零工的一个以“边缘化身份”“模糊地生存”的人物[28]。如果他选择到长衫或短衣当中一个,可以进入封闭而和谐的秩序里,可是他却对这两方毫不关心。孔乙己与其说是不能扎根于长衫贵客或短衣零工的,不如说是他从未想过进入这两种人群当中一个。那么,学者将孔乙己解释为“自我规定”的“虚妄性”[29],即他不直面不可能进入长衫世界的现实,而仍然觊觎其长衫世界,笔者认为这解释需要再思考。虽然孔乙己“只能”有一个选择,他的关心一直向着相对来说少污染的,秩序以前或秩序外面的孩子,不是等级化了的哪一方。
在这里,再回到孙伏园的回忆去吧。他将鲁迅对《孔乙己》的说法概括为如下,比较长一些,可是要引用: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蕴着极丰富的情感。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以流於推崇。《呐喊》中有一篇《药》,也是一面描写社会,一面描写千人:我盯读完以后,觉得社舍所犯的是弥天大罪,个人所得的却是无限同情。自然,有得题材,非如此不能达到文艺的使命;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欢如此。他常用四个绍兴字来形容《药》一类的作品,这四个绍兴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法,姑且写作“气急虺隤”,意思是“从容不迫”的反面,音读近于“奇迹海颓”。
《孔乙己》的创作目的既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那么,作者对于咸亨的掌柜,对于其他的顾客,甚至对于邻舍孩子们,也未始不可用《药》当中处理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等的方法来处理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题材的关系,《药》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难是国家民族命运所系,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态度的“从容不迫”,即使不像写《药》当是的“气急虺隤”,也还是达到了作者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目的。鲁迅先生特别喜欢《孔乙己》的意义是如此。[30]
鲁迅将《孔乙己》跟《药》相比评价更高一点,这让我们觉得意外。因为无论分量还是结构,一般认为《药》更是完美的“像小说”的小说。《药》的主人公担任跟“国家民族命运所系”的任务,孔乙己则是“无关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因为如此,鲁迅说写《药》时只能“气急虺隤”,而写《孔乙己》时“从容不迫”。鲁迅所说的“气急虺隤”也许是与“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31]这告白有关。这表示遗憾不计较小说结构上的必然,而不辞“气急虺隤”运用“曲笔”。与此相反,写《孔乙己》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从容不迫”,也就是说,能充实于小说写作,因为如此,作为作家的鲁迅“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然而,就描写“苦人”和“一般社会的凉薄”来看,这两部小说很像。孙伏园说了三次,如同《药》,《孔乙己》也有“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目的”。郑萍和张靖对比小说的前半部与后半部的变化,而说“到了文章后半部,由于隐含作者的愈加显露,更是在整体上同情倾注于孔乙己,使文章前一部分的‘快活’空气,渐被悲哀的气氛所笼罩。在秋风的萧瑟中,一切显出悲凉的光景”,[32]这解释可以说跟作者的意图完全一致。
要之,孙伏园的回忆所说的与其说是鲁迅批判孔乙己,不如说是“同情”孔乙己,而他的矛头针对“一般社会”。也许因为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能一时将自身的现代性体验折射到孔乙己的身体。孔乙己是即将被推出的仍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封建社会最后的下层文人,这一点非常的明显。虽然如此,鲁迅以“同情”描写他,因为他是“苦人”,的确与长衫贵客和短衣零工有所区别。之所以他是苦人,是因为他是不像咸亨酒店的其他人物(“一般社会”)孤独地忍耐着他们的“凉薄”。也许,孔乙己就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或《孤独者》的魏连殳这两人离乡之前的身份。甚至可以说他是以忧郁的声音呐喊“救救孩子”的另一个狂人,因为孔乙己是在咸亨酒店向孩子说话的唯一的人物。
四、跨过“门槛”
孔乙己是一个咸亨酒店顾客的玩物,又是将这一和谐空间弄出裂缝的唯一人物,可是他有一段时间不出现。这时候咸亨酒店有传闻,即是他偷丁举人的东西而被打断了的腿。过中秋,秋风凉了一些,没有一个客人,这一天下午他忽然出现了。
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33]
孔乙己以狼狈的姿态出现,对了“门槛”下面垫一个蒲包坐着,请一碗酒。蒲包是出门远行的时候装东西的用具。孔乙己将蒲包一边垫着,一边其绳子在肩上挂住,而且他对了门槛坐着,不是柜台。笔者认为,这是推测孔乙己的“以后”的关键性线索。因为这明显表现出孔乙己已有离开鲁镇的决心。
况且孔乙己再不是以前的孔乙己了。
(听到孔乙己请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34]
听到掌柜提起欠钱的话,孔乙己很颓唐,虽然如此,“这一回”以现钱要求“好酒”。而且掌柜像往常一样拿他玩耍,他“这回”却没有任何分辨而直说一句“不要取笑”,甚至他将掌柜所说的“打断腿”矫正为“跌断”。虽然叙述者“我”说孔乙己“很像恳求”,笔者认为对此有待重新思考,这是天真的叙述者的视角,“我”万万料不到孔乙己已有坚定不移的决心。
将孔乙己对着的门槛更为戏剧化的是他的手。将温了的酒放在门槛上的“我”看见他的满手是泥。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35]
以上是“我”最后看孔乙己的模样,又是这小说里印象最为深刻的句子。丸尾常喜说“‘我’在孔乙己满是泥的手发现了他的求生意志,开始触及到他的‘寂寞’”[36]。笔者要关注的是孔乙己的求生意志,不是“我”的发现,因为天真的叙述者“我”接近于一个单纯的观察者,他不会察觉到孔乙己的内心。虽然如此,读者倒会从满是泥的手感觉到孔乙己的“求生意志”。所以孔乙己的变化跟要跨过“门槛”的求生意志有关,也就是说,他从咸亨酒店或鲁镇摆脱就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
被打断腿的孔乙己以满是泥的手爬着来店的,好像四足兽一样,直到咸亨酒店,一路上孔乙己在想什么?他可能笼罩着说不尽的“耻辱”。这耻辱是12 岁小伙计的“我”难以想象的情绪。虽然孔乙己的处境只不过是谁都漫不经心的下层文人,或者因为就是如此,仍然也要坚持作为文人的自负。这样的人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四足兽的时候,他满脑子不都是一片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吗?喝完酒的孔乙己在这耻辱中再以满是泥的手“慢慢走去了”。完全和到店时的一模一样,坐着以满是泥的手爬着跨过门槛离开咸亨酒店和鲁镇。
我们可以从《白光》的陈士成也读到“满手是泥”这意象。陈士成是一般和孔乙己被提及为“科场鬼”,可是他们之间不同之处倒更多。陈士成站在科场的照壁渴望其里面,让七个学童回家而一个心思地追求“白光”,最后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37]的尸体被发现。渴望照壁里面的陈士成和向内室毫无关心的孔乙己,抛弃学童的陈士成和向孩子说话的孔乙己,追求一个消失点而终归死去的陈士成和爬着也要跨过这和谐空间的门槛的孔乙己。这样看来,与其说是孔乙己“始终游离于空间之外”[38],不如说他先是试图挤向和谐空间的裂缝,而觉察到其不可能,最后毅然地摆脱这一空间。
孔乙己便是丸眉常喜所说的“即便蒙受耻辱,也要生活下去的读书人”[39]。就想象孔乙己的“以后”,笔者认为其重点在于这耻辱“包含着对‘敌’的‘憎恶’,具有生发‘憎恶’的力量”[40]。众所周知,鲁迅年幼时候“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在所有的侮辱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想走异路,逃异地”[41]。在仙台,看有关日俄战争的的幻灯片时候,鲁迅“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42],之后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是因为他可能感到耻辱。然而,丸眉常喜虽然从孔乙己的最后读到其耻辱,可是好像读不到孔乙己爬着跨过“门槛”的充满憎恶的内心。丸眉常喜就说叙述者“我”终于“开始触及到他的‘寂寞’”,从而“我”“已经不是几个月以前的那个少年了”[43],也就是说他从孔乙己的最后倒读到叙述者“我”的成长。丸眉常喜的读法是将这小说看作描写叙述者“我”的成长的成长小说的。然而所谓成长小说不可避免归结为与其社会和谐[44],在这一点,“我”的成长的意义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与咸亨酒店的法则和谐。因为如此,在丸眉常喜眼里,孔乙己的后影只能解释为“笼罩着惨败的读书人的生命所放出的悲凉之光”[45]。笔者这解释是一种误读,丸眉常喜对天真的叙述者的叙述深信不疑,之结果,他从“凝视孔乙己的悲哀”的“我”看到“清澄的目光”[46]。
就将《孔乙己》读解为与世界和谐,还是向这和谐的裂缝,其解释的线索可以从孔乙己以满是泥的手爬着跨过“门槛”察觉到。《狂人日记》的狂人也瞩目孔乙己跨过的“门槛”。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47]
狂人呐喊着,如果很想摆脱吃人的罗网,只要肯跨过“一条门槛,一个关头”的“这一步”就足够。狂人向大哥说服“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48]可是人们不肯走这一步,摆设罗网成群,互相鼓励而牵制。反讽的是,践行狂人所说的跨过“一条门槛,一个关头”的是一个颓败的文人孔乙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启蒙家或革命家。像鲁迅的生平向我们显示的,让人肯跨过门槛的力量是耻辱和憎恶,不是意识形态或理念什么的。
李长之在批判鲁迅的文章里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49]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将鲁迅思想以“进化论的生物学”为限制,虽然如此,非常重要他首次从鲁迅看到对生命的肯定,对此竹内好说“卓见”[50]。孔乙己也是为了要生存跨过门槛。像吕纬甫和魏连殳,孔乙己的离乡也许归结为失败而回到故乡,无论如何,分明的是他跨过“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了。
五、小结
这文章的起因是再读鲁迅的小说中偶然触目于在《孔乙己》的最后段落里的“门槛”。《狂人日记》的狂人向不肯跨过门槛的人表示焦急和愤怒。让人肯跨过门槛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之所以这“门槛”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就现在我们的大学和生存觉得更是鄙陋,倒不如19 世纪末20世纪初鲁迅和孔乙己的时代。虽然只是需要这一步,我们都不肯跨过门槛,而且将其看作一片不可能跨过的巨大的墙壁。一个穷迫的下层文人孔乙己果然能不能跨过这一门槛?这好奇或期待就是这文章的开始。
问题的线索能从天真的叙述者和以满是泥的手爬着跨过门槛的孔乙己的后影找到。到现在,许多学者将叙述者的叙述如实地接受而将其确定为真实,结果,将孔乙己的失败和没落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学者之间有一些区别,或者将孔乙己看成受到封建毒害的旧时代最后的文人,或者看成独自忍受人们的嘲笑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天真的叙述者,作者将读者引导混沌和误读之中,可与此同时,期待着怀疑叙述者的读者。笔者首先推迟对叙述的真实性的判断,而开始读《孔乙己》,这样一来,以满是泥的孔乙己的手和鲁迅自身体验的耻辱重叠了。这耻辱是12 岁的小伙计不能想象的情绪,在他的眼里只能看到孔乙己的失败。就孔乙己来说,这耻辱成为憎恶和复仇的根底,好像鲁迅。所以孔乙己的跨过门槛是忍辱负重,不是失败者的零落。他的离乡可以解释终为从这和谐的咸亨酒店摆脱出来的“脱走(escape)”。
当然,我们不能轻易地断言孔乙己跨过门槛“以后”的成败如何。黑暗的社会可能让他沮丧,以失败告终,归结为回到原点。就像痊愈后成为候补的狂人,再度教“子曰诗云”的吕纬甫,终于成为杜师长的顾问的魏连殳,孔乙己的“以后”或者也反复做“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51]的蜂子或蝇子的飞行。虽然如此,跨过“门槛”意味着他即将做之前绝不能想象的体验。而且通过让我们听到其体验,扩大我们的认识和想象力,那么,即使再回到原点,孔乙己不会是之前的人,同样,听者也不是之前的听者。因为如此,即使跨过门槛只不过是鄙陋的一步,可以说一种生成新的历史的行为。最后,附上一句话,让孔乙己肯跨过门槛的动力是耻辱,然而,如今我们或者是轻率地将我们每一刻受到的耻辱替换为无聊的阿Q 们。
①该文原发表于《中国文学》第85 卷,韩国中国语文学会,2015 年11 月。
②⑧[30]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83 页,第84 页,第84-85 页。
③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89 页。
④[日]藤井省三:《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Baek Geomun 译,坡州:Hanwool Academdy,2014 年,第102 页。
⑤[11][27][36][43][45][46][日]丸眉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1-42 页,第50-57 页,第64-65 页,第73 页,第73 页,第74 页,第74 页。
⑥中国文学史家对《孔乙己》的研究,参见李宗刚的《〈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东岳论丛》2012 年第4 期。
⑦[14][17][18][20][23][24][25][26][33][34][35]鲁迅:《呐喊·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1 页,第461 页,第457 页,第458 页,第457 页,第457-458 页,第458 页,第459 页,第459 页,第461 页,第460-461 页,第461 页。
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编:《新青年》第6 卷,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3 页。
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 页。
[1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27 页。
[13]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66 页。
[15]就《孔乙己》的空间形式,郑萍和张靖解释为“从空间知觉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我发现,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似乎是空间形式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孔乙己》中,鲁迅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技巧突破单一的时间叙事模式,追求空间化的效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体现了‘格式的特别’”。郑萍、张靖:《〈孔乙己〉叙述的空间形式》,《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5 期,第67 页。
[16]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79-68 页。
[19]《阿Q 正传》的叙述者在第一章字字句句地说明他给自己的主人公取“阿Q”这个名字的缘由,这倒引起对“阿Q”这名字的合理性的怀疑,之结果,叙述者只能履行有限制的角色。可以参见拙著,《阿Q 和叙述者的角色履行:再读〈阿Q 正传〉》,《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第二辑,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16 年版。
[21]王金胜:《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重读〈孔乙己〉》,姜振昌·刘增人主编《鲁迅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 页。
[22]对“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进行了正式的讨论是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他主张詹姆斯的作品除了几篇以外都是被“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的。“他所说的故事无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都被陷于很深的混乱,其本上被自欺欺人甚至做错判断或又恶意的反映者叙述着。”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Lee Kyoungwoo 等译,首尔:Hanshin 文化社,1990 年,第340 页。按照伯特·阿波特(H. Porter Abbott),之所以作家制造结巴、疯子和说谎者等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因为“除了巧妙地发生模糊的效果以外,还有许多长处。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叙述本身-有难处被趣味、偏见和盲目污染的- 会成为主题的部分。H·伯特·阿波特:《剑桥叙事学导论》,Woo Chanjae 等译,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10 年,第151 页。
[28]展绥:《边缘化身份与模糊性生存——〈孔乙己〉细读》,《语文建设》2002 年第9 期。
[29]姜振昌、刘增人主编:《鲁迅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4 页。
[31][41][4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1 页,第437 页,第438 页。
[32][38]郑萍、张靖:《〈孔乙己〉叙述的空间形式》,《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5 期。
[37]鲁迅:《呐喊·白光》,《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5 页。
[39][40][日]丸眉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秦弓·孙俪花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47 页,第41 页。
[44]就成长小说来说,和谐的自我形成这方向非常明显。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一系列的失误后自我发现、认识和完成自我,其主人公从黑暗的迷路进入准确的真理的轨道,也就是说,达到教养世界。”Jin Sungbum,《关于德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成立的考察》,韩国黑塞学会,《黑塞研究》第5 集,2001 年,第143-144 页。所谓成长小说,我们从哥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认识到其虽然蕴含着对时代与文明的批判,究竟其目的是让主人公确立与自己所属的社会要求的市民身份认同。如果《孔乙己》读解为成长小说,就不可避免地达到叙述者“我”与酒店世界的和谐这结论。
[47][48]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51 页,第452 页。
[49]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 页。
[50][日]竹内好:《鲁迅》,东京:未来社1961 年,第10 页。
[51]鲁迅:《彷徨·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