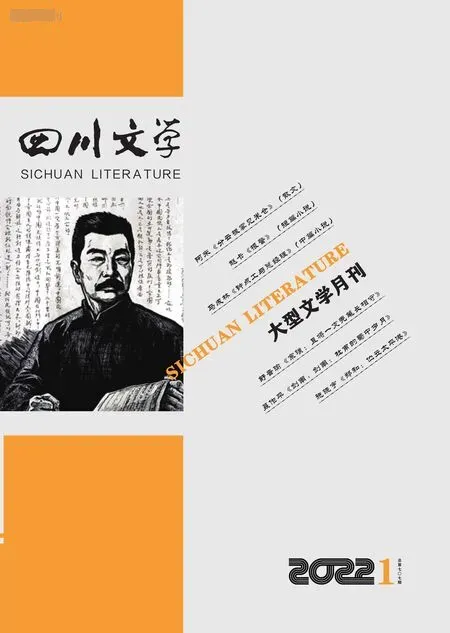分云拨雾见米仓
□文/阿来
晓得光雾山之名起码二十年了。
川东北巴中市南江县,每年深秋,以光雾山上的灿烂红叶为号召,吸引人前往观光旅游。
对我个人,只说红叶吸引力不大。我们所处的地理纬度上,何处秋山无树?何处秋山之树经秋霜浸渍,而不变幻出艳丽重彩?毛泽东年轻时的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说的就是,秋风起时,这景象从南到北布满四季分明的大半个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旅游业兴起,以红叶为号召,过红叶节,仅四川而言,也不只光雾山一处。不只一次,光雾山红叶节,我也受到邀请,却终究未能成行。找过一些写光雾山红叶的文章来读,并不感到特别的吸引。
就这样,不但未亲身前去,还受经验主义支配,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以为光雾山就是一座孤立的山,山上比别处多树,且多是秋天变红的树种。当地因此开发一景区,买票上山,坐观光车,在几处观景台停车拍照,然后结束旅程。我知道奔一个地方,如果只看红叶,要去得恰逢其时,这要天气帮忙,才能见艳阳下树树红叶灿烂放光,于是惊艳、赞叹。这是运气好。倘若运气不好,到了地方,或者叶还未染颜色,或者一场风雨,已将红叶尽皆摇落。“树树秋声,山山寒色。”通常的情形往往是,看红叶而未见叶红,办红叶节而霜期不来。这种尴尬,在单以红叶为号召的景区,往往在所难免。红叶总不肯按期而红,即便红了,存续的时间也要由天气决定长短。所以,我没有专程去过红叶景区,除非是顺道遇见。某几种树在秋天变红,就如别的树种变幻出黄色或其他颜色,只是大自然中植物界停止光合作用,准备进入冬眠时的一个自然表征,跟春天树叶初生时的各种浅绿,跟夏季盛大汪洋的深绿是要进入生长周期,进行光合作用没有本质区别。这种种变化,都是时序流转,四季更迭。我有点儿想不明白,为什么独独是红叶的那一阵,才值得观赏。
今年十月中旬,终于有了光雾山之行。
首先是因为主人盛情邀请,更因为红叶之外的另一个理由:南江县编辑了一套囊括当地历史人文及自然地理的丛书,出版前要在当地做一次郑重发布。当下提倡文旅融合、全域旅游,摸清家底是起码的工作,但往往又常是被疏忽的工作。我看了丛书纲目,不是局限于一个景点,而是南江全境,从历史到地理,因此乐意前往,至于山上的红叶,那就是个顺便。
从成都半天到南江,过县城而不停留,直奔光雾山镇。公路顺江流蜿蜒,村镇愈稀疏,峰愈峭拔,谷愈幽深,森林愈茂盛,树木愈高大,云雾愈缥缈。细雨时来时不来,山上少见红叶,黄叶也并不灿烂。我并不失望,山高涧深,水落石出,林木萧瑟,确是群山秋深的味道。到了光雾山镇,两水相汇处,三峡相交,山腹上立着正在落叶的树,山头都隐在云雾之中。主人解嘲说:光雾山,光是雾的山。酒店门前,一株老核桃树,绿叶凋脱,裸枝遒劲,粗粝树干上寄生着苍老的苔藓,还有两丛叶片狭长的蕨,虽饱吸雨水,却也显出枯萎的样子。时序流转,秋之为气,植物们大多显出疲倦了想要入冬休眠的样子。这就是秋天的样子。
下午开会,说那套将付印的书。洋洋五大本,人文方面,从历史遗存到民间风俗,面面俱到。几本书共同的一个特点,从地理入手时,说光雾山少,说米仓山多。因此得到两个新知识:
其一,米仓山大,不只提领整个南江县,还绵延到更广阔的地域,光雾山只是米仓山脉在南江境内的最高峰而已。
其二,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接续穿越秦岭到汉中盆地的子午、傥骆、褒斜、陈仓等古道到四川盆地,去蜀,有金牛古道;到巴,则是穿越巴岭米仓山脉的米仓古道。
既如此,我在会上也提一个建议,希望这套丛书增加一本自然之卷。既然要说米仓古道,就得说清其穿越的地理;既然南江一地旅游,以自然观光为号召,当然应该从生物学角度对公众进行自然知识普及和自然生态教育。所以,应该有一卷书,讲讲地质构造,讲讲山脉,讲讲水文,讲讲植物,讲讲动物。
散了会出来,见晚霞漫天。四围的山都显露出来。接天处,一座座似断还连的峰。灰白色的陡峭崖壁。崖壁石缝间兀然耸立的树,该是松与枫之类,斜张开的树冠剪影,仿佛在模拟古人笔下的山水画卷。主人说,这会开得好,下了半个多月雨,终于停了。景区刚过了红叶节,但秋雨连绵,秋叶未被霜染渍,便凋零飘坠。雨一停,天放晴,有了晴好的白天和下霜的夜晚,这下,红叶就要出现了。
这个夏天与秋天,常常被干旱所苦的许多地方,反常地被前所未见的雨水所折磨。不只是红叶未红的焦虑,是家园毁败,生灵涂炭。
不过现在雨停了,蓝天衬托出红霞漫天。
第二天早起散步,天还没亮。循着隐约的路,听溪声沿山谷上行。三公里后,天渐渐亮了。东方刚刚露出一角蓝空,雾就从谷中升起来,掩去了一切。这就是山中雨后初晴的典型表现:初升的阳光使山谷中水汽蒸腾。转眼之间,雾就郁闭了四野。不要说山,就是高壮些的树,其树冠也隐而不显。不因望不到秋山秋林而失望,我下到溪边。古人写过的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累累涧石是秋;涧石间绿色菖蒲擎着干枯花葶是秋;水流上不时漂来几片黄叶,也是秋。
归路上,路旁崖壁上,开黄花数种。蔓而垂之,疏花自上而下有序相间,是明黄野菊。直茎上举,花朵细密,是密舌紫菀。紧贴岩壁簇生蔓延,丛丛黄光照眼,是东南景天。这也都是秋。
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种规定性的秋天。
欧阳修夜读书,未见秋色,静夜中“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而生感叹:“此秋声也”,而作《秋声赋》,传诵千年。秋,既是四季时序之流变,更牵扯人的生命节律与感慨。这样的清晨,看落叶逐水,看秋菊丛开,听见云雾中树树秋声,更感生命之美丽与时光之无情。
山道盘旋,乘车上光雾山。
光雾山是一座大山。绝不是我先前以为从前山一两个小时上去,再从后山一两个小时下来的那种孤立景区。
渐渐地,山谷深陷,峡底终不可见。树愈高大,林愈浓密。几次停车瞭望,都觉得该是目的地了,却只是停在大山鼓起的腹上观见林海苍苍。山越高,下方的峡谷越显出雄浑与幽深。秋风吹拂,阳光融霜,森林正褪去夏天浓绿的妆色,泛黄,泛紫,这是森林要休息了,树干中与枝头上充盈的水分正回到土石下的根部,制造光合作用的叶绿素正在褪去,叶片中的花青素浮现出来,连绵的森林将幻变出响亮的黄和鲜艳的红。森林将在脱尽叶片,在严冬的风雪中沉沉睡去之前,要在一年中最明净的阳光里,在最湛蓝的天空下,来一次色彩的大交响:万众树木气势磅礡,高声歌唱!
但现在,这一切还在酝酿之中。连绵旬月的冷雨刚停,所有的树,无论椴、榉、槭、栎、柳,湿漉漉的叶片沉重低垂,正在等待阳光。只有阳光的魔法,才能使它们变得干燥,变得艳丽,才能在风中轻盈翻飞,像是精灵附体。现在,阳光把从它们体内蒸发出来的水汽汇聚为雾,升腾为云。如果来此山,只为红叶,当然就会失望,就会抱怨。也因此,陪同游览的主人也一直为光雾山红叶将红未红而抱有歉意。我宽慰他们大可不必。红叶,更准确地说,“层林尽染”的彩色秋林,无非是森林从春到冬四季流转中,一次生命循环的高调休止。现在,群山和森林正在酝酿那最华彩的生命礼赞。山溪消落,垒垒石出;老树静穆,高立崖间。一切都蓄势待发,只需接连几个高天丽日,一身轻盈的树们就会众声喧哗,热烈歌唱了。
现在,只看一团挂在崖间松树上的雾,一朵停在静静水潭中的云,屏神静气,感受那些气息流动,感受秋林彩色大爆发前最后的深呼吸,这一切都是人走入大自然最美好的体验。
下车了,沿着设计好的步道在山腰的密林中穿行。不要太介意游人的喧闹与拥挤,让自己和眼前的树一样安静下来,也随着大森林呼吸的节奏来一个深呼吸,身体中立即就充盈了山野的味道:根和泥土,光和光中的叶子,岩石和流水,风和鸟鸣,大树和沉默。伸手抚摸,空手时是一缕风、一束光;满手时,是叶,是枝,是干,是一棵树,是一群树。一切都是真切的质感。一切都在告诉:这是秋天的森林,森林的秋天。
看见了会变出红叶的树种,有些是常见的,比如俗称为枫的槭;比如,紫红树皮上有着漂亮纹理的野樱桃。还认识了当地特有树种,巴山水青冈。主人介绍说,这就是光雾山红叶的主力树种。眼下,水青冈圆形而略显狭长的叶片还是绿色的,只在有着浅浅锯齿边缘处微微泛黄。水青冈是这片森林里最为通直高大的树,特别是那些粗壮的老树,发达的根系半裸在地表,紧抓住岩石与泥土,在地面模仿出树冠的图案。这些水青冈,不论是成群簇生,还是独立一处,都腰身挺拔,径直向上,未达一定高度时,坚决不枝不蔓,一直达到超越其他树木的高度,才在二十米三十米的高空中,展开华美的树冠,显现出引导群伦的领袖气质。它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其他树则成为心甘情愿的陪衬。桦树、榉树,甚至松树和柏树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本就低矮的杜鹃和黄杨之类。阔叶灌木山矾正在花期,却只是悄然绽开低调的花序,在高大的乔木下开得不声不响。
捡拾到几颗巴山水青冈的种子,坚实的圆果坐在只及半身的半圆形壳里,煞是可爱。橡树的种子是这样的,栎树的种子也是这样的。所以,水青冈和它们在分类学同属一个科。这个科的共同点就是种子的样貌,并从这种共同点得到一个共同的名字:壳斗科。
步行完这一段山道,再乘车转去另一段更漫长的步道。这回,要去的是光雾山的最高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
海拔升高,水青冈群落消失了。道路旁,斜出于峭壁陡坡的是桦、是松、是柏。路旁渗水的岩壁间还长着草本的报春与苣苔,报春花会在初春开放,苣苔则开在夏天和初秋,现在它们花期已过,行在路上,却可以在萧瑟秋景中想象它们开花时生机勃勃的春与夏。
在这个高度上,最具观赏价值的,是杜鹃花树。
当所有树都在秋天显出枯寂的面相时,杜鹃花依然充满生气。阔大的皮质叶片依然一片深绿,涂了蜡一般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簇生的叶片中央已经捧出了明年夏初才会绽放的花蕾。眼下,这些圆形的花蕾都被鳞片状的萼片紧紧包裹。覆盖了苍茫群山的树,大部分正在或将要“木叶尽脱”,唯有一树树杜鹃,依然叶片深绿,在冬天将临的时候,在枝头孕育着来年盛大的绽放。它们开放该是明年五月间,杜鹃鸟在绿树幽深时声声啼唤的时候。“杜鹃声中杜鹃开,杜鹃岭上杜鹃来。”这是我为另一个杜鹃盛开的山岭题的碑文。现在,离明年的花期还远,落叶翻飞的秋后,还有一个沉寂的冬天。眼前这些杜鹃长在奇峰危崖之间,每一树都各各不同,各自构成一种奇特的姿态,都是人工不能造成的奇特美景。唐代诗人白居易看见过这样的奇景,还曾想把这样的杜鹃移栽到自己的庭院,但这些高山杜鹃总是野性难驯,所以他称叹:“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
前两天,山中细雨飘飞时,这蜿蜒的山脊上,早已是白雪纷飞。顺着人工开辟的阶梯,登上一座小峰的最高处,四周都是绿光灼灼的杜鹃树,树下还有未化尽的残雪。主人在为我描绘明年杜鹃开放时的绚丽景象。我没有出口的却是两个反诘:
反诘一:难道此时孕育花朵的杜鹃就不值得观赏?
反诘二:既有如此夏天有如此绚丽的杜鹃花海,为何一直只说那些红叶?
现在,我们在光雾山也是米仓山的最高处,居高望远,山势浩渺苍茫。眼下,我们就置身于一片壮阔地理的中央,在一处风景观赏发生的现场。也是在此时,我才晓得,光雾山如此雄浑阔大,却只是米仓山脉的一小部分。米仓山横亘在川陕交界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作为南北的地理分野横亘几百公里,又还只是古代与秦岭并称的巴岭——今天称为大巴山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巴山西南是四川盆地,隔着汉中,大巴山北方是秦岭,是关中,是黄河,是北方中国。我们深入地理,是为构建具体而直观的完整体认。进山登高,不是迷失于局部,而是体察整体。
光雾山最高处,也就是米仓山脉的最高点,山脊呈东西向如巨龙蜿蜒,北面是陕西南郑,南面是四川巴中。林海覆盖道道山梁与深峡,阳光蒸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云雾,不断蓄积,不断上升,不断飘散,扑面都是饱含草木芬芳的林野之气。云雾使山幽谷深,在明亮阳光下,更显得雄浑邈远。当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越秦岭到四川,白居易和他的组诗《东川行》行时有妙句:“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不就应的是眼前之景吗?只不过,要看“一树红花山顶头”,得待来年春深时了。这“一树红花”写的正是米仓杜鹃。
意欲离开,导游坚持再等待一阵子,说,可能马上就能看见过山云,看见遮蔽四野的浩荡云海。导游说,雨后初晴,南面山谷水汽蒸腾不息,此为条件一。条件二,来自北方的干燥冷空气南下,与南坡上升的水蒸气在山脊相遇。条件三,两种气流在山脊顶牛颉颃,最后,冷空气终于占了上风,往南边山坡缓缓下泻,把湿热气流中的水汽都凝结起来,于是云海形成。近午时分,果然就等到了冷空气从北方蓝空下来,翻越米仓山脊时,与南坡蒸腾的水汽相遇,两股冷热干湿不同的气流猝然相遇,覆盖山脊的雾幔瞬间生成。自北向南,向下流淌,填满下方山谷,转瞬之间,脚下就已然是云的深渊。我们置身的山顶,已然如蓬莱仙山,成为载沉载浮的孤岛。几座石灰岩的孤峰隔云海遥遥相望,上面站着一两个人,一两树扎根于岩石间的柏树与杜鹃。天地一片静寂,突然有一两只鸟开始大声叫唤。云的波涛开始涌动翻卷,海上仙山的幻景渐渐消散。唐代诗人元稹两度翻越秦岭巴岭入东川,他是见过这种景象的,有诗为证:“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元稹写此诗,是第一次使东川时的公元809年,距今已忽忽一千二百多年。人的社会变迁巨大,自然景观却还如千多年前。古往今来,人文记忆与自然景观相互映照,叹兴亡,味永恒,都在这山水诗文中间。
下山途中,远远望见金黄灿烂的树林在山谷中蔓延数里。午餐后穿行其中,识得是落叶松迎来了它们的高光时刻。在米仓山中,别处未见落叶松踪迹,只见它们在这片叫作大坝的宽谷中连绵成片,判定应该是人工栽种,晚上翻阅南江县政协所编文史资料,真就读到一篇文章,回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地建国营林场,伐木支援国家建设,后又在伐去原始森林的迹地上种植人工林恢复植被。证实了我关于落叶松来历的猜想。落叶松虽名为松,其实是杉。其柔软的针叶羽状排列,春发秋脱。白天缘溪行,穿梭于落叶松林中,风过处,黄色针叶簌簌飞坠,枝柯间,阳光亦被染成了一派金黄。不独红叶,灿烂黄叶,亦是一派秋光!
也是缘那条溪流下行,将外来的落叶松林走过,就是本土树种的自然林地。风忽偃忽起,阳光忽强忽弱,野樱桃树黄叶飘飞,落在溪上,落在光润的涧石之上。也是在这幽静深谷中,见到另一种水青冈:米心水青冈。半山腰上的巴山水青冈和松与杉一样,是一茎向上,通直而雄壮。米心水青冈则是丛生的,一丛多达十几茎,依然通直,斜升着向上支撑开巨大的树冠。溪谷狭窄处,常见一丛水青冈伸枝展叶,将溪水全部掩蔽于它的树影之下。风悄然起时,有泛黄的叶片脱离枝头,轻盈飞坠于潺湲的溪流中。秋更深时,米心水青冈的叶子也会变得一片艳红。现在,那些提前飘落的黄叶,在清澈的溪水中载沉载浮,流向山外,传递米仓群山秋天日深红叶将燃的消息。
在光雾山镇的第二个夜晚,弄清了落叶松的来历,又上网查阅水青冈的资讯,确认水青冈确是造成米仓山红叶胜景的主力树种。壳斗科植物中一个专门的水青冈属,全部生长在北温带,中国大陆共有五种,米仓山中即有四种。我这一天,已经在米仓山中识见了两种。以后,若有机会恰逢米仓山红叶灿烂,就有了具体的一种树,也就是满坡满谷的水青冈树的形象作为依托了。更何况,我可能更爱看这些树如何在春风中萌发新芽,虽然说,春天众树的萌芽,不若秋天的红叶黄叶那样绚丽,但千树万树抽芽展叶时,那深晕浅洇的绿,春潮一般荡漾的绿,不也一样动人心弦?
红叶只是时序上的一个点,而群山众树的荣枯,却是生机与美感十足的四季变换,是与我们肉身和情感呼应的生命节律。如此想来,光雾山拥有四季美景,却只说红叶这一个准确时间都难以把握的点,难免让人感到遗憾。这是就时间而言。浩荡米仓,只说一座光雾山,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是就空间而言。红叶,光雾,光雾,红叶,改一句成语,正是一片红叶障目,不见了四季之美;只说光雾,而不见了更加雄浑多姿的米仓全山。夜里看各种材料,回味白天所见景观风物,禁不住种种感慨。
现在的窗外,空中有星光闪烁,天真的晴了。天地相接处,立着几座峭拔岩峰,又回想起白天所见的米仓山独特地貌。高处,石灰岩质侵蚀严重,危崖壁立,孤峰参差,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往下,大山的腹部,却饱满浑成,林海绵延,支撑这种地貌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层。两种岩层,在同一座山上,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质景观。记得地质博物馆中有一个说明,两种岩层形成于不同的地质年代,一个是寒武纪,一个是震旦系,两相配合,才造成眼前的地质奇观。
新的一天,照例早起,在两河相会处,昨天是逆一条溪水往上,往米仓山主峰的方向。今天,我沿河向下,发现是另一个景区的大门,便自觉止步。只在四近河两岸看水、看山。看水,涧水冲激,水底下裸露出纹理清晰的平整岩层。看山,见处处祼露的危崖高壁,无非是涧中平整的岩层被扭曲错动了,斜向着,甚至壁立着陡然升高。米仓山中坚实的花岗岩地层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错动剧烈、溶蚀也剧烈的喀斯特地貌。在我以往的经验中,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地区是广西、是贵州、是云南,不意却在米仓山中也遇见了。比之于广西贵州一带喀斯特灵秀俊逸,这米仓山中的喀斯特,更有种偏于北方气质的高拔雄浑。
这在我,不啻又是一重惊喜。
水声与鸟鸣中,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写的诗句:“惊喜。惊喜。我对群山的一隅久久注视。”
来光雾山一行,这意料之外的惊喜已经是第几重了?早餐时,我把这惊喜算给陪同的主人们听。
一重,光雾山之美,不只是红叶,是四季流转中,山、水、森林丰盈枯寂的交替流变之美。
二重,南江之美,何止一座光雾山,南江形胜是提领了全县地理形势的米仓山脉,是磅礴浩荡之美。
三重,不想米仓山脉中还有如许雄峙一隅、鲜为人知的喀斯特地貌:形成幽深曲折的涧,危临深谷奇树斜敧的峰,相互错落,水绕山环。
主人笑而不语,那表情分明是说,后面还有更多惊喜。
再上路,进了早上没进成的景区大门,往在光雾山镇汇合后的两条河的下游去。
导游说此去的地方是两河口。
我们所在的镇子,就是一个两河口。只是没有叫两河口这个地名罢了。四川盆地周围山地植被丰茂、水源丰富,有峡有沟处,涌泉成溪,有水奔出,相汇成河。小河与小河,小水与大水相汇处,都可以叫两河口。所以,两河口是山中最常见的地名。我们此行无非是从一个不叫两河口的两河口去一个直接就叫两河口的两河口。
在我经验中,山中叫两河口的地方,往往是交通要冲,人烟辏集。但这个地方,没有一座房子,只是两河相汇,只是顺河而来的公路,在此相交,只是座水泥拱桥,架在两河相交处的三岔口上。
河两岸几乎垂直的悬崖,夹峙出逼仄深峡,要努力仰头,才能看见柱柱奇峰直入云天。站在跨河的公路桥上,两河从不同方向来,在光滑如玉的石灰岩河床上飞珠溅玉,在眼前汇聚,又从峡中南流向远方。我下到河床上,只是为和那些清冽的水流更近一些。岩石河床深陷时,水便静止了,在乳白嫩黄的岩坑中形成一个个碧绿的深潭。遇到河床岩层断裂错动处,便飞溅起浪花:跌落、翻涌、回旋。秋深了,水位跌落得厉害,露出大片曾被淹在水底的岩层,被水流打磨侵蚀的岩层。水在每一寸岩石上都留下了痕迹。水把一整块一整块粗粝的岩石打磨光滑了,像一块玉,像一面镜子了。同时又马上来破坏它,这里啮出一条缝,那里吮出一个孔,就从这一道裂缝、一眼小孔,把一块巨岩,日夜不停,消磨成砂。就是水这种日积月累、亘古经年的销蚀打磨之功,造成了眼前的幽谷与群峰。造成地球表面最多变最奇异的景观:喀斯特。
我行走在出露的岩石上,看着脚下柔软的水,捡一粒碎岩,轻捻一下,它就在指尖化成了细砂。
虽然是深秋了,我在岸边岩缝中发现了有植物还在开花。草本的摇着几只蓝铃的是某种沙参。木本的,细密的花蚁聚于嫩枝上的,是某种水柏枝。抬眼几十米,嶙峋的岩缝中长着柏与松,视线再上升两百米、五百米,云雾飘荡的孤峰上斜敧着栎与枫。
这是与米仓山顶截然不同的,各美其美的深峡奇观。
我扮演的是一个游客的角色。本是为观赏红叶而来,却在这山水间领略到一重又一重惊喜。这些惊喜都是拜多样性所赐。植物的多样性,地质面貌的多样性。一朵花从细部给人欣喜,整片山水从宏观给人震撼。
还在河床上发现了一片满是贝类化石的岩层。应该是几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的物种纪录,几亿年前的海洋生命胜景。它附着在更厚实的岩层上,薄薄的一小片,是无生命的岩层中开出的一朵生命之花。在这寂静的幽深山谷中,被风雨不断剥蚀,即将消失殆尽。
在岩层裸露的河滩上盘桓,水、石、云、树,石头的空间,流水的时间,让人在有感与无感之间。然后,我们被导引去看一座庙。我爱山水人文,独对庙观向来兴趣不大。便独自留在庙外,静观以不同姿态耸立于面前的座座奇峰,与奇峰上棵棵不同姿态的树。是真的美,真的无言,按佛家话讲,那美真在住相与不住相之间。也许这时引用陶潜的诗是合适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后来才意识到,两河口才是此次米仓山之行的真正高潮。
从庙里出来,行几里路,又回到两河口桥头。来了一个人在这里等候我们。来人是南江县文物局局长。
他先把我们引到公路路肩上方,在一面壁立的悬崖根部,拨开醉鱼草灌丛的遮掩,看见了岩石上方形的石孔。石孔不只一个,而是一列,均匀地间隔着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斜升向上。有些石孔中还残留着已经碳化的木头残迹。不用提点,马上就反应过来。古栈道遗迹!从先秦开始,就已贯穿秦岭与巴岭的古栈道!贯穿秦汉、魏晋、隋唐、宋元的古栈道!这些古栈道越秦岭到汉中盆地叫子午,叫骆傥,叫褒斜,叫陈仓;再从汉中盆地越巴岭到四川盆地的古道叫金牛,叫米仓。
毫无心理准备,过去只在古代典籍中相逢的米仓古道遗迹就这样突然出现,赫然在目!米仓浩茫,当底还藏着多少惊喜!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所在之处,不只是一片奇山异水,更是通向历史云烟深处的那条过去只在纸上相逢的米仓古道了。
我现在就置身在真正的米仓古道上!在这里,地质的历史与人文的历史完美叠合!
公元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循着秦汉时期即已开辟的古道从古长安出发,翻越秦岭巴山来到四川盆地,留下了观察古栈道遗迹的记录:“沿着岩壁的一条道路几乎只能架设在桩柱上,大概能激起马可·波罗的赞叹,因为那时的欧洲看不到这样的工程。”李希霍芬来时,已是中国人精神委顿的时代,“巷有千家月,人无万里心”。古代的许多道路,已经湮没于黄沙榛莽,被人遗忘。李希霍芬从黄沙中发现了被中国人遗忘的通向西域的道路,并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然后,他南下,发现穿越秦岭巴山的汉唐大道:“这是一段古时候就有的道路,2.5至3米宽,建成阶梯,围着护栏”。在某些特别的时空,历史会显得特别意味深长。站在米仓古道的某一节点上,想起李希霍芬的发现与描述,更想起,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凿通西域的张骞,出生地就在米仓山北边。由李希霍芬想到张骞,正是在云水苍茫的米仓南边的群峰深谷中间。
来不及展开思绪,令人兴奋惊异的发现还在继续。
还是被主人引导,循栈道的遗迹下到河床。就在那道水泥公路桥的上方几米远的河道上,在那条北来的叫作寒(韩)溪的河上。在被水冲刷出岩石层次分明的河床上,连接着从岩壁下来的栈道,两列规整的石孔,等距离伸向河心,河中波浪下,还可见到同样的石孔。这是一座桥的遗迹。文物局局长说,把桥孔中残留的碳化木材作碳14测定,这是一座秦汉时代木桥的遗迹。经测算,该桥当时的宽度在3米以上,长度达30余米,因此可见,这道桥即便是夏天洪水期也可通行车马。在这河上,几十米的范围内,还有数列清晰石孔,那是年代更晚的另外两座古桥的遗迹。这些珍贵的古道遗迹,对普通游客来说,都隐而未显,我们一行也差点忽略过去。后来补看南江县提供的相关材料,当地政府为全面认识挖掘当地旅游资源,数年前就已多方展开资源调查,包括此次我来参加的丛书出版,也是这系统开展的工作之延续与扩展。但这些资源在手,如何全面展示与呈现,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充满可能性的巨大课题。
离开古桥遗迹,沿寒(韩)溪上行一段,遇到又一次河流分岔。在这里,我们离开公路,攀石阶到悬崖上去,要去徒步走一段米仓古道。相近的路况,李希霍芬是走过的:“道路于是离开了河流,沿着山坡向上蜿蜒……踩着一种因长年使用而被磨得十分光滑的石灰石铺成的阶梯上行,时而一下子就有40至50阶,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这些文字,恰是我们正在跋涉的古道写照。除了路口上想象古道行旅的现代雕塑和电视剧里古代军旅的旌旗悬垂路旁。悬崖,悬崖下的碧绿深潭或白浪翻涌的大小跌水、石阶,都还是一千年前、两百年前的气氛与模样。米仓古道和秦岭巴山中的其他古道一样,其实是分两种方式开凿出来的。在岩石上打孔,楔进木桩,其上铺板,称之为栈。《战国策》中就说:“度栈千里,通于蜀汉。”这既是一种路的形式,也是一种筑路方法。眼下,我们所走的路,也在悬崖之上,但不是“栈”,而是从石壁上掘出一条路来,当地话中,叫“碥”。李希霍芬也经过了这样的路:“大段的路都是在坚硬的角闪石上凿出来的”,这样的开凿之功在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李希霍芬说“那时又没有火药”。
当然,古人从北方入川,穿越秦巴众山,这样的古道必然频频走过。将军走过,士卒走过,商人走过,盗匪走过,流官走过,诗人也走过。虽然不一定就是米仓,但所经地理,所受苦辛大致都是相同的罢。
杜甫入川,留下实景记录:“栈云阑干竣,梯石结构牢。万壑敧疏林,积阴带奔涛。”不就是我们穿行古米仓道中真实的气氛与情景吗?杜甫写此诗,是公元759年冬天。
又过了几十年,公元809年,诗人元稹从长安出发,以监察御史身份到东川巡察,也是从米仓道上往返的。他也有诗句留下古道上的风景速写:“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那就真是眼前山水的真实写照了。元稹和米仓古道缘分不浅,六年后的815年,他被贬官为通州(即今辖南江之巴中)司马,更深味人生旅途之艰难:“物色可怜心莫恨,此行都是独行时。”便已将古道上羁旅漂泊之感,上升为普遍的人生哲理了。
移步换景,云在天上,溪在深涧。在悬于陡峭岩壁间北行数里,溪谷再次分岔,又是一个不叫两河口的两河口,再次在悬崖上见到十余石孔,孔中出露的栈木历历在目,生满青苔。不禁让人张望良久。
从绳桥上越过溪涧,对岸崖脚是一块平地,几株大树笼罩着一座木头房子。一株是结着很多小果的野枣树,另外几株不是枣树,但都亭亭如盖。
新盖的木屋是仿古驿站的意思。旁立一块碑,上书三个醒目大字:截贤驿。截人者谁?萧何。截了哪位贤明?韩信。
这是中国人都烂熟于胸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楚汉相争,刘邦退出关中屯兵汉中,背靠米仓山厉兵秣马,心怀远大。却未识得前来投奔的韩信之帅才,虽有萧何保荐仍置若罔闻,使得韩信乘夜出走,顺米仓道南下欲回楚地故乡。萧何月下飞奔追寻。接下来就是当地版本的故事,就在此处,就在这道湍急溪流上,恰逢大雨,陡涨的山溪冲毁桥梁,老天要替汉朝留下开国帅才,萧何才在这溪边驿道追上韩信,并在驿站中与韩信作竟夜之谈。结果当然是韩信心中意转,再回汉军大营,刘邦升坛拜将。这样流传千年的故事,就发生在眼下这寂静无人的空幽山谷中,使这米仓古道又增一段生动的历史传奇。
所以眼前这道叫寒溪的流水也叫作韩溪。
临行前一晚,我们宿在另一个镇上,住进新开的精致民宿。独立的木楼一面临水,背后是正在泛出秋色的森林环抱。夕阳西下时,我坐在楼下案前一边弄当地上好红茶,一边翻阅当地文史资料。回想这两天的行程,随手在电脑上敲下一行字:分云拨雾见米仓。这就是记南江之行的文章题目了。
南江之行,本为光雾山红叶而来,南江一县旅游业,也长时间以此为号召。只因每年气候条件不同,红叶显现的时间并不能准确预报。但我不是失望的游客,并不以此为憾。未见红叶,却上了光雾山顶峰,看见了此山独特的植物,和这些植物构成的不同于他处的生态景观。又在光雾山顶发现辽阔浩渺的米仓山脉,由植物群落及于其地质景观。就这样由点及面,就是当下提倡的全域旅游吧。又于米仓山腹地发现古道遗迹,并于古道上追寻体验,由自然地理及于历史人文,这样的道路韩信萧何走过,元稹走过,白居易想象过,就这样由平面及于纵深,就是目下所提倡的文旅融合吧。
此次短暂旅行,所见所感如此丰富,打开地图,发现这两天游览只在南江县北川陕交界处的狭长地带,看案头资料,不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遗存,却布满南江全境。这些资源,本都由米仓山、米仓古道所聚合串联。黄昏降临,此行尚未正式结束,就令人于独坐时不断回味。
案上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是在两河口告别的文物局局长发来一组照片。一组佛菩萨造像,由一块独立的巨石雕琢而成。造像广额阔鼻,庄严裸身的是串串璎络,一眼看去,就是尚存有印度风的隋唐风格。这也是米仓古道上的文化遗存,此行未能触及的米仓风景中的另外一面。
米仓古道,不只是金戈铁马,不只是商旅往来,还有不同文化交互影响,相与往还。
已经在米仓山上和主人约过,暮春夏初,杜鹃鸟啼时,来看杜鹃花开。那就再约一次,看完杜鹃花开,再沿着米仓古道,一个个河流分岔或汇合处,去瞻仰一路上不同时代的摩崖造像。体会如何是佛祖西来意,中国人又如何接纳了佛教东渐。作此想时,便恍然看见,岩上云间,慈悲垂目的佛菩萨像前,随风飘坠,落于溪涧的不是莲花,而是片片杜鹃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