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从某”类术语辨
马英杰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说文解字》中的“从某”类术语,包括“从某”“从某象形”“从某某”“从某某某”“从某,(短语)”“从(短语)”“从某从某”“从某从某从某”“从某从某某”等,以及在这些术语基础上添加声符形成的形声类术语。(1)《说文解字》云“从某”,大徐本中绝大多数作“从某”,小徐本皆作“從某”。“从”“從”古今字,许书“從”训“随行也”,“从”训“相听也”,若用字之本义,当以“从某”为佳。另外,“从某”类术语的分析,是以许慎的文字学为考察对象的,而且《说文解字》除了是一部文字学著作之外可能还有不少经学色彩,因此参照当今的古文字学水平来规范和评价《说文解字》体例,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不那么合适。
《说文解字》中的“从某”,依照段玉裁的理解,是指一字在形体或意义上与“某”相关,相应地,部首之下的“凡某之属皆从某”是指属字与部首之间在意义上的从属关系。由此观点出发,段玉裁认为,《说文解字》说解用“从某某”和“从某从某”之类的是会意字,“从某某声”之类的是形声字。更进一步,段玉裁认为“从某某”之类和“从某从某”之类会意术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联属会意,后者是并峙会意。上引段玉裁对“从某”的看法其实是对三个层次问题的回答:第一,“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的区别提示了“从”字在用法上的何种特性;第二,“从某”类术语与六书有何种对应关系;第三,“从某”类术语与六书在《说文解字》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清代以来的学者大体上同意段玉裁的看法,但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段玉裁的理解与许书颇有出入之处,提出“从某”只是用以分析构形,与六书无关。(2)李运富:《〈说文解字〉“从某字”分析——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二》,见王宁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4-73页。诚然,段玉裁的看法不尽合于《说文解字》,但若以为“从某”与六书毫不相关恐怕也不尽然。本文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由“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的区别入手,考察“从某”类术语的用法、“从某”类术语与六书的关系,进而探究“从某”在《说文解字》说解体系中的用法和价值。
一、由“从某某”与“从某从某”之别所见之“从某”用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3)本文引用的版本:大徐本为(汉)许慎,(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景清陈昌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段注本为(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景经韵楼刻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本句注文中,段玉裁提出《说文解字》中会意字有两种释例,一种是“从某某”,如“人言”和“止戈”,是“二字联属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者,第二种即“从某从某”。段注中又说:“(‘从某某’者)往往为浅人增一‘从’字,大徐本犹甚,绝非许意。然亦有用两‘从’字者,固当分别观之。”
段玉裁在“一”部“天”和“吏”字之下,对于“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的区别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天”,大徐本“从一大”,段注云:“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于六书为会意。凡会意,合二字以成语。如‘一大’‘人言’‘止戈’皆是。”“吏”字,大徐本“从一从史”,段注谓:“此亦会意也。‘天’下曰‘从一大’,此不曰‘从一史’者。吏必以一为体,以史为用。‘一’与‘史’二事,故异其词也。”段玉裁的观点影响很大,比如胡韫玉《六书通论》认为,“从某某”的意思是“合数字以成一字,其意相附属,而其他皆无所兼者”,“从某从某”是“并峙为义,二文之意不能更贯言之”。(4)胡韫玉:《说文解字索隐·六书通论》,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中·六书总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4页。张度也认为:“其文顺叙者则训为‘从某某’。其文对峙者则训为‘从某从某’。皆会意之正也。”(5)张度:《说文解字索隐·六书易解》,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中·六书总论》,第467页。质言之,段玉裁主张所从之字可以连读的即二义联属为一事,说解用“从某某”;从不同侧面表述字义、无法连读的,说解用“从某从某”。这种看法,本文暂称之为“联属并峙”说。段玉裁依据此说将《说文解字》大徐本中193个“从某从某”之字删去一“从”字。
1)“珏”部“班”字,大徐本作“从珏从刀”,段玉裁从小徐本更为“从珏刀”。“班”为“分瑞玉”,“刀”为分玉之具,“珏”为已分之象,“刀”“珏”不可联属。“班”与“冎”部“剐”字相类。“剐”,段玉裁云:“‘冎’者,分解之皃。‘刀’者,所以分解也。”但段注本正文却仍延续大徐本不改,作“从冎从刀”。“班”字一“从”而“剐”字两“从”,可见段玉裁并未能贯彻“联属并峙”的原则。
3)“走”,段注本作“从夭止”。段注云:“夭部曰:‘夭、屈也。’止部曰:‘止为足。’从夭止者,安步则足胻较直,趋则屈多。”“夭”是走之貌,“止”是走之用。“夭”和“止”并峙,也无法联属。


若将“联属”的理解,从联属为动宾、主谓等短语扩大到联属成句,固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的区别也会因此而消失,因为段注本《说文解字》中存在不少“从某从某”可以联属成句的例子。
6)“癶”部“癹”字,大徐、段注本作“从癶从殳”。段注云:“从‘癶’,谓以足蹋夷也。从‘殳’,‘殺’之省也。”段玉裁分别说之,然解释为“以足蹋杀之”亦通。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从某某”的情况中不无“并峙”的现象,“从某从某”亦未必不可“联属”。以“联属”和“并峙”划分“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理由尚不充分。
实际上,二者的区别在于“从某某”会意中,前两字“从某”是“从某之属皆从某”的意思,后一“某”仅提供义符或形符。而“从某从某”会意的后一“从”字,不仅起到了区隔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与前一个“从某”一样,都在于说“从某之属皆从某”,所从的是构件之“意”。构件之“意”是指造字者借字义所表达的造字意图,不局限于字义。(6)“意”“义”二字的具体分别,参见王红岩:《“意”与“义”的辨析》,《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如“類”字大徐本云“种类相似,唯犬为甚。从犬,頪声”,段玉裁谓“说从犬之意也。类,本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再如“下”字从属于部首“上”,“薅”(“拔取田艸也”)从属于部首“蓐”(“陈艸复生也”),虽然属字在字义上与部首完全相反,但不妨碍它们具有共同的指向。这种引申或指向就是构件之“意”。“意”与《说文》的“属”“类”的涵义有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属”是字的上位概念,不仅表示部首是汉字构形的“字源”“字头”,也是许慎建构出的概念范畴,需要从经学等多种角度来理解。(7)顺真:《许慎〈说文解字〉的逻辑—认知构造》,《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
对比大徐本中的一些形、义相近的字可以发现,“从某某”会意的第二个“某”是取其形或义,而“从某从某”会意两个“从某”皆取构件之意。如:
9)“示”部“祫”“祟”
“祫”,大徐本:“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从示合。”“祫”用“合”本义。
“祟”,大徐本:“神祸也,从示从出。”从出,取在外为祸之意。




13)“人”部“伍”“什”“佰”
“什”,大徐本云:“相什保也,从人十。”段注引《周礼》郑注云:“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佰”,大徐本云:“相什伯也,从人百。”段注:“佰之言百也。”这里的“十”和“百”从的都是本义,用“从某某”。
“伍”,大徐本云:“相参伍也,从人从五。”段注:“凡言参伍者,皆谓错综以求之。”“伍”用的是“五”的“错综参伍”之意,而非具体数字,所以大徐本释作“从人从五”,与“从人十”和“从人百”有别。
14)“犬”部“狧”和“狊”
“狧”,大徐本:“犬食也,从犬从舌。”舌非口,不能食,这里从的是以舌舔食之意。
“狊”,大徐本云:“犬视皃,从犬目。”用“目”之义。
15)“火”部“煣”、“革”部“鞣”
“煣”,大徐本:“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声。”“从火柔”即以火柔之,“火”和“柔”皆用其字本义。
“鞣”,大徐本:“耎也,从革从柔。柔亦声。”释“鞣”为“耎也”而非“耎革也”,意即“鞣”字是“耎革”的引申而不限于治革,从革乃取其软意。

17)“水”部“衍”与“洐”
“衍”,大徐本:“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洐”, 大徐本:“沟水行也,从水从行。”二字都是“从水从行”,但字义不同,原因在于取意不同。
以上几组例子显示,“从某某”会意的第二个“某”用的是构件本义,而“从某某”的前二字“从某”和“从某从某”的两个“从某”,指的都是“凡某之属皆从某”,所取为构件之“意”,即构件与“某”相关的共同指向。也就是说,“从某从某”的后一“从”字,在《说文解字》中并不特殊。
二、“从某某”“从某从某”与会意字的关系
通常认为,“从某某”与“从某从某”对应六书中的会意。但在大徐本中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反证。
大徐本“从某某”之字中,存在少数明确的非会意字:如“木”部“”字,大徐本“从木,阙”,段注谓“谓形不可识,无由知其形声抑会意也”;再如“巴”部“”字,大徐本云“阙”,段亦云“阙其会意、形声之说也”;又如大徐本“日”字说解曰“从囗一,象形”。还有一些很难理解为会意:“玉”部“瑞”字,大徐本云“以玉为信也。从玉端”,但很难说“端”与信有何关系;“囗”部“因”字,大徐本“就也,从囗大”;“豕”部“豙”,大徐本“豕怒毛竖,一曰残艾也。从豕辛。臣铉等曰:从辛,未详”;“卪”部“卸”,大徐本云“舍车解马也,从卪止午。读若汝南人写书之写”,“午”和“卸”关系也很不明确。
“从某从某”是否全部为会意字也存在可以讨论之处。


以上例子显示,大徐本中“从某某”和“从某从某”的字不全是会意字。也就是说《说文解字》中会意字的范围只是与“从某某”和“从某从某”类有所交叉而已。这一现象,传写错乱不见得是唯一因素。若对大徐的文本保持足够的慎重,那么原因更可能是许慎并未将“从某某”和“从某从某”与六书中的会意直接对应起来。更宽泛地说,可能许慎并未将包括“从某某”“从某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某声”等的“从某”之类与六书直接对应起来。
若要说明这一点,必须全面分析《说文解字》说解中的“从某”类术语,以厘清包括“从某某”“从某从某”之类术语在内的“从某”类术语与六书之间的关系。
三、《说文解字》“从某”类术语分析
《说文解字叙》中,许慎十分重视“文”和“字”的差别,他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以“从某”类术语的视角看,说解不用“从某”类术语的大部分是“文”,说解用“从某”类术语的是从“文”得意的孳乳字。根据有无“从某”类术语和“从某”类术语的不同类型,《说文解字》中9353字的说解可以分为如下八类:
(一)类I 无“从某”类术语者
在分析以“从某”类术语说解的字之前,需要在《说文解字》中划出的是说解中没有“从某”类术语的文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说解中无“从某”类术语的文字中大部分是象形“文”,也有一些指事和抽象的“文”,还有少数会意字和形声字。象形字自不必说,指事字有许慎标出的“上”“下”二字,“抽象字”是今人的划分,很难用六书归类,比如“丶”和“丨”。下面主要谈此类中的会意和形声字。

说解中不用“从某”类术语的还有三个形声字:“齒”下云“口龂骨也。象口齒之形,止声”;“”下云“艸木盛然。象形,八声”;“厹”下云“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三者象形部分不成字,故不云“从”,与“从某某声”的形声字是有差异的。
(二)类II “从某”
“从某”类术语中有仅云“从某”者。“从某”之字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某,某声”的形声字,在《说文解字》中多见。


第四种用六书可以分析为形声包象形,这种字《说文解字》中有2个:“牽”下云“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禽”下云“从厹,象形,今声”。
(三)类III “从某某”等及其变式
“从某”类术语中有仅用一“从”,“从”下有数“某”者,包括了“从某某”“从某某某”等等。用此类术语说解的字中,绝大多数是会意字,但也有少部分非会意字。会意字中,数个“某”可以汇为短语的,用“从某,(短语)”与“从(短语)”两种变式表达。说解用“从某某”等及其变式的字可以分析如下:
1.IIIA:会意。说解用“从某某”“从某某某”及其变式,其中“从某”之下的“某”皆取“某”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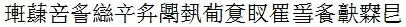

(3)IIIAc:IIIAa的变式,形式为“从(短语)”,“从”下用短语的形式陈述数“某”的关系,部首外的“某”取其义。如“闰”云“从王在门中”,“歬”云“从止在舟上”,“骨”云“从冎有肉”。根据“某某”之间的关系,此类又可以分为三种:
IIIAc1:短语描述由数个“某”构成的动作行为,如“弄”云“从廾持玉”,“休”云“从人依木”。这种字在《说文解字》中有37个:屰丈弄戒兵秉隻蒦糞耒贙盥休負兼舂帚白付伐弔縣夾曓夰谷婦戍凥史折。
IIIAc2:短语描述数个“某”之间的位置关系。在《说文解字》中有52字:閏葬窋突竄戾歬莫臦窅看奮羼典甘号央舛桀杲杳囷囚困早臽兇寒穿勽庫仄厃光燊炙閃闖區堯俎辯孱辱戌肅料屚。

2.IIIB:会意,形式为“从某某”“从某某某”等,取部首外“某”之形。“从某某”与“从某从某”的会意字,不仅有取义和取意的区别,还在于“从某某”会意字可以取部首外的“某”之形,用六书可以解释为会意包象形。
(1)IIIBa:其表述形式为“从某某”“从某某某”等。
IIIBa1:取“某”之形的字,如“牢”云“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夫”下云“从大,一,以象簪也”;“”云“从卜,兆,象形”;“匘”云:“头也。从匕;匕,相匕着也。巛象发。囟象匘形。”此类在《说文解字》中有49字:中卉尒番牢登足反支胃箕盇夅亼舍倉啚夒回秫匘卯勻鬽畏嵒廛庶碞磬婏夫畺斲戈孑孓高谷牟疋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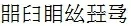


3.IIIC:非会意字,形式为“从某某”“从某某某”等。“从某”之外的数“某”之一仅提供作为构件的形,不参与会意,与IIIB以形会意的会意字不同。如“谥”云“从言兮皿,阙”,“因”云“从囗大”,“”云“从又屮”,这类字在《说文解字》中有13个:瑞邍謚睔因頪豙螷卸牖。

(四)类IV “从某从某”等
“从某”类术语有用有数个“从某”者,即“从某从某”“从某从某从某”等。与类III相同,类IV中也有少量非会意字。类IV可以分析如下:
1.IVA:会意,数个“从某”都是取“某”之意。“从某从某”字中大多数属于此类。

(2)IVAb:“从某从某”的会意字中,存在一类字,前一“从某”是指某一大类共性,后一“从某”指大类中小类的共性,大小两类性质比合成义,可以训为“某之某者也”。如“婢”为女之卑者,“搜”即艸之生于鬼者,“”是马之八岁者,“牭”是牛之四岁者,“儒”是人之软者,“仲”即人之排行居中者,“苗”是“艹生于田者”,“”是“血理分衺行体者”,“”是“艸之相丩者”。《说文解字》中此类字有65个:蓏苷蒐苗半咠讷譱章妾興緊堅杸役棥萑瞢蔑幼死隋等筮觋彤致枓皣貶邑昌旅栗禾疢伊倌煩須髦薦麀喬洐洄覛婢蠅坤埾堇恊垒。


与IIIAa和IIIBa相同, IVAa中也有象形字:“于”下云“于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般”下云“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
IVAa和IIIAa及IIIBa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清晰的界限,但模糊的空间是有限的。IVAa中之“从某”可以视为取义的有13个字:舁取雧刵魝合馺冤沙。在IIIAa中可能是“从某某”但是取意的有14个字:囮察容帥妟佞義仚庶。IVAa中由于取形而与IIIBa有所交叉的字有7个:矦胤兜森業离。
(五)类V “从某某”等及其变式加声符
此类的形式有“从某某,某亦声”“从某某,某声”“从(短语),某亦声”“从某,(短语),某声”等,其中“从某某”等及其变式的用法与类III相同。VA和VB类似,形式为“从某某,某亦声”;VC和VD为类似,形式为“从某某,某声”。VA和VC取“某”之义,与IIIA类似,VB和VD取“某”之形,与IIIB类似。
1.VA:形式为“从某某,某亦声”,会意兼形声,其中“从某某”部分取“某”之义,这与IIIA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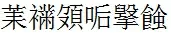
(2)VAb:VAa的变式,形式为“从(短语)”,取“某”之义,与IIIAc1类似。《说文解字》中有2字:竀。“竀” 下云“正视也。从穴中正见也,正亦声”;“”下云“楚人谓卜问吉凶曰。从又持祟,祟亦声。读若赘”。

2.VB:形式为“从某某,某亦声”,其中“从某某”部分取“某”之形,与IIIB类似。


3.VC:形式为“从某某,某声”,其中“从某某”部分取“某”之义,与IIIA类似。
(1)VCa:“从某某”部分与IIIAa类似,《说文解字》中有4字:碧嚋衋疑。
(2)VCb:“从某某”部分变为“从某,(短语)”,与IIIAb类似,《说文解字》中有1字:彝。“彝”下云:“从纟;纟,綦也。廾持米,器中宝也。彑声。”
(3)VCc:“从某某”部分变为“从(短语)”,“从”下用短语的形式陈述数“某”的关系,取“某”之形,与IIIAc2类似。《说文解字》中有1字:宜。“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声”。
4.VD:形式为“从某某,某声”,其中“从某某”部分取“某”之形,与IIIB类似。

(2)VDb:“从某某”部分变为“从(短语)”,与 IIIBc类似。《说文解字》中只有1个字:巠。“巠”下云:“从川在一下。一,地也。省声。”
(六)类VI “从某从某”类加声符
此类形式为在两个以上“从某”后缀以声符,声符有三种形式,“某亦声”“从某声”以及“某声”。
1.VIA:会意兼形声,形式为两个以上“从某”和“某亦声”,其中“从某从某”类的部分与IVA类似。


2.VIB:形式为“从某从某声”。这一形式与“从某从某,某亦声”似名异而实同。比如“释”字大徐本云“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从睪声”,小徐本云“从睪,睪声”。此类字总共有三种:
(2)VIBb:与VIAb类似,《说文解字》中有1字:嶞。
(3)VIBc:累增字,与IVB类似,《说文解字》中有1字:授。
3.VIC:形式为“从某从某,某声”,其中“从某从某”之类的部分与IVA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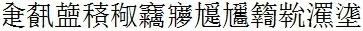
(2)VICb:“从某从某”部分会意,可解为“某之某者也”,与IVAb类似,此类字在《说文解字》中有6个:薻曾梁槱酱。
(七)类VII “从某从某”与“从某象形”“从某某”及其变式的嵌套型
“从某”类术语比较复杂的形式是“从某从某”与“从某某”“从某象形”“从某,(短语)”或“从(短语)”等的嵌套型,如“从某某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短语),从某”“从某,从(短语)”“从某从某从某某”等等。同样,“从某”是指从“某”孳乳,取“某”之意,而“从某某”之是取“某”之义或取“某”之形。
1.VIIA:“从某从某”与“从某象形”的混合型,只有1字:鬼。“鬼”下云:“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
2.VIIB:“从某某”的部分取“某”之义:

(2)VIIBb:“从某某”以变式“从某,(短语)”出现,这部分相当于IIIAb,如“”下云“从寸,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说文解字》中有3字:疐。
(3)VIIBc:“从某某”以变式“从(短语)”出现,相当于IIIAc。

VIIBc2:短语描述位置关系,相当于IIIAc2,《说文解字》中有1字:敻。“敻”下云:“从,从人在穴上。”
3.VIIC:“从某某”的部分取“某”之形:
(1)VIICa:“从某某”的部分取“某”之形,相当于IIIBa。
VIICa1:“从某某”部分相当于IIIBa1,如“眞”下云“从,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说文解字》有两字:眞履。
VIICb2:“从某某”之“某某”重形,相当于兼IIIBa2,《说文解字》中有1字:競。“競”下云:“从誩,从二人。”
(2)VIICb:“从某某”以变式“从(短语)”的面貌出现,相当于IIIBb,如“恆”下云:“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说文解字》中有2字:恆或。
(八)类VIII 嵌套型加声符
以上将《说文解字》中“从”类术语分析为八类。现将这八类术语的用法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不用“从某”类术语的情况共有四种:第一种是象形字、指事字和抽象字,即为许慎所说的“文”,第二种是无法用“从某”类术语说解的会意字,第三种是省略了“从某某”或“从某从某”的会意字,第四种是既非“文”也不是“从某”而来的形声字。
第二,“从某”之属。“从某”指“凡某之属皆从某”,是说某字与其所从之“某”具有共同的意指,也可以说是某字“从某”孳乳而来。依六书说,“从某”之字中有“从某某声”的形声字,“从某象形”的象形兼会意字,类似“舜”字的象形兼形声字,还有类似“牵”字的形声包象形字。

第四,“从某从某”之属,包括带声符的“从某从某”之属。大多数“从某从某”指一字同时具有两个“某”属的意指,其字义由两种意指会意而来。也有个别字中的“从某”仅是形符,与字义无关,如“从贝从斦,阙”的“質”字,但这部分字与“”等“从某某”的非会意字有何区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带声符的“从某从某”之字与此类相同。
第五,“从某某”和“从某从某”两类的嵌套型,包括带声符的嵌套型。这类的“从某某”和“从某从某”与上述第二、三类相同,之所以需要嵌套,是因为提供义符或形符的“某”与另一个构件比合后组成的“从某某”不成字,否则用“从某从某”即可。这类字可以认为是嵌套了会意构件的会意字。在此之上增加声符的字与此类似。
四、“从某”类术语的作用及其与六书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归纳中可以看到,《说文解字》中的“从某”皆与“凡某之属皆从某”之“从某”相同,是说某字与其所从之“某”具有共同的意指,也可以说是某字“从某”孳乳而来。“从某”类术语是一套用于说明文字意义来源的系统,与六书的关系并非直接对应,而是互相配合。
六书与“从某”类术语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关于这一点,陆宗达已经指出“文”和“字”是汉字的历史发展,而六书是汉字的构造法则,二者并不相同。(8)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46页。也有学者认为:“从‘六书’的认知来源上看, 源于整体上认知的‘归纳’法与许慎的‘从某、从某’式的点画或构件与本义对应的穷尽‘分析法’相隔。”(9)张蒙蒙:《“六书”的生成及与〈说文解字〉关系探讨》,《郑州师范教育》2013年第5期。我们不必同意“六书”源于归纳而“从某”源于分析,但将二者区分开来是有道理的。可以进一步说明的是:象形在《说文解字》中并不局限于独体象形,还有“从某象形”“从某某象形”;会意,《说文》中有不用“从某某”或“从某从某”说解的会意字,而另一方面,“从某某”“从某从某”中也存在非会意字;形声,《说文》有不言“从某”的形声,也有结构比较复杂的“从某某从某声”。
“从某”类术语与六书的配合关系,体现在“从某”类术语提示了文字孳乳各阶段的节点,而六书说明了文字孳乳各阶段的途径。
“从某”类术语起到了提示文字孳乳各阶段节点的作用。举例来说,“口”是象形之文,通过形声孳乳为“曰”(从口乙声)。“曰”可以通过形声孳乳为“朁”(从曰兓声),可以通过会意孳乳为“”(从虤从曰),可以通过象形孳乳为“”(从曰,象气出形)。“口”也可以通过象形孳乳为“”(从口象形),“”可以通过象形孳乳为“”(从省象形)。“口”通过象形孳乳为“只”(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可以通过形声孳乳为“”(从只甹声)。“口”还可以通过会意孳乳为“”(从口从内),“”可以通过会意孳乳为“矞”(从矛从),可以通过形声孳乳为“商”(从,章省声)。在象形之“口”不断孳乳的过程中,先通过形声、会意、象形三条途径增加形、义或声符,孳乳为“从口”的“曰”“”“豆”,形成了孳乳过程的第一层次的节点,而后三者再通过“从某象形”“从某某声”“从某某”“从某从某”等途径增加形、义、声符,形成了由“从曰”“从”“从豆”之字组成的第二层次的节点,以此类推。“从某”类术语,表达的不仅是字的构形,也包含了其孳乳过程中途经的节点。反过来说,根据“从某”可以明确一字的最初来源,并能完整理解其形成过程。
六书,是说明由“从某”所提示的各个节点之中的途径。比如“齿”下云“口龂骨也。象口齿之形,止声”,就是说“齿”字的形成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仓颉”造出齿之形,其途径是象形,第二阶段是从象形到止声,途径是形声。再如“禽”下云“从厹,象形,今声”,“禽”的形成有四个阶段,一是“仓颉”造出“厶”,其途径是象形,二是从“厶”到“厹”,途径是形声,三是从“厹”到“离”,途径是象形,四是从“离”到“禽”,途径是形声。又如“亼”下云“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亼”的形成由两个阶段,一是“仓颉”造出“入”,途径是象形,第二是从“入”到“亼”,途径仍是象形。又如“丧”下云“亡也。从哭从亾。会意。亾亦声”,“丧”字的形成有“哭”“亡”两个来源:一是“哭”,“仓颉”造“口”,途径是象形,由“口”到“吅”,途径是会意,由“吅”到“哭”,途径是形声;二是“亡”,“入”“”都是“仓颉”造的象形,再由二者会意形成“亡”。最终,“亡”和“哭”会意形成“丧”。
“从某”与六书配合起来,展现了《说文叙》中所说的“形声相益”的文字孳乳过程。许慎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段注说:“‘形声相益’谓形声、会意二者也。有形则必有声,声与形相軵为形声,形与形相軵为会意。‘其后’,为仓颉以后也。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其后文与文相合而为形声、为会意,谓之字。”段玉裁的看法,重点在于六书,所以他将“形声相益”理解为在“文”之形上或益以形,或益以声,这种看法影响至今。(10)黄德宽:《形声相益:汉字孳乳浸多的主要途径》,见《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1页。段玉裁的看法是正确的,但由于忽略了“从某”揭示出的文孳乳的复杂历程,所以不一定全面。所谓“相益”,是指形符和声符的反复迭加嵌套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若干阶段逐步完成。这个过程中,象形字、形声字和会意字都可以被新的孳乳字嵌套其中,象形、会意字可以益以形符、声符,形声字也可以益以形符、声符。正是在“从某”类术语与六书的配合之下,《说文解字》展现出一幅巨大的文字孳乳衍生图景。
五、余 论
本文在对《说文解字》全书“从某”类术语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考察其在《说文解字》中的作用和价值。然而在上文归纳之外,《说文解字》的“从某”类术语存在三处例外。
第一处是“心”部“意”,大徐本作“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在本文的归纳中,“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属于IIIAc1,“从心从音”属于IVAa,二者不可并存。小徐本作“志也,察言而知意也。从心,音声”。段注本校为“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
例外的存在,说明《说文解字》在千年的流传中窜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代表《说文》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内在规律。因此大徐本或许不像段玉裁理解得那样已经面目全非。“从某”类术语的精细化研究,比如对大徐本中在“从某某”之间缀入解释的研究,或者对“从某”揭示出的许慎理解的文字孳乳脉络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
-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中美贸易争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