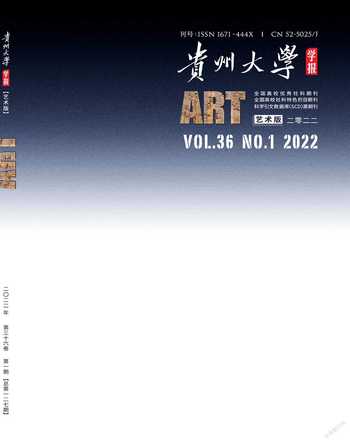从《太太万岁》和《不了情》看张爱玲电影与其小说的差异及其成因
王一平 张体坤
摘要:作家张爱玲以文字为载体呈现出的小说世界与编剧张爱玲以影像为载体描摹出的电影世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展现了一个如拉康所言的象征的世界,是建立在秩序与规则之上的,是二元对立的。而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却是多元的,非秩序的,“符号态的”。
关键词:张爱玲;象征;符号态;《太太万岁》;《不了情》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2)01-0082-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2.01.012
本文拟以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与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the semiotic)理论分别阐释张爱玲编剧的电影与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常常展示出被象征秩序控制的世界,在这些电影中,秩序伦理常常高于情感与感觉,意识压抑潜意识;而她的小说世界则可以说是符号态的,是非象征化的,是诗性的,呈现出的是被意识压抑之下的世界。
在拉康的阐释中,象征界与想象界相对,“俄狄浦斯情结”是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分界点。在产生“俄狄浦斯情结”以前,主体处于想象界,最初,婴儿会自动将镜子中的个体等同于自己,这是原始自恋阶段。随后,参照对象转向母亲,即小他者。当婴儿发现母亲没有“阴茎”,便产生了“阉割情结”,因而便需要象征的“父亲”的引领,这便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考验,度过这一阶段后,语言被完全引进,参照的对象也从具体的他人,变成了一个个“能指”[1]433。由此,个体也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欲望对象从小他者变成“父亲”代表的大他者,也即象征秩序,如伊格尔顿所言,象征秩序“事实上乃是现代阶级社会的父权的、性的社会的秩序”[2]。在拉康理论的基础之上,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符号态”这一概念,与象征态相对应。她认为,“符号态出现在镜像阶段之前,它是跨语言的而不是前语言的,……符号是互动、情感、感觉意义的载体”[3]111-112,符号态某种程度上是原初的,是冲动的;而“象征态是通过‘客观束缚’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产物,这些束缚通常源自于物的(包括性的)差异和具体的、历史的家庭结构。”[4]16-17因而,当主体进入象征态之后,符号态必然受到压抑,但并不会被完全淹没,相反是一种对于象征秩序的否定与逾越。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我所谓的‘革命’,首先指被压抑者的复归,然后仅指被压抑者的复归给标准化社会交换的陈规带来的惊讶冲击甚至变动冲击。”[3]109大体而言,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与拉康的“象征界”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
编剧张爱玲的电影是“象征”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却是“符号态”的,因而可以说张爱玲的电影和小说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第一部分拟选取故事框架类似的电影《太太万岁》与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电影《不了情》与小说《色·戒》两两对比,借助拉康与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帮助,具体阐释这两对文本与影像之间的差异;而第二部分则着眼于探讨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即为什么同一个创作者在不同的载体之下却创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是否可以说是“市场逻辑”的影响,又或者“符号态”只能存在于“文本”之中,却无法通过“影像”展示出来?
一、何种差异?
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与《不了情》基本遵循着欲望叙事的法则,这两部电影的整体故事框架都搭建于“象征秩序”之下。在关于电影中欲望叙事的评析里,拉康的“象征界”理论被广泛运用。拉康认为,欲望诞生于需求(need)转化为要求(demand)的过程中,需求是本能愿望,而主体接触语言之后,需求也变成要求,即人们所说的爱。[1]594在这一过程中,对母亲的欲望被象征秩序压抑到无意识之中,并在象征秩序之內转移至大他者的欲望,也即“欲望着他人的欲望”,齐泽克将这种象征秩序中的大他者欲望称之为“父亲之名”[5]。更为广泛地说,金钱、权力、爱情等都属于象征秩序中的欲望,而常见的欲望叙事电影也常以这些欲望的满足过程作为故事主线,《太太万岁》与《不了情》这两部电影同样如此。
《太太万岁》上映于1947年,由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常见的婚外恋故事,故事的开始,妻子陈思珍(蒋天流饰)与丈夫唐志远(张伐饰)十分恩爱,但丈夫事业不顺。随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丈夫事业发展,获得财富,在朋友的介绍之下瞒着太太另娶了一个姨太太。到故事的后半段,妻子逐渐发现了丈夫的外遇,同时丈夫工厂破产,姨太太也跟丈夫决裂。此时颓废的丈夫百般哀求之下获得妻子的原谅,两人再次和好如初,在家庭与事业上都回归到电影开头的状态。整体上,这部电影是一个圆形的叙事结构,它虽然名为《太太万岁》,却自始至终都以男性视角为主,前半段严格遵循着欲望叙事的法则,讲述主人公唐志远如何获得金钱与性资源,即象征秩序之下两种常见的男性欲望;后半段则是欲望的破裂与秩序的回归,丈夫失去了财富与额外的性资源,但挽回了婚姻,再次获得世俗的幸福,也进入象征秩序之中。这部电影一方面展现了象征秩序之下,大他者欲望的虚假;另一方面亦反衬出秩序(在这里是婚姻)之强大。电影的点睛之笔在结尾,当这对夫妻和好如初,在饭店偶遇曾经的“姨太太”,却见她正以相同的话术寻找着新的猎物,这一情节无疑是对欲望乃至整个象征秩序的嘲讽。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统摄之下,这部电影中的两个女性做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如太太,虽然偶有反抗,但始终受限于伦理道德,甘愿受婚姻的约束,走入世俗的幸福;另一种则看准了父权体系下,男女地位不平等之间所留下的空间,利用男性的欲望满足自身的欲望,实则仍被象征秩序所玩弄。可惜的是,这部电影所采取的立场也基本止于同情与嘲讽,未能更进一步探索象征秩序压抑之下的,更原初的欲望与幻象。
《不了情》同样上映于1947年,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太太万岁》基本以金钱为故事发展的驱动力,而《不了情》则以爱情为叙事核心。电影一开始的故事与英国名著《简·爱》十分相似,贫穷的家庭教师虞家茵(陈燕燕饰)进入富有的中年企业家夏宗豫(刘琼饰)家工作,担任夏宗豫女儿亭亭的家庭教师。在朝夕相处之中,虞家茵与男主人夏宗豫之间逐渐产生了爱情。然而此时,夏宗豫的太太——住在乡下的病女人突然出现,并在虞家茵面前宣誓主权。在道德与爱情之间纠葛的女主角最终选择了道德,远走厦门。因而,这实则是一个道德伦理战胜爱情,象征秩序打败欲望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出彩之处有二,一是在女主角犹豫之际,直接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两个虞家茵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个形象是幻象,代表着欲望、爱情与想象;一个是现实,代表着秩序与伦理。因而这里以直观的方式,将象征界与想象界置于同一空间当中,同时在对话当中打破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现实的虞家茵因为父亲曾经娶姨太太给母亲带来伤害,所以不愿意再做另一个家庭的第三者。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导致虞家茵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缺少来自父亲的“原初之爱”,而这种“爱”实则正是被象征秩序压抑之下的欲望;当虞家茵遇见夏宗豫——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时,这种压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并转变成象征秩序之下的爱情,获得了正当的名义。因而这里的对话,不仅是欲望与秩序的对话,更是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前的原初欲望以另一种形式进入了象征界中。不过,随着幻象的破灭,逾越也就此结束。这部电影另一个特别之处则在于,在《简·爱》中失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在这里获得了话语,并进入象征秩序,这未尝不是对于父权体系的不彻底的反叛。
总体而言,这两部电影的叙事框架虽然各有新意,却都未能进入更深层、更复杂的探讨。与之对应的,张爱玲的小说却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描摹。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与电影《太太万岁》同为一个男性与两个女性的三角恋故事,小说《色·戒》与电影《不了情》则同为底层女性与高层男性的婚外恋故事,然而在具体的呈现中,小说与电影大相径庭,这两篇小说呈现出的主体状态某种程度上都是“符号态”的。如前文所述,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与“象征态”体系独立于拉康的主体的三维世界划分。郭军认为,“符号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拉康在想象界与象征界之外提出的第三项——“不可能者”(the impossible)、“不可说者”(the ineffable),符号态中“是一些异质和非理性的因素,构成一股潜在的颠覆力量,时刻威胁着井然有序的句法,使理性的思维无法完全按自己的方式界说事物。”[6]更进一步来说,在艺术创作中,符号态的能动性得以发挥,“通过穿越象征态建立的分界输出符号态的能动性,艺术家的创作描摹出一种重生。通过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艺术家将一种不合群的冲动引入象征秩序。”[4]53这股冲动是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是本能的,原始的与非象征的,张爱玲的小说便是如此。
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与电影《太太万岁》相似,以一位男性的恋爱经历为故事主轴,却将叙事重心放在女性身上,但是两者的叙述过程与结果大相径庭。从过程上看,《太太万岁》讲述的实则是男主角面对婚姻时的选择,而《红玫瑰与白玫瑰》则可看作是男主角佟振保一生的性经历,这种叙述策略直接展露在小说中的三次身体书写中。第一处,佟振保在巴黎嫖娼,对于妓女身上气味的描写,“外国人身上往往比中国人多着点气味,这女人老是不放心,他看见她有意无意抬起手臂来,偏过头去闻一闻。衣服上,胳肢窝里喷了香水,贱价的香水与狐臭与汗酸气混合了,是使人不能忘记的异味。”[7]156-157而妓女对于自身气味的介意更让佟振保感到不舒服,因而,第一次的性经验对于佟振保来说并不是愉悦的,原因则是身体的不相契合;小说中第二次身体描写,则是佟振保与王娇蕊初见面时不经意的接触,“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7]162尽管两人的身体只是透过肥皂得到了间接的接触,情欲却已然萌发;第三次则是与佟振保婚后,孟烟鹂的便秘,“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尾纹。”[7]196人物百无聊赖之际对于身体的把玩某种程度亦直接点明了便秘背后的心理动因,正是性需求的无法满足导向了身体的病态。由这三处身体描写亦可得知,这篇小说中无论男女的感情与行为的,都是以身体需求为驱动力的。而婚姻非但未能成为限制,反而成为遵循性本能的保护伞,佟振保与王娇蕊的偷情几乎未受到婚姻的制约,而佟振保婚后更是开始频繁嫖娼,反倒是面对初恋玫瑰时,因为她是“正经女人”而无法与之发生性关系。因而,这篇小说所阐明的无疑正是“性”对婚姻伦理的冲击与颠覆。在最终走向上,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与电影《太太万岁》看似相同,内在意涵上却十分不同。电影《太太万岁》的结尾,丈夫回归家庭,这是合家欢式的,是以“家”为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胜利,是二元的;而小说的结尾,佟振保回到家中,继续生活,然而夫妻二人之间的嫌隙已经无法弥补,在“家”的秩序之下,“性”作为一种威胁性元素始终存在着,佟振保最终选择“做个好人”,看似是妥协,实则是斗争的延绵,是异质与多元。
类似的,小说《色·戒》与电影《不了情》虽然同是讲述未婚女子与已婚男子的婚外恋故事,但小说《色·戒》对于象征秩序的探讨,从“家”延伸至了“国”。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情感与直觉如何介入象征秩序并引起紊乱的故事。女主人公王佳芝作为一个特务,却“入戏太深”,爱上了汉奸头子易先生从而导致刺杀失败,自己也因此被杀。小说呈现了两种行为模式的对立,王佳芝遵循快感原则,她的结局由三重快感叠加而得:性的快感(权势是一种春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8]317);消费的快感(六克拉的粉红钻戒[8]316);表演的快感(在学校演爱国历史剧时是蹩脚的演员,在易先生面前做特务,却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8]319)。而易先生几乎与王佳芝完全相反,他的行为举止由“实用原则”主导,权力、秩序、政治立场高于私人情感与性快感。由于这种对立,王佳芝的出现本身便是对于象征秩序的打破。张爱玲对于这两种行事原则基本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小说的结尾中,昔日的太太们一如既往地闲话家常,“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8]324。紊乱与颠覆最终又归于日常,而日常之中,又充满着暧昧与含糊。与之相比,电影《不了情》的探讨则基本止于道德与情感的困境,象征秩序本身并未受到挑战,亦未有什么波澜。因而,无论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是《色·戒》,张爱玲的叙述都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式的。克里斯蒂娃在评述乔伊斯等人的作品时便提到,“通过揭开十九世紀遮盖在性欲之上的神秘面纱,弗洛伊德的发现表明了性欲在语言和社会,以及驱力和社会象征秩序之间的连结作用。”[4]65在张爱玲的这两篇小说中,“性”的描写(不只是性)正代表着这样一种驱动性的力量,横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中。而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亦可看作是一种诗性的革命语言,在社会秩序内“进行对抗社会秩序的实践。”[4]62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张爱玲编剧的这两部电影中,主体基本都是象征界统摄之下的“正常人”,在欲望纠葛中走入迷途,又在社会秩序的指引下回归正轨。而与之对应的两篇小说,虽然采取了类似的故事架构,主体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元性,理性不再是唯一法则,非理性与理性交锋,原初本能介入社会秩序,两者的斗争又在日常中绵延。
二、何以差异?
张爱玲从作家转型成为编剧与战后的时代氛围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婚姻关系,张爱玲在战后的上海成为“敏感”人物,文学事业亦受挫。也正在此时,张爱玲在柯灵的引介下结识桑弧导演,为文华电影公司创作了《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两部影片,成功进入影坛。因而,要考察这两部电影与张爱玲小说之間差异的成因,首先应关注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创作者本人在此时的转向;而在此之外,“电影”与“小说”作为媒介的不同,也对张爱玲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文的探讨也将从这两方面展开。
张爱玲以《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部作品实现从作家向编剧的转变,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市场化转型。这一点在张爱玲在《太太万岁》上映前夕所作的《<太太万岁>题记》一文中便可看出,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明确指出了电影与文学的差异。
文艺可以有少数人的文艺,电影这样东西可是不能给二三知己互相传观的。就连在试片室里看,空气都和在戏院里看不同,因为没有广大的观众。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马路英雄型的;他们勾肩搭背走着,说:“去看电影去。”我想着:“啊,是观众吗?”顿时生出几分敬意,同时好像他们陡然离我远了一大截子,我望着他们的后背,很觉得惆怅。[9]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张爱玲对待文学与电影秉持着不大相同的创作意图,因为电影受众之广与传播方式的不同,似乎势必要与观众更为亲近,也需要更加通俗化。然而对于这种自然而然的要求,张爱玲的态度又有所迟疑,她一方面希望能靠近观众,另一方面却又不免惆怅。因而她在这篇文章中同样提到,中国观众对于“传奇”的过分习惯,而《太太万岁》却是“浮世的悲欢”,是更日常化的。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创作心态,张爱玲在创作《太太万岁》时既保留了一定的文学性,同时又不免添加热闹的剧情,使整个故事维持在公俗良序的框架之下。
张爱玲创作意图的市场化转型也体现在电影上映前后的评价之中。在电影上映之前,时任《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副刊主编的洪深看完《<太太万岁>题记》,在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我等不及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 作家中的一人”[10]。然而,在电影上映之后,洪深却又以一篇《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问答》,猛烈批评这部电影。他虽然承认“作者是有才气的,所以有些地方确实是好玩,而卖座亦佳”,但是对于电影的内容,他十分不以为然,并一改此前之评价,“它不够成为‘高级喜剧’,因为高级喜剧应当是对人生的‘健全与清明的批评’Sane Sriticism”,他并指出,这部电影只有对“太太的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度的怜悯”,并对电影结尾“妥协”的结局提出大力批评,认为女主角陈思珍不像是民国出生的女性。[11]同日,《大公报》亦刊登了另一篇《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了<太太万岁>》与之对应,这篇文章同样对《太太万岁》予以批评,它先是指出,《太太万岁》的出轨主题实则是市场跟风行为,“电影老板们苦口婆心地一年总要拍上十部‘家花那有野花香,只怕野花不长久’的片子,这类戏是太太们欢迎,先生们赞成”。该文作者对于这种内容大加批判,并指责该片的创作者对“反动的火焰”袖手旁观。[12]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从创作意图到文艺界的评价,实则存在着两种矛盾,一则是市场的欢迎与批评界对于内容不够高级深刻的矛盾,另一则则是着眼于电影本身,是动荡的社会环境与电影内容的不问国事之间的矛盾。前者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当创作者选择面向更广大的受众时,便同时放弃了更为诗性、更为自由、超脱于象征秩序之外的表达;而后者却恰恰是张爱玲在电影中保留了一定的作者性之体现。在1944年的《童言无忌》中,她便说过,“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13]因而,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张爱玲对于政治的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是一贯的。张爱玲的市场化转向从结果上亦是成功的,当时便有报纸以《张爱玲埋头编剧——<不了情>剧本报酬六百万》为题刊文。[14]这篇报道指出,编剧《不了情》报酬的六百万足够支撑张爱玲半年以上的生活,可见张爱玲市场化之成功。总体而言,市场化的要求必不可免地影响了张爱玲的电影创作,从而使她的电影脱离了小说的非理性叙事模式,走向象征秩序内部的欲望叙事,这种转变既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亦是因为创作者本人在创作剧本时秉持着与小说不同的写作理念。
从创作内容来讲,张爱玲编剧的电影明显受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影响。张英进曾提到,郑树森认为张爱玲的剧作类似好莱坞经典的“神经喜剧”(Romantic Screwball Comedy),而神经喜剧介于高雅喜剧(high comedy)与低乘喜剧(low comedy)之间,高雅喜剧擅长以对话刻画人物;低乘喜剧则强调身体语言,神经喜剧吸取两者之所长。[16]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太太万岁》与《不了情》应当属于神经喜剧的范畴。而另一方面,据其弟张子静回忆,成为编剧之前的张爱玲已经是一位电影爱好者与影评人,[17]更有甚者,李欧梵推断,1940年的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可能启发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8]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喜剧作为经典好莱坞时代广受欢迎的一种创作类型,本身便建立在市场认可的基础之上,因而,当张爱玲在这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之下从事编剧创作时,亦不免走向好莱坞式的叙事模型,如张英进便指出,好莱坞浪漫喜剧习惯以“妥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中同样如此。[15]由此,张爱玲编剧的电影无法摆脱伦理家庭等母题的限制,从而走向颠覆与超越,亦是情有可原的。
综上,无论是创作意图,外部影响还是时代环境的制约,都是从张爱玲本人的创作转向出发并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分析的,是较为个性的。而除此以外,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文字与影像作为媒介,从生产到接受环节都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也影响着创作者的写作。
张爱玲小说与其编剧电影的差异或许可以用“蒙太奇”与“长镜头”这两种电影技法来做比拟。如前文所述,张爱玲在这一时期编剧的电影是好莱坞式的神经喜剧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而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对于蒙太奇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巴赞认为,“蒙太奇的运动可以是‘察觉不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经典影片中,这种情况最常见。在这些影片中,镜头的分切无非是为了按照一场戏的实际逻辑或戏剧性逻辑来分解事件。”[19]65与这种形式相对应,内容上这一时期的好莱坞喜剧通常是流畅的线性逻辑叙事,戏剧性强,熟练运用巧合等剧作方法,主题在伦理道德的范围之内,典型代表如《费城故事》《育婴奇谭》等。因而,受到好莱坞喜剧影响的张爱玲创作的《太太万岁》与《不了情》亦可以说是蒙太奇式的电影,《太太万岁》中对于巧合的设置便是典型的例子,电影中,女主角丈夫的妹妹与女主角的弟弟在水果店相遇,两人素不相识,为了买最后一包凤梨产生争执,随后镜头转到女主家中,两人再次见面,误会化解。这样的巧合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得以实现,既制造了笑点,亦成为两人感情的开端,是“欢喜冤家”式的浪漫爱情喜剧中常用的手法。而在《不了情》中,蒙太奇的手法运用使得女主与自己的幻象被放置在同一空间中,进而通过两人的争执展现矛盾的激烈。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蒙太奇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拼接,如巴赞所言,蒙太奇“帮助电影用各种方法诠释再现的事件,并强加给观众”[19]66。由此也可看出,蒙太奇既具有欺骗性,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与之对应,蒙太奇式的电影在内容上常常是逻辑的,理性的,是精准又巧妙的现实再现。因而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剧作内容基本停留在象征秩序之内的矛盾调和,而没有走向更为感性,更为深层次的颠覆。
而张爱玲的小说,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长镜头”式的,如学者冯勤所言,“张爱玲‘影像’化叙事独特的中国魅力,首先展现在长镜头的运动,……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那从容含蓄的固定长镜头不但有利于意象的营造及其内涵的发掘,而且颇能充分自然地展示东方的情韵”[20]。他认为张爱玲小说的“长镜头”式书写是受到电影艺术影响后的有意为之,这一点笔者认为仍然有待商榷。无论是長镜头理论的提出还是法国新浪潮的实践,在时间上都晚于张爱玲创作高峰期的1940年代,而当时尽管长镜头已经逐渐被运用,但冯勤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文献来佐证这种实践对于张爱玲的影响。不过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本文,确实呈现出与长镜头相似的特征。比如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和王娇蕊在车厢中重遇的场景:“振保在一个妇人身边坐下,原有个孩子坐在他位子上,妇人不经意地抱过孩子去,振保倒没留心她,却是笃保,坐在那边,呀了一声,欠身向这里勾了勾头。振保这才认得是娇蕊,比前胖了,但也没有如当初担忧的,胖到痴肥的程度”[7]190。随后,两人便展开谈话,而公交车亦继续前行。这种对于固定空间内流动中的生活状态的捕捉,与侯孝贤电影中常见的展示列车行进的长镜头十分相似,《恋恋风尘》与《南国,再见南国》中都有多处这样的镜头。因而,在这种“类长镜头”式的书写中,张爱玲的小说展现出了与其电影截然不同的特质,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直觉的,非理性的对于真实和日常的捕捉,而这也正符合巴赞对于摄影本体论的认知,“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19]13。然而与此同时,正是由于摄影“本质上的客观性”[19]11,电影与小说得以区分。这种“客观”一方面使得张爱玲小说中极为细腻的心理描写无法合适地以镜头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镜头天然客观地展示原貌,因而无法留白,亦无法隐藏。如小说《色·戒》的结尾,易先生在喧笑声中走了出去,小说中这一人物就此隐匿。然而电影如果要呈现这一动作,必定先要展示出人物的存在,而人物的存在必然又伴随着某种状态与气场。李安导演的电影版《色戒》在呈现这一场景时,演员的表演加上导演的镜头调度便直接使易先生这一人物带上了一层悲情色彩,而小说中此处却是留白的。因而,镜头之下是无法隐藏的,然而正是这些隐藏之处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超越与颠覆。
以上是从作品生成的角度进行差异成因的分析,而在作品接受上,小说与电影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观看电影某种程度上是象征秩序主导下制造出的一次对于非象征秩序的模拟。劳拉·穆尔维便指出,好莱坞的主流电影满足了观众的双重快感,一重是纯粹的观看癖的满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的一部分;另一重则是对于观看癖自恋的满足,电影在这里承担了镜像的功能,观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仿佛回到了拉康所言的镜像阶段,是对自我构建的一次模拟。[21]吴琼的观点与之类似,他指出,电影院正是一种拉康式的阅读,他更特别强调电影院观影所带来的集体性与匿名性对于满足观众快感的意义,观众“在对观影情境及影像的认同中、在认同的快感中来尽情享用自己的欲望,享用由观影情境和影像氛围所激发的无意识症状”[22]。因而,可以说,看电影这一行为可以说是电影生产者、观看者与传播者共同参与的一种对于象征秩序的“虚拟”的颠覆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质上仍然是为了化解非象征秩序主导下的非理性、符号态等对于象征秩序的动摇。张爱玲编剧的这两部电影自然亦符合这一普遍性的特点。而张爱玲的小说虽然面向大众,但亦带有“超越通俗”的创作自觉,其小说“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又有作者的创新期待”[23]。由此,接受角度上电影与小说的差异,或许也是影响张爱玲小说与电影差异的原因之一。
大体而言,张爱玲的小说与电影在内容风格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既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创作者本人的转向,亦源于电影与小说作为截然不同的创作载体,在生成与接受上的差异。
結语
综合以上,本文大体采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从拉康的“象征界”到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对张爱玲的小说与电影进行了两两对比,指出张爱玲的电影对于象征秩序的遵循,而小说却以符号态超越了象征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张爱玲本人在创作小说与电影时的不同理念,亦是因为电影与小说作为不同的媒介,在传播与接受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别。
参考文献:
[1]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63.
[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娃自选集[M].赵英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M].张颖,王小姣,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5]斯拉沃热·齐泽克.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M].穆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郭军.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与革命[J].外国文学研究,2003(01).
[7]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张爱玲.色·戒[M]//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N].大公报(上海版),1947-12-03(009).
[10]洪深.编后记[N].大公报(上海版),1947-12-03(009).
[11]洪深.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问答[N].大公报(上海版),1948-01-07(009).
[12]莘薤.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了《太太万岁》[N].大公报(上海版),1948-01-07(009).
[13]张爱玲.童言无忌[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03.
[14]文海.张爱玲埋头编剧,《不了情》剧本报酬六百万[N].新上海,1947.
[15]张英进.穿越文字与影像的边界: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性别、类型与表演[J].易前良,译.当代电影,2009(11).
[16]张楚.张爱玲编剧电影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3.
[17]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18]李欧梵.从《魂断蓝桥》到《倾城之恋》和《一曲难忘》[J].书城,2006(05).
[19]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20]冯勤.论“影像”化叙事在海派小说中的本土化走向——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为中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21]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M]//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40-642.
[22]吴琼.电影院:一种拉康式的阅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
[23]石晶晶.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上海四十年代张爱玲文学传奇[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04).
收稿日期:2021-09-30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发掘、整理与资源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62)。
作者简介:王一平,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张体坤,文学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 Ailing's Novels and Their Film Adaptations Viewed from Long Live My Missis and Love without End
WANG Yiping/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ZHANG tikun/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311,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ctional world portrayed by the writer ZHANG Ailing with words as the carrier and the film world presented by the screenwriter ZHANG Ailing with images as the carrier. ZHANG Ailing's films shows a symbolic world as what Lacan stated that is in binary opposition based on orders and rules. However, ZHANG Ailing's fictional world is pluralistic, disorderly and “semiotic”.
Key words:ZHANG Ailing; symbol; the semiotic; Long Live My Missis; Love withou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