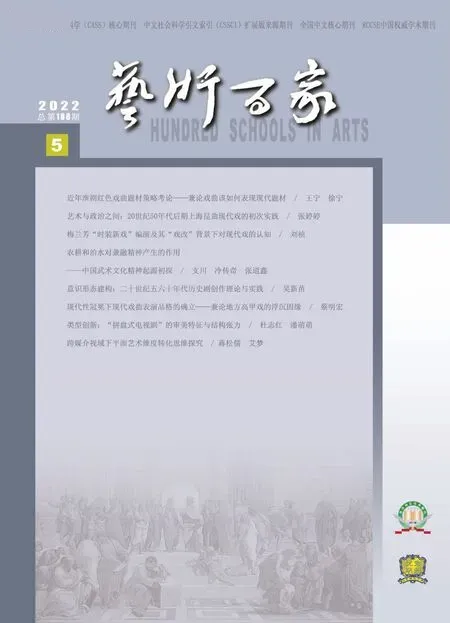波兰电影学派文化调性的离调显现∗
岳大为,丁帜扬
(哈尔滨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在欧洲,波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电影大国,波兰电影学派(Polish Film School)是世界电影艺术流派中的重要一支。 波兰电影述说波兰民族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特殊回忆,以勇于直面真实又不失人文关怀的视角描绘波兰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沉稳坚毅,娓娓道来,展现了波兰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特质。 同时,执着的探求精神赋予影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波兰电影学派大多选择淡化历史背景,使观众能透过层层迷雾体认普通人的境遇变化,并试图带领观众挖掘生活背后的复杂真相和人性深处的奥秘。基于此,文章研究波兰电影文化调性的离调过程,探讨其内涵在历史变迁中的发展路径。 “离调”一词原本是音乐学中的概念,指在单一调性范围内调性扩张和功能增强的手段,简而言之,就是指音乐作品暂时离开一下原调的调性,到达新调后不在新调上巩固和发展,只是用这种短暂的偏离简单过渡,继而回到原有调性上,离调的目的是揭示和展现作品原本调性中更为深刻的内涵意蕴。[1]12笔者将波兰电影离调显现的过程抽象为“本—失—寻—归”四个阶段,一步步探寻波兰电影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责任感与自尊感:原本的波兰精神
波兰历史上有太多的名字值得铭记,如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发现钋和镭两种新元素的居里夫人、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的肖邦等。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足以看出这个民族的智慧,无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波兰都为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波兰的历史甚至长过俄罗斯等大国,11 世纪至15 世纪是其国力强盛阶段,16 世纪至17 世纪初可谓是巅峰时期,国土面积的扩张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波兰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漫长的历史,让自尊感和优越感深深刻入这个国家的基因中,然而波兰的巅峰时代随着俄国等国家的崛起而结束。
因为这一段辉煌的民族历史,波兰在欧洲有着独特的文化身份。 波兰电影产业的萌芽时间甚至早于法国,在卢米埃尔兄弟之前,波兰人就发明了“运动起来的照片”。 20 世纪10 年代末到30 年代末,波兰更是迎来了电影发展的“小高峰”,单是影院数量就从100 多家增长到700 家左右。 尽管国力衰微,但由于受宗教文化熏陶和民族尊严影响,波兰一直有着大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20 世纪30 年代是波兰电影最初的“本真”阶段(表1),在这期间波兰电影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左翼先锋派电影。 这类电影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追求电影的社会功用,在加强戏剧冲突的同时希望能够充分反映社会问题。 第二类是哲学性电影。 这类题材聚焦人类生存等一系列“终极命题”,希望通过深度思考来回答人类群体普遍面临的根本问题,或追问人类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第三类是商业电影。 波兰电影从“本真”阶段开始就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通过解构这些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波兰民族精神的内核——责任感与自尊感。 这两个简单的词无法将波兰精神尽数表现,但就电影而言,波兰精神中的责任感与自尊感在银幕上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表1 20 世纪30 年代的波兰电影
二、“迷兰”探路:波兰电影学派的萌芽与借镜
20 世纪40 年代中期之后,“迷失于弥漫烟雾中的波兰”应该是对波兰不失真实的诗意描写。 一场战争几乎毁灭了刚刚发展起来的波兰电影事业,这时的波兰电影就像一个“走失的孩子”,原本有高贵的血统、辉煌的历史和既定的发展路线,却因为几番灭国复国的悲怆记忆和战争的硝烟,只能在迷失中寻找方向。 波兰电影捡拾起属于自己民族的记忆,波兰电影学派的文化内核在此发端,在效仿和借镜中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
二战的尘嚣过后,20 世纪30 年代留下的电影院中,能够正常放映电影的仅剩5 家。 此后20 余年,波兰电影一直在摸索中前进。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后,国际影坛上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电影潮流——波兰电影学派。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数出生于20 世纪20 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战争毁掉了他们的青春,所以他们坚定不移地试图将战争的负面影响通过电影作品表现出来。 波兰电影学派的创作初衷是帮助人们坦然面对战争,用自身独有的艺术视角和极尽细腻的创作手法将历史进行人文化复现。
1957 年,波兰电影学派正式进入大家的视野并引发了国内外的热烈关注与探讨。 波兰电影学派的艺术家们开始拒绝接受社会现实主义及其所属文化内容,认为其不能代表客观现实和民族文化,同时,开始追求另一个目标,即让艺术能够脱离过度的浪漫主义和民族神话,这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影评人齐格蒙特·卡乌任尼斯基曾说:“这是一次打击,它针对的是不计一切代价成为英雄的大众理想,针对的是盲目爱国主义的邪教异端。”在一个刚刚结束战争且还未对其进行探讨的国家,波兰电影学派制作的电影使公众开始参与一种深刻的情感对话,这种对话对公众而言具有治疗作用。 这些电影展现不远的过去发生的故事,探讨波兰人的灵性以及他们的前途等议题。
(一)波兰电影学派的诞生
波兰在二战期间未能发行一部故事片,就连之前建立起的电影业基础也几乎损耗殆尽。 1956 年10月,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上台,宣布取消此前因为崇拜斯大林而发布的一系列国家条令和崇拜政策,波兰开始“去斯大林化”,波兰电影的生产体制由此开始发生变化。 波兰电影人将创作视角投向二战及其带来的后续反应,希望通过电影来揭露二战后的现实,在这段时间,波兰电影进入短暂的成长时期。 波兰电影学派的诞生固然与政治契机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但也绝非“灵光一现”。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波兰有一批左翼电影人就曾提出“电影必须对社会有益”的口号,并组织建立“创作社”小组,然而直到1956 年哥穆尔卡上台,他们的这一构想才得以付诸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电影先驱安杰伊·蒙克和安杰伊·瓦伊达都曾在“创作社”小组供职。 自此,波兰电影学派发源并逐渐开枝散叶,波兰电影举起了属于自己的大旗,讴歌人民的曲折抗争经历、爱国主义情怀和不屈品格。
《下水道》(Kanał,1957)由安杰伊·瓦伊达执导,是一部二战题材的悲剧电影,也是波兰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 影片将华沙起义作为背景,写尽起义中战士们的百态。 它的上映引起了波兰人民的热议与追捧。 这部影片的复杂历史背景和敏感题材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观众想要知道作者挑选了什么样的事情并运用了怎样的手法来进行艺术化创作,这是影片大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影片历史内涵丰富,艺术造诣高深。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瓦伊达可能是为了规避审查而让电影风格含蓄内敛,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瓦伊达的创作思考是在灵魂层面对人的拷问。 影片并未大力歌颂或鼓吹起义军的勇敢,也并未大尺度地批判苏联当局,相反,介于两者间的“透气”使电影的悲剧性冲突拓展了思考空间,从而深化了影片的价值。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却能让观众感受到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对人文主义关怀、历史真实一面的探讨和刺激观众思考这些要素一样不少。 1957 年,《下水道》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引发了人们对波兰电影学派的讨论,波兰电影正式开启了新纪元,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别样表达方式获得了国际电影圈的关注。[2]12-13《下水道》是瓦伊达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波兰电影学派温情脉脉地将悲悯细腻的人文情怀融入电影当中,洋洋洒洒地将浪漫主义加入音乐当中。 现实主义风格清楚地向观众揭露了历史真相:苏联的政治出卖固然是将波兰人民推向深渊的黑手,但波兰民族独有的“波兰癖性”——无可奈何却又盲目的爱国主义也使这个国家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迈向战争的熔炉。 《下水道》的主题并不是讴歌,与此相反,它是用相对客观、流畅简洁的镜头记录战争背后真实的流血牺牲。 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片不同,瓦伊达更关注个体,关注他们丧失信仰时的无措以及在战争中受到的精神创伤。 影片中,将士们在生理性死亡之前精神支柱已经崩塌,因为在下水道中,面对阴郁、恶劣的环境,生理性死亡与精神崩溃并无区别。 (图1)

图1 《下水道》中人们被困近景镜头
(二)波兰电影学派的多元启示
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国家、灭国后受到文化侵蚀、毗邻大国、后殖民时代的复杂历史等因素使波兰电影受其他国家电影的影响较深。 波兰在二战后的废墟中重新捡拾起电影产业,开始效仿和借鉴电影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其中借鉴最多的是西欧和美国。 波兰电影学派奠基者瓦伊达曾表示,《忠勇之家》 (Mrs. Miniver,1942)、《桂河大桥》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纽伦堡大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1961)等美国影片开拓了波兰电影的视野。 此外,诸多意大利电影,如《铁路战斗队》(The Battle of the Rails,1946)、《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1945)等,仿佛唤醒了波兰人民的记忆,大量电影人开始以波兰人特有的视角对战争进行记录和创作。 起初的效仿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例如受意大利现实主义的影响,波兰电影圈内兴起了一波“扛机热”,主要是记录人民生活的真实处境。 亚历山大·福特的影片《巴尔斯卡五少年》(Five from Barska Street,1954)就是受这种创作原则影响的典型作品,影片没有秉持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是选用一种流畅自然的风格和成熟老练的手法。 这部电影一举夺得戛纳电影节奖项,亚历山大·福特在国际电影圈内风头一时无两。 之后,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执导的不少影片,也都是对战争年代祖国景象的记录、再现或追忆。 平实真诚的创作方式让波兰电影逐渐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为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波兰电影学派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波兰电影学派的离调特性初现
严厉的“斯大林模式”被取消后,波兰人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开始急切要求文艺作品可以反映真实的人民生活,直面时代问题。 当时的波兰电影人也开始希望使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来揭露现实,他们认为国家机器操控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粉饰现实、遮蔽真相、压迫人民。 导演扬·科特、亚历山大·福特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人道主义”“粉饰现实”等词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代名词。 恰好当时一批高才生从国际著名电影学府罗兹电影学院毕业,其中就有瓦伊达等人。 他们创作的电影不同于之前的电影,多为先锋题材,多数都在表达自我对社会的思考。 冷战背景下,处于苏联势力下的波兰民族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波兰失国复国的碎片化历史,为波兰电影提供了新视角,波兰电影由此开启了诗意、阴郁、自省的文化调性,这对民族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有开创意义。
波兰电影内容多元、题材多样,简单地界定波兰电影学派难免有失偏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现重塑了战后人民的精神与信念,对表现波兰人民意志和推动波兰艺术发展都有里程碑式意义,波兰也确实需要波兰电影学派作为一双眼睛来注视、回望整个民族历史。 在又一次政治高压之下,波兰电影业被限制,而波兰电影人坚决反抗,不断在银幕上尝试各种新的可能,他们的作品中充满波兰精神。
三、在演绎中深化:道德焦虑电影
瓦伊达凭借《下水道》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之后,深沉阴郁、画面暗淡、色彩寡淡成为波兰电影学派的标志性特点。 波兰电影学派探讨社会道德文化与民族同一性问题,为他们之后的“道德焦虑电影”打下了基础。 他们还原其他国家对波兰犯下的罪行,记录战后波兰人民的真实处境。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并非刻意强调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不幸,而是客观、流畅、简洁地讲述事实,用一双温情脉脉的眼眸注视国家和民族的艰辛历程。
在波兰电影学派的发展历程中,“道德焦虑电影”以其丰富的哲学思考和醇厚的人文情感颇受观众青睐,是对波兰精神的又一次升华。 20 世纪70 年代中叶到80 年代初,波兰电影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立足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并提出思考。 1979年,瓦伊达在波兰电影节上公开提出“道德焦虑电影”概念,这次公开发言也正式为波兰电影正名——记录现实与历史是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创作“道德焦虑电影”的主要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呈现了对个体的关注,表现复杂丰富的人性特点,用几近极端的处境来讨论道德层面的进退两难,以及个体在面对选择时的进退维谷,深剖“焦虑”。 作为导演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就生活在国家集权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双重伦理环境中,个体与社会、生存与死亡、集权与民主、真实与浮华之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在电影当中得到了别样审视与思考。
(一)批判后极权主义
“道德焦虑电影”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特点,是对国家机器统治下社会真实被掩盖的批判。 捷克作家哈维尔提出的后极权主义,有别于与传统理解中的“集权”“专制”,波兰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好契合后极权主义。 波兰人民接收到的信息无一不经过粉饰与伪造,工人阶级本是被解放的最大群体,实际上却被资本家奴役,阶层分化致使底层人民饱受欺凌和压迫,毫无自由和公平可言。 一个充满谎言、水深火热并且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致使波兰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道德焦虑电影”便是以这些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批判当局,针砭时弊。 电影《大理石人》 (Czlowiek z marmuru,1977)、《没有麻醉》(Bez znieczulenia,1978)等都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揭露当局欺骗人民、歪曲事实、篡改历史。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
瓦伊达在1976 年就已完成《大理石人》(图2)的创作,1987 年该片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影片中,主人公涅什卡决定将当时的社会劳模布尔卡特作为自己毕业作品的拍摄对象,为了搞清楚劳模传奇的一生,涅什卡采访了多个相关人物,渐渐勾勒出布尔卡特立体丰满的形象。 因其独特别致的创作手法,许多电影人一度将《大理石人》和《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相提并论。 这部影片从侧面表现了20 世纪50 年代波兰社会的政治氛围,是东欧地区首部控诉斯大林主义的影片。 瓦伊达为了让当局批准他拍摄《大理石人》,经历了长达13 年的奋斗,电影首映结束时,全体波兰观众自发起立唱波兰国歌。 在波兰,《大理石人》一票难求,票价甚至被炒至原价的10 倍以上,3 个月的观影人次就已突破 300万,是20 世纪70 年代波兰最负盛名的影片之一。《大理石人》风格朴实明快,内容针砭时弊,叙事手法的运用更是堪称典范,剧中涅什卡四处奔走、采访调查,打破了时空逻辑上的叙事顺序。 现如今的电影中不乏采用这种叙事策略的佳作,然而40 多年前的《大理石人》能够自然运用这一策略,在制造悬念的同时让观众逐渐抽丝剥茧、拨云见日,实为难得。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影片使用了黑白色调,具有波兰电影特有的寡淡意味,使观众更能回味历史。

图2 《大理石人》剧照
《大理石人》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斯大林模式”下被欺侮、被伤害的波兰人民的生活图景:善良的波兰人在二战结束之后无私奉献,为祖国的复兴建设添砖加瓦,但这样的赤子之心却被当局扭曲。 这立马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人们从《大理石人》中看到的不是涅什卡的毕业设计,而是千万个布尔卡特被政府欺骗乃至伤害。 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被唤醒,波兰民众一方面为欺骗者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愚昧和无力感到羞愧。 《大理石人》内容深刻,它没有选择当时政治风向下的“拍脑袋”填鸭式政教题材,而是一部摆脱创作窠臼、让观众独立思考的优秀作品。
四、破困再现:波兰电影学派的离调终归
20 世纪90 年代初,东欧剧变的引线在波兰点燃,电影是受政治影响较大的艺术门类之一,波兰电影产业受到波及,发生了巨大改变。 历史上,“危”和“机”总是并存。 当时,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好像对波兰电影的发展不那么有利,但对波兰电影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再也没有那样几近严苛的政治审查制度来影响波兰电影的创作风向了。 同时,波兰电影业由国家行为变为市场行为。 内部,国家经济衰退,外部,波兰影业受到好莱坞影业的排挤,内忧外患使波兰电影一度陷入低迷,增长乏力,多重问题交织。 (表2)波兰电影学派再一次对民族电影业有了新的审视,在摸索中逐渐寻得一条新路径。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条新路径是具备波兰民族特色的电影发展之路,让波兰电影以全新的风貌迈入新世纪。

表2 1989 年后波兰电影产量
1989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波兰经历了东欧剧变、社会转型,波兰电影业开始市场化和商业化转向,波兰电影学派面临困境。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波兰电影产业刚起步转型,效益几乎降至历史冰点,为数不多的在映影片中有半数是美国影片。 一部分走投无路的波兰电影人为求生存,开始对美国影片进行简陋粗糙的模仿,然而最终票房惨淡,这使很多波兰电影人对自由市场下的民族电影失去希望。 对电影而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不是件容易的事,组织混乱、争夺少量的国家补贴、法律法规缺失,这些使本身就四分五裂的波兰电影圈陷入瘫痪状态。[3]82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使面临崩溃的电影业得以维持是波兰政治体制改革初期的最大成就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波兰人民对政治持既关心又讨厌的态度,一度有电影批判家认为波兰将有一批要被“禁言”的政治电影现世,但最终他们期待的结果未能出现。 基耶斯洛夫斯基1981 年拍摄的政治题材电影《盲目的机遇》(Blind Chance,1981)公映后赢得了不错的反响,影片运用的“三段式”剪辑手法被后来的许多影片效仿。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波兰电影摆脱了政治囹圄却又陷入经济桎梏,有波兰导演表示这一时期的波兰电影再一次失去了自由。
20 世纪90 年代初,在外漂泊了9 年的瓦伊达回到了这片曾经熟悉、现在陌生的土地。 觉得陌生是因为他发现“政治系列电影”已然消逝,体制改革和各方复杂的势力交错使波兰电影业面临几乎“无片产出”的处境。 在这样的恶劣背景下,瓦伊达依旧坚持创作,全力拉动波兰电影产业这块巨石。 凭借高深的艺术造诣和熟练的拍摄手法,瓦伊达执导的《塔杜斯先生》(Pan Tadeusz,1999)大放异彩,票房是当时其他热门电影的几倍。 此外,像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样的导演,也努力寻找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点,以便把波兰电影推向国际,其拍摄的影片真实记录了波兰人民的生活景象,深邃的思想颇受赞誉。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波兰电影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蹒跚前进,转型过后的电影市场把第一次机遇给了商业电影。 1992 年,瓦迪斯瓦夫·帕西科夫斯基拍摄了电影《狗》(Dods,1992),这部电影的上映使波兰国内观众和电影人重燃了对国产电影的信心,对转型过后艰难度日的波兰国产电影有着里程碑式意义。继《狗》之后,资本敏锐地察觉到商业电影在波兰的发展前景,恰巧当时波兰国内的商业电影并未受到重视,因此《杀手》(Killer,1997)等一系列商业电影陆续面世,为之后波兰商业电影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特别是1993 年至1994 年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执导的系列剧情片《蓝白红三部曲》(Trois couleurs)使波兰乃至全世界观众大开眼界,影片呈现的和平、自由、博爱精神让电影主题意蕴深刻。 这一时期的商业电影帮助波兰电影业度过了行业寒冬。
到了21 世纪,波兰电影不再因恶劣的外部环境而忧虑,而是慢慢沉淀,不断探索民族底蕴,寻找属于波兰民族的风格,后来其凭借温情款款又不失悲怆深邃地讲述民族故事逐渐崭露头角。 2000 年,波兰电影学派奠基者瓦伊达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这不仅是对一位电影创作者的肯定,还标志着波兰电影学派的成熟。 之后,一批优秀的波兰电影,如《修女艾达》(Ida,2013)、《盗走达芬奇》(Vinci,2008)、《基督圣体》(Corpus Christi,2019)等,不断显现波兰电影学派独有的离调式风格。[4]92-97
从迷失到模仿,再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波兰电影逐渐形成了波兰风格。 虽然波兰电影学派的巅峰时代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之久,但波兰电影学派独有的离调性一直延续至今。 波兰电影创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体制上的不断调整让波兰电影产量有所增长,并且使波兰电影出现了新的创作趋向——视角越发具象,关注人物及其在历史中的独特价值。
(一)管窥波兰万象的叙事电影
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执导的《修女艾达》在第27 届欧洲电影奖颁奖典礼上一次性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风头一时无两。 作品在独特视角之下,用含蓄的手法探讨个人在历史事件中是自觉参与还是被动卷入的问题。 《修女艾达》中,艾达的沉默内敛和颓废严肃其实都反映了战后国民的精神创伤、信仰危机和焦虑内心。
叙事电影《修女艾达》具有米兰·昆德拉式“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深邃哲思。 亲人骤逝、阅尽人间霜华的主人公艾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选择? 影片的整体叙事恰恰可以体现波兰电影学派颇令人意外的逆转,乃至颠覆。 一方面,在毫无自由的修道院中,人物在沉默内敛的“封闭式”空间里生活,每时每刻都想挣脱牢笼。 另一方面,主人公离开了修道院,追寻自己所要的自由。 艾达尝试了俗世的生活,但她很快就发觉这种生活沉闷而平庸,信仰似乎成了艾达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的终极救赎。 值得一提的是,以一种突破禁锢的方式表现灵魂救赎也是晚近中国电影学派的常用方式之一。[5]34-41《修女艾达》表现了基督教教义中人必须不断认识自己的观点,这种自我认知的历程可能是一次信仰的逃脱,再回首时,信仰就又一次成为返璞归真的终点。
无论是否是刻意而为之,影片最后那种宁静祥和的气息让观众感受到信仰区别于俗世欢愉的美感,这也预示着艾达最终没有回归凡人的生活,而是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重回信仰的教堂。 上帝的美在于宽容和不语,宗教并不歧视艾达的出身并领养了她,让她忘却前生,身心安宁。 影片的结局一改往日波兰传统电影的叙事方法,艾达的人生道路就像离调一样,最终回到起点,但却是新的“起点”,当艾达坚定地走回修道院时,她最终皈依信仰。
(二)喜剧犯罪题材电影
犯罪题材影片《盗走达芬奇》是尤利斯·马休斯基的代表作。 该片将场景设置在监狱,采用黑白回忆与彩色现实交叉的蒙太奇手法。 这部电影从各个角度展现了波兰人民欢迎全世界的态度。 影片逻辑严密,故事围绕一幅真迹和两幅赝品的去向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从电影色彩美学的角度看,影片处处向观众展现了克拉科夫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如著名的红色双塔建筑圣玛丽大教堂,具有独特的欧洲文艺气息。 和一般的战争片不同,片中波兰特有的彩色屋顶和尖塔随处可见,导演以一种热诚的姿态,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风光无限秀美、旅游资源丰富的波兰。 影片滤镜色彩丰富,赓续了波兰电影独有的画面美感,也保持了波兰电影含蓄、内敛、幽默、流畅、细节充实的特点。 同时,这一部冷色调的黑色喜剧也进一步创新,给看惯了忧郁基调的观众换了口味。
(三)宗教题材电影
很多人会将波兰这个前苏维埃阵营国家归类为无宗教国家或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家,然而现实恰恰相反。 早在公元966 年,波兰就正式接受拉丁礼仪,自那时起,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影响波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波兰电影学派的诸多电影中显现的多愁善感意味,正是受天主教哑忍和原宥教义影响,再加上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因此波兰电影呈现浓烈的消极、阴郁风格,蕴含无可奈何的牺牲精神。
克日什托夫·扎努西是波兰电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拍摄的战争题材电影《仁慈之心》( ̇Zycie za ̇zycie,1991)就是一部展现波兰宗教文化的优秀电影。 故事发生在1941 年纳粹入侵波兰时期,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有人逃脱,所以军官迁怒于一位少年,少年被吓得浑身瘫软,另一位也被关在集中营中的修士科尔伯见此,决定代替这个少年接受惩罚。 电影并未刻意渲染恐怖氛围,而是使用给人温暖感觉的暖色调,简明流畅地讲述了一个陌生人用自己的“死”换取另一个陌生人“生”的故事。[6]76-77在我们看来,故事中的修士科尔伯虽然伟大,但选择不免有些荒唐,实际上,在基督教教义中,科尔伯的牺牲以及种种隐忍行为都是为了赎罪,是虔诚的、干净的。
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波兰电影《基督圣体》,蕴含丰富的主体性和悲悯的人文关怀。 从宗教角度讲,这个故事试图通过主人公这个有着“流氓”“罪犯”“神父”等多重身份的人物来告诉观众,一个人信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真心向善,是否能用干净通透的目光看待人世。 影片涉及宗教与人性问题,就宗教而言是宽恕和救赎,就人性而言是真诚与善念。 从逻辑调性来分析,不管是宗教、教会、神明,还是人类社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宽恕精神。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过去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可能是想以后能够成为一位善良平凡的人。 影片探讨是否该给犯错之人重生的机会,最终借丹尼尔之口说出“宽恕是爱”,并表示任何人,哪怕是有罪的人都可以当神父,甚至可以当得很好。 然而在人性的视角之下,只要你犯过罪,那么有罪的烙印将跟随你一生。 观众可以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某种人,做好某件事。 影片最后小镇发生严重车祸的情节,参考了2010 年发生的“波兰总统专机失事事件”,这场事故也是政变。 导演有感于这起意外对波兰政局及人心的影响,所以在《基督圣体》中借用车祸对小镇人民造成伤害的情况来呼吁人们重新团结起来。 这样的开放式结局、离调性显现更凸显了主题的深刻含义,促使当下大众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
五、结语
当下波兰电影备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很多电影制作者用相似的手法创作。 波兰电影学派在离调过程中受到许多阻碍,但后来因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的内容而受到观众青睐。 波兰精神的延续使波兰电影在国内乃至国际影坛大放异彩,波兰电影学派的内核不断得以延续与再现。 虽然战争让波兰电影学派在前期发展受阻,但遭受苦难的灵魂却为波兰电影插上了翅膀,仅从电影角度来说,“德国人毁了波兰,却救了波兰电影”。 此后波兰电影蓬勃发展,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让世界看到了波兰故事和波兰精神。
世界电影在迅速发展,现今各国电影已不能满足于仅追求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寻得平衡。 许多人认为现在的波兰电影逐渐丢失了本真的民族文化,转而以好莱坞模式为创作风向标。 如果说波兰电影是简单跟风,那是以偏概全,但这种情况应当引起警惕。 当今的时代趋势时刻提醒所有国家去探索影视作品创作的新可能,如利用VR、元宇宙技术等等。 电影内容方面,如何在紧跟国际浪潮的同时融通民族文化内核,并在银幕上进行深入阐发,是当下每位电影人都要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