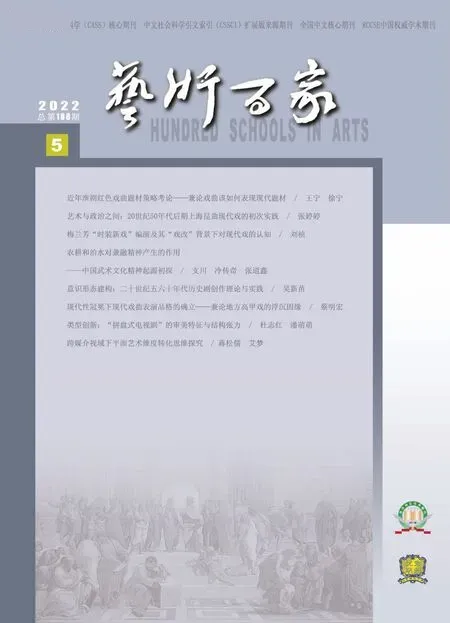吸收、融合与再造∗
——《中国形象——全国优秀青年雕塑家作品展》简评
薛问问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9 月9 日,由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宁波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形象——全国优秀青年雕塑家作品展”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闳约美术馆开展。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0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本次巡展面向社会共征集了600 余件青年雕塑家作品,组委会通过多轮讨论,最终选出了近百件(含特邀)代表作品。
雕塑作品对中国形象自觉地表达,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共同诞生。 事实上这个现象并非仅限国内,在19 世纪,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均通过古典复兴的方式强调自身文化身份与符号,将其视为国家文化与民族天才的象征。 我们似乎可以说,19世纪就是将艺术形式与广义的政治、历史、文化自觉建立联系的时代。 这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20 世纪初那批留洋学习雕刻绘画的中国学子们。 中国本土的现代雕塑肇始于上海美专1920 年创立的“雕塑科”,初步确立了雕塑学科融通中西的学术框架。 其后留洋学子们陆续归国,在他们的创作中已有将中国传统雕塑语言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风格进行结合的成功尝试,不少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已成为今天无法绕过的经典,如《轰炸》《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 20 世纪50 年代后苏联现实主义、80 年代西方现代主义,以及千年之交当代艺术的引进、传播与交流,一次又一次丰富了中国本土现代雕塑的视角和语法。
本次展览上的特邀作品——吴为山先生的《黄宾虹》(图1)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雕塑主流①创作近20 年的重要转向——重视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挖掘,传统艺术中意境与造型语素的再次激活。 中国雕塑乃至艺术与西方雕塑不同,后者的“本体”意识较强,即这门艺术相对其他艺术媒介,其所不可取代之处。 然后一代代艺术家在实践中将这个边界,以及边界所围绕的内核明确下来。 这是一种自觉的校准,围绕在逐渐被发展出来的“本体”轴心周围,出现周期性的返回轴心的运动,但真正遇到诸如现代主义这样需要突破僵局的情况时,又会处处针对性地反对这个核心。 而中国雕塑则一方面一直有着“塑绘同源”的传统,绘画雕塑乃至书法不分家,另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某个对象之时往往会指向这个对象外部更大的世界,以勾连出想象与意蕴的空间,《黄宾虹》便是这种美学的代表性体现。

图1 《黄宾虹》,吴为山,铸铜,190×65×65cm
作品仿佛是画家晚年画面中的山石化成了这位大师的形象,廓形凝练又富有变化,就像是浓墨勾勒出的山形;长袍肌理嶙峋,宛如巨石,让人联想到大师用墨“黑、密、厚、重”的特点;塑痕酷似石头的质地,又有“以点作皴” 的 通 感。 塑 像厚重的同时又丰富多彩、丘壑空灵,整体给人的物质感觉正如石涛所云,“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和大师的艺术高度相得益彰。
这件作品浑然一体的外形与物质感或许也让人想起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 的《巴尔扎克》,但其引导出的联想层面不尽相同:《巴尔扎克》所建立的世界是作家凌晨起身后裹着睡袍在院中散步构思的精神世界;而吴为山的这件作品承上启下,运用“大写意”的手法,人物传神生动,集墨色、笔意、物质感与境界于一身,不仅通过肖像搭建起黄宾虹本人的绘画世界与中国传统书画的关联,也链接了观者对天地自然的感知。 这是由具象的造型出发,但又超越造型本身,“意”字为先,呈现了中国艺术中独特的世界观与境界。 以吴先生为代表的雕塑大家为青年一代的创作者们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奠定了本次展览注重自身历史文化主体性,同时兼容并蓄的总基调。 参展雕塑作品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本土雕塑语言的进一步探索
西方雕塑与中国雕塑很大的区别在于其对立体与纵深空间的强调,这种传统源自希腊艺术盛期,在文艺复兴时进一步明确。 因而西方雕塑中的圆雕往往需要环绕着多角度观看,而中国雕塑并不强调作为欣赏者的主体需要去绕着一个客体看,这在中国人的艺术观中似乎太“刻意”了,世界应当是在与“我”的交互关系中逐渐呈现——就像观赏中国画时,随着卷轴的缓缓打开,观者的身心也在景中移动,作品与人形成一种对等的主体间关系。 这种艺术观以及中国传统雕塑绘画间紧密的联系,使得本土雕塑相对西方雕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平面性”。
这种特点在近年来被艺术家越发自觉地利用,如作品《七君子》,它直接呈现出来自中国古代雕塑的平面性特征。 雕塑与绘画水乳交融的传统来自武梁祠石刻,来自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来自大足石刻石窟变相,来自山西元明两代的悬塑等。 《七君子》中的人物造型简单质朴,蕴含着古拙之意,又恰好与老照片的年代调性吻合,身体的衣纹刻画简洁利落,让人联想起石窟雕刻中率性的刀法。 其背后的山石在“造境”的同时也运用了传统语素风格,与人物共同构成一幅凸显高洁之气的画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的铮铮风骨纳入中国人薪火相传的精神中。
这片山石不仅在风格上继承了传统绘画、寺观壁塑中的山石表现手法,其形状构思也颇为巧妙,似硝烟,似隐有金戈铁马之声,举重若轻地烘托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氛围。 作品中的人物来自真实历史照片,在看似“简化”又糅入了比照片更多的联想空间与信息量。 形式从来不仅仅是形式,而是连带着背后一系列的文化指向与时空联想,就像根须连带出其所扎根的土壤。 准确巧妙调动的形式语言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杠杆中的支点,往往能够暗示更大的信息量,作品繁简之间的张力也由此形成:形式虽“小”,却能容纳一个巨大又赋予人无限联想的平行世界。
雕塑是三维的艺术,但作品的三维纵深厚度与作品质量并无直接因果关联,在早年间的一些批评话语中,中国雕塑中的平面性被看作消极因素,而今天越来越多的雕塑家开始将其作为积极因素,无疑得益于对传统语汇的深入研究与文化自信。 在西方景与人共构的浮雕作品中,对景的使用逻辑与中国雕塑区别甚大,而西方圆雕中的景更是囿于集中式构图与比例等方面的范式约束而凤毛麟角,因而中国雕塑这种与绘画共生所形成的美学结晶就有其独到的价值了。
二、跨媒介语境下的塑绘同源传统
跨媒介这一提法在艺术界已经至少有十余年的热度,这本不是个新事物:古代中西方绝大多数的雕塑都是上彩的,在一件来自现实世界形象的作品上赋予色彩、纹理等等本就是人类最朴素与自然的认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绘画雕塑间的关系往往是互相依存、在效果上互相增幅,界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尤其在一些庙宇、教堂等古代大型工程中,多种手段并用,壁画、浮雕、雕塑在建筑中并存共生、相互烘托的情况屡见不鲜。 而媒介间的区别与独立性、各个媒介的所谓排他的“本体”则是近现代出现的观念。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彭汉钦的作品《石榴花开》(图2)像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1892—1942)那张著名的油画《美国哥特式》一样,呈现了某种典型气质。 不同的是《美国哥特式》中的刻板、保守、严谨在这里变为老两口在面对镜头合影时的朴实、拘谨与羞涩。 与《七君子》相似,《石榴花开》也是一件让人联想到照片,又不同于照片媒介表现力的作品。 若观众从侧面看这件作品,会发现人物的大腿长度被缩短了,这种类似传统寺观造像的压缩处理手法是为了减弱在正面观看时的透视纵深感,使得作品看起来具有一种“肖像画”的感觉。 艺术家的手法纯熟而洗练,糅塑绘于一体,将绘画中的笔触、色彩与含蓄而精到的体积刻画整合得天衣无缝,因此《石榴花开》不仅是一件好雕塑,在多处的绘画性表现中甚至能看出四川一带帅气而入微的油画风格。

图2 《石榴花开》,彭汉钦,树脂着色,190×110×95cm
绘画与雕塑的跨媒介在今天的语境下其实已经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属于广义的认知结构层面:即在雕塑中借用、呈现绘画的知觉结构,以跨媒介、融媒界的方式形成新的感知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宾虹》的物质性带来的墨色通感、塑痕肌理与水墨画皴法间的通感,以及《七君子》中自觉的平面性与强调绘画感的构图,均是广义上的塑绘同源。 第二层意思则是像作品《石榴花开》与传统着色雕塑那样,将绘画与雕塑两种媒介直接糅合。
中西方的古代着色雕塑,均是各自的绘画性高度发展之前的产物,西方雕塑与绘画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分家,而中国文人画与雕塑造像则在宋代开始分家,这两次的转折无疑推进了绘画与雕塑两个媒介更加专门化的发展,但也使得一些巨大的可能性就此湮没。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雕塑和绘画甚至长期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如“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分列‘塑作’(包括装銮)、‘木雕’两门,与人物等其他画科并列”[1]10,这不仅体现了后世艺术观的变化,也说明了今人对雕塑作品的感知、评价、创作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少当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将这一断裂的传统重新延续,并使之向前发展,这也指出一种可能:对作品的感知先天是整体性的,天然感知对应的应当是融媒介。 抛弃表面涂绘的雕塑是后来的历史,并非天经地义。 在绘画雕塑两个媒介均高度发展的今天,再次将它们进行恰到好处地融合,非但不损及各自的“本体”,更可能有相得益彰的化学反应,《石榴花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多重风格的自觉融合
中国艺术中的境界不一定只属于文人化的世界,在李煊峰的作品《八女投江》(图3)中,境界也可以凝练为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 构图中八人互相依靠,憔悴而疲惫的身体仍顽强矗立,她们不仅代表了千千万万抗争的同胞,褴褛的衣衫、不屈的形象也象征着国破山河在的大地,脚下的大江惊涛拍岸,让这八位女战士宛如中流砥柱。 作品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写意手法结合,铸就了一座民族在苦难中抗争,受尽屈辱而不屈服的纪念碑。 这些语言风格并未停留在形式本身,而是恰如其分地还原了历史情境:衣着、面部塑痕的肌理与质感在现实层面上如实体现了东北抗联的艰难困苦,我们甚至能感觉这些战士脸颊上的硝烟和灰尘;最左侧姑娘身上已破破烂烂的衣衫仿佛树皮,进一步建立起林中游击战的情景想象。

图3 《八女投江》,李煊峰,树脂,190×45×90cm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作品的构成语言与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融合:人物的头部总体形成一条水平线,靠近中轴线位置略有变化——两位姑娘托起一位已经负伤的战士,艺术家将她处理为眼部受伤的状态,面部的模糊化使其虽处于最高点,但形象并不过分突出,而是与其余几人形成一个金字塔形、整体感极强的群像。 作品实现了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与高度的形式自洽间的平衡。 另一件的风格融合则更为明显,这便是邓柯的《凝融——抗击冰雪灾害》(图4)。第一眼看即是现实主义与构成主义的结合,人物放大的双手,夸张的动态与体积起伏又让人联想到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那些团块感与力度十足的版画和雕塑作品。 珂勒惠支是糅合了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大师,邓柯这组人物的表现主义风格并不十分明显,但相似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冰与人两个三角形团块之间明—暗、光洁—褶皱的对比。 刻画强烈的衣纹起伏仿佛在水中浸泡过,给人以阴、湿、冷的身体感知,更好地凸显了作品主题发生的环境。

图4 《凝融——抗击冰雪灾害》,邓柯,树脂,200×100×130cm
以这两件作品为代表,本次展览上的多件现实主义作品均吸收了新古典主义中的构图骨式或现代主义的构成元素,将现实元素组织在理性、清晰、形式感突出的作品框架中,说明红色题材、现实题材在形式多样、强调现代感的今天仍拥有巨大的可能性。
四、重新激活的材料与物质性
一般认为,主题性雕塑往往更强调“文以载道”,需要依托人物形象向公众传递具体事件或人物所代表的精神,故多在构图、造型层面变化;而在雕塑艺术独特的材料与物质性层面的探索则付之阙如。
本次展览中的作品《新青年》(图5)则打破了这一既定认知,并且其关于这些命题的探索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以降的材料试验,更多来自中国雕塑传统中非常独特的一脉——以不同物质质感间的通感与错觉体验为突出语言的明清案头赏器摆件。

图5 《新青年》,钱亮,玉石、锔钉,70×25×28cm
传统社会中的士人、文人审美逐渐塑造了一个围绕文人意趣的文化生态:从书法绘画到案头赏器、文房四宝、家具建筑至庭院与园林的布置,每个环节都与另一个环节发生着关联。 赏器摆件作为这个系统中的节点之一,因具有一定实用功能,或重视工艺,或作者身份是工匠等等原因,被认为与纯艺术作品有别。 以往多将这类作品纳入工艺美术,不放在中国雕塑范畴中讨论。 但这些物件所蕴含的影射、通感、观念、错觉等一系列综合艺术感知效果,所构建的意境与情境,所撬动的想象与深层的文化指向等都比狭义的工艺美术要丰富得多。 它们往往像一个模块,能够与案头可能存在的别的摆件、笔墨纸砚等共同构成一个“场域”。 这个场域蕴含着人和自然、人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关联,方寸之间便能勾连出审美空间的巨大能量,毫无疑问,能够被称为艺术品。
《新青年》继承的便是这个传统——一本石料雕刻出的书。 它并未取材某一期杂志具体的封面,而是将知识与启蒙化作一个书籍的纪念碑。粗粝厚重的封面应和了我们对那个年代厚重而澎湃的历史感受,悠悠百年激荡的中国革命,似乎已结晶化成为了一个沉甸甸的实体,书体虽然已皱,依然硬朗倔强地挺立,仿佛丰碑,又似百折不挠的革命者的精神。 书页洁白,好像打开后随时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赏器摆件讲究趣味,通过一种材料模拟另一种材料的质感,营造视、触觉方面的幻觉与错觉,构建的是文人审美与精神世界,其中一些下品停留在眼花缭乱的工艺炫技对官能的刺激上,这也使得此类作品中的大多数不被看作艺术品。 而《新青年》遵循了文人赏玩之物的感知效应与材料工艺语言,但又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它有趣味,但超越了玩赏趣味;尺寸不大,但量感十足;有幻觉与错觉,但构建的是人间历史与沧桑;有工艺技巧,但自觉而克制。 背面完全保留石材原貌,正面的“粗制”手法运用物质的视触觉与石材的重量与坚硬赋予记忆以质感。 这件作品好似相对抽象的历史真正化作了物质形态,呈现在了观者的面前。
理论家孙振华指出:“西方现代雕塑中的材料,常常是纯材料的, 它针对的是剔除文学性、剔除情节性后对纯物质材料的追求;而中国当代雕塑家在进行材料探索的时候,常常渗透着观念的因素,它们常常是有意味的,有情感象征意味和特定意义指向的。”[2]29这种意味、情感象征和特定的意义指向,或许一定程度上来自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物质材料的态度与看法。 进而中国雕塑中这种独到的材料与物质处理方式,乃至其背后折射出的艺术感知方式,显然能够为当代雕塑注入新的活力并进一步拓展其外延。
五、结语
本文无法尽现这次展览的作品全貌,仅从几个角度分析,旨在管窥近年雕塑创作中呈现的新趋势。 中国现代雕塑诞生刚超100 年,但在这短短1 个世纪的时间中却可谓变动不居:一方面缘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我们需要自觉地挖掘与延续传统雕塑的优势以求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西方雕塑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次次影响着本土的艺术家;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号召文艺为人民服务,而艺术的形式自律与更新又难免会曲高和寡;雕塑既有极强的公共性,但其媒介特征又决定了其与民众的距离相较绘画、摄影、电影等姊妹艺术还是远了一些。 幸运的是,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美育传承集体记忆、滋养人民心灵、培育社会美德的作用也越发凸显;国家与市场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助推艺术多元面貌的形成,也使得艺术为大众服务与艺术家个性化的探索表达可以兼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形象”就具有了两层内涵:一为现实层面的形象,即万千同胞在生活劳作中的面貌与精神气质;二为艺术家们从社会不同视角产生的切身感受,进而形成的艺术作品的视觉、风格形象。 后者既从属于前者,又有其独特之处,二者合二为一,形成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生成的“图像证史”——其丰富性、调动起的感知与共情实现了比文字更为饱满与立体的效果。
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优秀艺术作品诞生的极好土壤,本次展览体现了青年一代雕塑家们的实践,他们能够继承发扬传统、兼容并蓄、推陈出新。 这些作品表现了多元的中国形象:英模、普通劳动者、文化、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象征等等,在凸显主题的同时又回应与发展了一系列雕塑艺术媒介自身的可能性,拓展了审美感知经验。 “以图像证文献不能证之史,以图像激发舍弃图像而不能发之史观。”[3]37这些关乎“中国形象”的作品生动地体现着如何看待自身、在表达与言说中对自我的再塑造,以及这些自我表达中的语法。 这三者相互作用,随时代变迁,既有稳定持久的内核,亦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扩大了我们理解自身历史的视野与范畴。
① “‘主流’指官方大型展览,重要的学术研究、学院的主干教学以及艺术评价体系。”见吴为山《写意雕塑的文化意义》,《美术观察》2020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