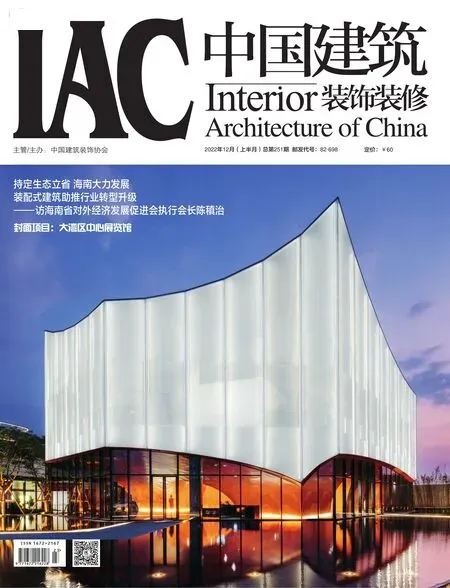我国书法与古代建筑的艺术共通性研究
董惠贤 董怀建
1 我国书法与古代建筑的结构共通性
1.1 我国书法结构
书法五体分别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书法中的点画是最细节的部分,也就是笔画的问题,由各种笔画组合成一个字,是书法最基本的单位。
自我国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便证明了点画的存在,表现为多线条和点画少的特征。例如,秦代小篆作品《峄山刻石》、《会稽山刻石》及《琅玡台刻石》等,都表现出了以线条为主的现象。直至东汉时期,点画开始大量出现,如东汉隶书《曹全碑》等,同时书法隶变也加速了点画的形成。可以说,随着五种书法字体的基本成型,点画的演变也基本完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点画是书法的基本结构,犹如梁、柱、屋顶等是我国建筑的基本结构[1]。
1.2 我国古代建筑结构
我国古代建筑由各种不同结构组合而成,结构种类复杂多样,主要建筑构件包括屋顶、墙壁、台基、柱、栏杆、铺地、瓦件、梁架结构以及斗拱等,通过科学合理的组合,构建出传统的建筑形式。一个建筑的构成必然是主客结构的构成,主客结构内容越丰富,其建筑表现效果就越复杂华丽。我国古代建筑最基本的主体结构,如柱、梁架结构、榫卯等构件形成的木构建筑结构,能够起到巩固与支撑建筑整体和形成特定结构的作用;而建筑的客体部分则起到装饰空间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功能,如鸱吻、脊兽和门窗等构件。
我国早期的建筑形态可见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中,在考古现场发现了大量木杆捆扎的技术和早期的榫铆结构等。这就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将木杆直接竖向插入土中,并在其上搭建木地板和遮风挡雨的草棚屋顶的架空干栏式建筑雏形。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我国商代的夯土技术趋向成熟,木构技术也有明显的发展。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就被认为可能是商初成汤都城—西毫的宫殿遗址,是至今发现我国最早的规模较大的木构夯土建筑。直至战国时代,生产工具进入铁器时代,木构建筑体系基本形成。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建筑以木构建筑体系为主,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融入各类风格样式,适应自然规律,从而不断发展与创新。
1.3 结构共通性
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与书法的演变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共同或交错进行的,书法点画的美感特质与建筑结构存在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4 个方面。第一,书法的横向与纵向笔画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体现在建筑中梁架结构与柱子的相互支撑。第二,书法中撇和捺笔画的飞动感在建筑中表现为延展的坡屋顶,撇和捺尾端拖出来的部分犹如屋顶脊梁尾端的飞檐结构。第三,书法中带有跳动感的点的笔画与建筑屋顶的装饰构件也极为相似,如鸱吻、脊兽等。第四,书法中精神外耀的钩笔画、体现婉转之力的转笔画和体现果敢之力的折笔画,与建筑落成后呈现给观者的直接心灵感受相似。
南宋姜夔在《读书谱》一书中写道:“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味。”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对生命与处世原则问题的看法,表现了人与社会、自然相和谐的特征。由此可见,人的审美追求在书法点画与古代建筑结构上都展现了共性的审美思想,也表达了共性的艺术审美特征。
2 我国书法与古代建筑的特征共通性
2.1 我国书法的特征
第一,从篆书的形态特征来看,金文展现出与自然物象相连、字形大小不一以及上下左右融合成整体的现象。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章法亦复落落。”这句话道尽了金文的形态特征。而小篆则与之有所不同,从秦代李斯的《峄山刻石》和清代吴让之的篆书中都可以发现其文字特征如同我国古代建筑般具有对称美感和轴线特质[2]。
第二,从隶书的形态特征来看,具有横平竖直和蚕头燕尾等现象,展现了如建筑梁架结构般的平稳之气和屋脊飞檐的震动之感,东汉的《张迁碑》和《朝侯小子残碑》等可以直观看出。
第三,楷书的美感特征可见于多数作品中。例如,智永的楷书作品《千字文》表现出飘逸灵动与俊秀之感,北魏《张猛龙碑额》表达了清钢与雄伟的刀感,唐代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展现了严谨、标准式的间架结构关系等。
第四,行书的特征开始偏向于动态,如王献之飞龙走凤般的《地黄汤帖》。
第五,从草书的作品中可见其特征,如王羲之的今草《采菊帖》和怀素的狂草《自叙帖》,其中展现的狂放洒脱之情,将草书的美感特征表达得十分明显[3]。
除了从书法五体的特征进行分析,也可从整体、局部、历史发展演变以及形式等不同方面探讨书法独有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从整体来看,书法字形结构表现出因人而异的特点,人的个性对其影响也会融于其中。从局部来看,书法字体呈现出八面拱心的特质,以东汉的《乙瑛碑》为例,可看出每个字都有一个字心,四面八方的笔势聚向中心,并有向上升腾之感。从历史发展和书法形式的角度来看,表现出五种字体之间相互杂糅的“越界”现象。例如,王羲之的《二谢帖》将草书和行书相融合;颜真卿的《送裴将军诗帖》将草书、行书、楷书的笔画相融合;更为突出的是郑板桥的《行书论书轴》将五种字体相互杂糅[4]。不同字体之间用笔结构、章法与节奏等互相参取、吸收、融会贯通的现象十分常见。沈增植的《海日楼丛札》中写道:“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唐孙过庭的《书谱》中曾言:“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书法形体的美感特质,表现了行中有“象”的特质,不同字的字形、体势、点画、线条等,都可创造出不同的意象。这种意象可以抽象为一幅画、一个建筑,甚至是流动的水流;这样的物象,可以是趋于动态的,近乎舞蹈的,也可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从书法五体来看,还是从整体、局部、历史发展等视角来看,都可以找到书法与古代建筑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
2.2 我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我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7 个方面。
第一,翼展的屋顶造型,即翼角翘起,犹如鸟雀腾飞的翅膀一般,将飞腾之感注入屋檐中,“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露远”形象地表达了此意。
第二,拥有坚实的建筑台基,且可通过台基的不同尺度反映出建筑的等级。近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先生曾指出,如同人双足的台基承托着似若人身的屋身和宛若人头颅的屋顶,相互组合形成如“人体结构”一般的建筑,这正是我国古代建筑特有的三段式特征。
第三,我国古代建筑的装饰部件和木装修,其建筑正面多展现为玲珑剔透的木刻造型,如前廊、勾栏、门窗、隔扇等虚实的空间结构,再如鸱吻、瓦当等结构部件。我国传统木装修无论在工艺技术还是在艺术造型上都具有极高的造诣,体现了木装修在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古代建筑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第四,建筑群主要由多重院落组成,正所谓“庭院深几许,侯门深似海”正是其真实写照。多重院落是我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空间封闭,具有内向型,其中也暗含了封建儒家思想的影响。
第五,在建筑色彩使用上有一定的原则,如白色的台基,黄色、绿色或蓝色的屋瓦等。自西周以来,色彩就具有区分等级、贵贱、高低的用途。例如,春秋时期的建筑护栏,梁上和墙上就有朱红、青、黄、白、黑五色描绘组合的彩绘。这五色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而且在后世的不断发展演变中,青、红、白、黑、黄五色还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中五方位和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大神兽及四兽之长的黄龙。
第六,建筑平面展现出整齐对称式和自由多变式,所有的宫殿、寺庙、坟墓、衙署和书院等基本上都采用对称式布局,仅有极少数南方庭院会采用自由自由多变式布局模式。
第七,由于古人在石结构力学特性上的认知不足,在古建筑中出现了仿木石结构的建筑。木构架由立柱和横梁组成“间”字构架,在建筑中起到主要的承重作用。
梁思成先生在建筑的艺术性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曾说:“看中国建筑就像看一幅卷轴画,我们打开画面是慢慢展开的,一点一点地才能完整地把这幅画所表达的空间感觉出来。”正如游览北京故宫一般,沿中轴线先从端门出发,经午门,跨内金水桥,穿太和门,感受三大殿的雄伟壮阔;过乾清门,参观交泰殿;再到坤宁门,经天一门、承光门、顺贞门,最后穿过神武门,这便是一个逐渐展开卷轴画的过程。中轴线笔直、简洁,却绝不单调;沿中轴线布置的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宫殿群令原本生硬的空间具有音乐般的节奏感,将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展现的淋漓尽致。
2.3 特征共通性
通过分析我国的书法特征与古代建筑特征,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艺术共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5 个方面。第一,篆书呈现出的对称之感与古代建筑整齐对称的平面布局相吻合。第二,建筑翼展的屋顶造型和间架结构与隶书中的蚕头燕尾和横向延展、竖向拉伸的结构相呼应。第三,草书和行书具有的灵活多变、飘逸飞舞之感,与古代建筑自由多变式的平面布局相似。第四,书法的八面拱心现象与建筑平面呈现轴线与中心性相互关联。第五,书法五体相互杂糅互参的特质与古建筑融合佛教元素、地方特色的现象极为相似。此外,二者还有很多特质共通性。例如,书法中的“计黑当白”与古建筑的虚实现象也有所关联,更与阴阳观念相联系。
3 我国书法与古代建筑的思想共通性
3.1 正德思想
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尚书》中写道:“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话表达了古代为人做事的三原则。从古代建筑方面来看,“正德”是指统治者不能将所有财富用于营造宫殿,要做万民的表率;“利用”是指建造建筑有利于万民,便于日常生活;“厚生”是指无论土木工程还是水利工程,皆要有利于百姓的生活与繁衍生息[5]。而这三点原则的核心就是要运用“惟和”的观念,不要有过激的违逆法则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建筑最高准则追求的是建造者(一般指君王)主体的道德美,要求便于百姓使用,并不过分强调建筑的永久性。正德思想不仅影响帝王贵族,对文人、百姓也有教化意义。
我国书法也不例外。最早的甲骨文内容主要是卜辞、颂德等玄学,与道德教化有关。经过后世发展,书法的日常应用扩展到多方面,如简牍、帛书、器物、石刻以及日常书信等,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与书法相关联,也与政治、法律、哲学、文学以及道德等领域相关联。在考古发掘的多数文物中,都与皇家颂德和文人书卷所表达的归隐田林或报效国家的情操等思想相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经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不断发展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其核心的正德思想并未改变。
3.2 阴阳思想和大壮、适形思想
直接影响我国书法与建筑的思想还有很多,如阴阳风水的理念,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我国古代建筑讲究追求大壮与适形的观念,大壮是指建筑要有震撼人心、让人景仰与畏惧的特点,但更多的则体现为等级制度及有主有次的礼制观念;适形是指在尺度与规模上追求适宜和谐,同时保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理念在书法中也有所展现。大壮思想主要体现在书法的主要笔画与次要笔画结构上,主要笔画起到的支撑整体的作用,如“书”字的竖向笔画、“或”字的钩笔画和“大”的横向笔画等。适形思想体现在书法文字笔画组成都要遵循适宜的尺度与比例,如进行合理的留白。由此可见,我国哲学思想对于书法和古代建筑等文化艺术形式的影响十分深远。
4 结语
我国书法艺术与传统建筑一直作为与人们活动有关的对象而存在,它们相互交织,和合共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传统建筑与书法艺术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影响下,在各自领域发展出了个性特征与共性特征,从精神含义到物象表现,从整体到局部,从过去到现在,不断相互发展与变化,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独有的文化产物[6]。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人居环境的美也是各种艺术的美的综合集成,包括书法、文学、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当然也包括建筑。必须要从艺术精华中提炼中国美学精神。”本文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逐步深层次分析位于影响物象表面背后的思想理念,并由此进入以主体观照和感悟为核心的又一个艺术审美共通维度。
——识记“己”“已”“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