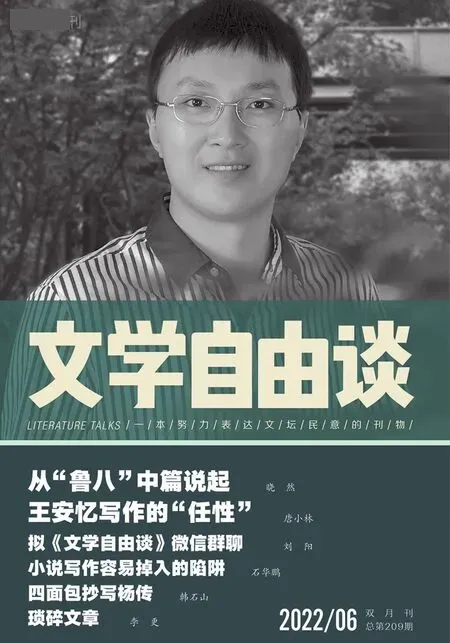舒文治小说的重与轻
□南 翔
舒文治是我湖南小老乡,他自1988年从学堂走向社会,就落地湘东北之汨罗——这里恰是我母亲的老家。已经九十八岁的老母亲,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跟随我父亲沿着粤汉铁路,一路南下,此后一直在铁路线上盘桓辗转,虽然七八十年翻然过往,母亲回家省亲的次数,掰着手指头也能数得过来,现如今发苍苍而视茫茫,却是一口乡音未改。
我以为,一个小说作者,几乎无法仅凭普通话而不染指任何一种方言写作——如果这种判断大致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赣方言是我虚构写作的资源之一。此外,还有一种资源就是来自我的“母语”(母亲家乡的语言),概因我安徽滁州籍的父亲离开家乡之后, 便讲一口普通话,虽然耳灵者还能听得出我父亲原籍的口音,他却从未在方言词语表达上给我哪怕最低限度的文学滋养。
我对文治充溢着湘方言,准确地说是汨罗方言的小说创作,怀着一种相互矛盾的心情。一则,希望其更为浓郁一些,以形成更为彪炳的特色,我可从中感受与汲取湘方言的养分——我从来觉得湘赣两省,若以方言表达而论,湘方言占据的优势十分明显,赣方言进入小说,迄少成功的范例。此是否与近代以来,湘人多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相关?他们分别在立德、立功的同时,也无法不把“立言”铺陈到四面八方,包括“娭毑”“堂客”这样冷僻的称谓,也录入了一本普通词典,进入到寻常百姓的视野。二则,我多少有些担心,文治的方言探勘耕耘,虽然未必是前无古人,却毕竟世易“言”移,现如今是网络语言的压倒性态势,如大雨瓢泼,似雷电连绵,譬如一个“内卷”才露头多久,便成燎原之势。还包括所向披靡的“鸡娃”、“社死”、“躺平”、“凡尔赛”……况且,任一地域包括城乡,方言其实一直都在变化着,年轻人与长者对同一语词的使用,音调及内涵都在潜移生变。明乎此,再来看文治的孤守,就多少隐含了别一种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段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我最早读到的是文治的一本评论集《远游的开始》,为一种精明而不失诚恳的表述感到诧异,以为一个案牍劳形的政务官岗位,有此耕耘,便见不俗。岂知他不甘就此盘桓,之后小说如打靶场的箭矢频发。此前读过文治上下两册的小说集《永生策划师》,那里面缤纷的语态,传奇的人性和故事的虚实,缠绕而摇曳,吐露出蛇信子一般的诱惑与凶险,突显出一位湘东北作家不管不顾的野心与个性。近读他发表在《芙蓉》第四期上的中篇《忍者飞飏》,得到的结论与古之殷侯相若,他是铁定一心:宁作我。
国人对“忍者”一词的了解,主要是1984年发行的“美国风”的漫画,以及三年后的漫画电视版。若是溯源,忍者是日本特有的一种特殊职业,“忍”即“隐”,有汉语词汇“隐忍”,简言之就是在古代日本一种受过特殊机构施以特殊“忍术训练”而产生出来的特战杀手、特战间谍。忍者,原本只是一种对于“忍术修炼者”的称呼,而某些自成派系的“忍术修炼者”本身就拥有众多门下弟子。
如此看来,作者的主人公取绰号“忍者”,便与读者所知的忍者渊源,有一种互文的关联了。文治将理论与创作打通,前面的“忍者”意味着坚守一隅、注重内收、寻求突击,后面的“飞飏”则意味着通过语言的法术达便而为轻逸。“犹如重物漂在昏暗的水面上”(但丁《神曲·天堂篇》)——如何在小说中解决重与轻的难题,这是作者孜孜以求的攻伐。概而言之,重与轻,实与虚,紧张与灵动,匍匐与飞扬……都是有出息的小说家落笔必佩的审美项链。这部中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既恣意又受绊,形同戴着镣铐跳舞。可为了有节制地宣泄一位忍者——逃亡者的憋屈、无奈与挣扎,还有恍兮惚兮的无穷的梦境——那是时时醉酒也无法置换的自我抽离,在此,第一人称的优势便呈现出来了——尽管我对第一人称写作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不止一次劝告一位热爱写作的研究生,多尝试用第三人称写作,以避免克制不住的自我情感倾诉。
“窗外,是一处与梦最为接近的地方,也可视为梦的一处产房。若说好莱坞是美国的梦工厂,那横店就是我们的梦工厂。我在横店一言难尽,白天,我得用手养活自己;夜间,我多用于做梦,鼠标和键盘是我的筑梦工具,我在写一个电视剧本《忍者神印》。”——这是三重的互文,一重是扶桑国源头的忍者,二是现实的隐忍者“我”,三是还想以自身经历与感受撰写一个相关忍者的电视剧本。覆盖其上的就是在梦工厂日复一日,编织着真实又迷离的梦境,究其实,一个隐姓埋名、慌不择途的文化人,在一个造梦之地,干着搬抬装卸,偶尔客串一些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不是店小二,便是过路人,总之不出贩夫走卒之辈,混得一日三餐。与“我”一道在这里混日子的还有老马、四郎……就这样,一个1990年代毕业于某师院地理教育专业的前诗人,早已把当年的一点诗情画意抛到了九霄云外,如今不仅与一些蓄意复仇的酒肉穿肠之徒为伍,还要日夜忍受思亲之苦,缧绁之忧,扳本之累——即便听到一句近似乡音清都话,都不免心惊肉跳,两股战栗。
“我”之所以成为横店沦落人,到底是相关对平淡教书生涯的不甘?抑或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总有一番出位抟浪的冲动?“我欠了清都一百九十七个人的债,其中不乏亲戚、同学、朋友、熟人,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我本意,不,我的本意是个深渊,至少,当初我没打算骗他们,我想借鸡生蛋,我的心思和很多人一样,都放在借鸡上,没心思琢磨生出的蛋怎么都是金蛋,要是寡鸡蛋怎么办?我老家将不能孵出鸡崽的鸡蛋叫做寡鸡蛋。我被一种想发财的心思抓住了,有如鬼扯腿——照我老家的说法,一个人一旦被鬼扯腿,他不死也要脱身皮。”究其实,投资、入股、分红,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无数不甘贫瘠与平庸者美丽如月的画饼。在此画饼的召唤下,类似“我”这样的小股东算是食物链中的中下层,噬人者也被人反噬。“背后的大股东,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直是团迷雾。”大大小小的股东数百之众,既有县府官员,也有花圈店的小老板,“我”尚未来得及厘清来龙去脉,就被打入另册了。
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经线是一位教师剑走偏锋、集资获罪之后的败走,纬线是隐忍在他乡的鼹鼠一般的生活。作者的意图并非在于藉此展现人心的叵测,也不止于警醒投资出位者的噩梦,更集中的一点,或在于通过一个亡命者的心理写实与活动轨迹,呈现一个冰冷又暖热的人间常识:不用担惊受怕的生活才真实而美好。当中风的父亲卧床在床不能事其亲,当女儿铃铃在睡梦中哭醒不能抚其颊,当可怜的老婆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不能护其身……一个男人的脸面与灵魂一道,成了风干焦脆之物,存留价值存疑。
作者活泛的措辞、不涉油滑的调侃与恰到好处的方言土语,将一个原本并不新鲜的故事,讲得惟妙惟肖,抽茧剥丝,甚是灵动。
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其实写什么不是写语言呢?不过搁在小说,语言的作用如雨后日晕,一圈一圈地放大了。文治的语言表达是有个性和魅力的。如:我娘家人逼我,债主们逼我,你咯不晓得好歹的野猪也逼我,再逼,我老子洗屁股嫁人,和你一刀两断,阳寒波,我说得出做得到,你晓得我性格。——活现了一位湘女的热辣。我读一些作家作品,包括一些熟练的写手,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不脱作家一个人的言语,如同“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沈从文语)。
又如:我有点想她,在想她的向度上会出现摇晃感,我要的就是这个,两个人的摇摇晃晃。我们曾有约定,彼此不问来历与家庭,我要她喊我冲哥,我给她取名阿斯敏,相互不知底细,心照不宣,身体更好“对食”。若是她回来了,我会用清都方言狠狠“作酱”她。“作酱”一词多义,可以指打情骂俏,可以指吃饱了无事生非,也可以指发酵之物达到膨胀之时,还可以指某种几近通神的手艺,而我和阿斯敏,用我老家话来形容,不过是“作肉酱”。——有意象也有铺陈,有谐谑也有一本正经。
还如:一房烟雾里,无数张脸朝我涌来,他们被置于我脑海中的放影机里,快进或快退,回闪或定格,独影或重影:老婆的脸、玲子的脸、老母老父的脸、仓宝的脸、骆远的脸、胥承望的脸、岳老师的脸、米副行长的脸、骆老师夫妇入棺的脸……他们是脸的海啸,瞬间将我淹没。——一句“脸的海啸”,将无数沧桑,一网兜尽。
文字的表达是艰窘的,它没有画面的斑斓,没有旋律的悠扬,没有月光的婀娜,没有日头的辉煌。
文字的表达又是幸运的,它有山道的崎岖,它有川流的婉转,它有跋涉的艰辛,它有登顶的狂欢。
汨罗经久流淌着一条滥觞于江西修水的汨罗江,两千四百年前,一位行吟江畔并纵身一跃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捧出了《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华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代诗人余光中曾来到汨罗江畔祭祀屈原,诗中写道:“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他用“蓝墨水”指代当代中华文脉,“汨罗江”则代指屈原。汨罗江文脉绵长,汨罗江流域作家群日渐显露,形成一股绵延不尽的地域文学现象,文治是其中一员骁勇之士,不仅自己努力笔耕砚作,且不乏上下挽臂、推波助澜之功。
文治刚届中年,文学的路还得靠他一步一步往前走,有试探就会有挫折,有跌宕就会有醒悟,有勇气就会有收获。苏轼言,“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野鹘是隼类猛禽,唯有振翅高飞,才能望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