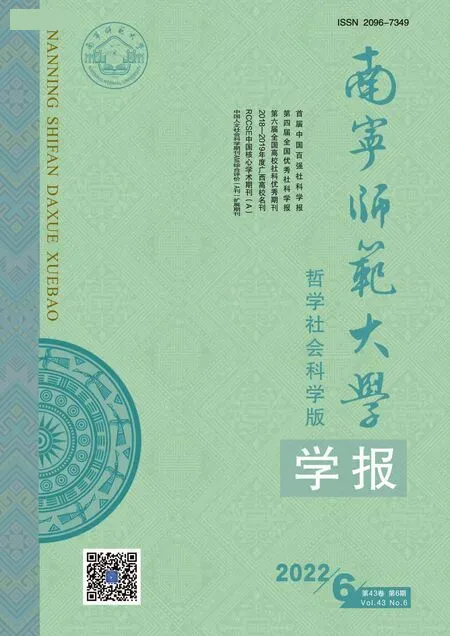凸显人民性立场的民间化叙事
——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错位结构研究
黄文富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23
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聚焦城乡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社会壁垒,叙述了关于“底层奋斗”的故事。小说在结构布局上反讽、戏谑、隐喻、错位、圈套交织,尤其是错位结构环环相扣,具有多重审美意蕴,富有民间趣味,突出民间化叙事的价值导向和审美逻辑。目前学界对该小说关注度显然不够,鲜见从叙事结构视角的解读。鉴于此,本人从小说叙事结构入手,探析其民间化叙事结构的“错位”逻辑,探寻其在民间化叙事结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错位的时空与荒诞的篡改
错位结构是传统民间叙事中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也是当代作家民间化叙事的重要策略。《篡改的命》通过不断布局错位结构来塑造人物形象、营造人物情感、展开故事情节。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叙事方式成为这部小说可读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一)源于对“他者世界”的想象
作为民间化叙事结构的重要表征之一,错位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复合式结构。从错位产生的具体原因来看,可包括动机错位、逻辑错位、语义错位等[1]162-163。《篡改的命》围绕“篡改”展开近乎荒诞的叙事,这种“荒诞叙事”的背后是源于小说人物对城市这个“他者世界”的想象。
小说主人公汪槐一家,他们世居农村、世代为农,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者世界”。在他们的想象里,进城市生活、改变农民身份是改变匮乏物质生活的唯一途径。户主汪槐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年前参加进城招工时,被乡领导的亲戚冒名顶替,错失了进城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不服输,对高考上大学充满了想象,于是把进城改变命运寄托在儿子汪长尺的身上。汪长尺是一个朴实、善良、孝顺的孩子,第一次高考上线没被录取,第二次高考又不上线,于是不得已以进城务工的方式来改善生活。怀着对城市生活强烈渴望的文盲贺小文嫁给汪长尺,进一步叠加了汪家进城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们的“城市化”道路并不顺利,在汪长尺身上发生了一系列错位的事件:被人拖欠工资、替人坐牢、因追讨工钱被捅伤、发生工伤、父母被迫变卖家产到城市乞讨、老婆被迫出卖肉体、把孩子送人、夫妻离婚等,最终被迫自走绝路。
这一连串的错位是由动机错位和逻辑错位交织形成的。首先是一家之主的汪槐,自己进城受挫后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固执地认为汪长尺是个天才,是个富贵命,于是努力供汪长尺读书。不想汪长尺第一次高考成绩上线,却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抗议无效反而摔断了双腿。但这些并没有挫败汪槐的进城动机,他依然坚定让汪长尺进城改变命运的想法。汪长尺原来并不十分配合他父亲的“进城方略”,想在家安心做农民,但贺小文的错位出现激起了他坚定进城的决心。因为贺小文怀孕了,汪长尺不想让孩子重复他和他父亲的生活,想让孩子在城里出生,“就是一个屁都想憋着到城里放”[3]110,于是义无反顾地进城。而如花似玉的贺小文,在汪长尺人生低谷的时候嫁到汪家的动机仅仅是因为汪长尺读过书、能进城。夫妻两人的错位动机一拍即合,叠加在一起,便开始了“城市化”的道路。他们对进入“他者世界”的想象和动机从个体角度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从社会的整体结构来看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他们正是在这样错位的动机、错位的逻辑支撑下进城,由此发生了一系列错位的意外事件,让人物的情感和现实、命运、梦想交织纠葛,最终出现了令人窒息的结局。
(二)从“自我改写”到“被人篡改”
从初心来看,汪氏父子及贺小文的诉求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眼里,农村粮食不值钱,牲畜不值钱,人没办法实现人生价值。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他们找不到出路,逃离这片乡土空间是他们改变艰苦生活现状的途径。从这个意义说,进城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方式。初心正常、动机单纯,他们不过是想通过正常渠道的努力来改写自己及家人的命运罢了。按照传统民间叙事的逻辑,这样的底层逻辑是符合人民大众的逻辑思维的。小说人物的这种诉求,再加上他们的勤劳朴实、苦干实干,尤其是汪氏父子还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基础,他们应该能够实现“屌丝逆袭”。这是很完美很励志的底层逻辑,也是小说营构合理性空间的一面。但事实上,他们的“城市化之路”充满了“错位”,原因与“篡改”有关。
最早被篡改命运的人是汪槐。他曾有招工进城的机会,但指标被冒名顶替,人生命运由此被篡改。其次是汪长尺,他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一生错位都与“篡改”有关。他人生第一次被篡改是高考成绩上线却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此后,他到县城务工阴阳差错顶替他人坐牢,一清二白的人生被“篡改”为有案底的人。后来在省城务工时受工伤,因申请赔偿金需要做亲子鉴定,儿子的DNA鉴定结果竟然又被人篡改,一生遭遇数次被他人篡改,人生轨迹也随之不断改变。作为两个男人命运的配角,刘双菊和贺小文的情感纠葛和人生轨迹也跟随着这两个男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强者世界对弱者世界的欺压,强者对弱者至关重大的命运却能轻而易举地篡改了。他们的篡改手法一个比一个夸张,一个比一个有想象力,一个比一个显得荒诞而具讽刺意味。汪槐参加招工被人冒名顶替,篡改他命运的人是基层的领导;汪长尺高考成绩上线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篡改他命运的人和帮凶是学校老师、冒名上大学的人及其强势的家族等。汪长尺顶替林家柏坐牢,档案由此被篡改,参与篡改的人及帮凶为司法系统里的个别徇私枉法之徒和他的同学黄葵及老板林家柏等人。再到儿子DNA鉴定结果被篡改,篡改的人及帮凶为医院当事医生、林家柏及个别目无王法的司法人员等。如果说,做工被冒名顶替只是一种违规操作,是比较低级别的篡改手法,那么上大学也能够冒名顶替,这个篡改的性质开始变得更为严重了,篡改的手法也更高一筹。再到汪长尺替人坐牢,这种篡改行为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行为了。然而,这还不够,后来汪长尺为了儿子成为城里人,被林家柏逼上自绝之路,这是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形同谋杀,杀人之罪何其大,这种篡改行径已经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而后来汪槐为了汪长尺投胎城里而以做法事的方式来进行篡改的行为则达到了近乎魔幻的程度,篡改之荒诞程度令人唏嘘。
在这场改变命运的角逐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命运被篡改,有的人朝好的方面篡改,有的人朝坏的方面篡改。显性叙事中,汪槐一家的命运都被篡改了,他们属于想“自我改写命运”却“被人篡改命运”的人。他们的初衷是想通过正常渠道改写自己卑微的出身和冲破现实生活的困境,但现实中接踵而来的一场场阴差阳错的意外,导致很多人命运情感交织纠葛在一起。显性叙事之下有隐性叙事,那就是还有一群“被人篡改命运”的人,他们是“篡改的命”中的利益获得者。副乡长的亲戚、顶替汪长尺上大学的人、协助篡改的部门领导和学校老师、林家柏等,他们从篡改他人的命运中窃取了好处。
(三)从“被人篡改命运”到“篡改他人命运”
既有显形结构又有隐形结构是民间化叙事文本结构的重要特征[1]120。一部好的民间化叙事文本的叙事结构往往是显形结构圈套不断、错位连连、引人入胜、扣人心弦,隐形结构隐喻性强、反讽意味浓、耐人寻味。《篡改的命》显形叙事中叙述的都是被人篡改命运的人,但隐形叙事里还隐藏着一群不露脸的以篡改他人命运达到改写自己命运的人,他们是篡改命运赛道上的利益获得者。
小说具有戏剧性冲突是主人公努力改写自我命运而命运偏被他人篡改的问题。从汪氏父子的遭遇来看,他们的经历是令人唏嘘的。他们本来是底层百姓,由于社会强恶势力、既得利益者的篡改,他们的努力成果被巧取豪夺,导致作为底层人物的他们的人生轨迹被一次次篡改,生活四处碰壁,无法实现底层人的晋位升级,无望实现改变命运的初心。但最为反讽和荒诞的是,汪氏一门不仅从“自我改写命运”的人变成“被人篡改命运”的人,而且最后还成为“篡改他人命运”的人。那就是汪长尺万般无奈之下以非常手段篡改了儿子汪大志的人生轨迹,汪槐则以民俗仪式的方式篡改了汪长尺的命运,而被父亲篡改了亲情关系的汪大志干脆将计就计参与篡改了自己的命运,三代人最终以“窃取”的方式实现了进城“初心”。他们三人的“篡改”技术“各有千秋”,汪长尺是忍痛割爱,汪槐是以魔幻的民俗化手段来篡改,最有技术含量的“篡改”就数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了。他在其父亲篡改自己出身命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事情做绝,把篡改做到更高层次。那就是销毁了亲生父亲汪长尺非正常死亡的卷宗和爷爷汪槐一家留有的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把所有关于自己与汪家关联的痕迹全部给擦掉。这是不认父母、不认祖宗、泯灭人性的操作。血缘关系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是关于人性、关乎社会道德、关乎人类情感的同类伦理关系。作者故意在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亲情伦理上下笔,展露人性在特定环境下的冷酷绝情,展现了人性的扭曲、情感的脆弱、亲情的苍白、人伦的失范。作者的叙事直击人性的困境,令人窒息。
二、错位结构的模式选择
错位结构本质上是矛盾体,矛盾对峙是错位结构的基本框架,也是小说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推力。《篡改的命》以错位结构为通篇布局的主体,“将现实、命运和人性一起置入存在价值、意义的罗盘,沉淀着作家的智慧和痛苦,在叙述中重建作家的审美理想和道德规约”[2]15。在错位结构上突出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物质基础与精神尊严、人性欲望与伦理秩序、亲情关系与外部社会关系等矛盾体的交织纠葛。
(一)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反差
人物情感错位是错位结构的核心[1]162。理想追求和现实处境的反差是构成人物情感错位的重要因素。小说中的汪槐一家几乎都是错位的人物形象。从整体结构来看,他们所处的乡土空间落后、闭塞,但他们是有理想的家庭,他们的理想是逃离闭塞落后的乡土空间,到城市去过有尊严的生活。
第一个萌生进城理想的是汪槐。他想通过参加招工的方式进城,但招工指标却被副乡长的亲戚给冒名顶替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怀揣着进城的理想,想通过培养汪长尺高考上大学、当干部来改变农民的身份。所以汪长尺第一次高考成绩上线而不被录取后,他第一反应是录取名额被别人冒名顶替了,于是义无反顾地去抗诉。奈何现实依然很残酷,没人理会他们,还付出了摔断双腿的沉重代价。后来又要求汪长尺去补习,补习不成又催促汪长尺进城务工。在汪长尺进城务工期间,汪槐还数次开启了进城计划。总之,进城改变家庭命运是他的理想。但现实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因素导致他进城失败,各种错位于是在他身上反复上演。
汪长尺显然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理想,他想通过高考上大学来改变人生命运。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后,他听从父亲的劝说去补习,补习没上线后进城务工。第一次进城受挫后,他进城的理想似乎减弱了很多。但后来在妻子贺小文的搓火下,他又坚定了进城的理想,想让孩子出生在城里。在城里打工遭受一系列打击后,他依然坚定在城市生活的理想,最后发现自己不能给孩子在城里的优越生活条件时,为了实现下一代在城里过优越生活的理想,他毅然将孩子偷偷送给了自己的仇家,以荒诞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下一代生活在城里的愿望。汪长尺身上始终纠结着城市生活的理想和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并甘愿为此牺牲自我。
(二)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的失衡
如果说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反差是方向性的错位,那么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的失衡则是汪槐一家实质性的错位。这种错位模式的矛盾冲突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鸿沟。小说中汪槐一家、刘建平等底层人物一般都是“要面子”的,面子就是底层人的尊严。汪槐一家怀着无比巨大的热情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都是有清晰梦想的底层人物,但是现实对他们尤其是对汪长尺来说简直就是“梦想粉碎机”,把他们的梦想一场接一场地粉碎,就连最后一点仅有的“脸面”都不给。而他们最大的现实是物质生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穷人都不配在乎名声、不配有资格讲尊严,他们的精神尊严被物质生活不断挤压。
这方面矛盾最突出的要数汪长尺了。正如东西在小说中表述的那样,汪长尺从小到大“做得最多的梦就是吃”[3]98,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饥饿叙事”就是他忍受匮乏物质生活的表现。但他天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而且极为敏感、要强。补习的时候,由于体谅父母挣钱不容易,他宁可挨饿也不拿父母给的生活费,但又无法解决生活费的问题。上课时饥饿难耐,但强烈的自尊心让他口是心非地拒绝了同学的好心帮助,最后却不得不去找在县城的同学黄葵解决温饱问题。在县城打工的时候,因为老板拖欠工资,饥不择食的他竟然同意替人坐牢。他父母因为体谅他打工不易而到县城乞讨,他怕县城的同学看到丢人,坚决不同意。在省城打工时,妻子贺小文要去给人家按摩洗脚,他起初也不同意,觉得那是没有尊严的工作,但经不起现实物质生活的压力,同意了贺小文去上班,甚至到后来就连对贺小文出卖肉体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在他“城市化”的道路上,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之间的矛盾斗争始终在他底层思维里此起彼伏,而两者斗争的结果是,物质生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蚕食他的精神领地。
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间的矛盾是汪槐一家错位产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他们的错位人生、错位逻辑、错位情感都与物质生活这一基本需求相关。他们居住的乡土空间里,亲情是温暖的。乡里乡亲之间的人际关系尽管夹杂着小农经济意识和势利眼的存在,整体上仍然保留着饱满的乡情关系。村民之间依旧你来我往、互助互连。但是他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极为匮乏,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距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仍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作者的这种错位结构叙事,把过度物化的现实生活活生生地揭露出来,给读者极大的反差感。
小说人物的遭遇是个案的,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的失衡让我们看到底层人往往处于为生活而不断放弃尊严的状态,他们错位的现实际遇深刻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三)人性欲望与伦理秩序的冲突
文本叙事中很多戏剧性矛盾无不交织着人性欲望和伦理秩序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成为民间化叙事乐此不疲的错位结构模式。《篡改的命》中人物的人性欲望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矛盾冲突穿插在文本的错位结构之中,成为或助推情节发展或增加悲剧氛围的重要方式。在主人公汪长尺身上,吃饱穿暖、不风餐露宿、生殖繁衍的人性欲望与他如影随形,时刻威胁着他对伦理秩序的坚守。为了饱腹一餐,他剃头追债、替人坐牢,“饥饿叙事”成为营构他错位人生的重要载体。如果说汪长尺的人性欲望还处于比较低层次的、比较保守的、与伦理秩序冲突还不是很尖锐的状态,那么妻子贺小文身上的这种矛盾冲突似乎更加明显了。她为了能进城,未曾与汪长尺谋面就嫁到汪家。为了能攒点钱,她到同乡张惠的按摩店给客人洗脚,在怀孕的情况下向客人出卖肉体,虽然刚开始她还心有抵触,后来却卖身上瘾,尤其是汪长尺摔伤下半身导致性功能丧失后,她由原来因为生活被迫卖身变成为了满足生理欲望而卖身。这时候,贺小文身上的错位,已经由原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人性欲望和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后来汪长尺性功能突然又恢复了,贺小文却依旧在出卖身体,因为她渴望挣钱,觉得挣钱的生活最实在。没读过书但长得漂亮的她必须马不停蹄地趁年轻挣钱,她无止境地卖身又反过来刺痛汪长尺的尊严,刺伤他的内心。汪长尺无法忍受孩子的母亲卖身,怕影响孩子未来作为城市人的尊严,于是他产生了将孩子送给有钱人家的荒诞想法。而作为社会强者一方代表的林家柏、方知之夫妇,他们物质生活丰富,但方知之却因婚前堕胎生不了孩子,生殖的欲望驱使她想抱养孩子。一方想送孩子,另一方想抱养孩子,汪长尺和林家柏的人生轨迹便莫名错位交集。总之,人性的欲望导致了小说人物身上的种种错位交织。
伦理界线不断被突破是当下人类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困境。现代社会,人们在追逐个性解放的同时,伦理秩序被不断挑战、突破、碾轧。民间化叙事中,伦理维度是非常鲜明而重要的,它直接决定一部作品的价值导向问题。这也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以及能否成为经典的核心要素之一。但伦理维度却不是那么容易拿捏的,太简单太直接地扬起伦理旗帜,则没有太多的可读性,易变成政治家的政治口号,而太过于隐喻则很容易让人“费解”从而丧失读者。东西在《篡改的命》中通过错位结构的运用,展示出令人窒息的社会丑恶的一面,激发了读者对这种丑恶社会现实的痛恨和批判,也顺势树立起了作品价值导向的旗帜。
(四)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纠葛
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关涉当事人对亲情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如何做出抉择的问题,体现的是家庭内部关系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对立。
从亲情伦理关系来看,汪槐一家的亲情关系是温情的。他们相互关心,相互体谅对方,努力为对方着想。汪槐和刘双菊为了让汪长尺安心读书而省吃俭用,汪长尺不忍心父母太辛苦,悄悄把钱塞还给父母。但自己却又不能解决读书期间的生活费问题,只好去找已经辍学混社会的同学黄葵,但汪槐不同意他跟黄葵在一起,认为跟黄葵一起迟早会被带坏。汪槐夫妇变卖家产到县城以捡垃圾为生,但汪长尺觉得这样很丢脸,不同意他们出来捡垃圾,父子因此发生了冲突。这时候汪槐非常体谅儿子的尊严,认为这样确实让儿子面子过不去,于是同意回老家生活。在省城带孙子的时候,面对经济生活的拮据,汪槐夫妇想去街上乞讨,又怕汪长尺自尊心过不去,便每天偷偷溜出去不给汪长尺知道。在处理家庭外部的经济关系时,他们把家庭内部的亲情关系看得更重,体现出底层社会温情的一面。
最受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矛盾冲突煎熬的是汪长尺和汪大志。对汪长尺而言,他很爱汪大志,渴望汪大志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但自己却没有实力,害怕汪大志不能拥有在城市生活的底气。于是把汪大志送给有钱人领养,但送出去之后汪大志就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了,他又于心不忍。在是否与汪大志断绝亲情关系的问题上,他内心反复纠结、煎熬,但最后他觉得外部的社会关系对汪大志更为重要,觉得父子关系在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面前已经显得不重要,于是果断地把汪大志送了出去。送出去后,汪长尺几次碰见长大后的汪大志,出于亲情的渴望,他几次想叫大志,但又害怕由此影响汪大志在养父母家的关系而忍住不叫。后来汪大志的养父林家柏出轨,本来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林家柏和方知之是夫妻关系,他们和现在的汪大志是一家人,汪长尺认为这种行为会影响到汪大志的成长,于是他果断站出来阻止林家柏的出轨行为。这一出面则暴露了他与汪大志的关系,林家柏为了彻底清除汪长尺在汪大志人生中的痕迹,逼迫他走绝路。这时候的汪长尺又面临着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抉择问题,如果他不顺从林家柏,汪大志就融不进养父母家庭中去,就得不到养父母家的信任和财富继承权。而走绝路则意味着他从此与汪大志永别,亲情关系将就此覆灭。他内心又开始斗争,反复纠结的结果是他选择保留汪大志的社会关系而自我毁灭亲情关系。汪长尺自走绝路之后,留给汪大志的仍然是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抉择问题。汪大志得知自己亲生父亲是汪长尺,并侦查到其亲生父亲的非正常死亡后,在处理与亲生父亲的关系上,他选择了更为有利于他当下生活的做法,那就是彻底删除他跟亲生父亲的关系,把富有财富和地位的社会关系看得比亲情更为重要。这是亲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纠葛,是人类血缘关系伦理和社会关系秩序的冲突,是良知与社会财富归属的较量。汪长尺父子的抉择反映了底层社会个体的无奈和追逐利益的时代中人们过度物化的情感。
三、多重错位下的悲剧语境与人文情怀
《篡改的命》情节曲折交错,结构错位连连,人物对立冲突一环扣一环,现实、荒诞、魔幻并存,形成多重错位下的悲剧叙事,彰显了作者善于调侃戏谑冷酷社会关系、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揭露和批判不合理社会现象的人文情怀与责任担当。
(一)人物对立下的现实隐喻
隐喻是民间化叙事的重要策略[1]121。叙事学语境中的隐喻是以象征、寓言、影射、暗指等言语机制进行指明对象、揭露真相、揭示内涵、阐明意义的一种叙事方式。对小说而言,人物对立冲突是小说矛盾的主体,但人物本身并不是对立冲突的根源,人物只是作家叙述对立冲突的工具。人物对立冲突的根源往往是隐藏在人物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制度、体制、机制等,而隐喻则是抵达人物对立冲突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语言运作机制。小说《篡改的命》中营构了多重错位的人物关系,隐喻了社会现实百态。
小说题目“篡改”一词就有深刻的隐喻意味。其隐喻着这是一个关于强者与弱者、明处的人与暗处的人之间的故事,双方处于不对等、不平衡的状态,暗示着是对社会上剽窃、私自变更信息、隐瞒真相而为、尔虞我诈的苟且之事和贼性行为的叙述。文本中的隐喻叙事就更多了,如:得罪两个警察之后,村里人竟突然变得人人自危,害怕警察公仇私报。因为他们仔细想想,好像都有一点小秘密,这些小秘密就像是一个个小辫子被警察攒在手里。想想就各个都心虚失眠,一个偏远平静的村庄竟然有如此多的小秘密,隐喻了人们内心隐秘地带的灰色甚至黑色。黄葵派人捅伤汪长尺后依然逍遥法外,十分得意。汪长尺冥思苦想复仇而不得,黄葵却意外地按照汪长尺希望看到的那样死于非命,暗示着坏人虽强必败、好人虽弱必胜、“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民间化叙事逻辑。在省城从事按摩服务行业的同村人张惠过年回家时,经常把自己的衣服穿到贺小文身上,把贺小文打扮得一天一个样,像民办教师、乡里干部、县里文工团演员、女特务、城市白领等,这则是对城市灯红酒绿夜生活的隐形描述,影射城市隐秘空间里一些男人们的嗜好和变态的审美观。汪长尺去县城派出所自首时与警察的对话、带贺小文去产检时与医生的对话、第一次与仇人林家柏面对面对视时双方内心的对骂等,使得城乡人物之间的对立跃然纸上。他们之间的对立影射了城乡之间不同空间生态的相互戒备、排斥、鄙视。至于贺小文的穷晕、不挣钱狂躁症,汪大志的农村过敏症等,则隐喻着城乡发展的失衡和对立。汪长尺的“城市化道路”更是充满多元化的隐喻,他善良、勤劳、苦干,满怀梦想却处处碰壁。城市似乎不需要他这种人,城市对他来说简直是“梦想粉碎机”。最后竟然只能以极为荒诞、魔幻的民俗仪式——“投胎”的方式进城,其“城市化道路”揭示了社会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融入城市之艰难,也隐喻了城市价值观念与乡土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兼容、不协调、不融合。城镇化是国家在特定情势下推行的社会化运动,从政治叙事角度来说,这是积极的宏伟的,但作者以底层个体的生命史、以民间化叙事的方式对城镇化的无光死角进行了揭短。
(二)城乡冲突下的底层隐忍
《篡改的命》中主人公是“弱爆”的,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仅存的善良、温情和尊严撒了一地。小说营构的矛盾关系中,城乡之间的对立冲突是直接的,两者的对立冲突并不平衡,乡村明显处于弱势。面对强者,隐忍与妥协是弱者的习惯思维。汪长尺第一次高考上线未被录取后,他并不站在父亲的一边选择抗争,而是选择了隐忍。此后,务工被拖欠工资、替人坐牢、被黄葵手下捅伤、出工伤、工伤鉴定被人篡改结果、老婆被迫卖身、送孩子给人家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隐忍。面对强大无情的社会现实,汪长尺一次次努力,一次次遭受挫折,面对不法分子的欺辱,他也曾经本能地进行反抗,但越是反抗越是被暴虐,似乎只有隐忍才是唯一的明哲保身之道。就像小说中他同学黄葵骂他的那样“不是所有的人都配有仇恨,想仇恨,首先你得有仇恨的资本”[3]81,而汪长尺似乎连仇恨的资本都没有。面对与他一生的悲催遭遇相关的林家柏,他无比痛恨,但转念又强迫自己换个角度来想象对方的好,把他想象成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人,甚至把他想象成是跟儿子汪大志有缘分的人。因为就在贺小文准备去打胎的时候,林家柏给项目经理送来了两万元工伤补偿款,而正是这两万元让他成功劝住贺小文不打胎,这才保住了汪大志,换句话来说就是林家柏保住了汪大志。他强迫自己有这样的想象,其实是想说服自己把孩子送到林家柏家寄养,是给自己纠结的内心寻找平衡点。这是汪长尺面对强大社会现实做出的隐忍与妥协,折射了底层人物的卑微和无奈。
小说人物的隐忍代表的是底层的隐忍。但作者写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隐忍并不是为了一味地展示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懦弱,如果是这样,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似乎就欠火候了。作者浓墨重笔地叙述底层弱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隐忍妥协,叠加突出强者的趾高气扬和得意洋洋,实际上是在为施暴者、强恶者的覆灭积蓄力量,那就是“人不惩天惩”。这是民间化叙事表现正义的惯用逻辑——弱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暴虐、碾轧,恶强者似乎总是高高在上,但结局坏人依旧是受惩罚的。比如像黄葵这样的坏人,他叫人把汪长尺捅了两刀,按民间叙事逻辑,黄葵这样做对于汪长尺来说就是仇人,他做梦都想复仇,奈何黄葵人多势众,汪长尺几次复仇而不得,让读者跟着汪长尺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但实际上这只是作者设置的一个圈套,作者只不过是想让坏人多得意一下而已,并不是脱离民间叙事的逻辑,那就是坏人迟早都是要受到惩罚的,只不过黄葵这种坏人被除“出局”不是汪长尺亲自动手,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被惩罚“出局”,且能按汪长尺希望和想象的那样“出局”。这种叙事逻辑印证了自古以来就已经烙印在民间思维里的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汪长尺在黄葵面前多次被欺负、施暴,而他连报仇的勇气也没有,给人看起来就是一个窝囊废。这只是在不断增加阅读者对黄葵罪孽的憎恨度,为后来黄葵的被害做了更为曲折的铺垫,为读者内心的憎恨“蓄压”,不断地叙述黄葵的嚣张作恶、汪长尺的“软蛋”无能无奈就是在不断地积蓄读者的憎恨之火,然后来一个意外——让黄葵受到应有的惩罚,读者的情感得到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这显然是东西设置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圈套。正是这样的结构,让小说情节更引人入胜,更具可读性。
(三)城乡冲突下的社会壁垒
篡改是对已有规则的改变,是对规则的破坏,而规则能被破坏说明有比规则更为强大的力量。它意味着篡改者处于强势地位,展示的是不公平、不对等的关系。在《篡改的命》中,有篡改他人命运的人及帮凶,也有被他人篡改命运的人,他们有的人偷偷摸摸地篡改他人命运,有的人赤裸裸地篡改他人命运,有的人命运往好的方向篡改,有的人被往坏的方向篡改。因为篡改,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汪长尺一生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的努力成果却总是被人篡改:高考成绩上线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进城打工被拖欠工资、追讨工资被人捅伤、工伤鉴定被人篡改结果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现实施暴、摧残,肉体、精神、灵魂、尊严被碾轧得遍体鳞伤。他认为自己贫穷、弱爆、没有尊严,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笨或者不够努力,而是自己出生在农村。因为出生在农村,他老婆住院时被医生骂“一农村妇女不应该这么娇气……”[3]118,所以他渴望进城,孩子也必须到城里出生。在他看来,城市出身、市民生活俨然是改变卑微身份的唯一途径,或者说是唯一的空间渠道,他把农民身份、农村出身、乡土空间当作了禁锢他物质生活、人生价值的枷锁。
错位结构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也有合理统一的一面。汪长尺把自己孩子送给仇人家领养的行为无疑是无比荒诞、扭曲的,但与无比物化的社会现实、无比强烈的城市渴望相比,从他个人的底层逻辑出发,这又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即存在就是合理。这种荒诞的合理背后是主人公对城乡冲突无法突破的极度无奈。按常规叙事,社会资源壁垒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应该是要被打破的,最直接的正能量叙事应该是直接对这种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抨击,底层人因为努力或善良最后顺利实现翻身,结局皆大欢喜。这样似乎更加符合叙事中的“民间逻辑”。但《篡改的命》打破了这种“民间逻辑”,底层人并没有得到翻身,而是一个个地沦为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牺牲品。底层人处处碰壁,坏人反而是风生水起,底层人完败,最后只能靠无比荒诞的民俗仪式——“投胎”来实现底层身份的转变,结局令人倍感凄凉和窒息。但这样的错位结构并没有弱化作者的价值导向,相反还极大增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悲情意识和人文情怀。因为这样的“错位叙事”更能宣泄作者对城乡对立形成社会壁垒这种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嘲讽、挖苦和痛诉。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绕了一个弯儿来展现民间叙事的价值导向。同是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作者用了不一样的“民间”方式实现同样的“民间关怀”,这是作者对传统民间化叙事价值逻辑的探索和突破。
结 语
综上分析,《篡改的命》以错位结构为主要叙事策略,突出展现了小说人物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物质生活与精神尊严、人性欲望与伦理秩序、亲情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多重对立冲突,形成多重错位下的悲剧叙事。文本叙事充满反讽、荒诞、幽默、魔幻,彰显了作者对民间化叙事的试验、探索和丰富。小说引发人们对社会观念过度物化、人际关系利益至上、伦理秩序失范、城乡发展失衡的反思,表达了作者对城乡对立下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强烈批判,体现了作者目光向下、聚焦底层、直视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情怀和人民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