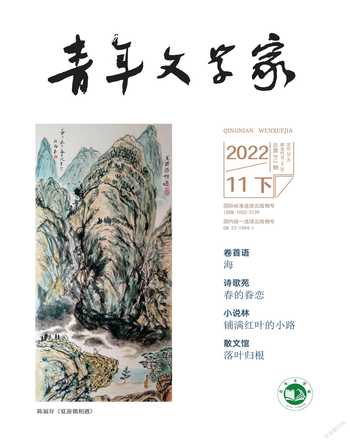落叶归根
刘倩岚

小时候,爷爷奶奶家在山上,我每次爬到半山腰爬不动了,便会大声喊爷爷。正在干农活儿的爷爷听到我的呼喊后,立刻放下手中的镰刀、锄头下来背我。爷爷个子很高,每个步子踩在青石板上都非常扎实。后来,爷爷奶奶搬到了山下,我也再没回过老屋。
2017年,爷爷去世,享年76岁。农村里讲究老人过世要落叶归根,以前住在山里的一大队的人便同我们一起回了趟老屋。
我记得那是高二的夏天,知了在树梢上不知疲倦地叫着,教室里的电风扇也在不停运转,正是午休的时候,父亲和班主任商量了一阵,便把我接走了。一路急匆匆的,回去的路上我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
第一天,我们张罗着酒席和乐队。农村有哭丧的习俗,爷爷生前认识的人都来祭奠爷爷。人过世之前好像都会有感应似的,听妈妈说,爷爷前两天还去给自己置办了一套新的中山装。我看着他穿着新衣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回忆起在我小时候,爷爷每次都到半山腰来背我,忽然觉得恍如隔世。
第二天,是送爷爷上山的日子。我们一行人一整夜几乎没怎么睡,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出发了。霧气晕染,溪水潺潺,抬棺木的队伍由爷爷的儿子、干儿子及队上年轻力壮的青年组成,他们走在最前面。我不经意间发现队伍里面还有曾经与我家有过过节的人,我纳闷儿,但是转念一想,不管平时发生了什么事,也比不上人的生老病死,这是一方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的时刻,于是乎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平日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赶来帮忙了。我们几个晚辈走在中间,我和我的几个姐姐一同回忆着小时候的事:小时候放寒暑假,我们几个便约好一起回爷爷奶奶家。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而山上有河、有野花,还有各种新奇的小事物,这对我们来说便是最大的吸引力。每次赶集,爷爷还会给我们买零食。正说着,前面便开始喊起了号子—开始走上坡路了。爷爷身材又高又壮,山路容易打滑,青年们抬棺很费力,于是便喊起了号子。耗时三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太爷的坟园,爷爷将要葬在太爷的旁边。先放炮,后刨土,最后对着爷爷的坟头磕了三个头,我们便同爷爷真正地说再见了。我们几个晚辈绕了一段路回到了老宅。回老宅的路长满了野草,老屋已经破得不像样了,甚至只能看到从前的一部分。听老一辈的人说,老房子是有灵性的,人住在里面有人气儿就不会倒;要是人走了就不会有人气儿,它就会归于天地万物。彼时,天已逐渐亮了起来,下了一夜的雨,初夏的野草总是很有生命力,经过雨水的点染,便更平添了一分新意。山路泥泞,大家相互搀扶着下山,我时不时往回望,想要记住这来时的路。很快,爷爷的坟园、我们家的老宅便淡出视野了。
回程的路上,故乡的一切都近在眼前:无论是小时候卖雪糕的小卖部,还是嬉戏打闹的田间河坝,都逐一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望着身后的那座大山,那架索桥,我不禁思考到故乡对于人们的意义,或许故乡就是祖祖辈辈都葬在一起的地方吧。人这一生,不管游历了多少地方,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根,所谓落叶归根,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