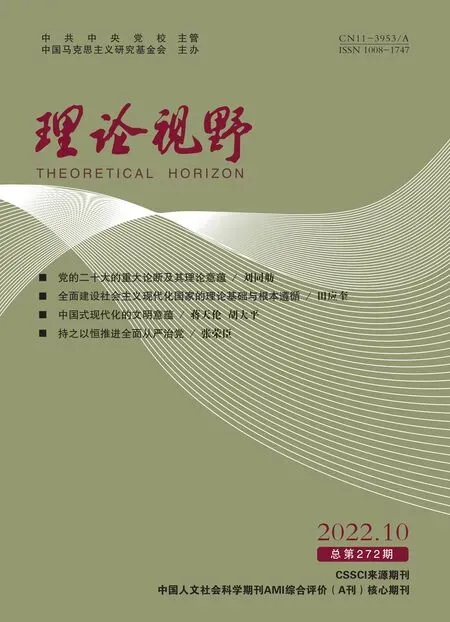恩格斯自然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
■周晔 朱珧
【提要】恩格斯自然观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探究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揭示出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不仅适用于对自然领域的认知,也适用于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解。恩格斯以自然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为人类社会实践历史地引申出一个全新的自然哲学构架:一是提出了从自然本体论出发界定物质范畴及其存在形式;二是提出了从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出发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过程;三是提出了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四是提出了从自然辩证法出发解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伴随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可实证的物理事实,科学进步所引发的认识结果日益向人们展示了以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为依据的、关于自然界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图景,结束了超验的形而上学决定论在自然观上的统治地位,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庇护所即非理性的主观感受中驱赶了出去,使自然的研究更为科学。与此发展相同步,恩格斯自然观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从“经验自然科学”过渡到“理论自然科学”,用唯物辩证法来解释自然、认知自然和改造自然,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确证了人类实践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一、恩格斯从自然本体论出发界定物质范畴及其存在形式
物质范畴及其存在形式并非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独创,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诞生之前,物质范畴已经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即把“世界的统一性”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抽象“本体”。然而,恩格斯从不抽象地谈论物质范畴,总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历史地探讨物质范畴及其存在形式,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使之发生“术语革命”。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
西方传统哲学在解释物质范畴时,尽管说法不一,但存在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就是仅从物的感性直观去理解对象,总是把自然对象当作一种“纯粹客体”来认识。恩格斯针对此种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的理论缺陷时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2]恩格斯认为,对于物质范畴这一根本属性,不能仅仅从物的感性直观去理解,而应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物质是人可以通过实践感知的,而不是被动的,不可认识的。恩格斯指出:“当然不知道,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以其他方式体验过;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3]恩格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使物质范畴建立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之上,为正确理解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恩格斯对物质运动时所遵循的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作出科学解释,他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4]
物质都是运动的,自然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恩格斯根据自然界的物质及其运动形式,把物质世界无限多样的形态和结构作了具体划分,概括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形式是由它们的物质载体按照时间先后,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蒙昧到文明的一般顺序逐渐展开的。此外,恩格斯认为,物质运动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是不灭的,“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5]。这就是说,在自然界中,物质形态的转化过程虽然有生有灭,但它总是从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运动,这不仅永远不会失掉转化的可能性,而且注定要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三)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物质存在于永恒的运动之中,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时间和空间。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对时间、空间与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他指出,“空间与时间在运动中才得到现实性”,“运动的本质是成为空间与时间的直接统一;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才被真正区分的空间”。[6]恩格斯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时空观的合理形式,他指出:“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7]“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8]与此同时,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及其变化过程必定服从于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时间和空间是有限性与无限性不可分离地统一的,他指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9]“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10]恩格斯认为物质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是由时间总体的每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环节组成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这一点在现代物理学中得到了科学确认。
二、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出发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过程
恩格斯在探究自然规律的实践中,发现“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11]。尔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依据,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并将其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12]。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恩格斯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入手,把物质的运动形式确立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出:“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13]根据恩格斯的论断,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总是通过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发生的。“运动的形式变换总是至少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14]
恩格斯在阐述“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时,还列举了大量的关于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成果,以此来证明物体、分子和原子之间的质量关系,他指出:“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15]“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一些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量度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所以这里只要发生质变,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16]“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17]在化学中,“在正烷烃中,……依据代数公式CnH2n+2,便有C3H8,C4H10等等,结果每增加一个CH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18]。“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想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在这些科学中量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探求的。”[19]恩格斯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分析了自然界中由量变到质变的两种基本形式,从而揭示了自然界中质量互变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阐明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规则运动、发展、变化的,构筑一幅关于自然界“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的总图景。
(二)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作为自然的普遍结构和自然运动的普遍规律,实际上就是指“运动本身就是矛盾”[20]。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给出这样的定义:“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对立,那么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21]为说明自然界矛盾运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恩格斯列举了自然科学中的大量事实,例如磁石有南极和北极的对立,电有阳极和阴极的对立,化学有化合和分解的对立,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排斥、相互转化,“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22],“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23]。这说明矛盾着的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是对立中的统一,在统一体中相互作用。
对恩格斯来说,运动中的矛盾不仅适用于自然领域的辩证转化,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思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24]恩格斯从自然界和人类思维这两个领域阐发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揭示了自然和思维都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的,说明了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内在一致性,突出了矛盾规律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三)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它是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25],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26]这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把转化、斗争建立在“自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原则之上,把矛盾看作是同一个东西自身与自身相矛盾、自己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辩证的否定不是外部强加的随意的否定,而是“扬弃”,是克服和保存的统一。他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27]“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再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28]“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29]在恩格斯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各种事物和过程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每个事物都是这个统一整体上的一个环节,根本不存在同周围其他事物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恩格斯把否定的否定的规律理解为自己与自己相矛盾、理解为“自否定”和“自己运动”,也就是说,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之所以能成为事物的“自己运动”的内在动力,只是因为这个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超越自己的内在冲动,构成了一切事物内在生命冲动或能动性的一般根据。
三、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在恩格斯看来,谈论人类历史首先必须谈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的肉体组织,而且还主要是由物质生产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的人。“两种生产”既是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按照自身需求来改造自然界的基础。正是历史发生的“两种生产”使得人类最终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也由于“两种生产”才造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一)两种生产理论
人的历史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自身的生产,它们都是与主体自身的能力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在前一种生产中,主体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解决吃喝住穿等生活需要的问题;而在后一种生产中,人类种族的蕃衍着眼于家庭形式与血缘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史前时期的“两种生产”作了一番考察,他们肯定了以自然分工为前提的财产公有和血缘关系上的共产制经济的原始社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具有原始部落自然共同体的特征。但由于当时缺乏史料的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原始的公有制”的具体组织形式、形成过程等尚不明确,没有做出具体论证。“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30]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根据最新的史料成果,对“两种生产”加以扩充,并做出新的说明。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1]恩格斯认为,从原始部落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来看,在经济关系和氏族交往关系尚未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血族关系无疑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探讨原始氏族部落的起源,不能仅仅只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还应从人类自身的生产出发。
(二)原始婚姻家庭的发展和氏族制度的瓦解
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刚刚从动物世界脱离出来的时候,尚无婚姻家庭这样一种独立的形态,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的瓦解,于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新的婚姻家庭形式开始出现。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32]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原始婚姻家庭的历史变迁:在原始社会初期,氏族部落内部存在着杂乱的两性关系,没有文明时代意义上的家庭形式。后来两性关系因氏族部落中的风俗禁例而受到限制和规定,便产生了家庭。具体说来,家庭形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即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专偶家庭等变迁。“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33]恩格斯认为,婚姻家庭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发展是同人的生存形式、社会性生产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体环境相适应的。
(三)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在人类社会历史早期,通过生产,人从混沌一体的自然界脱离出来成为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主体,也是在生产中,经过人作用过的自然界内在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存在的双向互动关系。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4]这里说明,一旦进入由人本身创造的历史,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就绝不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原始部落自然共同体的没落、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等形式。以血族团体、血亲婚配为基础的原始部落自然共同体,由于新形成的社会统治形式,即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抗和冲突而被摧毁,组成为新的文明时代的国家取而代之。恩格斯指出:“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35]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简单的血族关系来维系的“自然规律”必然要为真正的“社会的生产规律”所取代,人类通过曲折的历史发展超越外在必然性的支配而获得更高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价值的实现就寓于其创造性的历史活动之中。
四、恩格斯从自然辩证法出发解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最关心的问题是将辩证法应用于对自然的探索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肯定。在恩格斯看来,自然始终是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前提,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自然界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必定服从于自然辩证法的规律,这些规律也会对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恰恰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劳动表现出来的。
(一)自然科学的进步对于人类思维变革的方法论意义
在《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导论”中,恩格斯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学之肇始的前沿成果。他指出:“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36]伴随着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是更加注重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经验事实之上。
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逐步获得独立地位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把自然科学研究加以片面化地发展和运用,忽视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规定性,其结果必然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科学给定性与社会历史性的脱节,总体与局部的分离,使得自然科学研究以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式出现。正是由于科学理论思维的缺乏和机械思维方式的过分推崇,使得恩格斯必须冲破资产阶级旧的思想束缚,阐明形而上学思维的矛盾及其局限性,论证辩证思维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科学思维形式,“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37]。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就是人的科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本身产生于人的科学,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活动为自然科学提供认识的普遍有效性、辩证思维方法等;另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科学从给定的对象研究中确证实验科学的最终根据,即理论思维和人的科学关于自然、实践、社会等的一般认识,推动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的确立和进展。
(二)“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这一科学论断。他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8]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为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过渡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认为,从“猿的活动”走向“人的劳动”并更高地迈向实践的观点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呼之将出了。通过劳动,类人猿不仅将自在自然变成它们的感性世界,而且在它们的劳动中还创造出语言形式。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39],“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40]。这里说明,从猿脑向人脑的决定性转变的关键是劳动,通过劳动的社会历史性的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恩格斯认为,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从“猿的活动”到“人的劳动”的转变过程绝不是任意的、孤立的和封闭的,而是在主体劳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历史地改变着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决定于主体生命表现的要素,也决定于主体不断与自然对象打交道的感性的自然界,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的。
(三)“人的两次提升”的理论原则
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导致的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赢得对自然的胜利正刷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通过自身的劳动满足“需要本身”,迫使人们通过更为复杂的劳动、更为精良的工具对自然发生作用,改写着“自然”的性质。在恩格斯看来,如果自然科学一旦屈从于狭隘的特定的阶级利益,它就必定要野蛮地对待自然,把自然当作任意掠夺和摧残的对象。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1]恩格斯在这里充分肯定了自然控制和驾驭自然的认识成果,但反对把自然简单地看作是人的生产方式的奴隶。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认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42]“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43]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是要界定“生产”是人类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但却同时获得了“人的两次提升”这一新的哲学范畴。
“人的两次提升”的哲学范畴,强调人要从异化的人的本质进入真正的人的本质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次是“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44];一次是“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45]。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把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实践成果用作对人的异己性的扬弃,只有这时,人类社会发展才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人才真正地上升为自然历史的主体。
注释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第519页。
[2][3][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6][37][38][39][40][41][42][43][44][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1页;第500页;第64页;第426页;第56页;第500页;第55页;第53页;第539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65页;第466页;第466页;第466页;第467页;第469页;第127页;第356页;第476页;第476页;第127~128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49页;第149页;第411页;第436页;第550页;第554页;第558页;第559~560页;第559页;第548页;第560页;第561页。
[6]【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31][32][33][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第42页;第77~78页;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