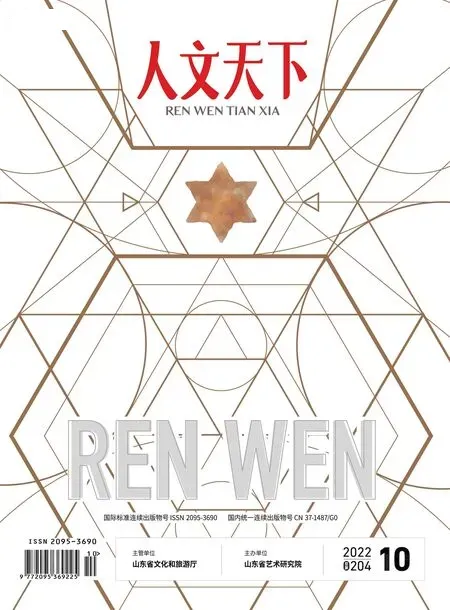俗世的兴游
——谢时臣《虎阜春晴图》中纪游意境的构建方法
■ 陈正觉
明代晚期,吴门地区的山水画大致上顺承沈周和文徵明的艺术脉络,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艺术面貌,这也致使美术史中将该时期苏州地区的艺术发展定性为吴门画派的衰落期。整体而言,这样的结论大体是无误的,但仍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一些非典型性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家,活跃在十六世纪的吴门职业画家谢时臣就是这中间的代表。
谢时臣身处吴门画派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其纪游题材山水画却不同于吴门时风,呈现出贴近世俗生活的面貌。同时,谢时臣构建纪游山水图景的观念也难以被明末以后追求文人“雅趣”的主流审美接纳,因此在明清时期的美术史视野中逐渐被推向边缘。然而,以谢时臣为代表的吴门非典型画家在意境构建上的特点昭示着明代晚期流派地域分野的复杂性,在当下的美术史研究中值得被重新发现。
一、谢时臣在美术史研究中的遗失
一直以来,吴门画家谢时臣都是作为吴门末流的支系以及步沈周、文徵明“后尘”的职业画家进入美术史研究视野的,而关于谢时臣及其艺术作品的具体艺术价值,在明清以来的美术史研究中,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被忽略和边缘化的状态,始终无法得到主流领域的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由于明清时期的绘画受到鉴藏家及批评家的价值导向与审美趣味的深刻影响,人为地产生了吴、浙二画派的分野,以此作为职业与非职业(行家与戾家)对立的基础。吴门的文人画风格受到追捧,相应地抑制了传承南宋院体一脉的浙派风格。铃木敬、任道斌在《明代“浙派”绘画研究》中开篇就提到:“人们不是以戴文进的出生地钱塘杭城来命名,称之为‘钱塘派’或‘杭派’,而是称之为‘浙派’,这无疑是为了与‘吴派’绘画相区别而已。吴、浙两地的对抗意识是强烈的。”①铃木敬、任道斌:《明代“浙派”绘画研究》,《新美术》1989年第4期。
单独从技法上来看,谢时臣的作品是不乏文人气息的,但同时他又吸收了浙派的笔墨技巧和世俗意境,再加上其职业画家的身份,对于明末以后的批评体系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认为谢时臣“气势有余,韶秀不足”②姜绍书:《无声诗史》,载于《画史丛书二》卷三,于安澜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页。;稍晚时代的松江批评家何良俊也对谢时臣评价不高:“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③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载于《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卢辅圣编著,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871-872页。
可以看出,明末以后山水画审美以“文人清雅”为单方面的品评标准,这是在吴、浙两地的比较中产生的相对概念。这种分野的副作用就是,如谢时臣这样兼取两种风格之长的职业画家在美术史中的身份标识进一步模糊了,最终消逝于其身后的绘画史研究中。这种标签化的划分与身影的迷失显然是有失客观的,直到近代乃至现当代,机械的吴浙二分的艺术史观念被打破,谢时臣的相关问题才被重新关注。
其二,谢时臣虽然作品不在少数,但由于其一生未入仕途,中晚期又隐居于山野,所以其生平多散落在时人的画评散记之中。其时吴中主流文人群体处于较为兴盛的时期,传派众多,且都以士夫阶层为主导,谢时臣职业画家的身份难以进入其交游的核心范围之内,因此在常规的古代绘画研究中极容易被一笔带过,最终无法避免地在历史中蒙尘。
由此可见,谢时臣之所以难以取得与文人画品评趣味的和解,主要是因为其不像苏州大部分文人画家一样宣扬超脱世外的“雅趣”,而是在其纪游作品的内涵中显示出接近于“俗趣”的意味。谢时臣贴近俗世的一面深刻地融入其山水画意境的建构中,忠实地记录了创作者在山水中的游观与生活的内容。
二、谢时臣的纪游与隐居
明代前期,地方之间的管辖和限制十分严格,人员的流动受到极大的约束,商业等经济行为也受到国家力量的抑制。由于历史原因,明代前期统治者对吴门文人压制政策极为严苛,因此明前期的纪游山水并未形成规模。
明中后期开始,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随着地方苛政的放松,经济社会开始逐渐复兴。其中,迅速繁荣起来的吴门地区形成了崇尚奢侈消费的社会风尚,社会习俗和心理上也逐渐偏向于享受物质生活。据地方县志记载,吴门地区“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①王鏊等:《正德姑苏志》卷十三,转引自关健:《吴门画派纪游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4年,第44页。,这种风尚逐步演化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集体行为。同时,吴门地区的人们在精神上也开始崇尚自由解放的思想观念,开始着眼于欣赏自然山水景色和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于是,多种外在的条件最终为吴门地区的人们找到了“旅游”这一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娱乐方式。
明代中后期的吴门地区,各阶层几乎全部参与到旅游中来,唐寅在《江南四季歌》中提到:“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②唐寅,应守岩点校:《六如居士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30-31页。这种极端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旅游活动已经十分普及。其中,虎丘地区在当时是旅游活动尤其兴盛之地,游览虎丘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张岱在散文《虎丘中秋夜》中提到:“虎丘八月半……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③张岱:《陶庵梦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作为地区文化的核心群体,吴门画派的文人阶层也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多以本地景观为描绘对象进行山水画创作,以此来更为直观地抒发情感和志趣。这类山水创作从题材和内容上可以归为纪游图一类,如《千人石夜游图卷》便是沈周在游览虎丘一带之后,对“山空人静”的山景的描绘。广义上来说,对自身或友人隐居结庐之地进行描绘的山水创作也体现了纪游图的一些特征,因此本文也将其归入其中一并论述。
谢时臣一生在江浙一带多次游历,其中在其故乡吴门一带游览较多。根据谢44岁时所作《江山胜揽图》,57岁时所作《独坐观泉图》,58岁时所作《山水花卉册》《杂画册》,60岁时所作《水图册》等作品的钤印“虎丘山人”,以及谢50岁时所作《虎丘图卷》题跋中提到其“独坐山斋,戏弄水墨以适孤兴”,可以初步推断,谢时臣此时期活动或隐居于虎丘地区,至少可以大致得出其44岁到60岁这十余年间结庐居住于虎丘地区这一相对可靠的结论。
谢时臣在虎丘的居住和频繁活动,为他依据该地区的自然实景进行山水创作提供了可能性。虽然无从得知《虎阜春晴图》确切的创作时间,但从其笔墨风格已经十分成熟这点来看,可以推测此画属于谢后期作品的范围。所以,《虎阜春晴图》极有可能是谢时臣晚年活动于虎丘时的写生纪游作品,是其在隐居的生活中对熟悉的景观和市民的旅游活动的描绘。结合前文所述十六世纪吴门地区的游赏活动盛况,不难看出,谢时臣在意境的构建上将明朗的生活气息与自然山水相结合,形成了“俗世的兴游”的审美意趣。
三、《虎阜春晴图》的意境构造方法
谢时臣《虎阜春晴图》(如图1所示)的内容十分简明直接,各色游人三五成群,登上虎丘欣赏春日山景。这种“兴游”的意境是谢纪游山水画中的核心概念,是其基于对虎丘这一对象呈现出的诸多信息创造出的一个独立于客观世界的艺术“秘境”,最终通过图式语言呈现在画面上,具体表现为一种市民生活的氛围。这种意境的创造被历史上的诸多山水画理论总结为难以捉摸的“非师”因素,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种意境的构建是有迹可循的,能够通过画面逆推出其具体方法。

图1 谢时臣《虎阜春晴图》(纸本浅设色)
(一)叙述重心的安排
《虎阜春晴图》的画面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远山,下半部分是近处的虎丘。值得注意的是,近景与远景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似乎前代传统中基本都会出现的中景被刻意减省掉了。若勉强将中间稍远处的坡岸作为中景,又难以与前面体量巨大的近景构成关系,因此将坡岸归为远景为宜。
单纯从图像上看,这种前后两分的构图极大地增加了近景的面积。在近处,从最下端的入口,到制高点虎丘塔,房屋林立、树木掩映,显然这些才是画面的叙述重心。这在今日看来也许十分寻常,但历史地审视这个问题不难发现,在谢时臣以前的立轴山水画中,这种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近景丘壑刻画的方法少之又少。如果将整幅山水看作一段乐曲,那么占比最大的、最详尽的虎丘旅游生活场景,毋庸置疑是其中的主要乐章,也就昭示着整幅画面的主题,即虎丘的游赏活动。
通过叙述重心的详略安排,谢将意境从单纯的自然风景转换为旅游赏玩的世俗生活,这种表达方式较之全景山水式的运营丘壑,显得更加轻松而具体,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突出旅游活动的内容,恰当地呼应此画“纪游”的主题和性质。
(二)空间视角的游移变换
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空间视角虽然没有西方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上的焦点透视那样准确、科学,但独立演变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空间构造方法。全景式山水画的早期阶段,郭熙提出了“三远法”,即高远、深远和平远的空间方法,这种方法更侧重于动态分散的观察方法和模糊性的视觉效果。“三远”的概念在山水画史的进程中被后代继承,之后得到黄公望、方薰等人的不断扩充与重述,此法最终成为传统山水画的基本空间法则。在纪游的意境构建过程中,这种观看方法更多地被运用在对局部景观的折叠和展开上面,能够突破视觉经验的限制,以游览讲述的姿态呈现场景的连续性。
谢时臣《虎阜春晴图》运用此法,使观看者不必限于山石树木的遮蔽,能够深入每一处景致,在画面中获得叙事性的游观体验。画面近景可以细分成若干部分:首先,最下方的虎丘入口从稍微偏高的视角铺陈物象,展现了游人纷至沓来、树木葱郁掩映的场景;其次,视点跨越呼朋引伴的游客,经过平坦的入口和小桥,较为低洼的石台、凉亭、步道、房舍、树木、小池位列其间,呈现虎丘山腰地带的观景平台,中部左侧的院落建筑向斜上方倾斜,这在传统语境下的山水画中是对空间改变的一种暗示,表明已经进入一个深远的视角;最后,沿着台阶向上则是云岩寺与虎丘塔建筑群,按照现实中的空间秩序,虎丘塔院落所在的位置与中间部分凉亭的高度并没有如此明显的落差,显然这里作者并没有如实地按照现实空间叙述,而是有意将虎丘最高处的院落抬高,夸大了虎丘高低起伏的丘壑变化。
整体而言,整个画面的空间是无法按照视觉经验严密衔接的,它遵从的并非视觉法则和物理法则,而是一种自由的观照,遵从流动的游览体验,在不同的层次展开不同的情景,再将游览过程中的几个场景组织在一个画面里,描绘游人在不同区域进行不同的游览活动,全方位铺陈了虎丘旅游的盛况。
(三)蹊径线索的串联
上文所述的空间变换,不仅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奇趣,还是构建画面意境的必要手段,使我们的视野“流动着瞟瞥上下四方”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页。,产生可游可居的审美感受。这种空间意识是通过有机的空间组织得以实现的,组织和穿插每一处场景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将山间的“蹊径”(广义上并非仅仅指山路,也包括所有起贯穿作用的图式或物象)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山间“蹊径”的穿插、隐现、高低角度与开合等要素,将画面中看似没有联系的不同场景串联在一起,使观者的视线能够走入山水之中。
具体而言,《虎阜春晴图》最下端,通过小石桥和一条横向的山路引领我们的目光进入画面;沿一条山路向上延伸,攀上山腰的观景平台,绕到凉亭的背面;接着沿石阶直入山顶的寺庙群之中;最终又顺着一条白练状的水口瀑布,引导视点回到虎丘的内部。通过对比虎丘实际地形可以发现,虎丘从最下处山门开始,确实存在一条向上的阶梯路,竖直向上连接了几处院落;但是,这条路在现实中是很直的,一路贯通到山顶,而画中整条线路时隐时现,蜿蜒曲折,将整个虎丘的入山、饮茶、登山、过桥、赏景等几段场景有效而生动地连接起来。可见,这条“蹊径”凝聚着谢时臣对空间精巧的构思,看似松散,但在空间的关键转折处进行恰到好处的暗示,令我们的视点回环往复于多个意境空间局部,视角不断变动,使画面充满游观的意味。
总而言之,谢时臣对画面主体纪游部分的构思意念是叙述式的,并且是委婉有序的叙述,由此,一幅各个阶层市民的日常旅游图景便全面铺展在观者面前。
四、意境追求与审美理想
从画面表现上讲,谢时臣也与大部分纯粹的吴门文人画家一样,画作都有清淡、空灵的效果,无论是笔墨的形式语言还是题跋的表述,都透露着谢时臣抒情自娱的文人趣味,这点是无疑的。在谢时臣以《虎阜春晴图》和《虎丘图卷》为代表的一系列纪游作品中,用笔率意轻松,用墨则多用湿笔,继承吴仲圭、沈周一脉的文人画法。明代姚旅所作的《露书》中记载,谢时臣曾自题:“嘉靖壬子春仲,樗仙谢时臣戏作小景,各赋芜句,聊遣孤兴,不足存也。”可见,谢心中始终存在遣兴抒怀的审美追求。但在意境的营造方面,谢时臣却有着与吴门主流不同的主张。以《虎阜春晴图》为代表,谢时臣极力构建一个具有生活化意味的意境空间,将吴门山水画中的隐居情怀和清雅诗意落到了实处,与俗世中日常活动的情景适宜地结合起来。这种“雅”与“俗”的综合性和中间性特点,实质上构成了谢时臣纪游山水画真正的审美理想。
如前文所述,明代中后期旅游之风盛行,吴门地区虎丘一带更是已经成为市民旅游的重要景点,《虎阜春晴图》中虎丘一带的场景很大程度上是较为写实地再现了游人纷至的现实状态。由此,吴门传统的一般性主旨一下子被打破了,画面意境也脱去了单调的“雅”的色彩,包含了生活的精神。这样的意境营造过程极大地降低了吴门主流文人画家画面的文学性,而是从直观的现实出发,直接进行图像的转化,部分摆脱了清逸的文学、诗学内涵对纪游山水画的渗透,这点与吴门的文人画倡导者们大异其趣。
结语
综上所述,谢时臣因其贴近俗世生活的创作意念与明末以后的主流品评趣味不相容,逐渐被美术史的浪潮所淡化,最终作为吴门画派末流被彻底边缘化。然而,谢时臣在其纪游性山水的意境构建上却透露出值得追溯和研究的内容。其山水意境的构建方法,首先是用画面空间的详略安排来突出旅游活动这一重点叙事内容,接着通过空间视角的变换、游动和铺展呈现游观的画面效果,最后借助“蹊径”线索将空间串联起来,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谢时臣作品中具有世俗意味的纪游主题。这种意境与审美的追求最终呈现了一个较为真实亲切的生活场面,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雅,相比于吴门画派后期类型单一化、内涵片面化的文人画意境,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扭转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