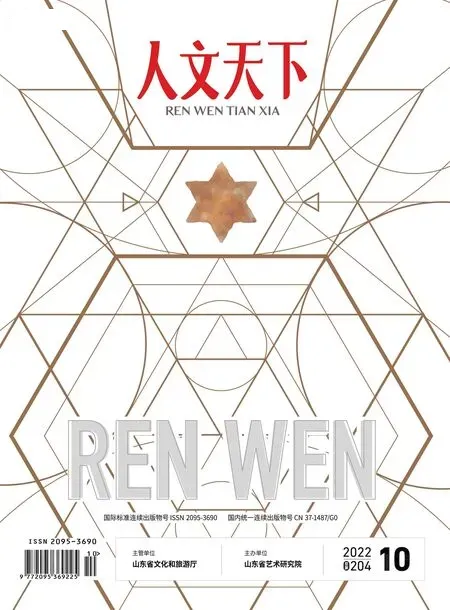《雍正十二美人图》中门窗元素的多重作用
■ 胡诗雨
20世纪50年代初,在紫禁城清宫藏品中发现一套共十二幅绢本设色的佚名画作,每幅画绘有一名处于典雅室内的衣着华贵的女子。尽管画上没有发现画家的落款,但在其中一幅名为《裘装对镜》(图1)的画作中,背景处用于装饰女子闺房的书法上落有三个别号,包括手书的“破尘居士”以及两方钤印“壶中天”“圆明主人”,这三个别号均为雍正皇帝胤禛登基前使用,而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身为皇子的胤禛接受了其父康熙赐予的圆明园,该园成为胤禛的府邸私园,故画中美人应与雍正有关。
《雍正十二美人图》共十二幅,分别名为《裘装对镜》《烘炉观雪》《捻珠观猫》《持表观菊》《倚榻观鹊》《博古幽思》《桐荫品茗》《烛下缝衣》《消夏赏蝶》《倚门观竹》《立持如意》《抚书低吟》。该画描绘了十二名女子,其中九名女子身处古朴秀雅的堂内,三名女子身处庭院之中,形貌昳丽,姿态各异。除了《博古幽思》(图6)外,其他画中的女子,无论是身处室内还是庭院,所在空间都被重重门洞、空窗或窗棂切割;同时,门窗大多直接承载画中女子的视线落点,月洞门外的覆雪幽竹与白梅,门槛上悠闲惬意的猫,窗外的喜鹊与双蝶,方形洞门外的竹石,等等,吸引着她们,在倾身注目间使这些单人女子肖像画丝毫未显刻板僵硬。可以说,门窗是《雍正十二美人图》中不容忽视的构成元素,它既是画面真实空间的构建者,也是画中人物精神世界的承担者,这两方面的融合与张力,打破了门窗在物质性与象征性之间的界限。下文将对《雍正十二美人图》中门窗元素的多重作用做进一步阐释。

图1-图12 佚名《雍正十二美人图》
一、透视与深邃空间感
从视觉层面出发,可以发现《雍正十二美人图》运用了西方的透视画法,特别是画家有意在人物所处的环境中增添门、窗或回廊,使画面摆脱宫廷正式肖像画营造出的平面性与庄严感。由于空间被门、窗、回廊不断切割,这些宽97.7厘米、高184.6厘米且与描绘的真人等大的人物作品,得以在细窄的竖构图中表现出深邃的空间感。西方透视原理在《立持如意》(图11)和《抚书低吟》(图12)两幅画作中清晰可见,建筑中各平面的边线随着空间的纵深,有意识地遵循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使画中美人身处更写实的室内空间。但这种透视技术的运用仍然不够熟练,如在《捻珠观猫》(图3)中,窗框尽管随着所在墙面从左下至右上进行纵深,但窗框、台面与地面轮廓线却完全保持平行,仍然呈现中国传统界画中的透视表现。
透视法自明朝传入中国,虽然在此之前,元朝时期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就已对中国美术有所关注并留下相关记载,但真正的中西美术交流直到明万历二十年(1592)著名学者兼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才真正开始。在金尼阁神父编的一本拉丁文集内,利玛窦写道:“中国人广泛使用图画,甚至工艺品上也用图画。但是他们的绘画技能,特别是雕塑制作方面远远比不上欧洲。他们没有油画知识和透视知识,因此绘画缺乏生命力。”①转引自邱春林编:《工艺美术理论与批评》(戊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3页。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雍正时期,欧洲的远近透视法和光影明暗法激起人们将之用于艺术创作的好奇,这为中国绘画传统带来异域新风。康熙皇帝对西方绘画新技艺尤其着迷,他曾要求耶稣会选派一位精通透视画法的专家,连同一位彩瓷画法专家到北京来。甚至在雍正七年(1729),时任内务府总管同时也精通西方数学的官员年希尧在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卷带插图解说的画法几何著作《视学》。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中略微不太熟练的透视中,也可发现那一时期的画家对西方技法的借鉴。
二、透漏性与女性空间建构
除了门窗在透视下呈现纵深感外,其自身的透漏性也使画面空间被不断分割与重组。由于《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有大量园林建筑月洞,即在墙垣上开出空宕,其透漏空灵的特质在画中得以呈现。几乎所有画幅都在美人身后以门窗或回廊的形式展现另一重空间:如果主体人物身处室内,则透过其身后门窗或回廊显示室外的庭院景观;若身处庭院,则透过远处门洞或回廊展现亭台楼阁的室内一角。因此,由于空窗与门洞带来的透漏感,足以使观众的视线往返于画中所构建的室内与室外多层场景,观众将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美人”不是被定格于平面,而是在一个有幽竹、白梅、奇石、瓷器、字画、古籍卷帙、案椅床榻、亭台楼阁所构建的力求真实的空间中。即使是没有绘制门窗的《博古幽思》一幅,画中陈设各种器物的多宝格也被画家分成两段绘制,使二者垂直交接,以夹角的方式在绘画平面中切割出空间感,而右侧的藏柜以斜45度角向观众延伸,制造出空间随之延伸的想象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营造真实空间感并不是历代仕女画必然追求的目标。在历代中国传统仕女画中,对主体人物身处的场景营造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背景空无一物,只有孑然独立的女性形象;二是背景中有部分器物或植物,但未设置完整、具体的场景空间;三是背景清晰交代出完整、具体的场景空间。由于唐代社会开放自由的女性观,以及唐代绘画品评专著《历代名画记》和《唐朝名画录》对仕女画的极高评价,丽人形象自唐代“开始脱离特定叙事框架和伦理目的,其姿容和装束成为绘画表现的主旨”①[美]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7页。。而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在“论妇人形相”一节,提出“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②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王其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尽管其将仕女画描述为衰落退化的画科有失偏颇,但也可从侧面看出,人们对仕女画的欣赏更多是从女性的形象特点如面容、体态、眉眼、发式以及线条设色的描绘方式等方面进行欣赏,场景环境作为对女子姿容起辅助的元素,画家则可以不用耗费太多心力与笔墨进行描绘。
因此,仕女画中场景营造的前两种方式在历代绘画中大量出现:第一类在于突出主体人物风姿容貌“特写”而简省一切器物和场景,仅描绘仕女袅袅独立之态,如元代周朗的《杜秋图》、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明代吴伟的《琵琶美人图》等;第二类则在前类基础上依照所需增添部分物件以实现组织情节、衬托画面氛围的构图样式,如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五代周文矩的《宫中图》、明代吴伟的《武陵春图》等,但仍未设置完整、具体的场景空间。
而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环绕美人所构建的极为充分的场景空间,画中绘制的物件,如天然几、床榻、翠帏、诸集、韵书、香几、花樽、金炉、香奁、笔、砚、金炉、古瓶、纨扇、棋枰、竹箫、铜镜、妆盒、绣具、西洋怀表、浑天仪等,多达数十种。《雍正十二美人图》绝不能被简单看作以个体人物形象塑造为主旨,用于展现女子面容、体态、眉眼姣好的容貌特征与身姿仪态,而是建构出在具体文化和社会条件下整体的女性空间。画面中蕴含着建筑环境、文玩摆设、花草植物、叙事情节、象征性结构等各项视觉元素,而这些元素以门窗为媒介在重重空间中共存与互动。
以《抚书低吟》(图12)为例,在画面最前端所表现的建筑空间中,美人右手持书卷,左手抚弄饰带,低头作沉思状,上半身斜倚在桌前,身后挂着一件书画条幅,上半截是展开的水墨山水画,下半截绘有一片带题诗的树叶,这是一个观众视线得以触及的开放空间;而美人身后的其他空间由门槛阻隔,上方悬挂的幔幕显示这是更为隐秘的内室空间;更远方从月洞中透漏出庭院中的修竹。因此,画面空间被分隔为三层,各自承担着不同作用——展现闺房文墨之气的开放空间、未对观众开放的私人空间,以及“竹”所代表的庭院空间。画中的门与窗洞既使物质上本该具有平面属性的绢本在绘画空间中被区隔为三层,同时门窗也是串联这三层绘画空间的媒介,其透漏性使这三个空间不再全然隔绝,而是被观众的视线沟通。也就是说,身于前室正中的主体人物首先成为观者凝视的对象,而内室与室外庭院虽然不是画面焦点,但通过门窗制造的空间指引观众将视线延伸而至,全然掌握画家构建的整个女性空间。
观照美人日常起居空间而非仅仅品评其体质、容貌和衣饰,这在明末清初之际得到重视。明末清初人卫泳在《悦容编》中专论美人的各项标准,其在“葺居”一节中为理想佳人描绘了这样的环境:“美人所居,如种花之槛,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宝栏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纵无金屋以贮,亦须为美人营一靓妆地。或高楼,或曲房,或别馆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与闺房相宜书画。室外须有曲栏纡径,名花掩映。”①虫天子编:《中国香艳全书》第1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29页。卫泳具体而微地罗列居住环境和其从事的活动,作为品评绝世佳人的两个重要条件,这种对美人日常生活空间性的观照,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三、界框与视觉次序
1986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在清宫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了雍正皇帝于雍正十年(1732)下的一道特别诏令:“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钦此。本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杆十二根。”②朱家溍:《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紫禁城》1986年第3期。这件档案中所说的作品即是《雍正十二美人图》,根据雍正皇帝的保存要求可知,这些仕女画像最初装裱在一架屏风的十二扇屏面上,“围屏”一词暗示着这架屏风是一个多折屏风。这些扇面高184.6厘米,观众在观看画中女子时应当几乎与视线持平,我们不妨推测,这种巧妙设计来自于作者在创作时所考虑到的观者视角。
《烘炉观雪》(图2)、《捻珠观猫》(图3)、《烛下缝衣》(图8)、《倚门观竹》(图10)、《立持如意》(图11)、《抚书低吟》(图12)六幅画作都将主体人物设置于门洞或空窗中,由此观者对画中美人的凝视不是透过冰冷的画框直面美人,而是在门窗后对美人闺阁之态的观望甚至“窥视”,在视错觉上消磨了现实空间与绘画平面之间的距离感,而是成为现实空间与绘画空间之间的对话。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同标准的空间、时间、观念和行为的“真实”之间,边框创造出必要的边界与转换。
“界框”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框景”手法中格外有所体现,由于门窗自身透漏性的造型特点,常作为借园林他处之景的“画框”,让几处不同的景物相互渗透以增添园林空间的层次与联通。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这一艺术手法也得到运用。同时,尽管《持表观菊》(图4)、《桐荫品茗》(图7)两幅画作没有将美人置于门窗之内,相反则是身处门窗正前方,门洞与空窗也完全发挥其“界框”作用,即以其圆形或矩形边框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元素框定而出,形成视觉上不同画面元素的“等级关系”,强化了画面主体人物相较于其他场景器具在观众视觉次序上的优先地位。
绘画中对于门窗的“界框”作用在艺术作品中不在少数,如清代张震《美人图》、清代叶道本《雪窗仕女图》、清代《乾隆帝妃古装像轴》,以月洞、空窗与窗棂为媒介沟通绘画空间与现实空间,如舞台般将主体人物呈现而出;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与《宫女游园图》,以及清代焦秉贞《仕女图册》等,画中的亭台楼阁除了辅助仕女生活空间的场景构建之外,也以门窗不断框定出仕女们齐聚一起弄琴起舞、赏景嬉戏、披图展卷等,画家试图将这些活动设置为视觉重心。此外,在一幅同样与胤禛有关的纸本作品《胤禛与福晋、格格》(图13)中,尽管五位人物体量没有太大差异,但胤禛作为唯一出现于月洞内的形象,与其他女性角色进行区隔。

图13 佚名《胤禛与福晋、格格》
四、内与外的意蕴交互
在圆明园中有一处景观“万方和安”,其中有胤禛题“山水清音”“滌尘心”等匾额,在《消夏赏蝶》(图9)中可以看到“有清音”和“居士书”的字样,再联系整架屏风最初立于圆明园,可以推测画中可能表现胤禛当时的私人园林中的场景。黄苗子先生即提出画中的建筑、园林、家具是根据圆明园所画。①参见黄苗子:《雍正妃画像》,《紫禁城》1983年第4期。
同时,胤禛本人对屏画的绘制应当也有所参与。在其中一幅《裘装对镜》(图1)中,美人身着裘装对镜自赏,其后露出的屏风一角清晰可见书法作品。“这两行多行草体书法,笔致与其在《胤禛像耕织图册》所书诗完全一致,题款则与其《行书金刚经》相同,可知画中的书字都是他的亲笔。”②杨新:《<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并且,为追求画面真实自然的效果,使御笔的书法作品被物件遮挡,一方面,宫廷画师不可能在未经帝王允许的情况下破坏御笔;另一方面,这种创作必须事先与画师沟通,胤禛才能在预留空间中书写。因此,屏画中的“创作构思和部分制作上,是画师与胤禛合作完成”③杨新:《<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既然胤禛参与绘制及构思过程,那么《雍正十二美人图》立意的主体性分析就需要放在当时还身为皇子的胤禛身上。他在美人图中构思的场景与形象想表达什么主题?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呈现其意图?
《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出现了多种花草植物——水仙、白梅、竹子、迎客松、菊花、佛手、灵芝、梧桐、荷花、萱草、玉兰、香兰、牡丹、月季、桃花、石榴花,仅有竹子这一意象出现在全部十二幅画作中。在屏风的十二幅画中,《烘炉观雪》(图2)描绘了单簇葱翠的修竹半掩在深院的入口,画中女子正从门后探出身来作观赏状。高耸的竹茎贴在画面右边,而这位窈窕女子则扶住左边的门,“它们对称的位置和相互呼应的关系暗示了语义上的可交换性”④[美]巫鸿:《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文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院门即为这种交换性提供媒介与可能。
联系胤禛登基前作过一系列关于圆明园的诗,其中有关于竹的一首诗《竹子院》:“深院溪流转,回廊竹径通。珊珊鸣碎玉,袅袅弄清风。香气侵书帙,凉阴护绮栊。便娟苍秀色,偏茂岁寒中。”⑤转引自朱家溍、李艳琴:《清·五朝<御制集>中的圆明园诗》,《圆明园》学刊第二期。诗中的娟秀之气反映出胤禛对院中景致赋予了更多女性特质,无论是在精英文化还是在大众文化中,“玉”都是对温润仁厚、秀外慧中女性的常用比喻,“玉肌”“玉颜”这样的字眼可以用来描绘美女,胤禛在诗中即用到了类似女性化象征的“碎玉”一词;同一联对仗中所使用的“清风”,也经常用来表现女子恬静美好的形态。再看各自的定语“珊珊”和“袅袅”,明确表现女性化的衣裙玉佩的声音、轻盈舒缓的仪态,可知“碎玉”和“清风”所暗示之物不为他者,正是女性。就像巫鸿曾指出,胤禛的诗中“很多诗意形象都具有双重功能,既描绘风景特征同时又把它拟人化”⑥[美]巫鸿:《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第179页。。在这种文学与语言传统中,胤禛诗中对女性意蕴的观照可以进一步肯定。
作为《竹子院》这首诗的描绘主体,传统中竹子象征虚心有节、忠贞不屈、高风亮节等精神品质,并且一般用于臣子或文士等男性角色,而在胤禛的诗中,则用于比附一位深居闺阁且腹有诗书的女子。之所以对传统象征性进行转换运用,将习惯上的男性象征符号转为体现女性意蕴,在于圆明园作为皇子的私人园林,可以在其间寄放胤禛慵懒闲适的私人生活,暂时远离种种勤政忧民的世俗职责与忧劳。在传统社会中,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往往只与男性角色所对应,而男性角色在政治场域“治国”“平天下”之余,回到“家”的场域才更多面对女性角色,女性柔情和泰、窈窕淑良的行为与德性是“家”这一相对私人化场域的存在依据。因此,若要在艺术中塑造出与世俗职责、政治事务相对立的私人生活空间,女性角色所具有的象征性由于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被运用。
如前文所述,胤禛将植物诗意的形象集中在画中外表、动态、情绪都极为写实的丽人身上,而这深刻的主题与画面中女子形象产生意义交互,正是通过门与窗所制造的空间加以呈现。门窗蕴含一定的精神内涵,在现实园林建筑中多有体现,如拙政园中嘉实亭后墙上开有一窗,窗外幽竹摇曳、峰峦叠翠,窗旁有联映照游者心境:“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驻足在此,应当心旷神怡,门窗正是以匾额与对联的文字形式使自然景观增添更多的人文意蕴。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也有近半数的画面中有胤禛亲题诗文以烘托意境,但作为绘画作品,更直观的方式是以图像来渲染这文质幽古的氛围。例如,在《持表观菊》(图4)中,蓝衣女子坐于桌前,冷色调的衣衫凸显其清隽姿容,身后的蓝色围帘掀起一角,只为展现围帘背后纵深室内空间中洞开的窗框,而窗框里正露出室外的茂林修竹,同为四君子之一的“菊”盛开在女子斜倚着的桌上,遥遥相对。窗不只是画中真实建筑空间的营造,更兼容着暗示人物德行品性的文化意涵,构建出另一重空间。
《雍正十二美人图》以人物种种赏景、品茗、抚书等娴静雅致之事,呼应门窗外另一空间中梅、竹、兰、蝶等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意象。类似的意义呼应或对比关系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出现。例如,“海上四任”之一的任熊在《大梅诗意图册之六》(图14)中描绘了一位临窗而立的贵族妇女与一位走街串巷的穷困贩妇,以窗棂内外贵族小姐与劳动妇女两相对比形成巨大反差,画面上的题字为:“东家大姑珠翠头,贩妇竿挑一裈虱。”图像与题跋“揭示了贫与富的差距,以此对社会的不公进行批判”①王宗英:《中国仕女画艺术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门窗内外不同意象发生意义交互,辅助构建画面内涵的丰富性,而这种表现力正是通过门窗创设出的多层空间加以实现的。

图14 任熊《大梅诗意图册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