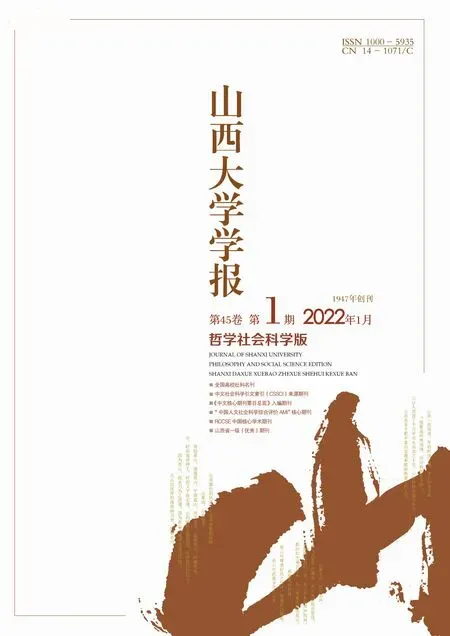“味”的变奏与传统艺术的审美之“味”
梁晓萍
(山西大学 音乐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国人极爱讲“味”,自古及今,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均可以“味”论之,评论一道菜肴好吃为“有味”,赞扬一个人会穿衣说“有味”,一个人讲的话动听委婉被誉为“有味”,表情丰富含蓄也被誉为“有味”;“味”有性别之分,有男人味,女人味;亦有身份之别,有教师味,学生味儿;“味”有地域之殊,有南方味,北方味;亦有季节之异,有春天味,冬天味,“中国俗语中此一‘味’字,真是大堪深味,亦可寻味无穷矣。能知其人其事之有味无味,此真中国人一番大道理,亦可称是一项大哲学”[1]101。艺术活动中,诗书礼乐,琴棋书画,悉可以“味”誉之,滋味、余味、韵味、至味、淡味、逸味等,都曾被古人用来论及艺术之妙,故在艺术中穿行,可以寻味、赏味、品味、玩味,为艺术所吸引,亦可尽情体味、研味、咀味、耽味。传统艺术之味,因人而异,因物而殊,因地而别,因时而分;含情则为情味,蕴意则有意味;情真则有真味,意假则含假味;为佛所化则有禅味,为道所化则有至味;诗有诗味,画有画味,乐有乐味,舞有舞味;文人之作有“书典”味,民间之作有“蛤蜊”味;豪放之作有狂味,婉约之作有柔味;味有层次之分,有高下之别;味有浓淡之殊,有止余之异;中华传统艺术中的“味”既有其区别于西方艺术、当代艺术的相对稳固性,又具有迎时而通变的开放性,此一“味”字,学问颇深,讲究颇多,能够谙熟其人其作之有味无味,明晓其书其画之味深味浅,何种风格,缘何有如此之味者,绝非凡夫俗子,当至少有哲学自觉之思。如是,则此一“味”字,因何而来,如何演进至艺术美学之域,其核心价值如何,对我们当下的艺术具有怎样的启迪,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探究。
一、从口舌之“味”到政治之“味”

人总是不满足于动物性的本能体验,总是朝着理性的精神之思不断前行。随着古人对“味”之体验的增加,人们将感官之味以“五味”加以提炼,并将之与“五行”这一古人对宇宙构成的朴素认识紧密关联,从而使生理层面的感官体验拓展至心理层面的精神体验,也使这一表达感官感觉的形而下概念部分地具有了形而上的特征。古人视“金、木、水、火、土”为物质世界存在与发展变化的五种基本要素,是为“五行”,而“五味”则为与此五种要素分别对应的基本属性,《尚书·洪范》最早将“五味”与“五行”相联系,其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8]119孔安国云:“咸,水卤所生也;苦,焦气之味也;酸,木实之性也;辛,金之气味也;甘味生于百谷也;是五味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并行于天地之间,故《洛书》谓之五行。”[9]188(《尚书正义》)与“五行”相连的“五味”之“味”,尽管依然未脱开咸、苦、酸、辛、甘等身体的直观感受,然其所指已通向人之身体以外的构成世界的一般物质与由物质构成的一般世界,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意蕴。这种在俯仰天地中“近取诸身”以通神明、类万物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古人借感性之物以把握抽象之世界、借感性经验以表达理性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品格。《左传·昭公元年》进一步从“气”的角度论及五味的来源:“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6]272,认为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自然界的现象为五味、五色与五声生成的基本根因,从而将“味”与宇宙自然关联在一起,“五味实气”[10]347的这种理解使“味”成为一个可以以形而下的具体物质把握形而上的自然规律的语汇,预示着“味”这一感官体验跃出感性而向理性衍化的可能性。
感官体验的“味”不断开掘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理性之思,跨越了具体的生理感觉界限而进入到更为宏阔的文化领域,人们以“味”论政,以味论言,以味论乐,直至以“味”论道的哲学之思,这些都为以“味”论美做了充分的准备。据《吕氏春秋·览·孝行览第二·本味》记载,早在夏朝,伊尹对商汤已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以“味”论政的言论:“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5]103伊尹从选食材、控火候、数烧制的烹饪之术谈及“口弗能言,志弗能喻”的“鼎中之变”与“久而不弊”的“至味”,借此而论及的则是天子行仁义的为政之道。这种借“味”论政之法在先秦典籍中比比皆是,“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6]300,认为饮食之“味”影响政令;“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10]347,以“和五味以调口”的重要性和“味一无果”的客观现实,论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为政之道。除了以“味”论政,先秦还以“味”论言,“币重而言甘,诱我也”[6]10,以“味”之甘譬、“言”之动听,听出了秦穆公在“言甘”背后的杀气;《国语·晋语一》曰:“又有甘言”[10]186,《诗经·小雅·巧言》曰:“盗言孔甘,乱是用?”[11]213此二语均以五味中的“甘”喻指甜言蜜语;又《易传·系辞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12]412,强调心意相同的言语如兰花的香味般沁人心脾。以“味”论“乐”在先秦文献中也常有记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6]333,晏婴认为“声亦如味”,谐和五声便如调匀五味,可以平其人心,和其德性,成其政绩;“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3]437,“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13]425,《乐记·乐本》中关于音乐的理解同样采用了以“味”论乐之法,继而论及音乐移风易俗,成就政事的社会功用;又《论语·述而》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4]89,此语既以“味”之美譬音乐之美,又以“肉味”之美与《韶》乐之美作比较,强调孔子自觉趋贤的良好品质。不过,需要指明的是,上述以“味”论言、以“味”论乐,最终均指向了政治的宗旨,可见在先秦时期,当“味”开始跳出饮食感官的直接体验而跃向更为丰广的人生体验时,直接或间接以“味”喻示政是“味”最为常见的一种意蕴旨归,然而,这种“味”尚未脱开“物质”的牵系,还未真正抵达形而上的哲学之思,真正将直觉感性之“味”提升到理性哲学之“味”的是老子。
二、从哲学之“味”到艺术美学之“味”
“味”在《老子》中共出现了三处四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15]39,“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15]17,“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15]211,这四个“味”共有三种内涵,即五味、无味、味无味。“五味”当为先秦时已经为人广泛所用的“五行”系列概念之一,与“五声”“五色”一起,均因被视为人之感官之欲的代表而成为老子批判的对象。“五味乱口”[16]513,物至则返,诚如“目将眇者,先睹秋毫;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口将爽者,先辨淄渑”[17]138,其中蕴含着的道理极其相似。“五味”为老子所鄙夷,真正为老子所推崇的是“无味”之“味”和“味无味”之举,这两处“味”,既不再拘泥和纠缠于具体的物质之味,也不追求以具体的感性之物揭示理性的生活世界之规律,而是直指老子哲学的本体之“道”的“无味”之特征和品味的悟道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创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道论哲学体系,成为当时最成熟、影响最大、且唯一以道命名的道论思想,其在诸子百家中的作用极大:“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本。”[18]27老子之“道”,取代了以往具有意志、主宰、人格诸多属性的“天”,成为一切的根源与归宿,其遵循的是“无为无不为”“有无相生”等价值原则和运行法则;老子之“道”,也跃出了社会、历史、伦理等层面,将思想视野从天地自然的现象领域提升至探讨世界本原、依据等本体层面,“无味”是老子“无”哲学整体框架下的一个重要支脉,是“无为”家族相似的重要成员。“无味”即“无味之味”,从内涵上讲,它并不否弃世间之“味”,是包含着“有”的味,然“无味”并非强调它是“味”的一种类型,而是强调形上之“道”的“无”之特征;而品“味”则需以“无味”为价值前提,遵循“道”之“无味”的价值原则。因需按照无味的原则去品“味”,故所谓“味无味”,即“味”道之“无味”之味,强调以“味”的方式体认“道”之“无味”的特征,由此可见,老子的“味”已基本脱离了形而下的依附,成为形而上的理性抽绎。这种理性抽绎,将“道”之最原始、最单纯,也是最高级、最深刻的“味”揭示了出来,从而成为被后世推崇的“至味”“足味”“大味”:“至味必慊”[16]1175,“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16]1426,“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19]3578。“无味”才是最高境界的道之“味”,“味无味”才是最好的体道方式,道家这种“味”的哲学思想以其以虚为本,虚中带实,虚实相生的思想气质孕育了中华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趣味,为“味”后来进入审美领域奠定了坚实而独特的哲学基础。
先秦时期逐渐向物的客观世界,尤其是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双向延伸的“味”理论最终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脱离了形下特质的牵绊而跃升至形而上的哲学之思,并在儒、道文化的浸染下,在名词的层面具有了“无味”“五味”的主要内涵,在动词的层面则开启了“品味”的接受美学先河,然这一时期的“味”还停留于体验-哲学的层面,意味尽管已相对丰富,然还未及至美学层面。经汉直至魏晋时代,随着“文的自觉”的全面开启以及人的自觉意识的渐次明朗,“味”才第一次进入艺术美学的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先是以“味”论玄,然后才有了以“味”论文,以“味”论诗,以“味”论乐,以“味”论书法,以“味”论画等审美理论之花的遍地开放,并以“滋味说”构成了魏晋时期“味”美学理论的一次盛景。
大体而言,老子之后,推动“味”进入审美领域的有两个重要的哲学基础,一是对老子“味”之思想有所发展的《淮南子》,一是魏晋时期崇尚老庄以调适儒道以使二者兼融的玄学思潮。
汉初《淮南子》对老子“味”思想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对其“无味”思想的坚持。其视“无味”为“道”的基本特征,“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16]756;其次,继承老子对“五味”的批判观点,倡导淡然之“无味”。《泰族训》曰:“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16]1413-1414除了继承,《淮南子》对老子的“味”思想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它使“无味”与“五味”发生了实质性的关联,《原道训》曰:“……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16]59-60,“道”生万物,则“道”之“无味”为“五味”之因,“五味”因“无味”而形,“无味而五味形焉”,从而在以“道”为本体的逻辑前提下将“无味”与“五味”作了调和,使“无味”成为比“五味”更高一层的本体之“味”,《淮南子》的这一思想对此后的“无味”论以及中国传统艺术之“味”美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玄学是在汉末儒家经学衰微,士大夫的精神家园——儒家正统信仰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下,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修齐治平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所进行的一种创新性的哲学反思,其中由“言能不能尽意”这一论题而展开的“言意之辨”与“味”的艺术美学之旅的关系甚为密切。萌芽于先秦时期的言意关系之思在魏晋时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王弼的“得意忘言”观对“味”艺术美学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周易注》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20]251这段注中,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王弼将言、象、意分为手段-能指(言/象)与目的-所指(意)两个层面;其次,承认言可以明象,象可以出意,凭言/象可以尽圣人之意;再次,在言/象与意的关系中,“意”才是最终需要存留的目的;第四,存言非得象,存象非得意,故想要获得“意”,必须舍象忘言徒留意,所谓“得意忘言”。
这种得意忘言的方法,使汉代注解式的章句之学一变而为魏晋以来玄学“体味式”的研读之法,不再忽略整体而拘泥于一词一句,而是宁肯“不求甚解”,也不胶柱鼓瑟,因词害义。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便有了魏晋时期以“味”论玄的新思路。对于难解之《庄子》,诸名贤孜孜以“钻味”之法并不受魏晋人欢迎,其虽有所获,然未及支道林标新立异,二者理解不同,高下有异,缘于诸名贤过于“钻”,而支道林则灵活体味[21]192。以“味”论玄,得意忘言者,这一时期的典籍中尚有不少,“引身深山,研精味道”[22]122;“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23]438;“郭泰字林宗……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21]4;“研味《孝》《老》”[24]368……“研精味道”“滋味典籍”“处约味道”“研味”等用法的广泛运用,凸显了魏晋时期以“味”论玄,玄思体味以“得意”之方法的普遍性,而这种“味玄”“得意忘言”的思维方法既激发了艺术创作挣脱旧有框框的创新之力,也使艺术美学之“味”呼之欲出,诚如于民所指出的那样,在艺术审美中,“味”并非立即表现于一般的山水诗中,而是经过玄学与文艺结合这个环节,“直到后来,才去其玄而追其言外之意,与一般审美上的虚与实,情与理的关系相关联”[25]228。
人的感知永远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对无限的向往因之成为老子哲学“无味”“味无味”的迷人之处,并在《淮南子》中将“无味”与“五味”统摄于一起,而魏晋玄学“得意忘言”的体味方式再一次以哲思的方式表达了古人对于无限的追求,也成为艺术“味”美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魏晋时期,陆机第一个直接把“味”运用到艺术理论中:“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26]130陆机指出,有时候文章写得清新空灵而柔婉简约,没有余杂之辞,浮滥之调,然却就像没有调料肉汁的餐饭般过分平淡,又像熟丝制的琴演奏的清曲过分质朴,可以说雅致却无法说艳美,这里,陆机借《乐记》中“遗味”的比喻,把“味”首次引入诗文理论当中。之后,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中“味”的运用不仅数量增加,指意也更加明确,全著共二十处“味”,仅两处指生理感官之“味”,其余皆用来指诗文富有审美特色的“味”以及品味。“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24]25,“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24]45,“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24]185,“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24]333,“深文隐蔚,余味曲包”[24]459,以上诸“味”,均指诗文或深或雅,或长或多的味道;“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24]61,“繁采寡情,味之必厌”[24]372,“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24]452,以上之“味”,则为体味、品味之义。可见,在《文心雕龙》中,“味”已成为衡量诗文之美的一个重要标尺,成为与文艺活动紧密相关的一个美学术语。
魏晋时期,“味”还被用于品人论言,品乐、书法以及绘画等各个方面,刘邵《人物志·九征》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27]2《人物志》是魏时为助推九品中正制的实行而创作的一部理论著作,其依据人自然的血气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形貌、声色、精神、才能、德行等综合质素进行品级分类,对人的品第,以中和为最高,认为圣人平淡无味又聪明有才,平淡之意的加持,一改往日品人时德性的单纯考量,改为顾及个体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形声境界,这种转变体现出来的是对人的一种审美观照。至《世说新语》品人论艺,“味”的审美意味更加突显:失却法虔之后的支道林,犹如失却钟子期的伯牙般精神颓丧,“风味转坠”,风度尽失[21]555;为王濛写诔文的孙绰认为彼此因“同此玄味”而交,故心犹清澈之水[27]728;豪爽的桓温之语很有余味,令散座之人“追味余馀言”[21]520,这些“味”均以审美之眼光打量人及其趣味与言行。
如上可知,以“味”论艺,尽管在孔子闻《韶》而不知肉味的故事中已露出审美的端倪,然直到魏晋南北朝,“味”范畴才摆脱了其中的附加指向,确立了其对于艺术的审美视角及其作为审美存在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味”理论代表是南朝宋山水画家宗炳的“澄怀味象”说和南朝齐梁间的批评家钟嵘的“滋味说”。一生遨游于山水之中的宗炳,在其《画山水序》最先论析了山水“质有而灵趣”的审美价值,指出观赏山水万趣,引发无限情思,不过“畅神”而已,这种山水畅神观,一改以往的山水致用观与山水比德观,仅视山水为以其形色、精神而使人产生愉悦之感的自然之物。以此山水观,宗炳提出了“贤者澄怀味象”[28]144的著名观点,“味”即体味,是对“象”的凝神静观以及在此静观中获得的审美享受,“山水以形媚道”[28]144,故盘桓于山水,绸缭于形色,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师于造化,应目会心,便可领略山水之味、自然之道与圣人之意。“澄怀味象”说通过“味”前的虚静心理,涤荡了各种杂念妄想,通过对“味”的对象——山水身份的重新界定,排除了强加在山水身上的实用功能,又通过“味”这一对审美对象的凝心怡神而自然抵达“味”的宗旨之“道”,从而以真正的同情之心成就了自然山水的独立之美,也成就了自觉自由的审美人生。
钟嵘的“滋味说”是针对当时诗坛堆垛典故而无病呻吟、奢求声律而缺乏真美、理过其辞而淡乎寡味等不良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审美主张。南朝齐梁时期,在创作方面有两种比较严重的倾向:其一是过分追求文辞、声律等形式,以致内容空洞,缺少真情;其一是崇尚虚谈,过分追求玄理,以致理念过盛,感性缺乏。这两种倾向都使诗歌艺术缺少了应有的“味道”,针对上述问题,钟嵘标举滋味说,强调诗歌当耐人寻味,“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29]10。钟嵘的滋味说上承老子、陆机之“味”,启迪了司空图、苏轼、王士祯等后来人关于“味”的理解,从而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文”与“人”均走向自觉的时代把“味”推上了纯艺术美学的发展轨道,使艺术活动打破了传统儒家以美刺讽喻、比德论善为中心的教化路径,而以悦情悦意的有味之味为艺术创作的追求目标,以品鉴滋味为艺术接受的审美宗旨,“创作了纯审美的批评方法”[30]9,使“味”成为中华传统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范畴。那么,艺术审美之“味”具有哪些重要的审美特征呢?
三、传统艺术之“味”的审美特征
至魏晋南北朝通过“余味”“澄怀味象”“滋味”说等命题使其审美特性得以确立的“味”范畴,其主要的特征要在唐宋元明清历代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的不断运用、反刍与变奏中,通过与独具中国特色的和、意境、韵等其他审美范畴的相融相揉,相兼相济,才逐步稳定、丰富与深化。整体而言,中华传统艺术之“味”主要表现为以有限达无限、化浓烈为平淡、虚心以悟道三方面的审美内涵,集中表达为余味、淡味、体味三个关键语汇。
其一,以有限达无限,集中表达为“余味”,是艺术之“味”在广度上的审美追求。“余味”一词最早出自佛学著作,刘勰最早将其运用到诗歌艺术美学领域,用以传递言简意赅、含蓄深远的审美特征。言语是有限的,而人的情感却是无限的,“意无穷”而“言有尽”是人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永久困境,延展至其他艺术同样如此,线条、色彩、音符、动作、表情,都有其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而对情感的全部、自由的表达却是人类永恒的渴望,于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便成为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追求。譬如食之“味”,有“初而甘”与“卒而酸”之分,后者是“余味”;荼之味,有初而苦与后而甘之别,后者为“余味”,对于诗歌,有初而文辞声律,再而言外之意,后者是为“余味”,有余味是中华传统艺术的审美宗旨,诚如杨万里所言:“夫诗何为者也?曰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31]3332这段文字中,杨万里以比喻之法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去词去意而诗有在”,一首诗歌,“词”与“意”都被去掉仍有东西在,这在的东西便是“味”,是最终留于口舌的“饴之酸”和“荼之苦”般的艺术之“味”,这段论述给“余味”以很好的理论阐释。那么,如何方可有“余味”?对于艺术,含蓄方可有味,“诗贵蕴藉,正欲使味无穷耳”[32]794,隐蔚之作,方有余味,“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24]25;“元、白、张籍诗,……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若收敛其词,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33]7。也即留有空白方可有味。南宋画家马元,他的画在构图上别具一格,多以“计白当黑”的手法结构画作,故其画画面简洁洗练,留白面积较大,给人以虚实相生和在想象中冲突现实拘约的审美享受,这就是“余味”。《琵琶》《西厢》,其中故事,无非布帛菽粟,然自元至清,一直为人传唱,原因就在于曲之背后,是为观者留下的可以因人因时而变的、可填补想象的空间,不同时代的人观之,均会获得咀嚼不尽的滋味,形成各自的审美享受,这就是“余味”。清人张岱指出其时传奇“但要出奇,不顾文理”之病时,亦以《琵琶》《西厢》为例,指出此二作并不怪异,然“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34]143。不仅诗歌、戏曲,中国古典音乐、舞蹈、建筑、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强调“余味”无穷的审美效果,一曲《高山流水》,一段公孙大娘剑舞,九曲回廊,《富春山居图》,哪一种艺术不因其留有余香的“味”而令后人无法释怀。“味”至在司空图,强调“味外之味”“味外之旨”,使“余味”的理论探索更进了一层,使“味”在长久性、滞留性的基础上又具有了多层次性,使对“味”的理解更加立体,更加丰富,也更达至无限。
其二,化浓烈为平淡,集中表达为“淡味”,是艺术之“味”在浓度上的审美追求。先秦老子的“无味”观已蕴含了淡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先秦时期,世俗之人常以“五味”之味为美味,以无味之淡味为非美,老子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并不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并呈现为具体的感官属性,其“味”乃“无味之味”,把无味当作味,是“以恬淡为味”(王弼语)[35]169;此“无味”并非真正的没有味道,而是一种薄味,一种宛如无味的平淡之味,这个“味”也就是自然之道。这里,“淡”在貌似无味中氤氲着“道”之真味,可以说,对“道”的感悟是获得“淡味”的内在依据,“淡味”就是“道”的本质特征,无而生有,有无统一。老子在哲学层面的“无味”“淡味”被后人延展为一种平淡之美,成为传统艺术,尤其是宋代以来人生与艺术审美的一种主要范式。宋代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典范代表,彼时,一方面,儒家文化以理学之名重归核心地位,终极精神信仰在儒释道的积极融合中得以重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空前高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836成为一代士人热情的呼声,另一方面,被宋人主动选择的道、释文化也在文人的人格与审美旨趣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形成了宋人尚理、尚淡的价值取向,恬静淡雅的主体审美精神,“简淡”“冲淡”的艺术表达,以及“淡”美的审美风尚,对于“淡味”的偏爱成为宋人独特的审美标识。
苏轼是这种“淡味”追求的代表人物,也是“淡味”理论的重要建构者,绚烂之极的“平淡”之味是其最为欣赏的“至味”,“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28]282,“宋人赋予‘平淡’美以兼综儒、道并集成佛、老的精微机制,而苏轼则是将这一精微机制阐发得最为透彻的人物”[37]126。在《与二郎侄》中苏轼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38]710绚烂之极的平淡,“既雕既琢,复归于朴”[39]363,是一种具有“老境”的极致之美,其看似无味却令人回味无穷。苏轼还通过其艺术创作展现了“淡味”,今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枯木怪石图》,是一幅极富“淡味”的画作,画中没有茂密的树木,玲珑剔透的石头,代之而在的是枯萎的枝干,丑怪的石头;画面简淡明了,墨色简洁自然,然在盘踞的怪石与探身盘旋而上的枯枝背后,体现的则为强劲的生命力,膏腴丰美,意味无穷,诚如其所激赏的陶、柳之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28]282,这就是苏轼喜爱的“淡味”,也是宋人喜爱的“淡味”。这种“淡味”,上承老庄哲学之思,下启明清艺术审美,在明人董其昌论作书“淡之玄味,必由天骨”[40]592的书法论中,在袁宏道以趣所论的“水中之味”[41]463中,也在清人张萧亭“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42]144、袁枚“言之有味”[43]182的“味论”中,还在近代王国维“言外之味、弦外之响”[44]19的审美渴望中。
其三,静心以怡情,虚心以感悟,集中表达为“体味”,是对“味”获取途径的一种审美揭示,其既包括创作过程中对意味的获取,也包括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对意味的凝悟。与崇尚理性因而在审美中也强调理性认识不同,中华传统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体味”旨在“味”,然通向“味”的路上,凭借的却是形象,讲究的是“澄怀味象”,故而“象”的获取,首先便要求体味者虚静其内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4]320,艺术创作,异常辛苦,身-心-手的矛盾常会导致“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24]320,虚静“志气”,澡雪精神,方有机会在“神与物游”中捕捉到合适的意象。接受过程同样如此,中华传统艺术多主张通过赋、比、兴等修辞手法,虚实相生的结构布局,抒情写意,创造意味无穷的审美效果,接受者则可从含蓄委婉的言、形、象中,经过千回百转的体验、感悟,觅得作品中丰富、多元、细腻、难言的复杂情感和形象背后的深刻意蕴,这种以己之想象,借神思之技而“梦里寻她千百度”式的审美过程便是“体味”。
仅虚静其心,尚不足以形成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体验,还需要反复体验、寻觅,不断咀嚼、研味,这是“体味”之“味”的另一重特征。审美绝非一次可以完成,多次反复交流方可有所得,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享受过程。清秋时,郑板桥于江馆看竹的一段文字,提到了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画竹过程,其主要论及的固然是画竹的不易,又何尝不是对“体味”竹美过程的一种揭示,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完成一次“味”绝然不够,还需要反复观赏、体悟,我们可以想见,正是由于郑板桥日日与“竹”相会,处处寻觅竹之“味道”,才有了其笔下灵动无比、充满生命力的竹子。“体味”是一种交流,反复“体味”是多次反复的交流,交流的次数越多,交流的时间越久,所“味”的“美”便也越多,心灵的自由便越大。诚如佛家看山看水,之所以能抵达真正的山水之境,同样在于反复地“看”,倘若没有这样的体味过程,山水之真面目绝然不会自行到来。元好问《与张中杰郎中论文》有言:“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45]40,百遍咀嚼是获取诗味的不二途径。赵构得王羲之“或数行、或数字”书画,“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46]3,由“初”而“末”的逐渐展开、深化之“体味”,是赵构获得王右军书画之“真味”的奥妙所在。
中国人的审美范畴往往因“近取诸身”,连类取譬而成,极富体验性和形象性,这种具身性的认知方式和体验性的话语类型,体现的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样态和文化-哲学智慧。儒家之“推”,庄子之“游”,老子之“抱”,公孙龙之“指”,这些用来指哲学之义理的核心之语均来自于口舌耳目的自发之义。固然,“字之原义,不足以尽其引申义,哲学之义理尤非手可握持,足所行履,亦非耳目之所可见可闻”,然而,“本义理以观吾人之手足耳目,则此手足耳目之握持行履等活动之所向,亦皆恒自超乎此手足耳目之外,以及于天地万物”[47]4-5,“味”这一艺术审美范畴便因口舌而来,并成为美感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味”这一审美范畴,基于“旦旦之所须”的“饮食之味”的感官体验以及“哲学之味”的形而上学转变,最终走向美学的“审美之味”;其美学内涵既体现为静心忘我的咀嚼过程,又体现为丰富多义、绵延不绝的诸种滋味,并通过余味、淡味、体味等“家族相似”之语,凸显了其通向无限、平淡的审美旨趣和静悟的审美之途。“味”这一艺术美学范畴,对当代中国以及全球社会精神生活中“和而不同”的审美追求依然富有迥异于西方审美的积极阐释力,对当下炙手可热的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依然具有范式意义,对当前文艺事业中的“重口味”和“寡淡无味”依然具有有效的调制作用,难怪有学者指出:“如果要寻找一个能够集中代表中国人艺术审美立场和态度的字眼,那实在是非‘味’莫属的”[4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