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跨界”
——记我在学术之路上的转折与探索
赵 牧
广西大学文学院

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这是多年来重复过很多次的话,但其中却有着不同的潜台词。最初在2002年春天参加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面试的时候,主持面试的费勇老师问我:“你学理工科的,怎么想起来考中文的研究生呢?”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喜欢,并为了证明自己的喜欢而费了不少的口舌,但其实我当时所想的,是自己实在不想在煤矿干下去了,再干下去也许真的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毕竟这不是一条立竿见影的道路,女朋友那边已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分手,要么考研,因为她那时听说,考上研究生就有办法把工作调动到一起去。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做过很多梦,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他以为这些梦大半都已忘却了,而且并不以为可惜,然而在我,却总还将精神的丝缕,牵系着那些逝去的时光。这中间大半的因素,就因为在矿业大学里学了工程测量这个专业,而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了煤矿这样的工作环境。想当初自己作为农家子弟,最为真实而又迫切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脱离农门,再也不跟“土坷垃”打交道了,因为这其中的辛苦以及屈辱,一代代的,已经成为难以抹除的印迹,刻写在我们的心灵上。但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是一所矿业院校,而后所从事的工作,竟比之当初在田间劳动的时候还要辛苦,所以逃离的冲动,从一进煤矿大门的时候,就已经潜滋暗长了。
从一上学就想着逃,到煤矿也是逃,而如今差不多逃无可逃了,这才想起来,人们所可能有的逃逸路径,就已隐藏在过去的生活经验中了。所以,当我脱离面试的语境而重新思考自己何以弃工学文的提问时,就禁不住再一次想起将近30多年前那个周日的下午。正值深秋时节,天空中飘着微雨,而我独自踩着自行车顶风走在返校的路上。我犹豫着要不要找个地方暂避一下风雨,就在这时,一辆带篷的机动三轮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猛一抬头,竟发现车厢内有一靓丽的女孩冲我招手。虽然车厢内有些昏暗,但我还是看清她乃我高一时的同学,我就因为她学文而选了文科,然而不幸的是,教地理的班主任似乎故意将她分在了三班,将我分在了四班,这让我很不开心,并因此而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是那时流行很广的一句话,我也一度对此深信不疑,但因为这女孩,我突然改变了想法。为此,教物理的老师还专门找到我,分析我的长短,忧虑我的未来,我虽忐忑,却终究没能告诉他这选择背后的诱因。然而分了班,虽就在隔壁,但这女孩却从此再也不能课间扭头问我数学题了,而下课后,即便每天都会从我们四班的教室门前经过,但可恼我的位置,距离门和窗都很远,我能看见她,她却看不见我,连想象中的眉目传情,也是不可能的。更可懊恼的,是我几次佯装经过三班门前,竟看见她正跟身后一位男生交头接耳,那情形,跟当初她与我,是极为仿佛的。我于是想起她曾经就这么咬着舌头给我说,若有机会到她父母所在的甘肃参加高考,像我这成绩,不说北大清华,考个重点应不在话下的,而为此,我也一度想入非非,但看她跟那男生亲昵的样子,估计这事儿已经悬了。这样想着,免不了怅然若失,但侥幸的心理,也不是没有,所以对于要不要改弦易辙,仍然是举棋不定。而在那个深秋的下午,当我骑车返校的时候,心里还在为这个问题纠结着,但她竟从幽暗的三轮车厢里向着我招手了。在那一刹那,我心里一下子涌出无限感动。不料再看她身边,竟是那个男生跟她坐得很近很近,而且看她向我招手,他也冲我笑了一下,只是这暧昧的笑容转瞬即逝了。
自那之后,我便又回到了原来的班级,继续数理化的学习了。因为此前的经历,我之喜欢数理化,倒并非实用的考虑,而像是一种逃避。然而从这经历中,我也明白自己,其实是有着所谓文人的善感的,所以当高考而入矿院,又从矿院而进煤矿,我所能给自己想到的逃离路径,除了文学,似乎别无选择了。但我那时对于文学的理解,更多还是创作角度,而一旦入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却发现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对历史、民族、国家、世界的悉数关心,冒出来的名词,都是启蒙、革命、救亡、现代、殖民以及后现代之类的。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除了不得不提的鲁迅、茅盾、郁达夫、萧红等,在列的却都是一大堆外国人的名字,什么福柯、德里达、安德森、本雅明、鲍曼、吉登斯、巴赫金,等等,简直就是外国名人堂,那么文学呢?作品呢?审美呢?诗性呢?“这些曾经以事件的曲折而吸引你的,命运的乖戾而感染你的,人生的无常而启迪你的种种阅读经验,被围在面前叽叽喳喳的术语遮挡住,几乎不为你所知了。”实话说,这的确是让我深感困惑,而又不以为然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第一学期课程结业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术语的狂欢》,后来发表在2003年第5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其中的看法,当然是不无偏颇的,但在当时,我却振振有词,以为像我这么一个外来的闯入者,竟一下子点到了中文系的软肋:“人们首先是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才来光顾研究的,……那么何不躲开各种术语的迷宫,写得更加生动感性点呢?术语里没有感应的神经,所以当术语在你的研究文章里狂欢乱语的时候,其实你已与那切近心灵的文学有着相当的距离了。因着文学而研究,结果却落得同心而离德,真是何苦来哉?”
然而报应不爽。我很快发现,理论无论对于我们理解这个结构化的世界,还是带有强烈审美意味的文本来说,都是必要的。远在读大学本科时,我就读过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著述。记得2007年春天到上海大学读博士,在蔡翔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给他表示,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躲避太行山上的测量实习而偷偷跑到图书馆看书,所看的书中,就有一篇他对张承志的评论,题目都还记得,所论的作品也有印象,但蔡老师却将我的这一表示当成了一种后辈的恭维话。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下的学术生态,已经“内卷”到学者们只顾着自己的那一亩八分地,基本上不再关心别人的学术写作了。曾经有学者表示,所写的文章大抵只有三个读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编辑,一个是老婆,因为他每每写完一篇文章,总是让老婆代为审校的。这或者是一种玩笑话,但在我,却从中体味到了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为人为学的寂寞。而就在这样的寂寞中,学术同道们在一些研讨会的场合里见到了,却也总是相互奉承一下,说早已拜读过你的大作,而你若认真,想要问个究竟,往往总会自讨没趣,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交的礼仪罢了。然而我对于蔡翔老师,却并非虚与委蛇。我那时躲到图书馆去,真的不仅仅是看小说,而且还对王晓明、陈思和等沪上评论家的文章,以及李泽厚的美学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些评论家或者理论家,不仅对于文学作品或者美学现象有着深入的解读,而且在表达上充满了诗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学术文章,应该也是以审美的表达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的。然而即便如此,我在暨南大学硕士读书期间,却也开始迷恋上了西方学术理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思想深度,以及在习焉不察的文本细节中发现并阐释自己所关注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能力,在很多时候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理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刘晓春老师的人类学的课堂上,而在其间获得的启示,我很快将之付诸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中。刘晓春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马歇尔·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等,他们带着西方的问题意识对于诸多原始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既让我们看到了丰富多样的人类学景观,又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田野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观念体系和学术机制为前提的。在如今的文化史和民族志的研究中,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描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换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为此补充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比如关于中国传统女子裹小脚的批判,比如致力于现代教育和医疗体制的建构,比如国际法体系的引入,等等,这些看似客观的描述中,其实在背后潜藏着一个颠覆性的逻辑,那就是企图改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中有关传教士配合西方的殖民者实施文化侵略的观念。在传统的近现代史叙述中,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被当作一条主线,所以殖民与反殖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但在传统的现代转换的视野中,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先进的”文化观念,却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性的刺激,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我们加入、融入世界主义大家庭的作用。应该说这两种叙述框架,原本就是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的,但它们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却各自都有着本质主义的倾向,并为此而试图将对方打入另册。之所以能够对此有着这么辩证的认识,显然是因为在刘晓春老师的课堂上所接受的人类学的理论,它们让我意识到西方启蒙现代性的逻辑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的情感结构,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前提的人类学,将原本时间维度上的进化论教条空间化了。社会进化论很大程度上是与启蒙现代性逻辑关联在一起的,但它却并非全然现代化的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是,传教士是以对待异教徒的眼光,观察和描述他们所能看到的“东方”世界;而人类学者,则将这些西方世界之外的原始部族安置在了进化链条的初始阶段。
像这样的一些认识,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都有涉及,而读到这本书,则是在王列耀老师的海外华文文学课上,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版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地有马来西亚“侨生”涌入中国台湾地区,并在那里率先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教育,显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些马来西亚侨生从“岛”到“岛”的流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上的各种错认,造就了他们文化认同上的多重吊诡,而无论他们回返新马分治后的马来西亚,还是滞留在中国台湾地区,或者更进一步远涉重洋,到英美接受更进一步的西方教育,都造就了马华文学在“中华性”和“马华性”论述上的复杂性。如何就马华文学内部的相关论述展开讨论,并且讨论中我们作为大陆学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供的“后殖民”视角,无疑具有极大的方法论意义。事实上,萨义德的《东方学》在当时之所以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是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传入有着很大关系的,而萨义德在讨论西方人如何想象和表述“东方”的时候所借鉴的方法,正受到福柯带有反本质主义意味的“知识考古学”的影响,所以后殖民与后现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那时候,我作为一名初入学术门槛的研究生,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由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几位老师引领着,不自觉地以它们为方法,开启了我对于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关注,并将目光投向了他们跨境流动的复杂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在他们的文学中的表现。

赵牧:《记忆的力量》
我一度将马华旅台作家群作为研究对象来确定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为此而写作了几篇相应的论文。其中,《诉说离乱与建构主体》探讨的是马华新生代作家创作中的精神和文化原乡的建构与拆解,而《侠义精神与中国想象》则是以后来作为武侠小说家而威震四方的温瑞安在中国台湾地区求学期间受国民党统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诗社的方式建构江湖和侠义的“中国想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因“解严”前后中国台湾地区主流意识的混杂和矛盾而遭遇的尴尬命运。像这样的论文,后来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当时却并不好发表。因为马华文学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一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东南亚华文文学本身在大陆学界,其实是边缘中的边缘,是普遍受到漠视的。要知道,在我们当下的学术体制中,人文学科相比理工科,是受到漠视的;而在人文学科中,文学研究本身就很边缘化,但就是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却又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鄙视链”,比如古代文学一向自视甚高,相关的从业者中有很多就想当然地瞧不上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就又以现代作为正宗,经常性地质疑当代文学的学科属性。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过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下一等的叫作“台”,台没有下一等了,岂不是太苦了,但“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很大程度上,当代文学就是文学研究中的“台”,它本来最受歧视,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对外开放的缘故,中国台港澳地区暨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相关的研究,却在很久以来,都处在“台”下,类乎自古以来尊卑有序的人伦关系中的“妻子”的地位。我本来就是外面的闯入者,对于这“鄙视链”还不了解,就一下子从萨义德的角度进入了马华文学,觉得在后殖民的视野中,马华旅台作家群的作品中,隐含了自我与他者的多重镜像关系。然而这样的探求欲念,却因为我的硕士导师李运抟教授的不建议而中止了,他所能给我的理由是,中国台港澳地区暨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他所研究的专长,我因为挂在他名下,他却又从暨大调出,怕落下并无实质性指导的口实,而希望我回到他所熟悉的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
我理解李老师的态度。我并不以为他也站在“鄙视链”的一端,但当时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的下学期,马上就要开题,却也不能不让我一下子变得焦虑起来。就在这时,我似乎脑海里灵光一闪,想起曾有一次到同门李海燕宿舍里聊天,以李锐的小说《银城故事》为由头谈起了当代小说中的革命历史重述的话题。就在那时候,我不知怎么的犯了好为人师与崇尚清谈的老毛病,用一种蹩脚的说山东话不是山东话,说河南话不是河南话,而又绝对算不上普通话的语言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说得李海燕同宿舍的两位女士直用媚眼剜我,而李本人也如坐针毡了,我才收住唾沫星子。唾沫星子是收住了,但笔杆子却不安分了,于是有了一篇题为《反革命的话语创造》的杂感,而这篇后来发表在远在美国的王性初先生主编的《中外论坛》上的杂感,就成为了我硕士论文的起点。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而此间的“后”,其实就主要是“反”的意思,但之所以用“后革命”而不是沿用最初的“反革命”,一方面是因为“反革命”这一带有历史遗存意味的概念可能带来歧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各种后学话语已经甚嚣尘上,而德里克先生的《后革命氛围》一书也译介到了国内,其中他对于“后革命”的解释,不仅包含了历史分期的涵义,而且将我先前的理解囊括进去了。因为这样偶然的一次谈话,决定了我此后十多年的研究重心,这不能不让我对李海燕同学心存感激。但当我的博士论文《后革命:话语与叙事》以《“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出版后,我就很少使用“后革命”的概念了,但从那时候就已确立的问题意识却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革命是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就是对于这一问题意识的概括,而从这一概括中,则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着明显的《东方学》的影子,所以,虽然从马华旅台作家群的创作而流动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革命重述方面,但在王列耀老师的海外华文文学课堂上的阅读经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大致形塑了我的研究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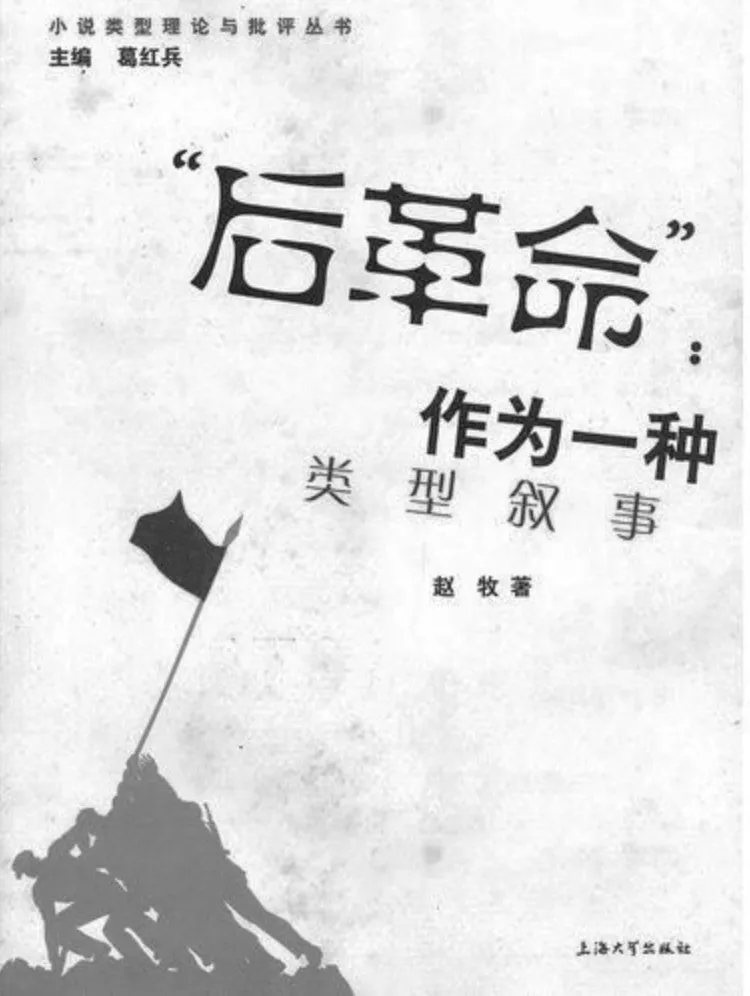
赵牧:《“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
此后因为因缘际会,我在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承担了《中国电影史》的课程,而在这将近十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早期的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积极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话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形塑了其间中国民众对于革命或者救亡的理解方式。这就不能不让我进一步思考,所谓的“后革命”是对于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叙述的颠覆,并从而“再生产”出了我们今天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那么,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难道就是铁板一块的吗?因为这样的疑问,我决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当代而转入现代,开始重新思考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并由原来相对单纯的文学叙事而拓展到了电影叙事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我注意到全面抗战时期,原先在上海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应云卫,因为筹拍《塞上风云》而从重庆率领剧组到内蒙古取外景,其间经过延安而受到党中央领导的接见,而毛泽东同志在跟剧组人员的谈话中所提及的民族团结话题,就影响到了他对于这部电影的故事结构方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触动。要知道,在我们通常的现代文学史讲述中,全面抗战时期的现代文学被划分为几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国统区,一个是沦陷区,一个是延安及解放区,这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呢,我们却似乎只浮光掠影地知道,而彼此联系的细节呢,却还有着很大的探索空间。于是,我决定将自己有关革命本身的探索,先行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作家的延安道路及其当代阐释方面,希望借助于一个个有着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区域奔赴延安的故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路径的选择之间的互动,而阐释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内,也散轶在那些不同方式讲述的传记和回忆录的材料里面。
像这样的思考就构成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作家的延安道路及其当代意义”的前提。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止于此。比如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些立场迥异和观念悬殊的作家,大多活动在京沪两地,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危机情势,尽管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传统士大夫的感时忧国之心,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他们的所忧之国,与我们现在所谈及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则又是一个很值得玩味而难以索解的问题。我们知道,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安德森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论断,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通过详细的考查,指出现代报刊业的出现为这种想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纸上得来终觉浅”,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视域所及,除了自己的“吾乡吾土”之外,就是作为他们主要活动地点的京沪大都市。远离这些大都市的众多边陲区域,恐怕大多只是出现在他们文本化的阅读经验里。全面抗战却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再也不能徜徉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或者北京的“文艺沙龙”中了,随着战争的推进路径,撤退到中国的大西南、大西北,而在广袤的穷乡僻壤中品尝着流亡的辛酸,成为他们所不能逃避的现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文本化的知识跟现实的观察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以及这个互动的过程,又如何参与形塑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成为我所重点思索的问题。

赵牧:《凝视的目光》
所以,随着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流动迁徙路径的考察,尤其是,随着我个人在此期间从中原地区而转入胶东半岛,又从胶东半岛的烟台流动到西南边陲的南宁,让我情不自禁地逐渐地又从对“作家的延安道路”及其当代阐释,转入更加广泛的区域,开始在“流动的现代性”这一名目下,认真思考起这些知识分子的迁徙流动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乃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等议题。不仅如此,因为这其中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更是越境而抵达了传统上被称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他们在与当地的华人社会的交融中又培植了怎样的根苗,并为后来的马华文学中有关“断奶”论的争执,“中华性”与“马华性”的辩证,埋下了几多因果,则又让我的思考,再一次回到最初对马华文学的关注中去了。
实际上,在我后来将近20年的游离中,马华文学已经在中国大陆学界渐成显学了,许多原先不为我们所知的马华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陈大为、黎紫书等,不但在大陆出版了他们的作品,而且有关他们的研究,也登堂入室,成为众多重要的文学刊物策划的专题。就在不久之前,一位朋友在聊天时,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想当初你关注马华文学时,马华文学还乏人问津,但不幸你没能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不然你也可算得上这领域的元老了。要知道,对于学文学理,我都没有长性,全随了当初那个女同学的眼波流转,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此,我当然是一笑置之。要知道,作为一个外界的闯入者,我一直就不曾产生过所谓的领地意识,相反,在不停地跨界流动中思考学术的现实指向,或正是我应有的边缘姿态,而既然身在边缘,又怎知下一站居于何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