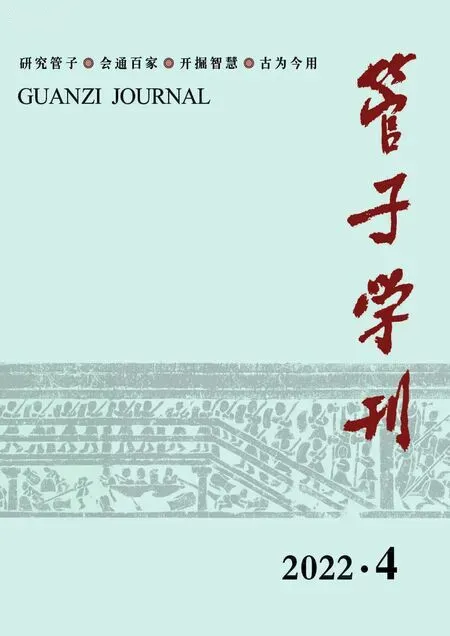“偶然”乃天地之“常然”
——《齐物论》“三籁”解析
黄 颖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筹],浙江 杭州 310058)
《齐物论》中的“三籁”是庄子哲学中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与命题。《庄子》文本对“三籁”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说明,这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与解释。《齐物论》以“齐”为题眼,本文亦循“齐同三籁”的思路进行阐释,立足“三籁”虽 “名不齐”而又在根本上“齐于道”这一根本观点,在《庄子》“四知”知识论框架下,重新建构“吾丧我” 之真意,揭示主体心灵持续向偶然性敞开的重要意义,展现《庄子》独有的强调偶然性的生成理论和知识论思想。
一、“三籁”研究的两种思路
学者研究“三籁”的思路之一是将“天籁”与“地籁”“人籁”相区分:“人籁”“地籁”在有形世界的层次,“天籁”在无形世界的层次(1)祁涛:《〈庄子·齐物论〉中“三籁”问题的再探讨》,《华夏文化》2013年第3期,第36-38页。;进而以其中的差别说明“吾丧我”(去除“成心”)之必要。如杨国荣认为“天籁”与“吾丧我”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丧我”要求从社会化、人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到本然而合乎天性的状态;《齐物论》通过区分 “人籁”“地籁”与“天籁”,庄子一层一层地消解了具有目的性的外在推动力量,突出了“自然之和”所具有的那种超越主宰、扬弃目的性的特点(2)杨国荣:《〈齐物论〉释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25、167页。。张和平认为“吾丧我”与闻“天籁”是一对能所关系,“天籁”是得道者精神世界的“心象”或“道象”,“人籁”“地籁”乃是不得不“物于物”,“天籁”则是对“籁”的超越、是“无物而不物于物”的;“吾丧我”是得道者秉有“若镜”之心的一种表现,分为秉守“无为”(心神内守)和“无不为”(顺物自然)两个方面(3)张和平:《“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13-120页。。
亦有学者持另一阐释“三籁”的思路,即不将“天籁”与“地籁”“人籁”相区分,而是认为“三籁”皆合于道,三者仅仅是道运行的不同态势;尽管将合于道之“三籁”与有损于道的是非“成心”相区分,但主体可以通过“吾丧我”的工夫复归合于道的状态。如郭象将“三籁”注解为:“声虽万殊,而所禀之度一也,然则优劣无所错其间矣。况之风物,异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则天地之籁见矣。”(4)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页。成玄英疏亦云:“夫箫管参差,所受各足,况之风物,咸禀自然。”(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6页。林云铭说:“风之吹万窍也,固不同矣,但使其为窍如此,即为吹如此。若皆自取其怒号者,谁为之邪?谁字与自己相应,暗指天也。”(6)方勇:《庄子纂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可见郭象、成玄英及林云铭皆以“三籁齐一”为要。陈鼓应认为,“人籁”是人吹箫管发出的声音,比喻无主观成见的言论。“地籁”是指风吹各种窍孔所发出的声音,“天籁”是指各物因其各自的自然状态而鸣(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46页。,即“三籁”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天地间自然的音响。牟宗三认为,“‘天籁’义即‘自然’义。明一切自生、自在、自己如此,并无‘生之’者,并无‘使之如此’者”(8)牟宗三:《才性与玄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陈赟认为在《齐物论》中,“吾丧我”描述的是一种“朝彻而后见独”的状态,向事物开放而后能“闻天籁”,自己与他者及其连结的自然状态得以呈现,得闻的“天籁”即人对天(天地万物)及其运行的领会(9)陈赟:《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认识过程由“知”到“德”的升进——以〈庄子·齐物论〉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40-46页。。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阐释“三籁”思路相比较,后者“齐三籁”的思路更为契合庄子哲学的思想气质。《齐物论》有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1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6页。将“三籁”分别论述,对应于“成心”与“吾丧我”,如此议论需抛下一端而持守另一端,这种对待的思路实产生了对耦,略显迂回和笨拙。“齐三籁”则采取了一种“暂置分别、择齐而同之”的思路,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根本问题展开论述:何谓“齐三籁”,如何为“齐”,以及“是非”为何“不齐”。照此思路展开的“三籁”阐释,既可呼应《齐物论》之“齐物—论”的题眼,又可呼应“齐—物论”的题眼,并且深契《庄子》向差异开放、不欲强调分别的精神。这一理路单刀直入“吾丧我”之境,避免产生对耦,与前一思路相比,显然更为利落和轻盈。故而本文将照“齐三籁”的思路展开。
只是,现有的“齐三籁”的解读中,关于“何为齐”“何为不齐”的论述仍较为简略,通常仅停留在“天道运行”“自然生发”等本体论的层面,较少关注《庄子》的生成理论和知识论,遗漏了《庄子》文本强调偶然性的特色。本文将通过论述“三籁”自然发生是“不齐而齐”、是天地间偶然性的激越与碰撞,揭示出“三籁”之“齐”根本在于“道之运行”。而后将视角转移到“人籁”主体心灵的知见层面,着力阐释主体心灵在一种向可能性开放的意志场域中,生命主体可从“道之运行”中领悟到自然之真意、生机之勃发,从而达至“成心”休息不滞、心中知见流转不驻之境界。
二、“三籁”之“不齐而齐”
(一)“地籁”之发生
庄子借南郭子綦之口这样描述“地籁”的发生:“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1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5页。众窍为虚,与“风”乍然相遇则一齐怒号:“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1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6页。有的像湍水冲击的声音,有的像羽箭发射的声音,有的像斥咄的声音,有的像呼吸的声音,有的像叫喊的声音,有的像嚎哭的声音,有的像深谷发出的声音,有的像哀切感叹的声音……发出的声音高低远近各不相同。“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1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6页。风的大小不同,带动众窍发出的声音也不相同。
在庄子笔下,“地籁”恣意飘响于天地之间,是大块噫气、随意而起,毫无规律可循——风吹到哪儿,声音便响在哪儿。“地籁”是此风彼风、此窍彼窍,在天地的偶遇;故而由此造就的此声与彼声,“吹万不同”(1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0页。。每一次声响都独一无二、独具特色,既不可复制、亦无法重现——“地籁”仅仅是乍然相遇、陡然涌现,涌动着奇趣的偶然性。
(二)“天籁”之发生
再来看庄子对“天籁”的描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0页。风与众窍充满偶然的相遇,造就了每一道“地籁”声响的不同;“吹万不同”即“天籁”亦是每一道都不一样。“天籁”的发生是“使其自己”,只有“自己”与“自己”发出的声响,并不另有他物将“它”叩响(16)郭象注云:“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一天耳。”成玄英注云:“故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邪……且风唯一体,窍则万殊,虽复大小不同,而各称所受,咸率自知,岂赖他哉!此天籁也。”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0页。。可以确定的是,“天籁”是“有”(一种存在意义上之“有”,而非实在经验意义上之“有”),天籁之从“无”到“有”,是一项活泼的、自然的变化事件。它也许借助一些自然之“事件”,来“吹响”自己。这项事件也许是道的转化——万物的状态随着道的运行自然而然地不断改变,但此“事件”凭借我们的经验与理性无法通晓。我们仅仅能知晓“天籁”发生了,在“荡荡默默”(1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02页。之中有“事件”发生了。它不断地响应着道、照面着“前来相遇者”,“相遇事件”不断地发生、“天籁”不断地奏响,天地之间一派蓬勃景象:飘逸着活泼的“天籁”声响,洋溢着雀跃的生命气息。
回顾“天籁”与“地籁”的发生,二者气势磅礴,其态势犹如“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而点燃这股冲天焰火景象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相遇事件”,是道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启示我们,“众窍”与发出“天籁”者自在地合于道需要保持“虚”的状态,敞开包容前来相遇的“事件”,敞开接纳偶然性的激越与流变。
(三)“人籁”之发生
庄子借子游之口这样描述:“人籁则比竹是已……”(1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9页。“人籁”好比箫管被吹响而发出的声响。类比“天籁”与“地籁”的发生,在“人籁”的发生中,首先“人”本身处在“不发声”状态,好比箫管拿在手里。随后“人”被“吹”而响,即遭遇了一个“相遇事件”,这个“相遇事件”改变了其“不发声”的状态,人好比箫管被吹动“发声”了,人呈现出“发出声响”的状态。这是“人籁”的发生。
庄子将人们头脑中对外在世界的是非判断、概念范畴等“物论”比作“人籁”。“人籁”的发生,是知见的发生。“人籁”之生动与杂多,从“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发若机栝”“留如诅盟”到“缦者”“窖者”“密者”(1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1页。等可窥一二。每一个知见都好似主体“遭遇”世界、二者摩擦碰撞的一声响。“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2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3页。“民”“鳅”“猨猴”“麋鹿”“蝍蛆”“鸱鸦”……此处各个主体出于不同的生存体验和实践经验(其中涉及到不同的对象、立场、偏好等),最后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知见。就此看来,主体知见的产生好比“地籁”,不同的窍穴遇到不同的风,吹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主体遇到不同的事和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发出不同的声音。庄子取消了“正处”“正味”“正色”,认为每一个知见或“人籁”俱是“吹万不同”——独一无二,与“地籁”“天籁”一般都是与自然、与偶然性的碰撞。
上文详细阐释了《齐物论》中“三籁”的发生。可以看到,在《齐物论》的语境中,“地籁”“天籁”及“人籁”的发生,俱是天地之间自然大势的流发运行;“三籁”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偶然中呈现出了蓬勃恣意、“吹万不同”的样态。若进一步将“三籁”放在《齐物论》“四知”的理论框架中,便能更加深刻地领会为何庄子独独将“齐”作为天地流行的“道枢”,并能通达《庄子》向无穷流变和偶然性开放的存在生成理论。
三、道与“四知”
《齐物论》之题解,实蕴含两层涵义:一为“齐—物论”,即对于世人常偏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不得悬解这一现象,庄子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通过“齐”是非知见、消解价值绝对性,化解执著。二为“齐物—论”,即对于世人仅仅关注事物之绝对差异,固执于事物静止凝滞、绝然相分这一认识困境,庄子欲从一种流变本体论的角度,通过揭示万物皆处于流转变易根本之道的运行图景,消解众人之“成心”。从二者的联系来看,“齐物—论”实际也为“齐—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本体论层面的支持。“三籁”一典出现在《齐物论》的开头,作为《齐物论》的一个部分,与整体密不可分;同时,我们在对此典进行阐释时,亦需紧紧联系《齐物论》这两个层次相照应观之,从“齐是非”的知识论和变化的本体论两个角度加以探究和检视。其中,“人籁”作为人心灵认识活动的产物,具有“物”的存在特征,照应于“齐物—论”,可从生成和流变的角度进行理解;更为绝妙的是,将“人籁”作为人内心的知见观点时,它又具有了“论”或“物论”的存在特征,可照应于“齐—物论”,直接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阐释。
从“人籁”是认识的产物这一角度看,知见是主体与“世界”相遭遇的过程中产生的:“人籁”不吹不响、吹而有声,此知、彼知皆是被不同“相遇事件”所“吹响”的。在《齐物论》中,庄子认为是非知见并无标准可言(21)释德清认为:“将要齐物论,而以三籁发端者,要人悟自己言之所出,乃天机所发。果能忘机,无心之言,如风吹窍号,又何是非之有哉!”见方勇:《庄子纂要》,第170页。明是非乃“天机所发”,即能了解“是非任自然”。,每一个知见都有其独特的、新的意义,具有纯粹的特异性。知见的生成契机,即主体遭遇的每个“事件”都不相同,每个生成意义与解释的场域都不同;场域总在流变,无法通过任何既定的原则来预测,也无法通过某种法则或规律来验证,仅仅是纯粹的偶然。这恰恰犹如“地籁”众窍被风鼓动,自然的偶然性在心灵与思想的孔窍之间奔腾着、曜跃着。为什么是这样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声音?为什么是这个在发出声响,而不是那个发出声响?庄子解答是:“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2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5页。偶然性的“事件”敲响了这一声,但其偶然性本身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不来自经验中可重复或可演绎的形式或逻辑,也不遵循线性演化的历史法则,它秉于道,秉于万物森罗却浑然无缺的整体之“有”。
从“人籁”作为内在性知见的角度看,需联系《齐物论》“四知”的知识论框架,即庄子划分的四种层级的知见:“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2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4页。第一层次的知见“以为未始有物者”,是关于“无”的知见,因为道“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2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46页。,是“渊漠的一的无言”(25)黄克剑:《庄子“不言之辩”考绎》,《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49页。。第二层次的知见“以为有物而未始有封”,是关于整体的知见。在此层次的知见中,尽管见到“天”“地”“万物”,但摄入知见中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浑伦整体,并无分界、亦无止境,此知亦是一类关于道的知见。
第三层次的知见“以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是关于齐同的知见。章太炎《齐物论释》认为主体生成的知见可分为两种,一者为“无相分别”,即“随先所引及婴儿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别”,是“未发”之知,是不成言之心意,主体与一切“有情”照面,所生“心意”(潜在的知见)皆有所分别;二者为“有相分别”,即“于先所受义,诸根成孰,善名言者所起分别”(26)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是已生之知,是能成言之“心意”(知见),念念相续,或成章句。“未发”之知见(“无相分别”)与已生之知见(“有相分别”)既是对诸“有”间断的认识,同时又连贯在对整体诸“有”之整全的知见中。此层级的“诸知”与“诸见”亦属于有关于道的知见。
第四层次的知见“是非之彰”,是“道之所以亏”,即损乎道的知见。在这个层次上,主体之“看”不再能对诸“有”之整体作周遍的直观,而是将目光固着、停滞于对诸“有”的间断的“看”中;诸“有”不再呈现为一个普遍关联而统一的整体,连绵的诸“有”断裂成松散的、零落的个体的“有”。在这样的知见中,种种分别遮蔽了流转不驻、活泼浑一的道,因此这层次的知见是有损于道的。
“天籁”与“地籁”的发生是因任自然、“咸其自取”,“人籁”即知见与思考的发生亦当如此。当我们的心灵向“思”与“见”的无限可能性敞开、向天地流行的自由勃发敞开时,我们将获得前三层次的知见,恣意徜徉在整体之道的流转中;反之,当我们的心灵固着停滞下来,我们便从世界整体的逍遥中滑落下来,生起第四层次的是非成见、彼此纷争,乃至“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2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6页。,身体劳碌疲惫,生命情意凝滞困顿。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
知见是非流变,其所独具的“美”和“真”是从不确定性中所禀赋的。《齐物论》言:“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2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5页。即是说,“人籁”的质感与风格乃是由不具形状的偶然性塑造的,虽塑其形却“有情而无形”。“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2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4页。时而感觉自己在梦中,时而感觉自己在梦中梦着;时而感觉自己醒着,时而感觉自己在梦里醒着。“有情”指的是:“是”与“非”嘈嘈切切、模模糊糊,但“被吹响”是真真切切——无论主体产生的感觉和认知有多么荒诞与两可,总归是有知见、有思想发生和生成,形成念念连续的思见之流。“无形”指的是知见的形式变换、立场流转捉摸不定,在与洋溢着偶然和不确定性的实践与时空发生碰撞时,知见间的差异便已经生成。更进一步说:“有情而无形”是“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3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4页。亦即,是非流变不定,乃是“我好似言说了什么,又好似什么也没有言说”。在思想的言说中,逻辑发挥着似有若无的作用,无法从某个确切的形式演绎中推导出可靠的结论。但在“是”与“非”之间、这一次“被吹响”与那一次“被吹响”之间,确实有着巨大差异,差异的生成恰是由于丰溢着偶然性的天地之道在跃动。庄子喟然叹曰:“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3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5页。一切崭新的声响、崭新的知见思考及新的意义的生成都源于其内在的“吊诡”——“世界”之于我是“吊诡”的,故而产生于此世的知见与思想本身亦是“吊诡”。在此意义上,“吊诡”乃是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大全;而恰是这个“吊诡”,才使知见之流转成为可能,使自由恣意的“人籁”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我们回溯与探究人们知见的生成能够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过程,好比“天籁”“地籁”“人籁”的激越。如庄子笔下丽之姬对未来及人生的领会和见解随时机的变换而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知见的产生是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机遇与赌博,没有人能预测或评估生命本身的状态与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铺陈成就“三籁”的场域里,交织着绝对的不确定性、演绎着持续的动荡湍流,每一个主体皆在天地流行大化之中徜徉。在这个流行之中,主体生命接连不断地与不同的场域相遇,与既在世界之中、又不仅仅只在经验世界之中的“事件”相遇,从而产生了纷繁复杂的感受和认知。在流变的意义上讲,生命主体与不同的场域、不同的“事件”的相遇、摩擦与碰撞,是全然偶然的,是不能够预期,是无关逻辑或理性、亦无关真理的(32)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认为,经验与超验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些莫可名状之物对于经验而言是吊诡的,对超验却是规律的,而这个鸿沟是一种“非关系”与“非场域”。参见杨凯麟:《书写与影像:法国思想,在地实践》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13-417页。。因此,主体生命的每一个知见与思考、每一个领会与觉悟,都是在碰撞着全新的可能性。而在此绝对的运动与流变中,主体生命恣意地领会到天地大道、世界流行的崭新意义。每一次思考活动及思想结晶都在打破既存的想法、冲破现有的界限,从陈规旧俗、陈腔滥调的意见中出走,孕造出全新的思想。这便启发生命主体,需要不断去发现、去发明新的生命和实践的可能性,让思想知见流转不驻、感应天地流行的浩浩汤汤。
“三籁”总是蕴含着偶然性与可能性。恰恰在不断生发的“三籁”中,在流转翻滚的知见中,生命的可能性不断地涌现着、跃动着。庄子说:是非与知见是“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3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3、66页。“未定”“彼是方生之说也”等语句揭示出知见不断处在流变之中:形构此“是”的场域与形构彼“是”的场域之间总是有着差异与分歧,故其内蕴和关涉的是非判断、价值概念等总是随着实践和时空的变换而幻化。生命主体的“思”与“见”持续地、动态地发生着,无穷的知见蓬勃生发,故有“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3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6页。。在源源不断的“思”与“见”之中,我们的生命也生机勃勃着、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着,在真朴生动的整体之“有”中自在恣意。
四、“吾丧我”之工夫
上文将作为“物之存在”的“三籁”以及同时还可作为“物论之存在”的“人籁”分别与“四知”相照应阐释,结合本体论和知识论两个哲学层面蕴示出《齐物论》“道通为一”的根本旨意。前文提到,“三籁”一典出现在《齐物论》的开头,作为《齐物论》的一个部分与整体密不可分。尽管对于“三籁”的解析完成了基于本体论和知识论层面的思考阐释,与《齐物论》整体思想风貌相对比,本文对“三籁”之解析仍旧还有一个思考之“空缺”:《齐物论》的工夫论观点。换句话说,《齐物论》通篇启示着一种轻盈澎湃、开放自在的心灵意志,那么,如何才能达至“人籁”肆意挥发、畅通无碍的心灵境界?只有完成了这一环工夫论层面的阐释,照应《齐物论》里鼓励消解“成心”、去滞存空的呼唤,本文对“三籁”的解析才能够实现思想体系上的完整。
首先,“三籁”所照应的工夫论,乃是觅求一种“虚室生白”的状态:众窍为虚,故而才能“吹万不同”;对应于主体心灵,则是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斋戒的状态——这便是庄子《齐物论》“吾丧我”的工夫。将这一论述主体心灵如何用功纳入到对“三籁”的解析环节中,才能够完成以“齐三籁”为根本思路的整体诠释。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3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3、45页。南郭子綦回应生命的态度便是“吾丧我”(36)南郭子綦进入到“吾丧我”境界后,其肢体被形容为“形如槁木”,其心境被形容为“心如死灰”,似乎“吾丧我”的境界是一种失去生命的灵动、毫无生机的状态。我们认为子綦并非失却生机。《大宗师》有言,古之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30、231页。可知真人随顺自然,肢体容貌或呈现出冬天冷寂萧杀的状态,或呈现出春天生机勃发的状态。子綦与真人的生命皆顺“天”(自然)为一,生机也与“天”一般生生不息、顺时流转。子綦之“形容枯槁”是与“天”(自然)相合而使肢体与心智呈现出一种“毫无生机”的相状。,使心为“虚”,保持心灵的敞开,保持“思”与“知”的无限勃发。思想与知见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3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1页。,没有定论、不知其所来也不知其所往,充满活泼的可能性,那么心便不该干涉与凝滞这种偶然与流变的特质。庄子在《齐物论》中反复说道:“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莫若以明。”“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为是不用而寓诸庸……”(3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6、63、70、75页。以此告诫世人不可执是非的任何一端,而应“袖手”享受思之无穷流转、知见之无穷流转。
其次,欲谱写一出流转不居、曜跃无穷的“人籁”,实现无穷之思、无穷之知见,也需一个主动拒斥和消磨“成心”(39)凯伦·卡尔(Karen L. Carr)和艾文荷(Philip J. Ivanhoe)认为,要求“去除成心”,与要求了解彼此间的差异和个体的独特性,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不怀有“成心”,即心灵变得澄澈(“明”)以反映事物本来的样子。参见Carr, Karen, P. J. Ivanhoe. The Sense of Antirationalism: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Zhuangzi and Kierkegaard, New York and London: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李耶理(Lee H. Yearley)认为,庄子将心灵比作镜子,是因为镜子仅仅只反映事物展示出来的样子,它不会施加任何阐释的框架,不作出任何有关于合不合适的判断,也不会显露出任何欲求。反过来,使得镜子蒙尘的,比如阐释的框架、有关合适的判断、偏好的欲求等等,即是“成心”本身。参见Yearley, Lee H, “Zhuangzi’s Understanding of Skillfulness and the Ultimate Spiritual State”, Essays on Skepticism, Relativism, and Ethics in the Zhuangzi, ed. by Paul Kjellberg and P. J. Ivanhoe, Albany:SUNY Press, 1996. pp. 152-182.黄勇认为,“成心”是我们心中先入为主和片面的观点,也是试图将自己的是非标准作为所有人都需遵循的普遍标准的这样一种倾向。参见Huang, Yong. “The Ethics of Difference in the Zhuangz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2010)pp. 65-99.的“丧”的工夫:我们需要斩断、舍弃一切使思考停滞下来的“成心”,消解与此种开放的心灵意志相抵触、相龃龉的质料,即存在于主体心灵之中的凝滞的是非判断、固着的价值准绳等。
一方面,主体心灵要消解某一概念范畴中的“常理”“常识”“情理”。这样的“常识”与“情理”将会凝滞和阻碍思考之无限发生,使得“思”和“见”凝定在某一固定的界限之中。因为,当人们对“常识”背后所圈定的界限深以为然,便会放弃对其他可能相异的知见的接受、拒斥不同意见,甚至攻讦相异的知见。实践经验和思维定势凝聚出了“常识”和“常理”,甚至以为是普遍性之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世人常以“常识”为牢不可破的“绝对真理”。但实际上,世界诡谲“吊诡”,难知其确实,主体认知的“常识”与“情理”仅仅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有限实践以及有限思维模式的产物。我们或许可以将多数人们属意及惯常的视角看作实践上的“相对客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视角是“真理视角”、信以为“绝对真理”,乃至恃其而凌驾于别的所有视角之上。
另一方面,主体心灵要消解对于“绝对真理”的执著。当统一的“常识”和“绝对真理”尚未形成时,人们便会陷入对“真理”的追求和争执中去,其表现好似儒墨二家之互相论战:“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4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3页。即,众人总是倾向于将自己进行思考、认识与解释的视角和范畴视为确定的“普遍真理”,用自己的知见去“纠正”或“攻击”别人的知见。于是,人们纷纷驰累生命,整日沉溺于争辩与攻讦之中,固执己见、以一己之“是”为“公是”。而在这种论战的活动中,人们“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自身情态日夜变化,如“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4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1页。等。在庄子看来,众人生命活力皆耗在这里,“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4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6页。
完成对“吾丧我”之工夫的诠释,“三籁”的阐释有了本体论、知识论和工夫论三个层次的构架。至此,本文对“三籁”呼应于《齐物论》思想整体的解析,最终达成了完整性。从解析之中可以观察到,“三籁”一典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齐物论》乃至《庄子》一书中所内含的“道通为一”本体论、“齐是非”知识论及“心斋”的工夫论皆可在此一典中寻得影踪。
结语
本文分别照应《齐物论》的本体论、知识论和工夫论三个思想层面,论证了在《庄子》持续敞开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视域中,“三籁”虽名为三种有所差别的物事,却在“天道”运行的层面上合于天地之无穷流转、契于自然之澎湃生机,是“齐”,非“异”。在解析“三籁”的过程中,《庄子》一书纵逸自在的“逍遥哲学”风貌也显露出来。总览全文,本文对“三籁”的解析还拘泥于《齐物论》的思想框架内,仅仅挖掘到了《庄子》蕴含的深厚哲学义理的一隅,欠缺更纵贯《庄子》全书的考虑层次:如对《庄子》“天道观”的本体论探究仍有不足,对“是非观”的研究也缺乏深入,对工夫论的挖掘也仅仅停留在“吾丧我”一典中。同时也应看到,《庄子》各个典故、各个篇章之间尽管看上去散落无序,但实有其内在的严整性,所以我们可以从更多、更广、更深刻的哲学层面来发掘“三籁”一典的哲学价值和诠释意义。如可将“三籁”这一经典概念和命题与《庄子》的政治思想对照诠释,正如《应帝王》载:“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4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94页。此语旨在提倡在政治空间中将人们从“经式义度”等固着的经验规训与行为界限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和人们葆有随机应时、“虚室生白”的空间,实现一种和谐融乐、充满生机的“治”,无疑与“三籁”所倡导的拥抱偶然性与可能性的思想特质相呼应。再如,可将“三籁”一典与《庄子》的理想人格“真人观”对照品析,如《大宗师》有言:“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4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29-231页。真人不刻意于喜恶及偏好、不强求于德性和成就,而是敞开随顺天地之间的偶然性与可能性;如此坦荡地迎接所有照面而来的“事件”,生命自会绽放出众美从之、“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的“天籁”。
《齐物论》“三籁”之喻启示我们,作为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与其执著于成见,不如“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4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页。,即剔除来自经验且固着于经验的常识与情理,避免一切常识及情理对思考的干涉;将“我”从物我、人我、彼此等的对象性关系中超脱出来,让生命畅其所快、恣其所能,交织出一种绝对的运动与流变。“三籁”一典也更启示我们当代庄子哲学学者,要不断让知见与思考自在自如,建构出一块块虚拟的思想平面;朝着这样的目标不懈前进:系统而不滞地叙述庄子大而无端的哲学思想且不失《庄子》所独有的自在恣睢的哲学气质。
——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