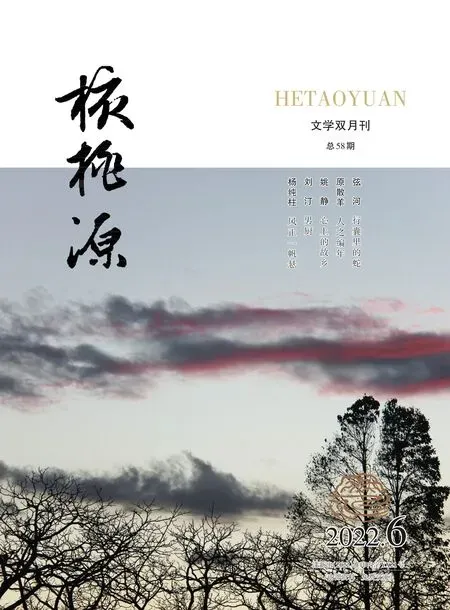人之编年(组诗)
原散羊
乌旦塔拉,命运与惩罚
题记: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
——阿尔贝·加缪
草原,是人们故意废弃的尘世
天凉了。荒原上的事物,开始操练水落石出
——野湖出于芦苇
——情人毁于歌谣
秋风正猎,谁人与过错,未经诞生即已熄灭
当我们开始爱上荒凉的风景
沙丘上站着三个人
此时,他们挥舞手臂,恰好与沙丘底部
老榆树上空空的鸟巢等高
此刻,若有人逆着阳光,从另一侧
给他们拍照:三枚刚从谎言里跌落的,金光闪闪的蛋……
一个女人在写史诗
去往乌旦塔拉的路上
一个女人在写史诗。到处吹动着风,到处漂浮着云
而她,坚持在语言中
完成反向私奔。比历史更悠久的雄性泪水
再也无法成为河流的源头。数量即正义,雌性的当代正义。
牧场岸边的卡夫卡
如此宽阔的水面
可不是2021年秋天,一个牧场谵妄地蓄意为之
草刚被歼灭,水流亡过来
周遭没有一个牧人
或者牛羊马匹,可以回答禁得起分歧的提问
在伊和淖尔,水中牧场的岸边,大风吹得我落了泪
乌旦塔拉的秋天更深一些
如果知道回去的路
需要哭声来导航,乌旦塔拉,你那几百万只红色的耳朵
是否已先于真相关闭地狱?
五角枫,蒙古栎,大果榆,甚至这个无法轮回的秋天
都在重蹈的覆辙里留下种子
并预约了明年春天,草原上最早的一台肿瘤切除手术
有些风景过几年就要重新看一遍
在乌旦塔拉遇见的每一棵树
都在教我说出这句话:
救救你自己吧,没有人比你更荒凉……
脚下的沙子咀嚼着行人的体重
咯吱!脚下的沙子,一下子就扑倒了我体内的墓志铭……
用十五万个不相往来的自己堪言孤独
乌旦塔拉,用十五万株火红的枫树
教会我养育孤独的儿子
十五万株枫树,就是十五万个隐姓埋名的自己
他们不断提炼天空的颜料
只为了让我有一页干净的旧病历
在乌旦塔拉,有人丢了十五万支弓箭,和一个可汗的消息
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戈多
从鞍山出发的人
只有在十月的乌旦塔拉,才能抖落大半生的铁屑
工业废墟的美和颓废感
他们曾经是秩序、力量和热情的戈多
而今坐在蒙古包里饮酒
每一口下去,共和国的螺丝钉似乎都更加纯粹一些
以坚果的形式会盟
看惯了红色五角枫叶
低下头,坚果就能看见陈年的自己
已经摆脱了舍利子的命运
正在长出异族的名字;毡与布制作的疲倦神像
而乌旦塔拉以北,监狱和寺庙都空了
他们只身携带荒凉,以深夜投宿的形式,会盟于法外之地
宝古图沙漠简史
题记:在黄金之丘
需要一个人抚摸大陆和生平
——叶舟
先知之死
轻信了草原
轻信,碧草与蓝天的接壤。河流和冷汗远遁眼中无沙的人
尽管避开世上所有的正午
命运,假借烈日的身份,割据肉体以肤色
肤色的监狱里
驻扎着一支逃命的野兽军团
它们是沙漠的弃儿,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暗示中
烈日之水
刚踏上宝古图
烈日就开始测量灵魂,并把潮湿的影子灌入大漠深处
每个人,都成了行走的暗河
嗬嗬,游荡的拴马桩
一丛一丛,史前蕨类的味道
早于宗教和藏匿,早于它们试图说明的另外一件事
烈日之水,漫过造字的堤岸
用一万具雄鹿的尸骨,围困八百里瀚海,驻跸自己的命运
人之编年
乃蛮部落的后裔
为农田喷完最后一遍除草剂,带着女人走进宝古图腹地
走着走着,风开始咒骂耳朵
走着走着,中年男人被浑圆的沙丘折磨成一柄弯刀
锈迹斑斑的落日
在大漠西侧伸了一个垂直的懒腰,仿佛要升起来
又仿佛在等待一个未完成的仪式——
剥掉女人身上的羊皮,拔除周而复始的繁衍,出于一种伤害的必要……
牵云之手
谎称自己有牵云之手
如此低垂的云朵,势必要传达某种交换信仰的温顺
所以从最高的沙丘上走下来的人
放生了一朵白云,或者是被白云放生的一只羔羊
远处在举行混血的婚礼
面色苍白的新娘失身于《史集》的无载:
“在宝古图沙漠,如果你
没有饱饮仇恨,遇到足够多的云,就会溺水而亡……”
祀木叶山
忍不住向西远眺
似乎就能看到大漠的边缘,和孤单的木叶山
乌云起于辽史,闪电照亮白衣观音
表里不一的时机在暗中成熟
圣人的额头,被劫去三根失火的木柴
战马驮走了所有的契丹皇帝
然后在一捆草中等待,等待另一个部落的怒火点燃铁蹄
沙湖里,唯有肥美的天鹅四时捺钵,岁以为常。
轮值之制
在沙漠里完成诗意的交接
盖满印章的手伸向天空,成为储蓄烈日的,火红的萨日朗花
辽阔的,强大的,北方的秘密
被删减,就挑选剩下的勇士;被焚烧,就变成蒙古火焰
真理和美从来都不复杂
一如这千年不变的沙漠,被取缔过沧桑,以及哭泣的权利
今天,一群人在金沙之下,埋下西瓜和歌声
他们轮番石化为巨鹿,任“群星在马厩里踢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