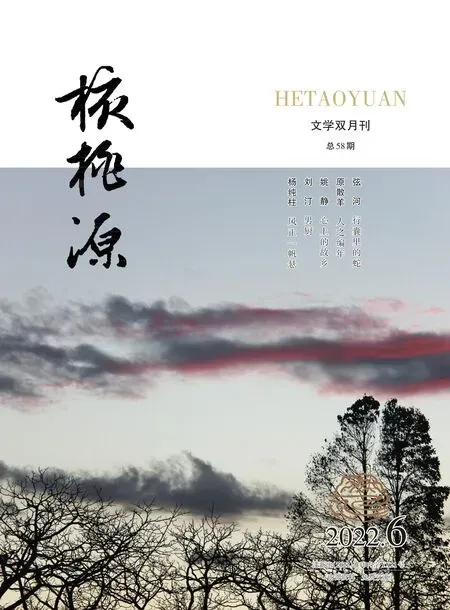行囊里的蛇(组章)
弦 河
鲁院的夜晚
必须有一种新的事物,让同样失眠的灯光,发出深夜的回响。
搁浅的键盘,空洞的字母,沿着爬过窗的月光跳跃,替代某个时空的思考者,剥夺哲学家的话语权。
此刻,我拥有时空的孤独,在镜体和本体的表象中,不断轮回,尝试与一个新的自我对话,辩驳。
让看见的,回归到一种萌芽状态。
为了与这夜晚的静,建立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必须从院子的大门口开始,将类似于苹果的海棠牢记于心,接受生命的相同点。
让蒲公英把卑微的使命,从黑暗中送到我的窗口。
地上的泡桐花,也如前人的步履,踏入历史的青砖。装着月光的镜子,把太阳的光借给了人间。
这是另一种光的延伸。我读故人书,便读到了今朝。便在月光的洗礼中,将院子里的春色传递过去。风吹着落叶,哗哗作响。
有人手持扫帚,将昨夜安睡的执念,送回了它们该去往的地方。
看见故乡
雪落在山峦上,把草木和大地包裹。在冬天进入冥想的农民,想念离巢的鸿雁。
彻骨的寒深入厚土。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认知,和城市的文明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翁子沟的土地上行走了一辈子,万卷厚的书页,他们只识得锄头、镰刀,只与山石和农畜亲切,只念想着锅中油米可食,地里有田可耕。
我常常在梦里,看见桃花落满了山坡,深邃的疼痛长出根须,死死地缠紧我的双脚。
桃,是仡佬族里神灵的庇佑。神灵对大地的洗礼是痛苦的,经历过坎坷才更懂得珍惜。蜕变的可能是,你要质疑一切符合常理的存在。
翁子沟上的经文是基督里面的《圣经》,是佛法里的上乘经文,也是道家里面的道法……我看见这片土地的父亲,看见这片土地的孩子,看见他们各自的眼睛,在时光的轮廓中彼此交汇,而又彼此不识……
在这片土地上,我成为父亲的时候,父亲又成了孩子。落满雪的院子,留着鸡鸭和猫狗少有的脚印。偶有鸟雀寻觅,传来空谷的回音。
桃花引
在我的故乡。桃花点亮了回家的路。
异乡的灯盏失去了力。孤独的屋子,印出一朵水印。
一朵喜欢风的花蕾,一说话就凋谢了。
一枚剥落的碎石块,落入山涧。
一说话就打扰了,风化的频率。
在遥远的地方看桃花,就像看一些生和死的宿命。有的死于无声,有的死于命理。
她的绽开,如胎动的声响。
摄鸟的人
仿佛从遥远的地方赶来,阁楼里的摄影师等不来停息的鸟。他们开始在亭子里熙熙攘攘,探讨春秋,争论人间俗事。
一株独立枯叶中的莲蓬上,飞来一只停息的鸟,带给这株假莲蓬生的气息。
鱼在水里欢。
仿佛这是一片没有鱼饵的净土。
古桥处
你坐在桥上打坐,又像是桥上酣睡的古人。
这是我。你看见的我。
不见船来人往,而风景依然如画。
醒着时静谧,依稀传来鸟声。
停息时,脚下的泥土松动。喧闹的明代,那些懂得历史余温的人才能看见,一轮明月穿过桥廊。
敢问客人,是否备了香烛?
食这人间烟火。
静物书
处于静止的,窗外的阳光。往往大的物体更显静态,小的物体才在尘世摇晃。小的物体更容易消融于世,小的物体更容易为卑微的事感怀。
旅行者。背包客。束缚于石头内上的灵魂。可能是通灵者。暗语。无知。介质。
从高空坠落的神坛,凋落泥土上的枯叶。果实即是信仰,果实即是存在
不!有风吹来,有人等雨。有人在冬日,隔着窗户晒太阳。
当风吹来的时候,一切刚好
春天的小鸟落在秋收后的稻田上,啄出沉睡泥土里的童话。我用手背撑起一架望远镜,在遥远的地方——
在遥远的地方的傍晚,我安静地如一片落叶了。
许久,我看不清楚它。她也终于像海的颜色了。
我折好一只纸风车,让它在田埂上自由地转。
当风吹来的时候。一切刚好。
桃花劫
我无法入睡,像落叶归根的寂寥。当你认识到,我是个没有春天的人。当你又一次看见我开,重生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原罪。
这有什么关系,我爱着的女子,她像花儿开放,偎依着她所爱的美男子。这是我要表达的,无关我生命的意义。
我负气逃离的屋子,现在它终于成了我无法挣脱的枷锁。
我好想再飘起来,飘起来告诉屋顶那只鸟儿,飞翔也许并不是自由。
鸟语者和鸟
相信鸟鸣的,侍养一只鸟。今生无缘成为一只鸟,即使说出鸟能听懂的鸟语。
他不能在树枝上筑巢,瞻望远空,瞻望灵魂深处剩下的空洞。那被绿覆盖的,生出一种忧伤和惆怅。
这只是模拟。把自己围困在鸟体内。看着世界逐渐变小。
树叶和雏鸟的存在,只是一种物体与另一种物体的碰撞。叶子活一生,雏鸟才学会飞翔。
树影
很远。但我感觉到了近。依稀的,弥散的光点,洒在我赤裸裸的身体上。
此时,我像一只狗。一只可怜的狗。花斑散落,以此乞求苟活的命。没有光走在黑夜,擦肩而过的陌生的人很低。
起初来到时,我与所有皆熟。自从脚步向前移动,就听见脚底下有骨子断裂,身体糜烂发出的低吟。
我一无所有地坐着,让阳光消失在树枝间。树下,刚好看见一个细长的影子在时间的刻度上摇摆。它像家乡的棕树。独立在我的窗前,却没有笔直的姿势。也许它想让我看的是,干枯的树皮上割开的年轮,演化了山的背影。
那一道残影,仿佛就要弯成斜阳的姿势。俯身拾起的岁月,抖一抖就给了远方一道狠狠的鞭子。
山寺听钟声
属于自然的水躺在手心,所有追逐得到宁静。我留下来。甚至不说一句话。
——我听见钟声,那时我的心才平静。
鸟语禅香。要去的路总是那么远。——“我听到钟声,我的心得到了安静”。
坐长时间的车,终于颠簸出打工生涯沉睡的疲倦。指尖的新绿,白雾萦绕。清晰的模糊的在午夜被惊醒。仿佛噩梦苏醒。
月明,松下,石子路。我一路走来就走到了心上。
绿叶之外还是绿叶
当山寺打开了门,时间就变得舒缓;禅音相迎,香烛在山色中退去色彩。
佛不语。每向前一步,身体的颜色就单调些。每向前一步,身体就轻了些。
拨开层层叶。深山古寺,鸟影飞掠,轻巧自如。我在穿过树丛的天空中看见一个我和另一个我。
我无法停止向前的步履。回家的路在石子上横横竖竖。
看不见来时路,前面的路就清晰了。
饮大关
水从山中来,春意盎然。
新绿开始骚动,从河面扑来,带来洋溪水源的纯净,带着喜气滋润。
即将享受酒香熏陶的花草,鸟鸣,飞鱼,以及朴实的人们,它们都在歌唱,祝福……
水从地下打起,武陵山脉的精气与五谷。融合,酝酿。
与水土,室温。雄鹰为翅。
饮大关,便饮尽一段过往。忆大关,便忆起一个快要忘却的乳名。在酒中沦为一个酒客,日出而耕,披日月之辉,筹日月之事。
你从远方来,要去往我的故土,将如我站在洋溪山顶上。这便是我要告诉你的,我厚实的脚步丈量过这片山脉的沉重。
行囊里的蛇
天边的霞晕,小时候是一座小小的山坳坳,每一次太阳从遥远的山脊升起,它就在眼眸里闪亮。
一天我只能看见它一次。
为了一次相遇,我背弃了父亲的镰刀、锄头。我放下了,喂养着稻花鱼的梯田和种满蔬菜的土地。
无畏的青春和孤独,它们扮演着农夫和蛇的角色。
长大后,我走到了离它最近的地方。辽阔的海岸,它走来,波光粼粼地洒落一地光阴。
无边无垠的滩涂和沙漠中,它走来,是如此静谧。
它那么的美,一直是想象中的美。
可蜷缩在行囊里的蛇,开始有了苏醒的征兆,随时准备窜出来。
困兽
走出去以后,里面的世界便没了我们自己。
“树欲静,而风不止”。窗,看见的是内心。我们必然在为孤独事而烦恼。在意识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渴望觉醒。而在觉醒后,我们又渴望得到质的升华。沉思者铺下的石子,最后都要成为大众跳跃的格子。
一种棋局,为谋大局者而生。布棋者,破开一种棋局后,又痴迷于新的棋盘格局。
他破局后,棋盘上棋子都有着不可变革的轨迹。
门,锁住的是自我。从一个屋子走出后,不过是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屋子。
偷月亮的人
偷月亮的人的世界,漂浮着未知的鱼。
一边在饮日月光,一边在刨开脚下的泥。假如没有接受文明世界的洗礼,他就会把月光埋在土里,等到有一天把偷来的月亮种下去。
山里的孩子,大海在很遥远的地方。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夜里收集月光。这是他的母亲纺织的生命线。
他要在白天寻找母亲藏起来的针,把月光编织成可以盛装月亮的网兜。
寄生学
关了窗户的屋子,很难听到外面的风声。
耳鸣,持续升温。偶尔经过一辆车,破开完整性。
当我沉寂这夜色中,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完成对立。
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空间,产生摩擦,这应该是,所谓的哲学?
我是在笔尖洗光泽的,虔诚的信徒,甚至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所谓的哲学于我而言,应该是这归途的暖意。
亦或写字楼里失去了自我,正在蜕变成机械化的白领?
这个世界唯一不可机械化的应该就是人性的觉醒。谁,将如何完成?将一种物质和另一种物质融合成化学反应。
闭上眼睛,我们将会在黑暗中撕掉,代表身份的标签,没有明确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在前行中找到归宿?
这一生,我将如寄生虫一般度过,将在潜意识中,自我辨别寄生体和寄生虫的关系。
取光的女孩
我看见一个小孩。她蹲在地上哭泣。
她问我吃什么。
我说我吃白云和星星。
我继续走。
她躲进我的影子。悄悄取走,我身体里的光。
作家
果酱瓶里装着,一片森林的盲盒。
在拆开的童话中,我们一会儿扮演主角,一会儿扮演阅读者。
结尾的部分,已经在脑海出现了很多次。一个作家说,不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自己的死,自己的苦难……
从此我举笔难安。
不,从此,每想在键盘上落下字母,就像在骨头上钉上,一枚命运的钉子。
生命的觉醒从命运的贫瘠开始。童话中,坏人得到了惩罚,好人得到了救赎。
应该是这样,开头,和结尾。都是为了救赎。
所有救赎里,都有一个作者内在的原罪。我们不是在救赎自己,是在救赎那活在童话里的影子。
父子煮茶
父亲指给我看,那株不知何时被他从深山移植小院的苦丁茶树。
苦丁茶,味苦,回甘。
但缺少“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诸多诗意的茶艺。它是一只土陶罐的回忆。
这是煮茶的下午。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在六月归乡。儿时山上的野果子,现在基本过了时节。只有地里的苞谷和时节蔬菜,葱翠的山脉,散发着原本的生息。
多少年了,我没有拥有这样的故乡。就像我漂泊在外,学会了茶具煮茶。这么多年,才把一套茶具带回家,为父亲泡一壶功夫茶。
煮茶,我和父亲的代沟。一壶茶要煮尽农民父亲和农民儿子的一生。
父子煮茶,煮的是搁浅的一片海。
父亲在此岸看炊烟袅袅,我在彼岸看腊月时节的荒凉。
一壶茶忘了,它为什么是一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