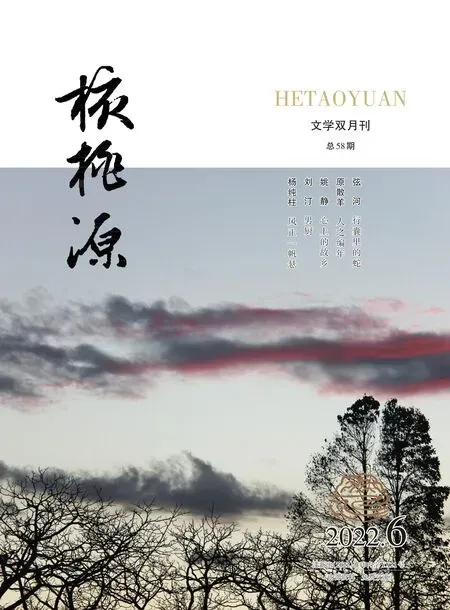五里坡(外一篇)
罗廷辉
南疆的黑山羊最是任性,圈养的驱赶进山放牧,就算牧草再好也吃不饱。而要是放牧惯了的,若关起来喂养,随便吃上几口饲草,就会挤到圈门口,一阵紧似一阵“咩咩咩咩”地大合唱,也不知道是在提醒该进山了,还是在恳求解除禁闭,抑或是在抗议,甚至是在骂娘?
家住五里坡,开门进山,我与羊群为伍,自然选择了放牧。这样一来可就再也没有什么周末和节假日可言了,有的只是日日月月,只是岁岁年年。休说风雨无阻,就是哪天天上下刀子了,不忍群友们饿肚子,我也只有头顶扣口铁锅,照例率群早出晚归。
早早吃过饭,背上背篓,拿上牧鞭,我又来到羊圈前。
圈门刚打开,迫不及待的群友们就争先恐后挤了出来,贯穿过几十米长的栅栏夹道,进入林子后就再也不服从我这群主的号令,纷纷往山道两旁潮水般四散漫开去,一个个饿痨般忙着觅食。
我也懒得管它们,自顾不慌不忙顺着弯曲的小径依山而下,等几分钟后来到村道上了,才从背篓里摸出一个装玉米粒的大塑料瓶,“刷啦啦刷啦啦”地摇了起来。
群友们听到熟悉的响声,顾不上再觅食,一个个疯了似地朝我狂奔而来。
要说在这个群里,有智商不济,体能欠佳的个体,那必然也只会是本群主了。你看那些家伙们,要不是为了避免一头撞到树干上,需要不断绕行,谁不是选的直线,抄的捷径?就是这几米高陡峭到笔直的公路上边坡,也都如履平地般直接冲下来,跳下来,谁也不肯多跑几步,顺山道绕行。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最短,这理论我并没有传授过,可你看我这些群友心里头是不是都有数?
奔跑到我跟前,大多数群友见我光顾着摇瓶子,忘了继续下一步,只管抬头看着我,躜着四蹄围着我急促绕行。而极少数性急的可就没那么老实了,一个个把前蹄搭到我身上人立而起,令我这尊贵的群主也一时灰头土脸颜面无存。要是都只是小羊羔子才如此孟浪倒也罢了,那样的话还可以看作是小家伙们不懂事,言行举止没个深浅,可偏偏为老不尊的也大有羊在,我真是恨不得无赖般凶相毕露一顿拳打脚踢。
问题是我又不是街痞,并不精通肢体语言,只能认栽,妥协,慌慌忙忙拧下瓶盖,甩动瓶子抖落玉米粒,逗引那些耍赖皮的家伙争着抢着去捡食。当然了,这一招在牧山上每天都要使用”N”次以上,我只能意思意思,点到为止,决计不敢把瓶子就此给抖空了。
接下来,我甩动牧鞭,放声吆喝,群友们就应声沿着公路开始向前行进。
喊操我会喊,带操我也带过,可是在这群群友跟前我算是黔驴技穷了。穷尽多少个春秋冬夏,我费尽了移山心力,终归还是没能教化它们,让它们学会列队行进。
这不?滥情的公羊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挑选着追逐着母羊调情;羯羊们明知道自己已经沦为太监,还在跟着瞎起哄;母羊们捉对约战单挑;小羊羔子们紧跑几步,四蹄点地,把自己整个儿横空抛起又落下,此伏彼起乐此不疲。就是有冒失鬼没掌握好平衡摔了个结实,爬起来还继续闹腾……
群友们不要说对成群结队的车熟视无睹,对震耳欲聋的喇叭声置若罔闻,把车逼停了,有的把鼻翼凑过去翕动着也不知道探究个什么,有的干脆在车身上蹭痒痒。什么叫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想必这就是了!
粗门大嗓的吆喝配合着牧鞭尖厉的脆响,好不容易挪出一条通道,才让前边的车仄棱着通过,身后整条路又被那群无赖给缝合得水泄不通。无奈之下,我只有把它们驱离车路,钻入了林间。
黑山羊性喜在陡坡上觅食,身手敏捷,穿行悬崖峭壁如履平地。就是与食岩壁睡岩窟,被人称谓岩羊的羚羊相比也不遑多让。黑山羊又素有豪侠风范,一只只莫不都如土豪般豪爽任性。啃几口野草树叶,“刷啦啦”撒下一把乌金,当是饭钱和小费;观一会儿山景,又“刷啦啦”撒下一把乌金;回到圈里,时不时就又撒下一把。很显然,是把一生当做了一场壮游,把日常当作进饭店消费,到景区观光,投旅馆住宿,在挥金如土买账单付小费。
我的群友们同样豪爽任性,却又心细如发,一到五里坡,就停不下领略小蹄子敲击黄土地石坷垃的快感,成天“哒哒哒,哒哒哒”奔走不息,可又担心我跟不上掉队了,弄丢了,于是一路奔跑,一路轮流沿途点省略号,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始终有迹可循,于是山崖间总有几条被加注了重点标记的依稀可辨的蹄窝印绵延不绝。
也难怪群友们对我如此挂心,五里坡上不拘什么野草,你若有那份心,只要弄到大理三月街药材市场,药材贩子们都会给出一个相应的价码。尤其是什么灵芝菌,青木菌,防风、双参、小红参、大麻药等等诸多品类都价格不菲。群友们都知道我背上的小背篓里,除了装玉米的饮料瓶,还装着一把小巧的锄头;知道小背篓和那小锄头的真实用途;知道我每天都要把这两者的效用给最大化,掉了队张皇四顾那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这不,就为了爬到那棵粗大的麻栗树上,采撷这丛开着黄里带粉娇中含羞的花朵的石斛,我又把群友们给弄丢了。四下里一阵焦急寻找,在隐约可辨被糟践过的草丛间,发现了打着指尖大小“黑点”的一条印迹,巡迹远眺,隐约看到两个黑色身影正隐入树丛。心里揣度着没把握很快追上前去,确保不致真正丢失,我慌忙取出玉米瓶,一边用力摇晃,一边扯开嗓门大声叫唤“嗳唦嗳唦嗳唦唦!”
没过几分钟,群友们沿着原路一个紧跟着一个争先恐后冲我狂奔而来。我不等它们扑到身上胁迫,就忙不迭地拧开瓶盖撒落玉米粒,还特意多抖落了几粒以示嘉奖。
总算只是虚惊一场,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顺势坐在一个草丛上小憩,而有只调皮鬼不是随大家伙在草丛间搜寻玉米粒,而是绕到我背后,把头探到了背篓里。
那正是被我冠以小贪雅号的家伙,她妈一胞两胎生下她和姐姐,看她差不多只有姐姐一半大的个头,打心眼里嫌弃,拒绝哺育她,是我用纯牛奶把她抚养到会啃青填饱肚子。她感念我对她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情,跟我很是黏糊。这不?她把背篓里的瓶子、锄头、草药,包括那丛石斛都逐一作了探究,可毕竟慧眼识珠,最终还是对我的耳垂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
五里坡,西坡较为平缓,松树林居多,东边却基本是怪石嶙峋的悬崖峭壁,多生杂木、藤蔓。若在雨季,漫山遍野都碧草如茵,我和我的羊群自然很少涉足东面。而到了冬春季节,天干物燥,西坡上纵然还有些野草非但不甘于向严寒低头,还执意要与干旱抗争,可也都被黄灿灿的松针捂了个严严实实。我们也只好把五里坡当作书页,从西坡翻到东面。
东面坡对我和我的羊群的深深眷恋是不言而喻的,唯恐我们彻底从她眼前淡出,每到仲春时节她总有惊喜奉赠。
那个时节,五里坡的树木都已勃发了盎然生机,远远望去,满目葱茏。可钻到林间,遍地的野草,却还在一派枯黄。这种时候,为了保证牧归时羊群都能把肚子撑得圆滚,我情愿多付出一些辛劳,不再强行制定放牧区域和线路,只是跟在后面任凭牧群自由觅食。
往往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一两株奇特的植株会赫然映入眼帘。那植株不长一枚叶片,一根光杆上或多或少就仅有一些花蕾或花朵,并且不论茎杆还是花蕾花朵,都红得发紫,绝无一丝杂色。
每次见到这种植株,我都会再也顾不上羊群,蹲下身来,摁住心跳,小心翼翼地把周围的泥土一点点刨去,慢慢把地下的根块根茎完整地挖掘出来。随后,我一定不忘取下连着植株的头部,还有尾部重新妥善埋回土层,把新的希望留待来年春天。只满心欢喜地把中间部分妥善装入背上的小背篓,再去追赶羊群。
这是种叫做竹节天麻的植物,是药材天麻当中的一个稀有品种。天麻种类有数十种之多,每个品种都有相应的价位,唯独竹节天麻的价格,就是问无所不知的度娘,也一问三不知。由不得我不将之引为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珍。
五里坡东面坡曾送过我惊喜,也给过我惊吓,惊喜当然多多益善,惊吓却仅一次都恨不能从记忆中彻底删除。
也是仲春,也是在尾追式的放牧中。时过正午,我汗涔涔攀爬到小白岩离国道仅十余米的林间陡坡,一堆小山包似的枯树叶在眼前突兀耸起。
不久前我还从这里经过,当时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铺满枯枝败叶,但绝对没有这么一大堆。
正纳闷间,随着“刷啦”一声响,一条足有碗口粗细的蛇,从枯叶堆顶部探着头猝然蹿出一米多高。
“轰”,一股热血骤然冲上脑顶,浑身热汗瞬间变冷,所有力气随即丧失殆尽。情急之下,我顺手抓住一棵小树才稳住了身子,避免瘫软地下,滚下陡坡。
这是一条布满黑斑的灰蛇,不,严格地说,应当是蟒,正“嗖嗖嗖嗖”地吐着蛇信的蟒!
天杀的笃定是盘在枯叶堆里下蛋,或者是孵蛋,受到惊吓蹿出头部,准备攻击。
我真的是太难了!所有斗志都已被蟒释放出的强大无比的气场剥蚀殆尽了,更要命的是还没有余地选择默默地定定神,缓缓劲,慢慢转身,悄悄溜走。
一只母羊在那蟒前边,一只小羊则在蟒的侧面,离蟒的身子都不到一米,却又都对死亡威胁浑然不觉,只顾啃食着几星点换做是平常决计看不上眼的青蒿。
那只十几斤大小的小羊,身边的蟒应当毫不费力就能一口吞了它。而那只母羊肯定也承受不住蟒的一波毒液注射。
那只小羊,是我亲眼看着从当初的小不点儿,长到现在这般大小的。至于那只母羊就更得我钟爱了,那是我这个群里第一只波尔山羊,现在才两岁。
记得她一岁时初次产羔那天,放牧地点蒿草尤其繁茂,群友们谁也不肯充当先锋打头阵,任凭我这群主极尽威逼利诱的能事,也都毫无作用。没辙,我只有一边“嗳唦嗳唦”地轻唤,一边踩倒面前的蒿草在前头开路。
等到钻出了那片草坡,来到了空地,我看着羊群还一时跟不上来,就坐下来稍事休息。她率先来到我跟前,还蹭了蹭我,又“咩”地打了声招呼,而后才伏下身子产羔。这家伙,年纪虽小,心思却是极其缜密,分明是自知没法自己把小宝贝弄回家,还怕蒿草太深我留意不到,刻意做出那一连串令人颇感不可思议的举动来。
这么可爱的精灵,你让我如何割舍得下?莫说两个,就是半个也都难舍啊!
不敢放声吆喝,也不敢抛掷石子驱赶,又不甘心忍痛割爱撇下不管,我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一幕惨剧的即将发生。
不曾想,时间就那么凝固了不上十分钟,先前机簧一般弹出的蛇头,竟然慢慢地缩了回去。
危情得以有惊无险地解除,我心头除了庆幸还是庆幸。等到驱赶着羊群逃出很远,心头的庆幸才又换成了隐忧。
不行,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五里坡可是我和牧群的领地,如若任由这么一个危险的敌人潜伏在暗处,岂不防不胜防,再无宁日?
患得患失好半晌,我想到了一个彻底铲除隐患的良策——借刀杀蛇!
有了办法,我不再迟疑,当即拨通了一个兄弟的手机。不想,不久前还在我面前赞不绝口,称道龙凤汤的他,听我说完就不假思索地连声说没空。
我也没多想,转而又给另一个兄弟发了微信。
这个兄弟微信回得还挺快的:哥,换了是以前,我要是不把这尤物弄来烹了,真的会一直失眠下去。可现在我们也得讲和谐,得爱护野生动物不是?
得,我抬起手就一巴掌拍在脑门心:真是不禁吓,一下吓懵过去,老半天回不过神来了。前头那个兄弟那么推崇龙凤汤的美味,却又以忙为托词不来猎杀这条蟒,那不也正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在心底里生了根,保护生态平衡的行为在实际行动中成了习惯吗?
随后,我又想起了五里坡上记忆中年幼时的原始森林;想起了那时候频繁出没,不时祸害牧群的凶残的狼;想起了刚成年时的乱砍乱伐毁灭了树木的荒山坡;想起如今放牧时经常遇到的成群的野鸡,不时误闯羊群的冒失的野兔,树上嬉戏的猴群,林间漫步的麂子;也想起了刚才那条蟒用实际行动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格言的诠释。
一度消失的森林早已在回归,一度迁徙的兽群也在陆续回归,而且回归时摒弃了野蛮的兽性,只带回温顺的和谐……
想到这里,心头便有热油在一波接一波地漫过。心情不再悸动,心间只剩下一个念头:今天,我欠那条蟒一个道歉!
之于我的群友们,五里坡是永不撤席的长街宴。而对于我来说,五里坡是药圃,也是菜园,常年跟随着牧群,不仅有野生药材可以任性采挖,而且还有野菜采摘不尽,野菌捡拾不竭。
五里坡上的树木最是勤勉,一棵棵早在严冬里就憋足了劲,一俟春风吹过,就开始较着劲儿发芽、开花、抽枝。攀枝花、棠梨花、杜鹃花,非但看着诱人,吃起来味道同样鲜美;青刺尖、刺桐尖、嫩无花果叶,漫山遍野所是鹅黄的和嫩绿的,不拘什么嫩叶新枝基本都是美味。
站着的树木多情,躺着的枯枝同样有义。在五里坡,不拘什么时候,哪个季节,只要接连下上两三天的雨,林子里那些年前枯死后折断,掉落在地上的枝丫便会神奇地复活过来,长满一丛丛一簇簇的黑木耳,白木耳,皮木耳和蘑菇什么的。
尤其是每年到端午节前后,雨季来临,铜绿菌、青皮菌、鸡油菌、扫把菌、松毛菌、谷凿菌、皮条菌、奶浆菌、石灰菌、红菌、白羊肝、黑牛肝、黄罗伞、白罗伞、黑鸡枞、白鸡枞、黄鸡枞、马屁泡凡此种种,就连名号都能装一背箩外带一箩筐的各种野生菌,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波一波又一波,多到让你怀疑人生。就算是到了初冬时节,热情如铜绿菌,执着如马屁泡等类的犹自不肯退场谢幕。
在那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下午牧归时,我的小背篓里基本上都会有些种类和品相都绝佳的野生菌,也时有过往的人停下车来求购。遇到此类情况,我历来不奇货居之待价而沽,来人如若熟识便拱手奉送,即便素昧平生,也从不讨价还价,给多少算多少。收获的喜悦得到了分享,就已满心喜悦,钱不钱的,反倒无所谓了。
掐指算来,已有些年没出山了,因为群友难分,因为五里坡难舍。就算有故友邀约出山小聚,也都一概回复:五里坡就在那里,我就在五里坡!
梦游白竹山
据说,要是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夜宿紫金山,于次日旭日将升未升之际,伫立峰巅西望,隐约可见白竹山顶霞光中一蓬巨竹直插云天。那竹子通体玉白,白竹山因此而得名。
传说听多了,却终无缘一睹白竹风采,徒余一腔憾事。
据说,白竹山峰巅下有一迷谷,迷谷内林木遮天,丰草掩地。谷底有一潭灵池,池中央是一个灵泉,灵泉常年迸涌,四时一般大小,灵池经年盈盈满池,旱不落,涝不溢,谷内景色绝好。
传说多了,却终无缘一览迷谷胜景,又添几许失落。
有遗憾有失落就会有惋惜,惋惜扯出牵挂,牵挂久了也就积蕴成了梦幻。一枕绮丽的梦幻,圆了我蛰伏心头多年的伫立紫金遥观白竹,亲游迷谷饱揽胜景的夙愿。
似乎观皎月聆清风坐以待旦,在紫金山顶待了一整夜,又像是恍惚间明丽的白昼就换作了静谧的黎明。银狐刚沉,金龟未升,头顶上铁青色的天幕越来越清晰。紧接着,才一眨眼,苍莽间的沟壑、群峰尽皆被曙色通化。
当第一抹朝晖由东山头箭射而出,越过紫金山顶落在白竹山巅,那里赭色的雾霭于霎那间被点燃了。点燃了的山峦、天际,迅即蓬勃出万道绮丽的霞光,绮丽的霞光间显现出一蓬硕大的龙竹。龙竹气根垒成的如重重壁垒似的根隐在了山后,赫然入目的是竹节遒劲分明,枝叶舒展茂密的成竹,还有支支茁壮着腰身,或高或矮如矛尖似箭镞直指云天的肥硕的竹笋。竹竿、竹笋和枝枝叶叶在霞光的映衬下尽显白玉光泽,悦目赏心,看着,看着,不由得醉了,痴了,看着,看着,不由得浮想联翩,直以为缘竹攀上,即可直抵南天门。
昙花虽美,终难得久久观赏,白竹犹胜于此。转瞬间,东升的旭日放射出万丈光芒,把那硕大的,令人一触目就无法再转睛的白玉竹子消于无形,登南天门的遐想也就被骤然无情掐断。
唏嘘叹惋之余,足以告慰的是迷谷胜景还在白竹山静候着游踪。
梦里不知身是客,神游迷谷,梦境中的我比现实中的我考虑的周全,非但预备了用于披荆斩棘开山辟路的长刀,并且还在谷外就紧紧地握在手心,对着一颗树干轻轻几刀,劈削出一块显目的白膘作标记,以便返程时辨认循迹。没走几步又如法施为一次,还没忘了回头看看先头那个标记是不是还在。说起来也倒真是,一片密林就是一个迷阵,稍有不慎必然迷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森林哟,顶上是参天的古木,古木下还有高大的乔木,随后是一层灌木,一层藤蔓荆棘,见不到一星一点的日光。让人直疑心就算是下瓢泼大雨,那雨水也将全都经由厚实严密的树冠顶端汇流成河,流淌到山下归宗入流了。更让人新奇不已的是密林间通常满地都是枯枝朽叶覆盖着盈尺的腐质土,而这林间根本就见不到这些,平地上铺垫着的是翠绿的草毯,行走其上松软舒适。坡地上也尽是少女秀发似的绿草,灵动着飘逸的神韵。除了这些,林间还绝无鹿鸣虎啸,草丛间也没有蛇虫爬行,就是连小鸟的啾啁和松鼠的身影也见不到,使人在悦目赏心的同时,也不由得疑窦丛生,无形的疑惧由此而生。游密林最担心的就是遭遇虎狼蛇虫,可鸟雀和松鼠是森林的精灵呀,没有了它们,哪由得人不疑心自己误入了死谷,心情也为之一点点地紧张起来呢?
这山谷难道真的没有一个生灵吗?如果有,那又上哪儿去了?带着疑虑,在梦境中继续前行,继续每前行几步就削块树皮作标记,继续痴迷地观赏。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多久,耳畔才听到百鸟啾啁禽鸣兽欢,眼前已是一片豁然开朗。抬头一看,头顶是块圆形的天,天幕上飘着几丝云彩,云彩洁白轻盈,把天幕映衬得分外蔚蓝,蓝得让人心醉。天幕四周是一周或高或矮参差不齐的山峰,一座座翠色四溢,绿得也是让人心儿又醉了。眼前的世界是一个既大且深,大得深得无法比的盆,盆沿是有些破损残缺,但这不仅不影响什么,反倒自成景致。
眼前遍地是如茵的芳草,满目是流淌的翠色。在碧翠的芳草地上,或浅蓝,或淡紫,或鹅黄,或嫣红,盛开着各色各样的山花,似浑然天成,又像是匠心独运的艺术家精心搭配过点缀过,促使人流连顾盼目不暇接。一树树丝条拂地的垂柳散布其间,使人遐想的门户顿开,不由自主联想到阿娜多姿蹁迁起舞的窈窕淑女的身姿,联想到秀女临窗梳理的飘逸的秀发。柳树间有走兽飞禽四散惊走的身影,并且没有一个回眸顾盼,均于瞬息间逃之夭夭,我不由得为猿人先祖选择直立行走姿势的高明而抚掌叹绝,不要说它们群起而攻,就是仅有熊先生和虎壮士迎上前来单挑,看似高大威猛,实则文弱怯懦的我也只有苦于没有土行孙的本事无法土遁罢了。
再前行几步,我终于知道方才何以在森林间遍寻小鸟雀和小松鼠的踪迹而不见了,原来小家伙们都汇聚到风景独好的这边来了。这不?小鸟雀们正扑楞楞地飞行于柳树间,跳跃在枝条上,载歌载舞向我致迎宾曲呢。而小松鼠们却像山村里既怕生又好奇的小顽童,在枝叶间探头探脑,让人顿生几分怜爱。
从小精灵们热情地夹道欢迎的情景看来,灵潭灵泉已近在眼前了。
我的猜测果然没错,拨开门帘般悬挂在面前的一排柳条,一股清凉潮湿的山岚扑面,一阵美妙动听的水声悦耳,一泓明镜似的清泉赫然夺目。走近前一看不由得抚掌叫绝——那潭潭底潭边竟都是用山顶那丛竹子一样悦目的白玉雕琢镶嵌成的!再看那水,一潭水就是一片天,湛蓝,湛蓝。此天更比彼天诱人不知凡几。头顶的蓝天只飘动着几丝白云,难免单调,久观之下心里空落落的,泛起莫名的惆怅。而眼前的这片天却游弋着金黄的,浅灰的,银白的,翠绿的,火红的五彩缤纷的“云彩”,一看之下就让人感到心底里盈盈充实,久观不厌。那金黄浅灰银白的是鱼群,翠绿的是繁茂的水草,火红的不用说就是倒影其间的山花了。
那泉水是喷泉,银柱般的水柱约摸一人来高的样子,让人疑心那是炽热的地心涌出水面,正要射向苍穹的激情,但我却宁愿相信那是一个刚出浴的少女,轻拥薄纱含羞带赧亭亭玉立。她养在深闺,不受外界喧嚣的侵扰,不羡凡思俗趣的绮丽,自甘把满腔忠贞的爱恋都献给这灵潭,献给那些天天汇集灵潭边柳林间群饮群嬉的森林子民们。甘愿守望着这座灵山,守望着那蓬白竹,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穷尽时空。
我为入谷前唯恐迷失此间,不惜耗尽体力挥动砍刀削路标的愚行而哑然失笑,想到的已只是取妻将子来此繁衍生息,星转斗移易尽岁寒暑酷。谁敢说这世外柳园不比陶公的桃园强?
正心猿意马,却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灵泉,正伫立于白竹山巅。白竹山的风,不似别处高山上的风一般如冰冻的皮鞭一样地生硬,抽得人呼吸不畅几欲窒息,抽得人汗毛倒立恨不得把头缩进肩胛骨。白竹山的风,柔柔的,暖暖的。
在柔柔暖暖的山岚中伫立白竹山巅放眼四顾,南面是绵延的无量山麓,东南有巍宝山,东边是紫金山,东北有苍山、鸡足山,北方接踵排列着普映山、老和尚山和太保山,西头极目远眺隐约可见高黎贡山,这些山峰都静默在淡青色的雾霭间。山峰间有河谷,河谷底有明镜似的洱海,有白绸似的西洱河、漾濞江和澜沧江。山脚下,坪坝间,山腰上,或城镇,或村庄,或山寨星罗棋布,或金黄的油菜,或碧绿的麦苗,或苍翠欲滴的核桃树美妙点缀尽情渲染。所有这一切,如烟似幻,让你分辨不清究竟是人间还是仙境……
——老年人群友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