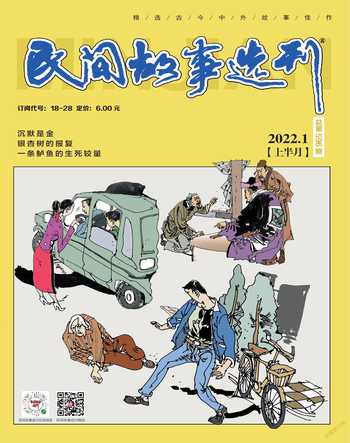故事创作理论也应创新
不知从何时起,在故事界,有这样一些几乎铁定的所谓故事的基本特征和创作理论,即故事要讲究新、奇、巧、趣、智、情、险。故事既是书面文学,更应具备口头传播的特征,故事的结构要单线曲折,主要构架是“一件事三两个人转几个弯”,同时,故事要有一个吸人眼球的核心情节,即俗称为“故事核”,故事的走向要在意料之外,但又要在情理之中等。
这一套新故事创作理论沿用了几十年,好像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笔者作为写故事的人,也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也不敢揣摩这个理论是否因为时空的转换而应该有所创新发展。长期以来,笔者不仅坚信不疑,还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早在2006年,笔者与浙江故事名家丰国需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推开新故事创作之门》的小册子,从素材来源、结构技巧、情节编排、人物塑造、主题提炼、悬念设置、细节运用和语言特点等八个方面,写了20余万字,依据和推崇的就是这么一套故事创作理论。此书一经出版,还被业界誉为新故事创作的基础理论之作,是故事写手入门的教科书。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还为此专门举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研讨会。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作者和编辑为能得到这一小册子而喜不自禁。我们俩也好像成了初入故事之门者的引路人,好像做了件好事。但是,最近,当我着手编辑自己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写成的故事新作品选《一字集》一书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我忽然发现,上述那些被自己一直坚持的理论怎么与我在一个月内创作出来的书没有多少关联度?是自己对故事创作的认知有了改变,还是故事的创作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是后者,那自己与丰国需合作写的那本《推开新故事创作之门》岂非是误人之作?此念一出真是思之极恐。
当年有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最受读者喜爱的故事家丛书,把笔者列入了其中,组织者反复与笔者通电话,对方除了一通极尽赞美的好话,还再三说这套丛书的入选者都是圈内公认的故事名家,能够入选就是对其在故事领域成就的高度认可,非但不用自己出钱,还会给笔者一笔稿费和几百本样书。但一听第一辑就要出版10名故事家的作品集,笔者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一机会。笔者搞了大半辈子民间文学,也算作是半个文人吧,文人似乎都有点怪癖,笔者也不例外,整理创作了几百篇长长短短的民间传说和新故事,但从来没有出过一本郁林兴作品集。
文人出书就像果农摘果,说白了就是其劳动成果的展示,笔者当然也跳不出这个俗套。这些年来,笔者东拼西凑也出版了20多本书。但是,笔者的书几乎都“不按常理出牌”,可以说确定的选题都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2016年出了本书,笔者选择了自己的30多篇作品,并为每篇故事撰写了这一故事背后的故事(包括素材来源、灵感触动、创作体会、事后反响等)。据说当时这一类型的书在故事圈还没有第二本。几年前,笔者又出了一本书名为《枫泾民间传说拾遗》的作品,这是笔者用几年时间为自己的家乡枫泾收集并整理的关于枫泾传说的集子,算是为深爱的家乡枫泾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留下的一点痕迹。
所以,我出的书从选题上来说,都带有我“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的性格烙印,最近出版的《一字集——郁林兴故事新作选》同样也是如此。
创作出版这本书的起因是一次与一位编辑朋友的说笑,因为笔者写了篇以“一”字为标题的故事,他要发表,笔者告诉他,其他内容可按杂志社的风格作适当调整,但标题不能改,或许哪天笔者要出一本全是“一”字为题的书。当时只是说笑而已,并不全然放在心上。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几家杂志社约笔者写一些以抗疫为主题的故事,笔者当即想到当时的说笑,决定正好趁宅家之际,索性写一本以“一”字为标题的故事集。所以,笔者从农历正月十二开始,上午睡觉,下午写稿,以一天一稿的速度,连续写了20多篇以“一”字为标题的故事,看看已经有10来万字,然后就停了笔。这些作品,笔者是边写边发,均散见于全国各地的相关刊物。不少稿子一经发表,又被众多的刊物转载。这些稿件虽并不都是优秀作品,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主题都是正能量的。
在杭州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选题审报单上,他们对这本书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该书是一本比较独特的故事集,所选录的故事作品,全部以“一”字为标题,这是至今为止在全国众多的故事作品集中绝无仅有的。所有作品以“一”字为标题,可以想象这样的选题较一般的故事创作而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充分体现了该书作者作为中国著名故事作家,对故事内涵的理解,以及在故事技巧把握上的深厚功力。该书将对故事作者学习、理解和增进故事创作技巧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同时,作者作为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级杂志《民间文学》负责终审的故事统筹,牢牢把握正确的导向,作品充满正能量,在故事创作中具有引领和风向标的作用。
出版社的推介词夸得有点大,但有一点笔者还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全部用“一”字作为标题,较一般的故事创作,确实增加了不少难度。
但最具挑战的,不在于全部采用“一”字题,笔者自己认为是一天写一稿的速度。试想,如果笔者硬照上面所说的故事创作理论,在20多天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每天写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故事作品的。那么,笔者在这20来天中,是怎么做到一天一稿的?笔者对故事固有的基本理论相对比较熟悉,但又不拘泥于这个创作理论,而是在创作时融入了自己新的理解、新的创作手法。
现在回过头来思考,笔者感觉当时自己的创作方法与传统理论有着极大的差别。当时,笔者一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心中根本不知道今天要写什么样的故事,更不要说已找到了什么核心情节或故事核了,脑子是一片空白的。等到落座,笔者才开始寻找要写的核心道具或素材。比如,看到桌上有方砚台,那笔者于是决定今天就以砚台为主角吧,然后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从网上查阅关于砚台的知识点和相关信息,据此开始架构故事的主要情节、设置人物和悬念、思考意料之外的结尾并提炼主题。待基本有了框架,就开始在键盘上敲打,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来不成熟的想法在写作时往往会冒出更加合理的构想,从而使作品更趋于完善。
比如,刊发于《乡土·野马渡》杂志上的《一块灵璧石》,笔者在写这篇稿子前,看到书桌上有一块石头,就想是否写写石头,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灵璧石曾被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石。于是笔者当即决定就写一块灵璧石。接下来思考,谁会拥有灵璧石,一般来说往往是玩石之人,但笔者以为写玩石者可能比较一般,就把人物设计成一个地质学家,他在地质考察中有个爱好,每到一处名山大川,总会捡一块石头作为留念,这样几十年下来,就收集了众多的奇石。为了赋予主题正能量,笔者把那块灵璧石设计成是一个七帆船型的模样,最后,作为打击乐家的地质学家的女儿,为了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晚会上演出,依托那块灵璧石,创作出了一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为主题的新打击乐曲《千帆竞渡》,这样的构思与结尾才使这一作品充满了积极意义。
实话说,这样的创作方式与传统的故事创作理论相去甚远,似乎也不值得提倡,甚至有悖于文艺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律,特别是一些老故事家,对笔者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认可,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笔者就是依这样的方式,一天创作出一个作品的。
其實,对故事创作理论,笔者一直认为创作要有领先半步的意识。2020年,因疫情影响,学校不能正常开学,要在网上授课,笔者得知这一信息后,就向学校了解了上网课的相关情况。在上海市开始上第一堂网课的当天,笔者就创作了故事《一堂网课》,并很快在《山海经》杂志上发表出来。后来,《一堂网课》还被改编成小品和情景剧,不仅搬上了舞台,还在市级比赛中获了奖。
理论往往会滞后于实践。笔者从《一字集》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故事创作的理论和创作的方式方法不能一味地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新故事的创作理论只有通过不断地探索、创新和发展,才能更有效地指导新故事的创作实践。
选自《松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