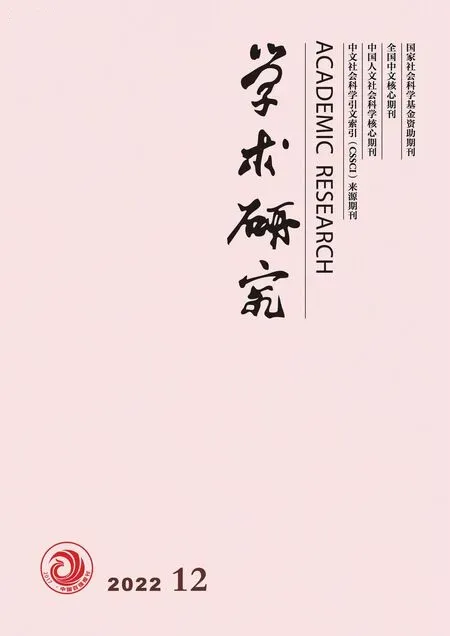STS视角下逻辑研究的三种进路*
臧艳雨
尽管“什么是逻辑”已经构成了逻辑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通常被视为客观的、必然的、分析的、自明的、先验的、普遍有效的。和其他知识类型相比,逻辑代表了那些最客观、最必然的真理,几乎很难想象其与社会文化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学等经验科学有什么关系。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兴起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经历了科学社会学、SSK、后SSK等阶段,渐成一研究思潮,对科学知识、科学实践进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分析,探讨其与社会文化之关系。这其中,逻辑既作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又是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针对逻辑的反思就成为STS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STS视界中,无论是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SSK的代表人物布鲁尔,还是后SSK的代表人物拉图尔、皮克林等,逻辑都是其无法回避的话题。但相比于对于经验科学的关注,学者们对于逻辑(和数学)的关注整体上较少,SSK的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探索了数学的社会学,曾感叹:“和自然科学相比,数学的社会学成果是稀少的,而形式逻辑的社会学,几乎是不存在”。①D. MacKenzie, Mechanizing Proof: Computing, Risk, and Trust, MIT Press, 2001, p.2.究其原因,一则在于逻辑的特殊状态。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传统二分,认为经验科学才可能与社会打交道,而形式科学(逻辑与数学)是纯粹理性的推导,不涉及经验与社会文化。二则在于斯诺(C. P. Snow)所称的“两种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哲学家和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学者之间还没有经常阅读引用彼此的著作,即使两个学科的发展是互补的”。②[美]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戴建平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STS学者需要关注逻辑学的理论进展。而事实上,20世纪后半期以来逻辑学自身的一些研究取向已为STS反思逻辑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与案例资源,如借助逻辑新类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逻辑哲学讨论重新思考逻辑建构主义论题,③臧艳雨:《审视逻辑建构主义:从STS视角看》,《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重新思考逻辑与实践的关系等。本文正是基于此而作,借助逻辑学研究成果扩展STS的逻辑研究进路,以深化STS研究,推动逻辑哲学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促进“两种文化”融合。
一、 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进路
STS视角的逻辑研究,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称作逻辑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logic),或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social studies of logic)。①STS在后期,其研究已经逐步摆脱了狭义的社会学范畴,这里为了术语的方便,仍然使用这两个字眼,不做区分。它关心的是逻辑如何受到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逻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里的逻辑,依照STS的研究范式,指向社会建制、逻辑知识、逻辑活动,而这也预示了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的三种进路。
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关注作为社会建制的逻辑。坦率地说,默顿并没有提出逻辑社会学概念,也没有对逻辑展开专门的探讨。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事业,整体上考虑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而逻辑作为科学中的一种(和数学一起归于形式科学)而被他讨论。他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探讨科学技术中研究兴趣的转移与研究问题的选择如何受到社会背景及文化价值的影响。他发现在17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对文学和宗教的兴趣在衰落,对科学的兴趣在持续增长。而在科学中,人们对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化学、植物学等的兴趣都有持续的增长,而同时,人们对逻辑的兴趣并没有增长。以17世纪英格兰出版的唯一科学杂志《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文章分类表为例,在1665年至1702年间,涉及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文章只有2篇(1668—1670年有1篇,1674—1676年有1篇),而数学有99篇,物理学685篇,生物学366篇,解剖学与生理学226篇,医药科学257篇,地学186篇。②数据摘自1665—1702年《哲学汇刊》文章分类表。参见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81。
默顿认为,科学兴趣的短期转移是由单个科学家的贡献所推进的,但是,发生在17世纪英格兰的大规模研究兴趣转移的现象,就不再完全是由科学的内在发展决定的,影响因素一定在其他方面。默顿受韦伯的影响,认为科学家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人们科学兴趣的增长与选择的“先决条件已深深扎根在哺育了它并确保它进一步成长的社会文化之中,它是长时期社会文化孵化生长的一个娇儿”。③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55.默顿由此将其溯源到文化与社会背景中,如新教伦理以及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逻辑,却被降到从属的位置,因为逻辑被认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但却可能使谬误长存,虽然逻辑是思维中的一种有用的因素,但对实在的检验并不来自学究的逻辑,而是来自事实的观察。”④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71.同时,经院哲学衰落,因为它充满虚假的教义,让人们远离上帝;而中世纪逻辑学也受到拒斥,它被认为是伪亚里士多德哲学,由于使用了严格的三段论推理而以假乱真。当然,默顿也并不认为它们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或完全是理性因素或内部因素单方面决定的,而认为它们是内部与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默顿由此探讨了科学的精神气质,以及科学运行的社会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强调通过构建恰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来保证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科学精神气质的实现等。
STS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张建军较早在我国提出了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设想。他指出:“逻辑哲学学科早已与科学哲学学科并架齐驱,而与科学社会学并驾齐驱的逻辑社会学却并没有问世”,⑤张建军:《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哲学动态》1997年第7期。并由此提出为了探索如何走出我国逻辑学发展的困境,要借鉴长足发展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建立作为逻辑学与社会学发展之边缘学科的逻辑社会学,利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逻辑学的发展,把逻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把逻辑教学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活动,把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社会系统来加以考察和探讨。因此,他建议,依照科学社会学的范例,逻辑社会学的研究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界内研究和界外研究。界外研究主要是逻辑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可分为逻辑的社会功能和逻辑发展的社会条件两个方面;而界内研究则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逻辑界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它关系逻辑学家、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研究,逻辑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分层与发展战略研究等等”。①张建军:《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哲学动态》 1997年第7期。在此思路下,我国的一些逻辑学学者进行了探讨,内容主要集中于探讨逻辑的社会功能,逻辑与科学、教育、文化、社会发展等的基本关系。如刘培育组织编写的“逻辑时空丛书”,晋荣东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王习胜、张建军的《逻辑的社会功能》,台湾学者的《中国大陆现代逻辑系统之观察》,等等。
这种基于科学社会学范式的逻辑社会学研究,可视为STS视角下逻辑研究的进路之一,将之称为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而张建军所提倡的逻辑社会学的界内研究和界外研究两条思路,由于逻辑的社会功能属于界内研究的第一个方面,除可在此继续深入(如探讨智能社会对逻辑教学和研究提出的新需求)以外,对于逻辑发展的社会条件研究,以及逻辑界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逻辑学家、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研究,逻辑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分层与发展战略研究等,仍有较大的可扩展空间,对于推动当前我国的逻辑学学科发展等仍有重要意义。
二、逻辑知识的社会学进路
逻辑知识的社会学关注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逻辑知识,顾名思义,即关于逻辑的知识,也即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它指一套必然地保真的推理规则,如分离规则(modus ponens,从p和p→q,推出q),或者一套有效的图式或真命题,如排中律(p或非p,记作p V¬p)。这条进路可以扩展出两条子进路。
(一)逻辑知识的争议案例
爱丁堡学派提出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要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中,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对于逻辑知识(和数学知识)给予了专门的讨论和关注(尽管他没有提出逻辑的社会学或逻辑知识的社会学这些概念)。他将逻辑(和数学)作为“知识社会学中最难克服的障碍”,②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2nd ed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83.认为它们代表了圣物中的圣物,这些圣物所具有的光环阻止了人们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尝试。如果这两部分无法得到社会学分析,那么知识社会学的论断就没有任何说服力。爱丁堡学派由此开启了对逻辑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进路,以社会利益作为解释资源,找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
早期爱丁堡学派主要使用宏观利益的解释资源,针对历史争议案例进行分析。这条进路后期经过巴斯学派的科林斯的进一步细化,在研究对象上不但关注历史案例,也关注当代案例。在研究方法上不但采用了历史分析,也引入了经验研究,如访谈、参与观察等。在解释资源上扩展了利益的内涵,不但包括宏观的社会利益,也包括认识、专业、职业等利益。在案例分析上细化了三步的分析步骤:1.分析实验数据解释的弹性;2.展示解释的弹性所带来的争论以及争论结束的机制;3.把这个工作与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联系起来。③H. M. Collins, “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11, no.1, 1981, pp.3-10.依照这一模式,在逻辑学的争论案例研究过程中,当选择一个争论案例进行研究时,首先展示双方就某问题争论的观点,其次展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共识如何达成、双方采用了哪些权宜之计、诉求于哪些解释资源、争论如何结束,最后把这一过程与更为广泛的职业的、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等背景联系起来。
由爱丁堡学派所开创并经科林斯所细化的这一进路,可以谓之逻辑知识的争议案例研究进路。在这一进路下,布鲁尔分析了20世纪早期发生在逻辑学家莱维斯(Lewis)与贝尔纳普和安德森(Belnap & Anderson)之间关于是用严格蕴涵还是用相干蕴涵来解决实质蕴涵怪论的一场争论,④David Bloor, Wittgenstein: A Social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Macmillan, 1983, chapter 6.库什(Martin Kusch)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胡塞尔与弗雷格、罗素等关于逻辑反心理主义的争论,⑤M. Kusch,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 Case Study and a Defense”, M. Kush(ed.),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pp.15-38.普尔克奇宁(Jormo Pulkkinen)分析了弗雷格和施罗德无法说服德国的哲学家接受数理逻辑的原因,揭示了其背后的哲学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影响①J. Pulkkinen, “Why Did Gottlob Frege and Ernst Schröder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Persuade German Philosophers of the Virtues of Mathematical Logic? ”, M. Kush(ed.),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pp.39-60.等。这一模式不但可以分析逻辑历史上的争论案例,也可以分析当代发生的争论案例,展示这些争论中社会因素始终存在,尽管它不一定是决定性的。
(二)逻辑知识的社会史
该进路的主要贡献在编史学上。20世纪80年代,受到数学社会史②H. Mehrtens, et al(eds.),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Mathematic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81.的影响,德国的学者发起了一个项目:建立逻辑社会史的案例研究。③V. Peckhaus, “Case Studie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History of Logic”,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vol.7, 1986, pp.185-186.以逻辑史学家为主的学者致力于对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发生在德国与英国的现代逻辑的出现进行历史的分析,试图找出影响现代逻辑出现的外在的因素,如在现代逻辑的起源与发展中,制度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制度因素、性别影响(女性)、④Karin Beiküfner, Andrea Reichenberger, “Women and Logic: What Can Women’s Studies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l Logic?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vol.6, 2019, pp.6-14.教育的影响等方面。⑤C. Thiel,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Logic”, V. M. Abrusci, E. Casari , M. Mugnai(eds.),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 Logica, San Gimignano, 1982, pp.175-191.该研究主要属于情境主义编史学。逻辑的社会史旨在找出影响逻辑史的社会政治条件因素等,因此,从编史学角度关注社会因素的介入,也就成为逻辑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可能进路,可以扩充逻辑的社会学研究。如布伦伯格·乔蒙特(Julia Brumberg-Chaumont)以社会史的视角分析了中世纪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状态:被作为一种人类学规范与社会规范,用以区分那些“逻辑上不能的人”(logically disable people),逻辑(和语法)从而成为欧洲教育系统的基本课程。⑥Julie Brumberg-Chaumont, “The Rise of Logical Skills and the Thir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the ‘Logical Man’”, C. Rosental, J. Brumberg-Chaumont(eds.), Logical Skills: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irkhauser, 2021, pp.91-120.罗森塔尔和布伦伯格·乔蒙特编写的《逻辑技能:社会历史视角》则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探讨逻辑的两种观念:一种作为内在的人类能力,一种作为可以训练和掌握的技能,关注历史上的逻辑使用所具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态。⑦C. Rosental, J. Brumberg-Chaumont(eds.), Logical Skills: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irkhauser, 2021.
在逻辑知识的社会史这一进路下,现有的STS研究大多是关于经典逻辑演绎系统的,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兴起的逻辑新类型(如非形式逻辑等当代论证理论、非经典逻辑等)则为该进路贡献了有利的案例资源。如非形式逻辑的提倡者、逻辑学家布莱尔(J. Anthony Blair)曾于2009年在我国做过一个系列讲座——《非形式逻辑的社会史》,详细论述了非形式逻辑起源及成长的社会背景,即它如何从20世纪央格鲁—美国的分析哲学传统以及北美的社会及政治背景下发源及成长起来,⑧J. A. Blair, “A Social History of Informal Logic”, the manuscript of the lectures by J. A. Blair at the Institute of Logic and Cogni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009.可谓贡献了一个逻辑社会史研究的案例。
而女性主义的逻辑社会史则亦是一条可能的进路。如安德烈·奈(Andrea Nye)曾提供了一个逻辑史的女性主义的视角,贡献了逻辑的社会史研究。她重读逻辑史,发现这个工程排除了特定的群体,让部分人保持沉默。比如,亚里士多德逻辑被设计来排除非希腊人,中世纪逻辑排除了非基督教人,弗雷格逻辑排除了非印欧语系人。三段论是为职业论辩家而生的,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庭或政治集会上抛出论证。弗雷格逻辑是和他的反自由主义、反犹太主义、超保守主义相一致的。⑨A. Nye, Words of Power: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History of Logic, Routledge, 1990.
此外,学界关于中国古代逻辑(及佛教逻辑)的研究既为逻辑知识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案例资源,①布鲁尔曾在其《知识与社会意象》中设想了可供替代的数学与逻辑。而反之,逻辑知识的社会史进路亦为中国逻辑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了中国特定的逻辑理论(名学和辩学),三大逻辑传统(印度、中国、古希腊)所受的社会限制以及文化制约如何造成了不同的三大逻辑知识体系,逻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如何,这是逻辑社会学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
三、逻辑实践的社会学进路
逻辑实践的社会学关注作为实践活动的逻辑。这种活动既包括了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知识的活动,也包括了特定文化群体的实践推理与论证活动。
(一)逻辑学家构建逻辑知识的实践研究进路
STS在SSK之后出现了实践转向,即后SSK,其所关注的重点也从静态的科学理论知识转向动态的科学实践。后SSK相比于SSK,对于逻辑的关注则更为稀少。由于后SSK所关注的实践大多是自然科学的实验与实验室实践,是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内外的社会技术网络的建构等,②A. Pickering, “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 A. Pickering(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26.在面对这些高度理论化与形式化的学科时,逻辑的实践似乎并没有类似于这些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的对应之物。后SSK的代表人物拉图尔认为,对于形式科学,目前还没有人有勇气对之进行一种仔细的人类学研究,而这项工作是应该做的。③B. Latour, Scientific in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6.皮克林探索了建构四元数概念的实践,却没有对逻辑展开探索,但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④A. 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114.“我们仍然对理论的、概念的实践知之甚少”。⑤A. Pickering(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40.后SSK尽管没有专门针对逻辑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但在后SSK的视域中,仍可发现其逻辑实践主要指向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知识的实践。在这一“发现的语境”中,后SSK研究逻辑学家如何构造和选择逻辑定理、规则、理论等,故皮克林对于数学概念实践的探索,拉图尔设想的对于形式科学的人类学探索,都属于此类。进入21世纪后,罗森塔尔(Claude Rosental)受拉图尔的影响,结合实验室研究和争论研究,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的方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模糊逻辑的一场争论,⑥C. Rosental, Weaving Self-Evidence: A Sociology of Logic,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其成果被称为“第一部系统地经验地探索形式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的著作”。⑦C. Greiffenhagen, “ A Sociology of Formal Logic? Essay Review of Claude Rosental’s ‘Weaving Self-Evid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40, no.3, 2010, pp.471-480.而罗森塔尔也是在STS领域明确提出逻辑的社会学概念的学者,他的著作《编织自明:逻辑的社会学》的副标题明确地使用了“逻辑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logic)这一字眼。这些研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考察逻辑学家在构造逻辑系统、逻辑知识时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揭示在这一动态实践过程中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等,这也由此成为逻辑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进路。
(二)另一种实践活动:人们的推理论证实践的研究
这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论证理论(非形式逻辑、广义逻辑、语用论辩术等)而提出的一种新思路,可将之纳入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并借鉴STS研究方法扩展这种研究,使之成为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可能进路。它主张探讨不同文化群体的推理和论证的具体实践,由此展开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分析等等。这种扩展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1.逻辑学中的自然转向。自然转向在这里用来指逻辑学对于经验世界的关注所带来的转向,关注逻辑的实践性和经验性。加拿大逻辑学家约翰·伍兹(John Woods)在2013 年出版的《推理之谬:将推论逻辑自然化》中曾用过这个术语,这里用它概括20世纪中期以后逻辑学研究的动向,可以把它分为“认知转向”与“实践转向”①J. Woods, Ralph H. Johnson, Dov M. Gabbay, et al., “ Logic and the Practical Turn”, Dov M. Gabbay, Ralph H. Johnson, et al.(eds.), 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 Amsterdam: Elsevier, 2002.两个取向。逻辑更多关注人类高级认知活动,以及人们具体的论证实践。在经典逻辑之外,陆续出现了认知逻辑以及非形式逻辑、广义逻辑等逻辑新类型。这种取向为思考逻辑与社会、文化、实践等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背景。
2.自觉逻辑与自发逻辑的划分。逻辑哲学家苏珊·哈克曾将逻辑划分为自发的逻辑(Logica utens)与自觉的逻辑(Logica docens)。②S. Haack, Philosophy of Log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6-17.自发的逻辑指向人们实际推理和论证的实践,自觉的逻辑指向人们对于推理和论证实践的理论阐述,从自发逻辑到自觉逻辑,是一个从非形式论证经过符号化表达,而形成形式论证的过程。STS对于逻辑的反思主要针对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系统的实践,即针对自觉的逻辑实践,探讨这一动态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的、认知的以及物的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自发的逻辑实践需要加以关注。
3.形式化的目的与限度。苏珊·哈克曾将非形式论证与其形式化表达之间的符合问题视为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人们的具体论证实践作为非形式论证,其评价既有逻辑的方面,也有修辞的、论辩的方面,而形式逻辑只发展了其逻辑的方面,即保真的方面。哪怕在形式演绎系统中,经典逻辑是最核心、应用范围最广的部分,但也有其特定的限度,如它不能表达时态、模态、道义等,因此才通过添加具体算子或修改基本公理等方式形成各种非经典逻辑。而对非形式论证中修辞、论辩维度的关注也促使了逻辑学“实践转向”、当代论证理论等的出现。
4.广义逻辑等当代论证理论对于具体论证实践的关注。当代论证理论挑战了形式逻辑在刻画日常论证与推理方面的局限性,强调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具体论辩实践。形式逻辑不能完全刻画人类的具体论证实践,在形式化过程中,论证的各种丰富信息被忽略掉。如把形式演绎逻辑应用于当代社会与政治论证领域,一些问题就会开始出现。比如当把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应用到日常论辩时,在把自然语言翻译为符号表达的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争议。又比如,翻译完成以后,会出现如下情形:一个论证在形式上是演绎无效的,但实际论证却是令人信服的;或者一个演绎有效的论证,实际论证却可能是前提真而结论假的结论。演绎逻辑对于有效性和无效性的评判标准并不适用于区分日常论证中的好论证与坏论证。基于此,北美兴起了非形式逻辑运动,荷兰发展了语用论辩术,试图对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非形式论证重新进行分析和评价,着重关注当代社会日常论证中——那些发生在报刊和杂志上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的、政治的论证——语用的、情境的、论辩的和修辞的维度,进行论证的识别、分析和评价,找出它的论证类型、论证结构、论证图式和论证规范。进而,如果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出发进行考虑,关于阿赞德逻辑的争论历史也表明,形式逻辑不是一个合适的文化比较的工具,尤其是面对非西方人的论证,需要一个更为丰富的逻辑概念。③C. Greiffenhagen, W. Sharrock., “Logical Relativism: Logic, Grammar, and Arithmetic in Cultural Comparison”, Configurations, vol.14, no.3, 2006, pp.275-301.由此而出现的广义逻辑主张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论证规则,将逻辑视为说理和论证规则的集合,并由此展开对于不同文化群体论证实践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④鞠实儿:《广义论证的理论与方法》,《逻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逻辑学中这种对具体论辩实践的关注以及由此形成的逻辑新类型,可视为对于自发的逻辑实践的关注,可以将其纳入STS研究视角中,由此扩充实践的概念,使之既包括自觉的逻辑实践,也包括自发的逻辑实践,从而扩展STS的研究进路,使之既包括针对逻辑学家构建逻辑系统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也包括不同群体具体论证实践的研究。目前STS学者主要发展了前者,后者正是需要扩展的领域。
5. STS学者对于自发逻辑实践的关注。从自发逻辑实践探讨逻辑的社会学,这条进路尽管没有展开,但从布鲁尔到拉图尔等STS学者对此都有关注。如果回溯布鲁尔的研究,早在他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中,他就曾根据阿赞德逻辑的案例对此有所探讨。面对阿赞德逻辑显然(apparently)包含有矛盾的推理,布鲁尔提醒我们直面这种论证实践,启示我们跳出现有的形式逻辑知识框架去重新思考作为论证实践的逻辑。布鲁尔通过分析阿赞德人具体的论证实践,指出这里并没有矛盾,在阿赞德逻辑的案例中,既存在人们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也存在与这种模式相关的各种理论阐释,后者即是各种逻辑理论和逻辑系统。布鲁尔指出,这种理论阐释在有些社会中得到高度的发展,而在阿赞德社会中,这种理论阐释达到的程度最低。依据布鲁尔对于知识的社会学定义,知识是集体共享的信念,那么逻辑知识既包括演绎逻辑知识体系,也包括人们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因此,阿赞德逻辑是阿赞德人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具有其合理性,它在阿赞德人的实际论证中建构起来,需要我们深入其论证实践中去考察。
可以说,布鲁尔是在对于演绎逻辑的反思中重建他的逻辑社会学分析框架,探求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逻辑的影响的。这种探求由此发展出一个二分进路:通过对演绎逻辑知识体系(如对逻辑规则)的社会学分析,他指出演绎逻辑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本性,指出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逻辑,如三值逻辑与二值逻辑处于同一个水平面;而通过对阿赞德逻辑的讨论,他又指出一个特定民族的推理规则可能因社会文化而不同,阿赞德人亦是这样一个可能拥有不同推理模式的民族。因此,无论是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要纳入社会学分析中。殊途同归的是,拉图尔将形式系统视为计算的中心,认为其是行动者网络系统中建构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手段。他对于阿赞德逻辑对称性的思考,也彰显了他对于逻辑实践的关注。
以上思考构成了本文主张的一种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新进路:基于当代论证理论。一方面扩充实践的概念,使之包含人们的推理论证实践,即自发的逻辑实践;另一方面持大逻辑观,①根据张建军老师关于基础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划分,演绎逻辑属于基础逻辑,推理模式属于应用逻辑。参见张建军:《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针对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实践与论证方式。在这一进路下,罗森塔尔对公共游行作为一种劝说与修辞工具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维度的探讨,②C. Rosental, “Toward a Sociology of Public Demonstrations”, Sociological Theory, vol.31, no.4, 2013, pp.343-365.克斯(W. Keith)等引入论证理论开展的针对科学政策的论证与对科学理论的批评研究,③William M. Keith, W. Rehg, “Argumentation in Science: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Science Studies”, E. J. Hackett, O. Amsterdamska, M. Lynch, J. Wajcman(eds.),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3r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pp.211-239.鞠实儿等针对中国古代论证实践的分析,④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以及利伯曼(K. Liberman)对于西藏辩经活动的人类学观察等,⑤C. Rosental, “Certifying Knowledge: The Sociology of a Logical Theore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4, 2003, pp.623-644.都是针对特定论证领域(政治论证、科学论证等)以及特定文化群体(中国古代、佛教)的论证实践和论证规则的探讨,这都是在此方面的有益尝试。
四、结语
STS视角下的逻辑研究整体上较少,但这确实是一个从社会文化角度理解逻辑的非常显著的尝试。而“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试图表明,逻辑也是社会学探索、人类学观察以及历史学分析的对象,是探索智识活动的物质与社会形式的有效的数据对象,可以纳入社会文化研究的范畴”。⑥C. Rosental, “Certifying Knowledge: The Sociology of a Logical Theore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4, 2003, pp.623-644.通过从逻辑学中借鉴其研究成果,扩展STS的逻辑研究进路,由此形成逻辑社会学的三条研究进路,探讨逻辑与社会文化之互动关系。三条进路各有其优势所长,彼此又有所交叉,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逻辑。因此,逻辑的社会学这一概念包含了一套基于理论的经验研究,是对逻辑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逻辑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的一个交叉分支,是逻辑学与STS的交叉分支,它拓展了STS的逻辑研究进路,也扩宽了逻辑学的研究视野,对于推进STS研究、逻辑学研究以及逻辑史的编写方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