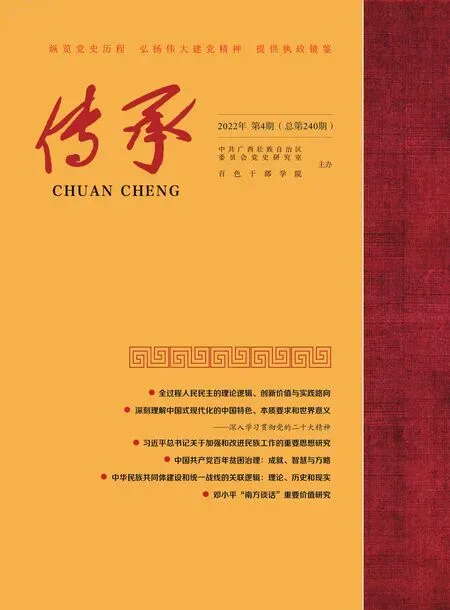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性的交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潍坊市杨家埠村为例
□ 郭文静,赵玉宗,孙亚楠
青岛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一、研究情况介绍
(一)理论应用
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西方文化在催生了现代技术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出与之相配合的完整的社会结构……当时中国社会在向其学习时,既丢掉了对传统的自信,又难以接受新秩序,未得其利,先蒙其弊[1]349,351。一个世纪之后,现代性伴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已势不可挡。当时,费孝通申明“传统力量和现代动力是社会变迁的双重影响因素”,同时肯定了二者相依相生对乡土重建的价值,并建构了“依托乡土产业的形式在‘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中构建中国现代性”的乡土重建思想[2]。如今,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乡村及以其为载体的文化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被解构,或在产业开发过程中被涵化[3]40,现代性的问题和它的进步意义同步而来。文化产业化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增强地区文化自信,在“文化基因”多样性的基础上构筑良好的 “文化生态”[4]111,进而推动乡村振兴。
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提高,依托乡村的传统手工艺类遗产衍生的旅游业,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旅游业是传播传统文化价值的良好渠道,通过带动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建筑、自然资本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地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5]。但一些深植乡土社会文化根基的传统手工艺,如木版年画、剪纸等,其审美与文化价值却仅能在较小的群体中获得认可,因此,应打破传统手工艺实物经济自产自销的模式,建立沟通当代旅游者的文化旅游场域,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当前,在旅游业介入的情境中,手工艺的发展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地方手工艺的传承者,另一类是代表现代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开发者,在政府引导和非遗所带来的资本发展前景的吸引下注入乡村。有研究表明,当地手工艺传承者和旅游开发者间的合作蕴含着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6],但现代性的力量在这场角力中往往居于强势地位[7],当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甚至传统的价值被忽略时会导向“虚假城镇化”“过度商业化”“被想象的遗产”[3]47等将文化表层化和碎片化的不可持续局面。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上的旅游业如何冲破实践中的枷锁、运用传统与现代性的力量做到“不忘本来”与“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以杨家埠“风筝年画之乡”为例,依据杨家埠传统手工艺类遗产的旅游发展实践,以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为基点,以费孝通乡土重建理论为导向,以“人”“物”“业”的角色转变为骨架,以传统与现代性的博弈为脉络,聚焦网络的联结中行为者的困境与冲突,以此探究传统与现代性的结合机理,为传统手工艺的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观察的视角。
(二)杨家埠非遗旅游发展沿革
杨家埠又被称为“西杨家埠”,行政管理上隶属于杨家埠旅游开发区。截至2021年12月底,村庄共有438户,1535人(1)数据来源:村委会工作人员;访谈时间:2021年12月。。杨家埠木版年画与潍坊风筝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木版年画制作技艺自明代起传承至今,已有650余年历史(2)数据来源:木版年画传承人;访谈时间:2021年12月。,几经繁荣与衰微。农业社会时期,当地人将手工艺与农时节令巧妙配合,繁荣时期有“家家印年画,户户扎风筝”之景。随着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到来,木版年画市场急剧萎缩,从业人数也随之缩减[8]。现今,这两项手工艺的制作基本上已完全分离,直接从事制作的总计在30家左右。该地的旅游业起步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其设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并分别于2002年、2008年制定《杨家埠民俗村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景区提升与修建性详细规划》[9]。经过一系列的耕地回收、村落拆迁建设及招商活动,杨家埠现有旅游项目包括村集体所有的“民间艺术大观园”、当地人经营手工艺品店铺的“风筝年画一条街”,于2019年建成的园林式仿徽派建筑群“梦里水乡”、商铺式仿古建筑区“文化创意梦想小镇”一期。
(三)研究方法
本调研组成员于2021年11月3日至2022年1月6日到杨家埠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研,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并以研究文集、政府网站报道以及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为辅助。深度访谈对象包括“风筝年画一条街”的从业者、非遗传承人、当地村民,以及旅游开发项目的从业者和运营管理人员、村干部,共16人。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传统手工艺的经营及传承现状、旅游发展的缘起和经过、访谈对象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感知与看法、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等。同时,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了解社区与企业的非遗生产、销售和旅游接待等活动。
二、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
(一)传统与现代性的新旧相生
“传统”指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仍能满足今日人们需要的遗产[10],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匮乏经济”的形态下形成了“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当物质资源水平较低的“匮乏经济”面临以“无餍求得”为特征的、扩张的“丰裕经济”时,“匮乏经济”体系无疑无法抵抗后者的瓦解之势[1]341-343,347,从而经历外源的、被动的现代化的过程[11]。非西方国家在处于这样一个备受冲击的发展转折点时,除去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的断裂”——“人类历史并没有一个受普遍性动力原则支配的总的发展方向,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与传统社会秩序间存在相互分离的断裂”[12]4,正如“丰裕经济”本身重技术、轻社会组织,导致人们置身其中,却不晓自身意义在何,使得社会缺乏完整性[1]350-351,“断裂的现代性”也产生如此的问题,而在我国前现代“传统”的生产生活中却贯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13]36。因此,现代性为传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需建立在历史文化传统之上[14]。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我国传统手工艺业被瓦解、乡村经济瘫痪时提出以乡土工业辅助乡村发展的学说,当今,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伴随着传统手工艺使用价值的消失,其蕴含的文化、美学等价值也一并退出大众视野,而随着整体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旅游业以另一种形式传播传统的价值,沟通传统与现代性,成为一些手工艺乡村的主要发展途径。
(二)手工艺类遗产的当代价值
“代表着传统和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成为今天与未来我们发展文化和经济的基础与资源”[15],旅游业对“传统”的开发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16],仍应遵循新旧相生的原则。当前,旅游业对于手工艺类非遗的开发仍趋向于以浅层的手工艺产品的呈现为主,忽视了文化的整体性和生态性[4]105-113,[17]53-59,深入探究传统的当代价值是对传统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前提。
1.生产方式: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到人的自我完善。与当前高效率、高产能的工业化生产相比,传统手工艺业的生产方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遵循一种有机、整体、综合的自然观,后者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人的智慧与技艺开辟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手工艺品是自然经由人进行的转化,人以自身的性灵描摹自然的精魂,它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精神需求,这种生产方式激励民间创造力与民生价值[18],昭彰着一种“个人从团体中获得他生活需要的高度满足”的完整社会组织[1]346。
2.文化价值:社会教化与精神娱乐。传统手工艺原先作为一种民间的艺术,反映着乡土意识与乡土伦理,蕴含着乡土哲学与价值观,在乡土社会中承担着文化教育、娱乐的功能[19]145。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按题材可分为“祈福迎祥、辟邪保平安”“吉庆欢乐、吉祥如意”“小说戏曲、神话传说”“民俗风情、生产劳动”[20]。在安土重迁的年代,这些手工艺品成为各地乡间相互沟通、增长见闻的渠道,无形中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41。木版年画等传统手工艺滥觞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中国人通过对天地自然之道的体察与敬畏,赋予其人文的内涵与意义,发展出相应的民俗与用品,使之为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服务。
三、传统与现代性的交织:从文化遗产到旅游资源
(一)手工艺从业者的进入和退出
截至2022年1月,杨家埠有6家木版年画手工制作画店,均为非遗传承人经营,以及一家下属寒亭区的事业单位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手工风筝作坊20家左右,其中天成风筝厂通过向节事花灯的转型成功发展成当地的龙头企业。大多数店铺坐落于“风筝年画一条街”,兼具作坊与展销功能。传统手工风筝因其保留的使用功能,以及向节事花灯的转型拓展了市场空间,使其当前生存状况优于木版年画。然而整体来看,当前二者均面临传承与发展的困境。这一方面源自外部的冲击,即同其他行业相比,手工艺从业者前期学习成本高,而后期回报低[17]44,木版年画研究所也同样面临着招生就业去向问题。另一方面,在于行业内的传承机制断裂。由于市场空间急剧缩小,一些家族传承出现断裂,旧时手工艺行业有“宁赠一锭银,不传一口春”的说法[21]22。当地重新从事该行业的年轻人与其他同行构成显著竞争关系,这种情况造成新旧之间愈发难以实现传承交替。特别是在面临当代机器制造的高效能、高回报以及手工艺业市场空间狭小、技艺提升艰难所带来的双重冲击时,部分青年手工艺人难免会认为前景渺茫。因此,改善当前从业者的利润与市场空间是实现非遗“活化”的动力,同机器制品相比,手工艺品的实用性虽已被不同程度的弱化,但其所蕴含的审美、文化、自然认知、价值观等艺术属性和文化属性却构筑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宝库,是当今各行各业在促进非遗的当代发展时所应汲取的重要养分[21]34,[22]。
(二)旅游资源的翻译与呈现:基于游客体验的视角
旅游产品相较于手工艺品具有不同的特征。从需求角度看,旅游提供的是一种由经历构成的“体验”[23],拓展了文化遗产的体验功能。遗产旅游者在旅游场域里不仅可以实现审美与娱乐的体验,同时能够在与惯常环境的对比中获得一种教育与反思[24]97。由于文化具有整体性,不仅有物质表现,背后还链接着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13]39,联系着文化主体的生产与生活,而非遗生长的社会环境已离群众远去,在现代性“祛魅”的进程中[25],大众对其已然产生一定的文化隔阂。因此,站在传统的当代价值角度,“翻译”与“呈现”可以超脱非遗的历史存在形式,筑起游客与被参观者间的联结[24]100。
杨家埠民俗旅游在2019年前的核心项目是“民间艺术大观园”“风筝年画一条街”。“风筝年画一条街”最初规划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了方便手工艺人招徕顾客,也为旅游发展服务。首先,从手工艺的实物呈现视角看,原手工艺经营者主要通过将年画装裱成画轴、画册,制作微缩版手工风筝、木版年画纪念品等形式满足游客的需求,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运营,导致该街出现部分店铺商品雷同且种类繁乱、主次不清的现象。其次,从手工艺品生产与销售方式视角看,同旧时年画作坊相比,旅游业使店铺改善了展销功能,但忽视了游客对主客互动和手工艺品及其制作深入了解的需求。部分经营者受从事手工艺业的思维惯性影响,作坊的制作空间仍以实用功能为主,难以符合外来游客的预期。同时,“民间艺术大观园”中的陈列馆和制作工坊,也仅展示二者大致的历史及制作流程,未系统且层次分明地呈现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手工艺发展历程。最后,从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画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旅游业主要通过情境营造、文化解说与互动以及参与创造满足游客文化体验的需求[26]。杨家埠当地一些手工艺人仍依赖于实物商品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缺乏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知识。尽管木版年画研究所工作人员能够脱离木版年画的历史存在形态及艺术价值的束缚,较关注民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及其创造性转化与发扬,但因其非当地人、非传承人的身份问题难以获得参与渠道。因此,破解上述困境,亟须搭建满足多方诉求的旅游发展平台。
(三)现代性的架构:政府功能与社区参与
有学者指出,传统手工艺作为民间的艺术,其所代表的传统向现代融入的重要性及其路径为构筑一个由“意义-故事-游戏”组成的动态开放的价值生产体系[19]146-147;吉登斯将现代性概括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12]1,旅游是一种作为现代性缩影的现象,具有“好恶交织”的特性,既有从游客视角出发所展现的“欢愉现代性”(Eros-modernity),亦有旅游业所体现的“理性现代性”(Logos-modernity)[27]27,41。然而,在以传统手工艺为依托的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接壤并非一帆风顺,二者需要不断地碰撞与调试,政府发挥功能与顺应文化主体性的社区参与是确保各方均能发挥价值的关键[7]3,[28]5。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级政府的推动与招商引资成为杨家埠依托手工艺类遗产发展民俗旅游业的主导力量。但非遗作为“活”的遗产,其真正的传承主体是人[29],是非遗社区及长期置身遗产行业系统内的人,他们最了解遗产的历史内涵与价值。政府的宏观引导,如若忽视对文化传承与发展本身的引导,而过于关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他者对自身文化的符号性认同等[30]27,则会使得旅游发展动力不足,从而难以支撑各项目的扩张与联动。这种对文化主体性的忽视,即文化持有者缺乏主动学习、参与、调试实现对现代化“自主的适应”的途径[28]5,也容易促使外来开发企业在“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将民俗文化遗产转化为消费品[30]27,从而不利于非遗社区群众提高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多名手工艺从业者依据自身知识与经验表达了对当地旅游业如何向好发展的观点,希望能搭建各方互相交流、沟通的平台。因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若发展主体仅将地方社区视为旅游发展的“背景”而忽视他们与旅游发展的联系,则会影响到旅游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31-32]。
结 语
杨家埠传统手工艺品市场的萎缩以及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使得社区中手工艺从业人员快速流失,进一步侵蚀了传承与发展的生命力。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旅游业,仅短暂地延缓了手工艺业的衰落,并未使手工艺品脱离实物形态向文化价值转化。旅游业介入的杨家埠传统手工艺业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它包括“风筝年画一条街”“木版年画研究所”,以及从社区中吸收少量展演人员的大观园。在民俗旅游发展方面,民间艺术大观园与风筝年画一条街表面上是一个合作系统,而实际上二者间架构松散,还未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与组织。长久以来,杨家埠手工艺业一直以“坐店等客”、大批量订购的模式销售,突然转变的小而散的需求形式使从业者陷入被动的应对期,加之对旅游市场需求认识的不足,当地手工艺从业者走向了旅游纪念品销售的单一道路,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困境并未得到解决。由于旅游业脱离了文化的主体性而存在,因此,其所代表的现代性与社区所代表的传统与文化割裂,在手工艺业逐渐丧失活力与社区凝聚力的情境下,旅游业也未能使其增色。
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非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其传承与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但传统手工艺因其生存、生长的环境存在特殊性与复杂性,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政府规划或资本主导,也应充分关注各类主体所能发挥的效用,并赋予其发挥效用的途径使其在实现自身诉求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杨家埠手工艺人的核心诉求是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基础上实现手工艺传承;木版年画研究所则期望获得身份认同,获得参与、促进民俗文化的弘扬与传播的合法性地位;引进的投资与开发企业试图以“筑巢引凤”式的旅游业获得投资回报,实现地方经济增长。非遗旅游开发离不开其背后的文化及文化主体,旅游发展本应为发挥文化主体性,实现各方目标提供平台,而实践中“传统”的“人”和“物”逐渐脱离现代性的嫁接,使得旅游业的养分输送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旅游业能否与社区深入融合,通过发挥文化的主体性满足各方诉求,是真正实现非遗旅游“活化”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