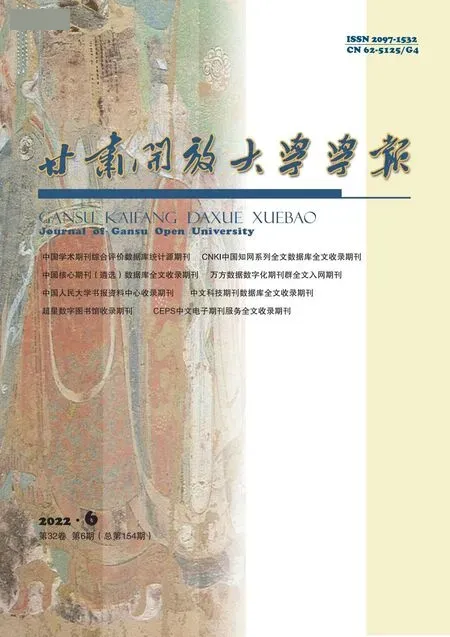梁晓声《人世间》中群体心灵家园建构的“强关系”解析
孙信信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梁晓声曾在《心灵的花园》一文中强调:“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1]156并且,他还宣称世间民众的物质和内心世界同属他的聚焦视野,“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2]梁晓声在《人世间》中以冷峻的思考去透视众生住房、就业、医疗等生存境遇,同时也以温情的笔触来关注世人亟需灌溉的心灵家园。梁晓声在随感《母亲播种过什么》中曾描述过那个时代下这群平民家庭的小儿女们,“似些孤独的羔羊,面对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政治风云,彷徨、迷惘、无奈、亲情失落、不知所依”[1]177。显然在《人世间》中,梁晓声将这种内心状态置于民间现实,真实可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3]194。这些同质性群体地位平等,在社会网络中互动频繁,在组织内部间形成“强关系”。人类学家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原则四个维度界定关系强弱,并认为“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的”[4]。基于此,可以看到小说《人世间》也呈现出社会不同特征群体间的亲密交际圈,如青年工人生活圈,官员干部交流圈,知识青年读书圈。他们在各自圈子内互动频繁、感情深厚、关系亲密,彼此间不仅互相慰藉情感,而且共享信息资源,“侍弄”心灵的苗圃,同建世俗生活中的精神家园。
一、“抱团围炉”以慰藉情感
情感与归属的需求是青年工人们抱成团维持“强关系”的出发点,并且同质化命运是友情开展并维系的前提。梁晓声参加知青集会时曾坦言:“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理解自己同类们希望继续保持群体依持关系希望彼此互助的心理需要。”[5]282对于当年留城青年,梁晓声也以体恤和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们“抱团取暖”的行为。《人世间》中青年工人之间并无利益之争,共享相似的特征和生活方式,社会平等地位促进彼此情感性行动的发生,同质性命运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同质原则意味着规范性的倾向是拥有相似资源的行动者互相吸引”[6]51,书中也称“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关系”[3]65。周秉昆与木材加工厂、酱油厂生存境遇相像的青年工友的友谊始于他一次真诚实意的情感分享。他将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即饱受涂志强影子的折磨,一五一十具实相告,这引起工友们的情感共鸣,共同的生命体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随后,周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内心自卑以及在酱油厂倍感屈辱的精神状态时,大家的表情都大为轻松,心理上感觉到了平衡。他们内心难以形容的愉快感,是出于对他身份地位的认同,“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7]103,而这恰恰是他们完全接纳周秉昆的前提条件。“沟通行动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他人被期待着对自己同情和移情,欣赏与交换自己的情感,从而认识到、同意甚至分享自我对他们的资源的要求。”[6]47周秉昆认为他们深切同情于他而心情凝重,也从他们身上终于找到突破心垒的豁口,痛快地宣泄完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从而得到情感与支持。正是这次敞开心扉的沟通,使他们相互得到情感慰藉,他们的友情也就此开始。
青年工人们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产生稳定的社会关系,在群体活动中互动互助、共享情感。“人之生,不能无群”[8]121,“人能群,彼不能群也。”[8]105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为群体,人的社会性集中体现于人的群体性。这些青年工人的群体性具体表现在以集体活动维持情感。霍曼斯“情感—互动”理论指出:“互动、情感和活动之间存在着互惠关系与正关系。个体互动越多,他们越可能共享情感,越可能参加集体活动。”[6]40从1973年伊始,中间或连续或断续,到2015年为止,这群底层青年们每逢大年初三便会在周家相聚会面。恋人们在此相识、相爱,朋友们交流上大学的想法,互吐生活不易的苦水,分享朋友出人头地的喜悦,等等。“参与者的资源越相似,他们越可能共享维持或保护这些资源的理解与关心。”[6]50素日里,这些底层青年们格外维护友谊,小说对此也做出解释:“当年物质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只能由感情与思想维系。”[3]38一有困难苦楚,他们便会集聚在周家出谋划策,排忧遣愁。如于虹因“黑画事件”被牵连而受到处分,周秉昆为其奔波解决。德宝夫妻关系亮起红灯,二人各怀苦楚寻要说法,周秉昆夫妇在家商量出处理矛盾的方法。周秉昆出狱后,朋友们能来的都来出力帮周家修房屋,不能来的也提供施工材料。周家小屋是具体客观的建筑,同时也是他们情感慰藉的归属地。“建筑则通过对一个实际的场所进行处理,从而描绘出‘种族领域’或虚幻的‘场所’。”[9]112“‘组织’是建筑的隐称。”[9]117周家这个房屋建筑作为共乐区“穷人窝”的代表,带有机能形式的特征,与这些底层劳动者生命体征相关联,呈现底层群众的生存环境。这种环境,“则是由可见的情感表现(有时称作‘气氛’)所产生的一种幻象”[9]117。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拥有相似生活、相似社会特征的周秉昆们组成群体,在专属他们的组织领域内,认真对待友谊以维持现有资源,用感情与思想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除青年工人外,“庙堂”中的干部群体也在专属空间内交流情感、互递思想。作为年轻党员干部的周秉义变相倒插门到岳母家后,与退休的正厅级干部金月姬建立起“强关系”。他们投入较多的时间建立亲密的感情,分享社会观点,彼此提供互惠性服务。每日晚饭后,这两位政治信徒近乎仪式性地聊天,金老太太从周秉义处满足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周秉义从金老太太处汲取当干部的经验。言谈投机间,横亘在两人间的出身阶层偏见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惺惺相惜的在位归属感。这种情感在日常来往互动中得以“非无限延长的一定时间的持续”[9]117。双方也用行动维持之间的情感。周秉义采纳老太太的建议,将外甥女玥玥接过来住,以便她以党的忠诚多影响知识分子周蓉,使其自觉与党保持一致。老太太顾全到周秉义做经济管理方面的想法,也为实现撑起干部家庭门面的心愿,利用自己的身份资源向省委组织部施加影响,提出调动周秉义工作的要求。周秉义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改变,原先为文化厅副巡视员,现在任军工厂党委书记。当军工厂遇到燃“煤”之急,老太太动用跨省的老战友关系,捐出存折里的现金,尽其所能助周秉义渡过难关。周家与金家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分别位于不同的街道位置,是不同的群体言语、行动以及思想的场所,它们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象征不同的阶层地位。这些同质性命运的行动者在他们所属的空间内各自交流情感、彼此慰藉心灵。
二、“并足”以共撑精神支柱
青年读者因大致趋同的阅读价值观和阅读方式而构成“阅读共同体”,他们将书香世界当作精神复归之所,从文学经典里找到狂热世界中的精神支柱。小说为大众呈现了“上山下乡”前后的青年阅读空间。面对读书,周家兄妹与郝冬梅、蔡晓光等年轻人的出身无“红”与“黑”之分,无“高”与“低”之别,文学消弭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平等对话。因为书籍,他们形成“强关系”,“促使群体中的读者结合在一起的凝聚力,会催生读者群体意识,即群体阅读目标和阅读规范”[10]。深处知识断层的年代,这些同道青年因共同的阅读志趣、阅读价值观而结缔出真挚的友谊。他们的阅读饥渴略带有积极对抗的意味,附丽着对另外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期待。文学在他们那里,既是向内的,又是向外的,既与个人生命史相关,又和社会、人类问题联系。他们搜集不曾读过的当时的禁书,积极开展地下读书活动,畅所欲言,并足而谈,碰撞思想的火花。漫步文学殿堂,沐浴启蒙思想的光辉,经受人道主义的洗礼,得以理性精神的浸润。
从阅读经验中构筑起的精神支柱伴随并支撑这些青年往后的生命旅途,阅读发挥它的社会使命,“成为一种传播媒介、智力发展技术和获取文化的方法”[11]。周蓉立言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她不仅对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如数家珍,还对中国小说广猎涉及。“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对文艺作品认同的深层原因在于读者对艺术家所秉持的价值观的认同”[12]。周蓉深恶痛绝女人在中国男性笔下处于失语地位的文学现象,青睐尊重女性的书,如《红楼梦》、唐宋传奇小说及《白蛇传》等。她热衷唐诗宋词、推崇孔孟文化,大发关于鲁迅、胡适的“狂妄言论”等。其精神风貌与思辨态度促使她自然而然地走上高校任职之路。“学术工作是跟生命,以及历史的使命感相联系的。”[13]社会问题和自身的精神探求构成其学术工作的动力。蔡晓光常到周家参加集体阅读,虽身为技校造反派头头,但起码没在周家摆出“造反有理”的嘴脸,反而文质彬彬、谦恭有礼。他非官即商的人生轨迹因结识周蓉而有别样的不同,他选择适合自己并热爱的导演职业。蔡晓光发自肺腑地坦白,是周蓉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特质吸引并影响了他。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文学力量改变了蔡晓光的人生,阅读开辟了他通往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道路。这正体现在《人世间》中,“梁晓声力图以文学的名义付诸拯救的行动”[14]2,“没有文学,没有拯救”[14]2。
从十七年革命文学作品汲取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深烙在青年阅读者身上,阅读审美政治化倾向会给读者带来不容忽视的持久影响。对1949年至1959年间出生的这代人来说,十七年革命文学“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对50—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15]21自革命胜利后,产生出强大的社会心理磁场,即个体的心理差异减弱同时群体凝聚力增强。这种集体价值取向催生人们对十七年革命文学的阅读期待。梁晓声曾在《母亲》一文中说到他想要本《红旗谱》想得整天失魂落魄,头脑中喜欢将“革命英雄主义”当作“精神食粮”。这种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萌生的文学作品阅读期待着重表现在周秉义身上。周秉义在进行文学接受活动之前及过程中,“基于自己的审美理想、阅读经验和接受动机投射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未来作品的‘既定图式’”[16],根植于学生干部身份经验、行事原则等其他原因形成特定的心理指向,会对文学接受的客体有一定的期待与要求。在阅读活动中,这会转化为读者的审美尺度,培养其革命理想主义人格。纵观周秉义一生,从兵团教育处长、学生会主席、军工厂党委书记、司长再到副市长,他都以牺牲小我、奉献大我的形象出现。他屡次坦露自己想从事教育事业的意愿,却每次都因大局需要而服从组织安排。在庸常凡俗生活中,从周秉义身上可看到“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光影,他是作者在意识形态话语下对拯救者形象的再创造。
青年从书籍获得精神支柱的体悟源自于梁晓声那代人自身真实的阅读体验。“检讨一代人文学阅读的历史,也许其意义并不亚于对一个时代的检讨,因为,它毕竟包蕴了一代人”“人生成长和思想寻求的全部隐密。”[15]21梁晓声在回忆性散文《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中提到,他们的阅读范围并不局限在促狭空间内,“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17]261。梁晓声在随笔《关于爱情在文学中的位置》回顾中国文学的面貌时,详细列举当年他曾读过的“十七年”长篇小说,几乎涉及当时的全部著作。作者又在《我与唐诗、宋词》《我与文学》等文中回顾“地下阅读”的亲身经历。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代表,梁晓声将自身生命体验的感悟、对独立精神的坚守、文学理想的诉求寄予在求知青年身上。
三、心灵家园建构的“强关系”思索
梁晓声曾阐明“内心世界是一种景观,它是由外部世界不断地作用于内心渐渐形成的”[1]156,内心世界是外部世界的投射。平民家儿女们生活在远离主流话语权的民间,集结在一起,相互安抚与安慰,从彼此身边获得人生的安全感,共同坚守民间价值本位立场,在心理上蕴蓄抵御外在压力的生命能量。他们秉持民间好人价值标准来抵抗政治环境的挤压。这些青年人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除了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外,还以好工人的标准要求自我以躲避政治的侵扰。特殊年代里,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耳目无处不在,颠倒黑白的现象也司空见惯。市“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同志威逼利诱周秉昆,试图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以抓住立功的机会,最终却一无所获悻悻离去。因为周秉昆坦白自己作为政治白痴,“我父亲就像我这样,政治对于他就是当一名好工人”[7]279,同时这也是身边其他人的政治态度。周秉昆们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履行着老太太的约法三章,并追求“六小君子”这无功利主义色彩的群体荣誉。对于女青年而言,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全身心经营其小小的安乐窝方为正道。“从《人世间》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坚守的这一信念,人类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度过文明的黑暗期。”[18]
戮力同心以民间正义反抗强权与不公。梁晓声说:“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19]黑画事件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各方力量的协力合作,从其背后可看到斗争哲学的没落与“好人哲学”的复兴。这种“好人哲学”的奉行是出于对社会的反思,民间正义的激发。正义除体现在小群体间的江湖义气,还彰显为民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义。吕川曾反思“我们”之间的义气的局限性。周秉昆受此激励,成为“民间”和“庙堂”文化的联络者,参与“天安门诗歌”事件而被捕。此番出于正义的作为触动赶超,他以摆花圈的方式在市区制造多起“反动”事件,以此表达对他者遭到非公待遇的不满。民间和庙堂话语虽隔着厚重壁垒而无法完成通畅完善的沟通,但也存在两种精神价值互相渗透的可能,这些小人物在相互影响中获得某种心理的支持,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诠释人间正义与担当。
同频共振以书“自娱”来避世忧世。周秉义、周蓉等人因不得意的精神状态产生共鸣并“隐逸”起来读书,虽在政治立场上属于“逍遥派”,但仍郁懑不平,心存忧患意识。狂热的年代吞噬了知识青年自我完善、自我高蹈的机会。周秉义、郝冬梅的大学梦化为泡影,周蓉的入团道路戛然而止,蔡晓光身不由己地“入世”成为技校造反派头头。混乱的社会使其并无一枝可栖,他们只能寄情书籍,从文学中找寻自我。现实苦闷使得知识青年们在“穷则独善其身”思想引领下走向人生的自适,摆脱烦恼与闲愁,是一种灵的追求。他们遁世读禁书,敢于敞开思想、大声疾呼,同情不幸者,具有浓郁的人情味,“自娱”带来的是情感性诉求的满足、工具性期待的达成。避世往往深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只能是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意识。”[20]由于书籍的滋养,基于仁心或善性的驱使,这些知识青年的忧患意识更明显深刻。“所谓忧患意识,乃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21]。这群知识青年们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书的一番评价何尝不是在借此表达对现实的感受。他们将这些书理解为反映战争与社会、革命与人的著作,蔡晓光暗比自己乃至其他人为葛利高里。忧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多事之秋,现实的浩劫使他们愈加关注现世社会。在探讨文学作品中社会现实与人物之间关系的背后,是在展现他们对所处年代下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处境的关怀。结伙读书不再只是风雅能事,而是寄寓其社会内涵与价值的交往途径,是无序时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思的表达方式。
对于草根阶层来讲,时代的艰难不仅显现在外在生存条件,还侵蚀内在心理状态。从“强关系”角度观照小说,可以发现城市平民家庭青年间的互动互助奥秘。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父母还是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人生状况。在同质性群体间的友情往往是底层青年温暖有力的依靠,他们靠江湖义气争取他人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7]356。围着“火炉”“抱团取暖”,“抱团”只是形式手段、现象,“取暖”才为目的、本质。“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17]262作为读者的我们拥抱启发我们“拥抱”的作品,这会引导我们深入文本,走进“强关系”下青年的精神世界。在那个特殊年代下,总有一群青年阅读者抵足而谈,在浮躁混乱中守得一方净土,从文学世界中找到人生的精神支柱,文学在梁晓声的笔下“闪现着宗教般的光芒,庄严而坚定”[14]1。在寻求心灵家园的背后,体现的是民间伦理道德抵抗极端环境的努力,是文学拯救知识分子人生的力量显现,是作家对“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这类永恒话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