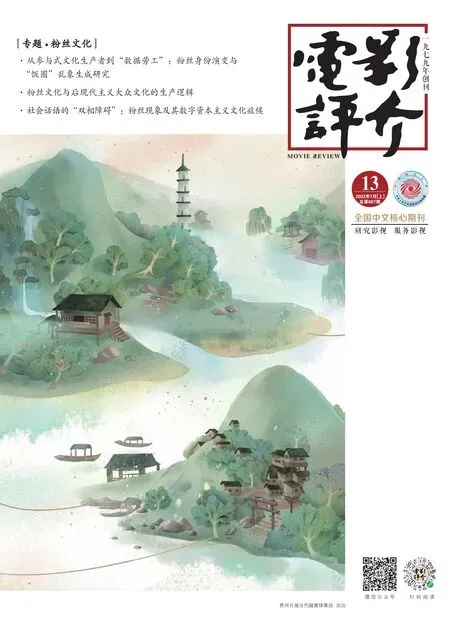《盲琴师》:存在主义的影像表征与潜叙事
徐梦晨
2021年12月10日,波兰电影《盲琴师》(马切伊·佩普日察,2021)登陆内地院线,最终以105.5万元的票房成绩收官。①数据来源于“猫眼票房”.《盲琴师》累计票房[DB/OL]http://pf.fe.st.maoyan.com/dashboard.从票房上看,《盲琴师》的成绩并不理想,但着眼电影本身,其艺术成就却不容置疑。实际上,该片于2019年在波兰本土上映,并在波兰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表现也十分亮眼。该影片改编自波兰天才盲人钢琴家米耶奇斯瓦夫·科什的真实人生经历,讲述了他杰出又饱含悲剧色彩的传奇一生。在《盲琴师》中,观众既能看到用非线性叙事勾勒人物传记的高超手法,又能看到盲人视角的创新镜头,既能感受到音乐之于电影的重要意义,更会惊异于可见影像对不可见精神、意志等内在世界的探寻和表现。聚焦意识世界的影像充满着存在主义的特征,其不仅体现在对“意识存在”的影像外化,也通过影像构成了对“意识存在”的潜在叙事,描绘了整个生成和变化的完整进程。在《盲琴师》中,观众随影像窥探盲人钢琴家的内心,从其内心透视整个人生。影片从个体生命出发,折射出存在主义的哲学力量。
一、存在主义与波兰艺术电影
存在主义可以说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在存在主义之前,基于逻辑性、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存在主义却将关注中心从世界的外在理性转移到“人”和人的精神意识世界中来。存在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经历了海德格尔的完善和发展,最终由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将存在主义推向了高潮。从萨特开始,存在主义开始渗透到文学、戏剧等其他领域,逐渐成为一种文艺内核。萨特认为:“当代哲学在本质上是戏剧性的”,“戏剧具有哲学意味,哲学又带有戏剧性。”[1]以存在主义思想为核心,萨特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开启了存在主义哲理剧的先河。萨特以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这些极限处境中,选择那个最能表达他的关注的处境,并把它作为向某些人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介绍给公众。[2]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在极端境遇下,基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利弊,做出了“自由选择”,由行动引发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是离别、湮灭等,这与萨特思想里所主张的个人为自我的自由选择承担以及他“虚无”的思想相呼应。而电影艺术本身的故事内核也是从戏剧发展而来的,可以说,萨特的戏剧创作为存在主义电影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存在主义电影,泛指主题或具体议题指涉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或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物象形态等能引起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电影。[3]从这个维度上来审视电影,一系列在极端矛盾下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精神世界,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个体自由选择及其后果的电影都可以被纳入存在主义电影的体系中。纵观世界电影的发展史,“存在主义”已然成为艺术电影发展的重要思想根基和方向。以《盲琴师》为切入点回顾波兰存在电影的发展,其根源十分深远——二战后,随着罗兹电影学院培养的安杰伊·瓦依达、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罗曼·波兰斯基、安杰伊·蒙克、克日什托夫·扎努西和马雷克·科特斯基等一批电影人进入电影业,成长为波兰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直到20世纪50年代,波兰电影学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波兰电影渐渐走向存在主义电影的创作方向,影响深远。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存在主义电影包括《绳套》(沃伊切赫·耶日·哈斯,1957)、《再见》(沃伊切赫·耶日·哈斯,1958)、《伟大战争的真实结局》(耶日·卡瓦莱罗维奇,1957)、《夜行列车》(耶日·卡瓦莱罗维奇,1959)和《修女乔安娜》(耶日·卡瓦莱罗维奇,1960年)、《夏天的最后一天》(塔德乌什·孔维茨基,1958年)等。20世纪70年代,战后宏大的民族历史主题开始消解,创作者开始将视角转向对个体及其心理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电影人以克里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为代表,其作品《红白蓝》三部曲、《机遇之歌》(1987)《爱情短片》(1988)等无一不在探讨人的存在、选择、意识世界的挣扎与最终幻灭,焕发着存在主义的思想光芒。
近十年来,波兰电影业人才辈出,波兰电影也迎来新的高峰,《猎人》(马辛·克里兹塔洛维奇,2012)、《修女艾达》(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2013)、《流浪诗行》(克日什托夫·克劳泽,2013)等艺术电影佳作享誉世界,其中存在主义的思想主题一直贯穿其中。《盲琴师》导演马切伊·佩普日察就是波兰存在主义电影创作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作为新世纪波兰电影的新生力量代表,早在2013年,就以一部《生命如此美好》征战蒙特利尔电影,并一举拿下第37届蒙特利尔电影届宗教人道奖。和《盲琴师》相似,《生命如此美好》仍然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聚焦的也是“残疾个体”的生命经历。在《生命如此美好》中,主人公因先天残障导致永久性肢体痉挛,并无法开口说话,疾病、残障成为他生命的阻力,但少年不断成长、不断突破,最终能够成功地进行自我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存在、个体与自身、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影片关注另一重点,这一存在主义视角也被延续到《盲琴师》中。
二、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电影潜叙事
萨特是通过“存在与虚无”的关系来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所谓“虚无”,就是指萨特思想体系中基础的“否定性”:一方面,他认为人的内在存在和外部世界一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自在”和“自为”。人的自在是他现在所处的生活境况,而人的自为表现为对已有的存在境况的否定,这种否定包含着对个人存在的探索和自由选择,以达成意识的自由,也是存在主义所谈论的根本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从否定上帝的角度去强调人的存在性,“上帝已死”的思想使得其与传统的神学存在主义和宗教存在主义产生了质的分野。[4]在电影《盲琴师》中,主人公米提克从小被寄养在修道院中,他在宗教的“禁欲”教育中依然保留着作为“自我”的“人性”,他对作为女性的修女们有源自性别的本真好奇和冲动,会偷窥修女沐浴;他接受修道院的教育,却不遵守教条化的音乐演奏风格,叛逆、自我,热衷于被修道院所不容的“靡靡之音”。这一切无疑可以看做是对“上帝”的反叛,“童年”这一叙事副线,可以看做是米提克在生命奋进中,“自由选择”开端。另一条重要的隐线则是米提克和父亲的关系——父亲因为米提克的眼疾而离弃他,这也成为他悲剧的开始,也可以说,父亲的否定奠定了米提克“自我虚无”的心理基础。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否定因眼盲而“被离弃”的境遇,而这个境遇是由父亲“定义的”。米提克也正是这个过程中去演奏、作曲,去完成自我探索和自我超越。
萨特在自己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阐述了关于人自身存在的观点——“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去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他本身就是他超越自我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和主观性的关系——这就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反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5]在《盲琴师》中,主人公米提克因为眼疾几近失明,经历了被父亲“谋杀”、抛弃之后,最终在修道院长大;因为钢琴演奏的风格不断被压制、否定;米提克凭借其音乐天赋,开启了自己的钢琴家之路,却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局限一路坎坷,不断被“抛弃”;但是米提克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始终在探索更高的音乐境界,以此实现自我。如果说,因为遗传基因而注定失明是米提克的“自身”,那么米提克学习钢琴,精进技巧,钻研演奏风格,作曲取得突破,在一次一次“被抛弃”的绝望中重新振作的过程就是超越“自在”而追求“存在”的过程。
同时,在米提克的奋斗历程之外,也需要看到作为一名盲人钢琴家,他的人生存在一种悲剧性,这可以看作是《盲琴师》传记体系中的潜在叙事线。对于米提克来说,生理的缺陷导致了其一系列不幸的人生遭遇,一步步加深了其心理否定与怀疑,最终使他走向自尽的结局。为了构建这一潜在叙事线,影片采用非线性的剪辑方式——“现实时空”的故事从米提克回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开始,逐步过渡到米提克前往华沙参加国际爵士音乐节,米提克凭借在此次音乐节的表现一举成名,新的生命历程就此展开。另一个叙事时空则是在不断的闪回中逐渐建立,儿时的米提克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但随着他的眼疾严重,父亲选择抛弃他,这是米提克第一次“被抛弃”;为了挽救米提克的生命,母亲将其带离家,送往修道院,对于米提克来说,母亲的离去是又一次“被抛弃”;米提克在修道院中学琴的童年,虽然得到修女的照顾,但也在孤独中静待“失明”的到来,虽然学习了钢琴演奏,但他喜欢的音乐风格却被看作是“靡靡之音”,最终修女也“抛弃”了他;成名前的米提克在餐厅演奏钢琴,但餐厅老板和饭馆的客人却对米提克看似疯狂、自我,实则天才的演奏风格并不理解,这也代表了他被“主流”抛弃;当他被制作人发现,并在华沙崭露头角时,一直陪伴他的伙伴也选择离他而去;当他找到心仪的歌手合作,并渐渐对对方暗生情愫时,女孩却选择终止合作,同时将这份爱情彻底扼杀;当他重新与人相爱,重新找到创作激情时,却在重压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钢琴家的传奇传记,同时也是一个个体走向毁灭、走向最终虚无的人生轨迹。萨特阐释到:“人的实在在自身存在中是受磨难的,因为它向着一个不断被一个它所是的而又不能是的整体不断地纠缠的存在出现,因为它恰恰不能到达自在,如果它不像自为那样自行消失的话。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痛苦意识,是不可能超越的痛苦状态。”[6]《盲琴师》中“抛弃”这一叙事线,正是萨特所说的“实在的痛苦”,而这一结局就是萨特所阐述的“虚无”的一种形式。
三、镜头与物象:存在主义的影像表征
作为一门以视觉为基础的综合艺术,电影能够在发展中成为思想表达的载体,始终要落脚到电影创作者对电影影像的掌控和创造中去。对于存在主义电影来说也是如此,只有通过一系列属于视听范畴的电影元素的表征,才能精确地向观众传达影片的存在主义思想。在影片《盲琴师》中,观众不仅能看到特殊镜头对人——特别是主角米提克——所属境遇的表现、对心理状态的隐喻;通过色彩和影调的变化,隐喻时空和人的变化;也能看到影片选取的特殊物象,揭示主人公自身存在的形成和变化;还能看到对在此传记片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音乐”这一元素的创新运用,最终呈现出的效果,让观众领略到故事之外的人生哲思。
对于存在主义电影来说,展现一个人的“存在”,必定离不开人的主观视角。但对于《盲琴师》来说,由于主人公存在视觉障碍的特殊性与电影的视觉性是相悖的,所以难以直接呈现出主人公米提克的主观镜头,但创作者依然通过特殊镜头的处理,既表现了盲人的视觉特性,又展现了一种更为内心化的主观视角。较为突出的镜头当属米提克在华沙国际音乐节的舞台演出前,尚未适应舞台的他迟迟不能进入演奏状态,他的慌乱、迷茫通过舞台暴露在观众面前,这时小景深转轴特写镜头深入到观众席的内部,放大了观众对于米提克的质疑。这组镜头可以看作是米提克的心理主观镜头,昏黄的灯光以及并不明朗的画面,暗示着他因眼疾窥视到的世界样貌:观众的窃窃私语、身上的配饰、包的拉链,无一不透露着观众的不耐烦、质疑甚至是嘲笑。从写实的角度去分析,这些观众席上的“细枝末节”是不能被处在舞台上并几乎失明的米提克尽收眼底的,所以,这组镜头的处理更偏向于对米提克的心理活动进行展现,融合了米提克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想象。相比于对观众席的窥探,影片在讲述米提克儿时失明的时间线时,通过“遮蔽镜头”表现米提克眼中的世界更为写实。在米提克的眼睛里,世界模糊而昏暗,像是小孔中的幻象。随着米提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镜头的遮蔽范围进一步扩大,也传递出一种更深的压抑感。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特意根据主角不同的状态,赋予了画面不同的色彩和影调——儿时的修道院是近乎黑白的冷色调;当米提克成名成家后,他开始活跃于聚光灯下,画面变得明亮闪耀。
除了镜头上、技术上的艺术创意,《盲琴师》在镜头内容的选择上也形成了一种“物象隐喻”的艺术效果。一方面体现在镜头对身体局部的选择上:在影片开头,米提克前往母亲的墓地,镜头首先呈现了一双在地上摸索的脚,比起开篇车窗内带着墨镜的米提克的正脸,这个身体局部特征的选取更能表现他作为“盲人”的生理特征;在儿时的时间线中,影片给米提克的红肿眼睛做了大量的特写,这样一双病态的眼睛一再强调着米提克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电影文本中还塑造了几组相互呼应的物象,对米提克的悲剧命运形成一种巧妙的隐喻。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关门”这一隐喻,当米提克一再“被抛弃”时,他回想起在修道院的日子,母亲关上门离开,修女也关上门离开。那扇被关上的门就是贯穿米提克人生轨迹的一个物象隐喻;米提克在家中演奏,钢琴上的花束随着他的演奏微微颤动,而花朵缤纷的颜色却只出现在米提克尚未生病时,幼年时的他也曾拥有父母的疼惜,母亲哼着童谣,教给他花朵的颜色,也许那就是米提克一生中最为“鲜艳”的日子,之后的苦难让生活“褪色”;当爱情出现,花朵也再次出现,这代表着米提克对生活的热爱、对音乐的热情再次复苏,但整个影调却不如回忆中那样鲜艳,“复苏”是短暂的,天才也最终选择以离开世界的方式飞向空中。
结语
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开辟出了在画面之内、在故事以内的第三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电影传达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对人和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提出疑问,并在电影文本中去不断求索。对于存在主义电影而言,对存在主义思想的探究和表达无疑是创作者的核心意图之一,透过《盲琴师》,能够再次看见波兰电影的内生力量,也瞥见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光芒。人在影像中生存,也在影像中完成存在主义的自我表达;影像为了表现人的存在,也被赋予了超出“呈现”之外的“象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