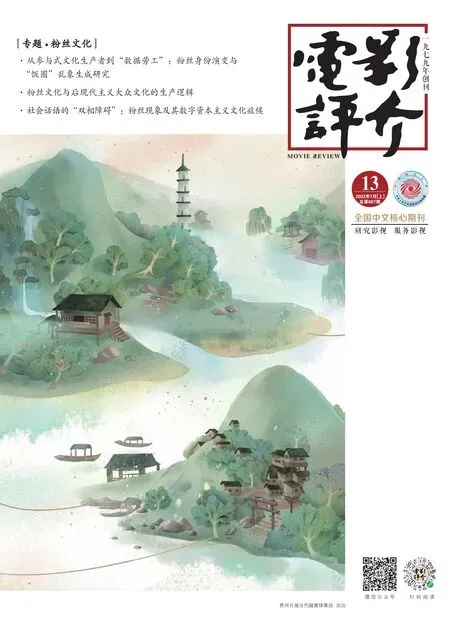粉丝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生产逻辑
刘 起
动画科幻情景喜剧《瑞克和莫蒂》(Rick and Morty)自2013年播出至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形成了忠诚且狂热的粉丝群体,“这部科幻剧集与其粉丝群体构成了一种世俗信仰,一种奇特的电子宗教”[1]。全宇宙最聪明、无所不能的瑞克被理解为“救世主”,粉丝们则是信徒,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型的神话系统。这部剧集似乎也能激发人们对于粉丝文化一种新的思考路径。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更新,这部作品引发的狂热粉丝文化已经不再像传统粉丝文化一样停留在接受层面,而是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生产逻辑,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一种反向的构成作用。
一、《瑞克和莫蒂》中的狂热粉丝文化
在IMDb网站最受欢迎剧集的排名中,截止2022年10月,《瑞克和莫蒂》以500万的打分人数和9.3分的高分,成为排名第13位的热门经典剧集。这部剧集在烂番茄网站也拿到了95%的新鲜度,并连续获得艾美奖第71届、72届最佳动画节目和两次安妮奖。[2]围绕这部剧集无止尽的网络讨论以及剧集引发的媒介现象,使其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瑞克和莫蒂》成为狂热粉丝亚文化的一个证明,是其在2017年第三季播出时引发的川香辣酱热潮。第三季第一集中,主人公瑞克在被问到人生意义时,戏谑地说出:“我并不是为了给妻女报仇,这是假的。一切只是为了麦乐鸡的川香辣酱,这才是串起一切的主线。”这句台词引发了粉丝们疯狂的热情,他们在网络上写下请愿书。于是,麦当劳20年前为电影《花木兰》推出的、早已被人遗忘多年的川香辣酱再次风靡热销,甚至供不应求。[3]
只有很少一部分通俗文化产品,能像《瑞克和莫蒂》一样,形成这样一个狂热、坚定、有区隔性的观众群体。从豆瓣上六季平均9.7分和一些短评中可以看到《瑞克和莫蒂》粉丝的忠诚度与排他性:“我就是不明白这剧分怎么会这么低,才9.9,难道有人没打五星?太可怕了吧!”“我们中间出了没打五星的叛徒。”“我认为能不能看懂本剧,喜不喜欢本剧可以作为择偶标准了。”①豆瓣《瑞克和莫蒂》第三季短评[EB/OL].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592971/comments?status=P.相当一部分《瑞克和莫蒂》的粉丝认为,观众必须有很高的智商才能理解作品中微妙的幽默、复杂的叙事和虚无主义的哲学思考。主人公瑞克是全宇宙智商最高的天才科学家,也是不折不扣的疯子、怪物。他整天醉醺醺的、满口脏话,但又聪明骄傲、愤世嫉俗,蔑视一切社会规则与道德准则。部分粉丝对主角的崇拜、热爱与模仿,更是将这种优越感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盲目的智力优越感、排他性的审美趣味,成为这些粉丝身份认同的标准。
显然,《瑞克和莫蒂》的粉丝们将能够看懂这部剧集并当作一种文化资本,因此产生一种品味上的优越感,因为文化资本“决定了人们评价、判断和辨别文化符号的能力”[4]。粉丝们这类特殊话语的构成和狂热行为背后的逻辑,即是布尔迪厄(Bourdieu)所谓的“文化等级”与“品味区隔”。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品味“作为对文化符号最直接的选择与表达,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模式以及群体区分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品味的差异体现的是一种分类逻辑,它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阶级区分原则”[5]。根据费斯克(Fiske)的理论,粉丝文化本身就包含某种歧视与差异,“粉丝”的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的歧视性格,他们清楚地划分谁有资格、谁没资格被称作“粉丝”。[6]
然而,笔者更想讨论的,并不是《瑞克和莫蒂》所引发的这一狂热粉丝文化本身——由粉丝圈独立构成的独特艺术世界,而是想从这一作品的文本生产逻辑来考察粉丝文化对于通俗文化产品生产的一种反向构成作用。
二、粉丝生产力——从第二生产到第一生产
《瑞克和莫蒂》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①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具有一种怀疑精神与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后现代主义文化采取拼贴和戏仿这两种主要模式。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02.[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9-363.文化产品,充满了拼贴与戏仿。从故事核心设定、人物设置到每一集的情节甚至标题,都能看到大量通俗文化产品的影子。主创贾斯汀·罗兰(Justin Roiland)本身就是通俗文化的爱好者,他早期创作的几部短片都是对经典通俗文化作品的戏仿,其创作思路和风格有些接近同人作品,《瑞克和莫蒂》也是基于两类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集类型——家庭情景喜剧与科幻剧而产生的。因此,从创作伊始,这部作品就与粉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察《瑞克和莫蒂》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生成逻辑与粉丝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作为一种受众研究的粉丝文化研究,转为一种基于互动论模型的粉丝文化研究。
通常意义上的粉丝文化是一种基于受众的研究。费斯克认为,“大众从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也是真正的大众文化。”[7]粉丝在解读大众文化产品时能够生产意义,因而是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符号/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正是粉丝文化。比如《瑞克和莫蒂》的粉丝通过在网络上制作各种视频挖掘文本隐藏的彩蛋、互文的电影,对影片进行深度解读,以及创作人物的同人故事等,虽然形式不同、介入文本的深度不一样,但都属于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费斯克将粉丝生产力分为三个领域,即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8],尽管三种生产力在能动性、创造性与策略性上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费斯克阐释的粉丝生产力依然停留在接受层面,是对原文本的二次生产——作为消费的生产。
“消费者的生产”这一概念来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他认为,消费,包括对艺术符号的消费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消费,也是一种生产。“与通常理解的那种规范、合理,既扩张又集中的,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有所不同,这种被称为‘消费’的生产(又称为第二生产)。”[9]但是,作为消费的生产指的是并非制造者的使用者对符号的使用,因此,属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接受领域,而不在生产领域。一部电视剧集在文化工业中的生产制作属于第一生产,在传播的接受过程中的意义生产属于第二生产。可见,无论是米歇尔·德·赛托或费斯克的研究都表明,粉丝文化本质上是观众、消费者研究的一种。在这些粉丝理论中,“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读者及其接受过程的问题,粉丝理论几乎就是读者理论和接受理论。从消极方面说,使得他们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作者和生产这两个环节,特别是大众文化的那种大工业生产在文化意义的流通中的作用”[10]。
因此,考察《瑞克和莫蒂》的文本生成逻辑或许可以发掘粉丝文化在文化工业中的生产潜力,使粉丝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接受层面的第二生产,而直接成为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潜在内容来源和环境因素,能够影响文本生产的逻辑。
但这种考察绝不是要回到文化研究领域保守的生产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体现在“对文化生产环节的强调,其背后的一个理论预设是,控制文化活动的是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过程。即使是文化消费行为,也是受生产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控制的,消费者是消极被动的”[11]。这种生产主义模式是一种消极的观众理论。考察《瑞克和莫蒂》的文本生产逻辑与粉丝文化的互动关系,正是要超越以上两种媒介研究的思路。
三、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戏仿与粉丝文化
《瑞克和莫蒂》对通俗文化产品的致敬、模仿,同时包含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主流模式,通过矫饰主义和风格化,通过拼贴——对过去进行模仿来彰显自己,提供保守的文化产品的主流文化往往采用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对抗性模式,后现代主义作者因为对虚无的深渊感到绝望而转向戏仿,包含一种风格、形式和内容的反讽化。边缘少数派的先锋艺术经常采用这种模式。《瑞克和莫蒂》作为一部通俗文化产品,却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空洞的拼贴,更多是在进行一种深度、复杂、有创造力的戏仿。
《瑞克和莫蒂》的故事创意脱胎自贾斯汀·罗兰的动画短片《Doc与Mharti的真实动画冒险》(The Real Animated Adventures of Doc and Mharti),主人公Brown博士和Marty McFly直接挪用了科幻经典《回到未来》三部曲中的疯狂科学家和高中生的人物形象。这部动画短片癫狂、无厘头,对美国通俗文化的经典作品进行大胆的反讽恶搞,虽然颠覆了原作的核心,但显然这部作品最理想的、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受众,就是熟悉《回到未来》及其他同类科幻电影的观众。一个不熟悉《回到未来》的观众,很难理解这部动画短片中那些直接的引用、间接的嘲讽与犀利的解构。
到了《瑞克和莫蒂》中,贾斯汀·罗兰延续了这种创作思路,建构了一部引用更加频繁、指涉更加复杂、解构更加彻底、反讽更加犀利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时空穿越等科幻设定、每一集的主线情节、剧中形形色色的外星人与科技装备,都充满了对科幻、恐怖、奇幻这些电影类型的致敬与借用。可以说,《瑞克和莫蒂》每一集的文本都指涉了大量经典的通俗文化产品(及严肃文化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集、小说、漫画、游戏等,指涉的方式多样,有着不同的深度,其目的与效果也截然不同。
这种模仿、借用从浅层到深层,包括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对人物形象、环境、道具或者科幻设定的简单引用、挪用、致敬。比如剧集中家里的海报、手办、科技产品,人物看的书籍、剧集等,经常都有现实中对应的作品。或是模仿《第一滴血》《机械战警》《终结者》《异形》《猛鬼街》以及漫威电影的人物形象,或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疯狂的麦克斯》、游戏《侠盗猎车手》《辐射》的场景等。这种引用类似埋藏在文本中的彩蛋,能够激发观众寻找彩蛋,而发现彩蛋的观众往往会获得一种与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快乐;二是对大量经典电影情节模式进行搬用、改编、颠覆。美国流行文化的很多重要作品,包括类型电影、流行剧集等,都成为《瑞克和莫蒂》的改编对象。如《回到未来》《盗梦空间》《黑客帝国》《疯狂的麦克斯》《侏罗纪公园》《人类清除计划》《割草者》《第三类接触》《头脑特工队》《伴我同行》《肖申克的救赎》等。莫蒂家的人物构成——父母、儿女,正是美国大部分家庭情景喜剧中的人物关系设定。第一季索性每一集的片名都直接借用一部电影的名字,并在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带有戏谑性的重写,以此赋予故事新的含义。
后现代主义拼贴戏仿的创作方式,增加了这部大众文化产品的复杂性与深度感,使作品如同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在对通俗文化产品进行反讽与颠覆性的改编时,也包含了对其中叙事套路或陈腔滥调的反思。并且,在高密度地引用大量文本时,文本与文本的叠加,以及在叠加中产生的冲突和异质性,就增加了故事的深度感。比如,有一集的情节设定模仿《盗梦空间》的多层梦境嵌套,却又加入了另一个重要的戏仿对象——在多层梦境之间穿梭追杀主角的连环杀手,这个形象来自《猛鬼街》的杀手弗雷迪,但《瑞克和莫蒂》中的连环杀手却过着充满鸡毛蒜皮琐事的中产家庭生活,将家庭情节剧的人物关系放置在一个恐怖片人物身上,同时嘲讽解构了这两种深受美国观众喜爱的类型。这些大量引用的内容交织构建了一个庞大、错综复杂的文本网络。
如果说,在这些通俗文化作品的接受过程中,粉丝群体通过各种解读赋予了作品超越作品本身的含义;在作者意图之上叠加了读者阐释,以增加了文本的厚度,那么在创作《瑞克和莫蒂》的故事时,贾斯汀·罗兰对这些通俗文化产品文本的戏仿、颠覆性反转,以及改造原有情节模式与主题思考,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源文本新的含义。可以说,《瑞克和莫蒂》的文本意图中天然包含源文本携带的作者意图与读者阐释。
这种包含大量指涉的互文性文本,首先需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调用过往的媒介经验来辨识、理解;其次多重拼贴的文本赋予故事更大的解读空间。于是,各种类型电影、流行剧集、游戏作品的粉丝在观看《瑞克和莫蒂》时,其感受的强度与愉悦程度远远超越没有看过这些文本的观众的感受。这些积累的媒介经验使观看行为变得更积极,带有更多的能动性,将观影过程变成一种包含解谜、寻梗的智力游戏。这也是为何《瑞克和莫蒂》的部分粉丝群体会产生智力优越感的原因。智力优越性,本质上是一种媒介经验积累。就如费斯克的分析,粉丝文化和正统文化在累积文化资本方面有共通之处。[12]
《瑞克和莫蒂》是粉丝们筛选出的经典之作。粉丝文化中,观众会挑剔地选择值得他们追捧的作品——创立电视剧经典。[13]粉丝们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它们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和对接受者的区分度”。当然,流行文化粉丝们对其追捧作品的迷恋还是带有某种局限性。学者詹金斯(Jenkins)指出,“粉丝们眼中的高质量和创新性,在别人眼中也只是陈规俗套。”[14]《瑞克和莫蒂》成为粉丝眼中真正的理想作品,即能够制造接受的门槛,从而形成对接受者的区分。《瑞克和莫蒂》的文本生成逻辑,先在地预设了一种理想的观众——有足够多的通俗文化媒介经验、有一定的好奇心、热爱解谜,即一种有很强参与性的观众。虽然《瑞克和莫蒂》的主创贾斯汀·罗兰批评过这些有智力优越感的傲慢的粉丝,但不得不承认,这部作品最终吸引的确实是那些有着大量媒介经验的观众。
科幻剧粉丝可以轻易地找到这部剧集的科幻设定与《星际迷航》《神秘博士》《飞出个未来》《迷离档案》等科幻剧集的相似与勾连。粉丝们借用旧的文本经验推理分析《瑞克和莫蒂》中包含多重平行宇宙与混乱时间线的复杂叙事,寻找隐藏的信息,创造属于粉丝们的智力解谜游戏。相对地,《瑞克和莫蒂》的创作者也在这种粉丝文化背景下为自己的目标观众与理想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带有互文性的谜题。
如果说在粉丝文化中,粉丝们将电影或电视看作是讲述自身故事的原材料和打造自己社群的资源。[15]那么在当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情境中,这种原材料和社群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除了《瑞克和莫蒂》,还有相当一部分当代流行文化的经典/热门作品,如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部分作品、热门动画《电锯人》都多少将粉丝文化作为文本生产逻辑的重要部分。昆汀·塔伦蒂诺模仿致敬美国邪典电影制作的作品《刑房》,昆汀·塔伦蒂诺的《死亡证据》和罗伯特·罗德里格兹(Robert Rodriguez)的《恐怖星球》,就是借用刑房电影(Grindhouse film)这一亚类型。这当然是B级片①B级片(B-Movies),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双片连映制度下生产的一种便宜、快速制作的电影,是作为一种比主流长片低一等级的长片被摄制出来的娱乐产品。参见:[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7.粉丝的昆汀作为作者导演的一种类型创作偏好,但这类作品隐含的一种生产逻辑,也是基于这类B级片粉丝文化的存在。
将粉丝文化看作后现代主义拼贴风格的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并不是说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只是为了迎合粉丝去制造符合他们口味的作品,而是指因为这种粉丝文化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当代媒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创作者才有可能将引用、模仿作为核心创作思路。
四、重新理解粉丝文化的生产力
在理解了《瑞克和莫蒂》这种后现代主义文本生成逻辑与粉丝文化的互动关系后,或许可以重新思考之前大众文化/粉丝文化研究的一些观点。
比如,基于粉丝文化语境生成的大众文化文本,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法国作者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式文本——“不断要求读者去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16]。这类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17]。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这一概念,对应的是一种更具先锋性,因此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的文本,比如新小说。这种邀请读者解读文本,带有强烈的审美上的精英文化倾向,想要制造一种开放的、召唤多重解读的文本。“作者式文本”催生了大众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概念——“生产者式文本”,比如富有创造力的通俗文化产品。生产者式文本虽然兼具容易理解与开放性的特点,但与作者式文本有着某种相似的保守之处,即依然停留在文本解读的层面,抗拒读者介入文本的生产过程。与之相反,《瑞克和莫蒂》这类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产品真正敞开了文本,邀请读者参与其中,将文本生产的权力从作为精英的创作者扩散到普通的媒介受众。
或者也可以重新思考法国学者米歇尔·德·赛托的游牧式解读概念,这一直是研究媒介消费和粉丝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米歇尔·德·赛托在“赋予大众阅读以灵活多变的‘战术优势’,同时也指出了其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和永久的文化基础这个‘战略劣势’”[18]。这正是传统粉丝文化的一种缺陷,即粉丝的文化生产是停留在接受层面的一种创造力。但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改变,越来越多拼贴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已经将粉丝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米歇尔·德·赛托所描述的“劣势”。
或者,再次回顾费斯克的一个论断:“大众文化是一个意义的生产过程,而决定这个过程的不是文化工业部门生产的文本产品,而是观众、接受者、消费者对于文本的接受消费过程。”[19]他认为“粉丝”是大众文化中相当具有生产力的一群参与者。费斯克的观点,以反对生产决定论的立场,强调接受过程的重要性,却依然处在一个文本生产/传播与消费/接受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原本处于消费环节的粉丝文化,共同塑造了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力量,一种能够影响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宰制性力量,并进一步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与文化土壤,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接受的二元对立。
《瑞克和莫蒂》的后现代主义拼贴戏仿来自粉丝文化的影响,可以说直接受益于大众文化产品,是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积极回应。但另一方面,这种模仿、借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大部分都带有某种戏仿、颠覆的成份,因此也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嘲讽、对抗。如果说《瑞克和莫蒂》的理想观众是通俗文化作品的粉丝,那么必定是一种理性、有思考能力的粉丝,这样他们才能接受《瑞克和莫蒂》主创对于源文本的嘲讽、颠覆。于是,《瑞克和莫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大众文化趋同性倾向的一种反拨,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既熟悉、亲密,同时又带着距离感、警惕感,这种矛盾的关系包含一种福柯(Foucault)所说的“抵制性力量”,进一步激活了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和对抗性。
结语
通过对《瑞克和莫蒂》的媒介生产与媒介接受的分析可以看到,随着粉丝成为一种覆盖全球的文化与社会网络,成为媒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参与性文化,已经可以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20]大众文化产品如同一架由多种元素装配而成的机器,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观众这一元素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传统的文化产品生产流通过程中,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单向度地接收、回应,反馈讯息却很难及时回流,观众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只有当整个的生产条件与流通条件发生改变时,观众才能够反过来介入及影响生产,成为机器运转中真正具有能动性的组成元素。在参与性的粉丝文化中,新的媒介消费经验带来了生产与流通条件的全新变革,也催生出如《瑞克和莫蒂》、昆汀电影这类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产品,由此,大众文化真正实现了双向传播互动,受众终于不再只是传播活动的落脚点,而成了新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