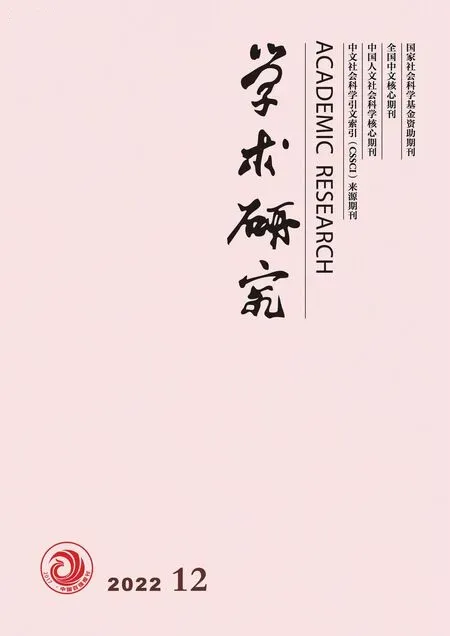马克思关于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
——兼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陈广思
特殊性(Besonderheit/particularity)和普遍性(Allgemeinheit/universality)是一对富有辩证关系的哲学范畴,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要素。区别这对范畴在这两种辩证法中的不同地位和含义以及对它们的内在结构的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特殊性
黑格尔辩证法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是:“黑格尔的普遍概念似乎总是‘主宰着’特殊性、行动能力和偶然性,同质的精神由于把差异和物质性逼到历史的幽暗深处,才得以创造了一个辩证法。”①[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这句语气不甚确定的话表达了黑格尔辩证法以普遍性支配特殊性(“普遍性—特殊性”)的结构。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相比于特殊性来说,普遍性是绝对第一性和优先性的,它同时包含着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关于同一性逻辑,黑格尔说:“普遍性,这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②[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1页。普遍之物是单纯的东西在自己的否定性中保持着自身的东西。绝对精神使自身对象化为外物,进而又扬弃这些作为它的否定物的外物,将它们当作自身的内在规定收回自身。这样,它在它的否定物(也即它的规定性)之中也就是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关系。关于观念性逻辑,黑格尔说:“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③[德]黑格尔:《小逻辑》,第332页。“每一个观念都是一种普遍化,而普遍化是属于思维的。使某种东西普遍化,就是对它进行思维。”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对黑格尔来说,只有思想才是唯一完全符合普遍性概念的东西,绝对精神是被客体化的思想,思想意味着对它的对象的观念化。凡是被思想所“思想”到的东西,都会转化为观念进入思想之中。思想因此对它的一切对象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性范畴的绝对同一性逻辑只有以它的观念性逻辑为前提才是可能的。绝对精神如果不是因为能够将它所有的否定物转化为观念,它就不能在它们之中保持自身,就不能实现绝对的普遍性。
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普遍性范畴以它的同一性和观念性逻辑支配精神在运动过程中所有的特殊环节和特殊产物。特殊性既被观念化,也被同一化,成为绝对精神内在的多样性规定,与它保持着同一性关系:“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特殊性中,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②[德]黑格尔:《小逻辑》,第331页。这是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结构的必然结果。在涉及现实领域时,黑格尔往往将特殊性范畴与个人的感性冲动和主观需要联系起来讨论,认为“各个人的特殊性首先在自身内包含有他们的需要”,③[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黑格尔十分警惕这样一种“独立特殊性原则”,即主体的特殊性无限制地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使之转变为一种非理性的秩序。他说:“特殊性的独立发展是这样一个环节,即它在古代国家表现为这些国家所遭到的伤风败俗,以及它们衰亡的最后原因。”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9页。正因为特殊性原则意味着非理性的原则,因此无论在哪个场合,黑格尔都主张用普遍性原则来限制特殊性。如果特殊性没有被“吸取”到国家这样一些普遍性之中,那么它就没有得到合法化、伦理化,因此而作为“罪恶”出现。⑥[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83页。虽然黑格尔也强调不能压制或摒弃特殊性,认为理念的发展需要赋予特殊性“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⑦[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页。但是特殊性的这种权利是在它们受制于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更根本地说,是在特殊性本身受制于绝对精神的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特殊性并没有摆脱被支配的性质。
黑格尔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这些理解深刻地影响着早年马克思的思想。但在马克思逐步确立了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之后,他不仅不像黑格尔那样根据普遍性来理解特殊性,反而是从特殊性的角度来理解普遍性,并寻求作为特殊性之全体解放的真正普遍性。这是一种完全颠倒的做法。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富含辩证法的因素,并且本身就构成了他的辩证法的本质内容。
二、马克思:特殊性、普遍性及辩证法
马克思没有从思辨的或抽象的层面来讨论过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他这方面的思想的理解,我们需要结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语境来进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一个重要的思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非普遍的,也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所具有的各种普遍性(资本的、政治权力的、上层建筑的或意识形态的)都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进一步而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具有历史性和特殊性,由此决定了每一个社会中现实的人与物都是历史的和特殊的,没有什么现实之物是真正普遍的。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我们理解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重要语境,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理解不仅在整体语境上区别于黑格尔,而且持一种完全不同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的特殊性原则。
(一)马克思:特殊性原则
关于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我们将从他在186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说起。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说:“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普遍](原译中的“普遍”为“一般”——引者注)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根据这段话来看,公有地并不会因为它的一部分被分割出去成为私有地而丧失其属性,因为公有地并不是因为是共同体(村庄、部落等)的全体土地才是公有地,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共同体才成为公有地,它具有普遍的属性。公有地代表共同体这个事实的背后,是它剥夺了诸多的私有地代表共同体的同样权力。公有地其实与被分割出来的那些私有地一样,都是不完整之物,都是构成全体土地的特殊性要素。但是,其中一种特殊(公有地)通过在其他诸多的特殊(私有地)中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而成为普遍,而其他的诸多特殊(私有地)则在这种被支配的关系中将自身保持为特殊。由此可见,普遍性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特殊性,就其是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的方式来获得这种普遍性而言,它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而特殊性在其中则是被支配的特殊性。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特殊的事物……本身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受限制的东西来对待,也就是说,受一种凌驾于它的普遍力量的限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日本学者见田石介针对上述马克思的话也得出类似结论:“德语中所谓一般,既不是特殊环节特性的平均或折中,也不是指各方面的共通性,同时,更不是指这些特殊环节的质料和实体。从根本上说,它是指实际存在的,在特殊环节里赋予支配性影响的东西。”③[日]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引文中的“一般”应理解为“普遍”。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一块土地的特殊性属性,我们才能够揭示公有地的普遍性的虚幻性和它与私有地之间的支配关系。这里包含着从事物的特殊性出发来理解现实事物的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也能够很快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也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而且他所警惕的“独特特殊性原则”本质上也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原则,因为它主张的不过是一种独特的特殊性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来获得解放和伸张的权利。
那么,当我们通过马克思认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之后,怎么理解那种真正的,以及既不支配其他特殊性也不被其他特殊性所支配的特殊性?我们从黑格尔下面这句话说起:“特殊性的东西也正是使自己同在自己之外的他物相关联。”④[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换言之,如果一种特殊性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特殊,那么它既需要在自身的实存中始终中介着这种作为它的否定物的“他物”,但同时也要时刻保持着与“他物”的差异或区别,既要避免被“他物”所支配,也要避免支配“他物”,总之就是要避免它与“他物”的区别性发展成新的同一性(黑格尔的特殊性概念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真正的特殊性的概念要义是一事物在自身的实存中始终中介着自身的否定物,它的存在本身是被他物所中介的存在。
马克思虽然没有从纯粹概念分析的角度讨论过真正的特殊性的概念,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着一种能够反映这个概念的特殊性原则。马克思在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来批判资本主义时,确立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特殊的,即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具体发展程度中,一个社会的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综合产生的结果。它在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包含与其他生产方式完全相同的形成要素,因此与其他生产方式必然是相区别的。如马克思在提到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的所有制的历史形成时说道:“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制(Eigentum)(“所有制”原译为“所有权”——引者注)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8页。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性反映了它的特殊性。在一个社会内部,一种生产方式哪怕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支配或支配另一种生产方式,但就其本身的形成过程而言,它仍然是特殊的。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推进了他的这种特殊性原则。一方面是对现实个人的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这句话后半段的原文是“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直译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无中译本中的“一切”一词(此词的出现应是为了对应“关系”在这里的复数形式)。“一切”一词在这里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误解,即认为个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根据马克思的总体思想,他在这里想表达的应是人的现实本质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内部诸社会关系的总和。前一种理解会把个人的现实本质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普遍本质,后一种理解则把人的现实本质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特殊本质。澄清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个人的现实本质的特定性和特殊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这表明人的现实本质不是单一的、纯粹自我关联的,它要获得现实性,就必须与他物——各种物质生活资料——相互中介。由于这些他物和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又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所以它们共同将现实个人的本质规定为特定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他成为特定的、一定的和特殊的个人。另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把这种特殊性原则推进到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之中。他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特殊的以太”表明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即一个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将自身的特殊性普遍化,以此赋予这个社会及其内部要素同样性质的特殊性。如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由于农业耕作是主导的生产方式,因此连这个民族中的工业、工业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带有土地所有制的性质。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页。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是一个特殊的总体,其内部每一层次的要素都存在“特殊的以太”,但所有这些层次的“特殊的以太”,归根到底又是由生产方式层面的“特殊的以太”所决定的。因此,在这层层的支配关系中,整个社会被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内而外地散发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总之,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只是一种被他的普遍性原则所限制的原则相区别,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现实事物的视平线。根据这一原则,一切现实事物都呈现出它历史性和特殊性的一面,哪怕它们本身总是受到凌驾于它们的普遍力量的限制,也不能消除它们的现实存在的特殊性。但是,上述“特殊的以太”除了表达历史的特殊性原则之外,其实也表达了支配性的普遍性概念,因为“特殊的以太”恰好是一种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来获得自身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概念。实际上,我们总是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中:当我们在讨论现实事物的特殊性存在时,总不可避免地讨论到凌驾于它之上的某种普遍力量的限制,现实中的特殊性都是被普遍性所“污染”的特殊性。这恰好彰显了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所具有的否定性或批判性一面:以特殊性为原则批判虚幻的普遍性。
(二)否定:以特殊性为原则批判虚幻普遍性
在理解和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最为强调的内容之一就是它所包含的否定性环节,并在自己的辩证法中也着重包含这一环节。但是,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以普遍性来“否定”特殊性的,那么马克思则完全反过来:他从特殊性出发来“否定”普遍性,当然这种普遍性是虚幻的普遍性。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支配性的普遍性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分工形式,以及形成各种共同体、等级或阶级的方式来垄断社会资源,由此产生政治对立关系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中,人类社会还无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现实的普遍利益在形式的普遍性与内容的普遍性方面总是存在错位(即在其形式具有普遍性时,其内容不具有普遍性;或者在其内容具有普遍性时,其形式不具有普遍性),导致其与特殊利益总会形成相互对立和斗争的关系。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537页。这些内容的进一步表达就是,现实领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存在的都只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特殊性及其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形式的普遍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了支配性的普遍性和被支配的特殊性,以及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被支配的特殊性总在自身中包含着作为自己的否定物的另一种特殊性,即支配性的普遍性;支配性的普遍性则总试图在每一种被支配的特殊性上与自身保持着“自由的等同性”,它受制于自身的特殊性性质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只能成为虚幻的普遍性。阿多诺说,我们不能过分热忱于把这种普遍性当作“肥皂泡”来对待,因为这样“不能把握普遍在现状中有害的统治地位”。①[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这也是马克思敏锐意识到的一点,他坚持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虚幻的普遍性,揭示其特殊性的根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阶级社会中的虚幻普遍性做了归纳,指出:“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这几方面内容所对应的普遍性显然都是由于分工、社会利益的对立和政治对立而产生的虚幻普遍性,我们只有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才能够揭示它们的虚幻性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无疑是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说:“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解读出多方面的内容:国家作为一种现实普遍物,总是由特定的特殊阶级所掌控的,所以它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不具有内容的普遍性,因此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争夺国家这种形式的普遍物的斗争,当某个利益集团争夺成功时,它就将作为统治阶级为自身的特殊性附魅上普遍性的形式,宣称自身即国家;因此,特殊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为了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普遍物而进行的斗争。如果说现实国家是由于其普遍性的形式无法获得普遍性的内容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普遍物,那么生产力的情况则相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展起来的世界性的市场竞争和交往是一种发达的生产力,它们作为人类财富本身是“物质的伦理实质”,④George E. McCarthy, Marx and the Ancients: Classical Ethics,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 p.158.应当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力只是资本的生产力,由资产阶级所掌握,并不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它在形式方面不具有普遍性。内容与形式的错位导致这种生产力同样也不具有真正意义的普遍性。同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身同一性时所具有的普遍性,建立在它用自身的特殊性来支配和统治其他一切特殊性的基础上,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有特定的历史性规定和技术规定,所以资本终究不能摆脱自身的特殊性根源的限制,为自身的普遍性创造出同样普遍的内容。就此而言,资本的普遍性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遍性。
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虚幻普遍性的历史合理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暂时的适应性,是阶级统治获得自身的合理性的条件。在此范围内,一种现实普遍性即便是虚幻普遍性,也包含着一定的真正普遍性的因素。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最初获得自身的统治地位时,人们关于共同利益的想象可能是真实的,即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这种共同利益最初的确是一种普遍利益。这是由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地位的条件是“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2页。它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最初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这个社会存在真实的共同利益,统治阶级将自身提升为社会普遍阶级具有历史合理性。不过,统治阶级自身的特殊性根源为它的统治设置了历史的限度,当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步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力将会慢慢遭受到否定,附魅在它身上的普遍性也会慢慢地暴露出其特殊性的面目。这样,最初的共同利益以及各种意识形态范畴(法、哲学、宗教等)的虚幻普遍性也就像泡沫一样被戳穿。统治阶级的历史合理性消失,甚至转变为一种反动性,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暴动或革命。因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性,并非虚幻普遍性被简单“还原”为最初的特殊性的条件,而是它将被新的特殊性所击败和取代的时刻。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为特殊性—普遍性不断地变换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条件,而且其本身还产生了一种关于虚幻普遍性的辩证法:虚幻普遍性不断地被自身的特殊性所否定,而这种特殊性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地错过自身,它的形象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不断切换,但始终无法成为自身。
总之,当我们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来“否定”现实普遍性时,实质上是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这种对立和分离“还原”为各种形式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把这种矛盾关系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如何解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最终意味着什么?
(三)对立统一:社会总体的转型和真正的普遍性
贺麟在介绍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时说:“矛盾就是统一体分裂为二和对立物之合而为一。”①贺麟:《黑格尔的同一、差别和矛盾诸逻辑范畴的辩证发展》,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3页。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矛盾关系是“统一体”将自身一分为二产生的,因此矛盾双方也将通过对立统一的方式回归这个“统一体”,以此解决双方的矛盾。阿尔都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关系任何时候都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本原”,而且也通过这个本原得到解决。②[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1-97、189-193页。
马克思在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矛盾概念。在他看来,现实事物的矛盾关系并未预设任何的“统一体”,它随着以这种矛盾关系为条件的社会总体的形成而形成,因此也通过这种社会总体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这种总体的转型而消失。对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以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价值)和普遍性(价值)的矛盾为例来进行说明。马克思说,在这种矛盾关系中,“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页。商品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才出现的,随着由商品交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总体不断发展,这种矛盾关系才不断发展起来。这种社会总体越是发展出复杂的内部结构,越是成为一种特殊的总体,商品内部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是随之发展出复杂的表现形式(例如货币与商品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等),越成为这个社会总体的主要矛盾关系的根源。正因为现实的矛盾是与产生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总体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矛盾关系阶段性的对立统一或初步解决依赖于它所在的社会总体的发展或转型。马克思说:“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3页。“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发展矛盾,商品交换带来了商品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但这种交换本身又使双方的对立关系得到缓解,当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寻找到等价物,并最终发明货币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可以借助这种一般等价物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地存在。商品的交换过程本身就为“解决”由这种交换所产生的矛盾提供了条件。当商品社会由于它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矛盾的不断发展而最终发生彻底转型时,这些内含的矛盾也都将消失,或者过渡为新的矛盾形式。
在阶级统治中所出现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形成和解决也同样如此。一个社会的阶级统治本身直接产生这个社会内部各种形式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以这些矛盾关系为主要条件而形成、发展和运动的。当这些矛盾关系的发展促使阶级统治发展到最极端的形式直至崩溃时,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实现一次转型,旧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将因此消失,产生新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因此,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阶段性的解决,总是以这种矛盾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它所构成的社会总体的消失、矛盾关系的形式获得新的内容为结果。
那么如何理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根据前面的思路,这种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促使以之为条件的社会总体发生彻底转型,即人类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充分发展的和社会化的生产力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本身都实现了最充分的社会化,国家、阶级、阶级统治以及所有狭隘的政治对立关系都消失不见,人与人在充分的相互联系中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由于虚幻普遍性被彻底消除,因此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关系也被彻底消除。马克思称这样一种社会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而来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得到发展的生产力,不再被特殊的阶级所掌握,而是归全体人民、归社会本身所有,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也由全体人民所支配。普遍性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社会现实地包含着真正的普遍性。
不仅如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还全面解放了特殊性,使每一种特殊性都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它通过消除支配性的普遍性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彻底消除了这种虚幻的普遍性,赋予每一种特殊性真正的“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如果每一种特殊性都能够在与其他特殊性充分的关联中获得这种权利,那么每一种特殊性就成为普遍性。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单独一种或少数的特殊性孤立地或者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获得了“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这是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而是在与其他所有特殊性的充分关联中,每一种特殊性都获得这种权利。在这种普遍的关联中,单个特殊性的主观任性和无节制性都被消除了,每一种特殊性都按照它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性的方式行动。这是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区别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后者只是追求一种或少数特定特殊性的解放,但前者追求的是全体特殊性在一种普遍的维度中的普遍解放和持存。以个人的感官感觉为例,个人的感觉和感官是完全内在于个人的,在黑格尔那里是标志着特殊性范畴的东西。在前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感觉既没有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囿于狭隘的社会关系。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感官不仅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且“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个体的感觉和感官充分社会化,每一种最内在的、特殊的感觉都具有充分的普遍性,社会的、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内在地沉积成每一个个人最内在、最个别和最特殊的感觉,使之具有充分的普遍性。这样,特殊性本身就是普遍性,普遍性本身也是特殊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在本质层面达到辩证的统一。这既是特殊性的全面解放,也是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
由此可见,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解决以及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是一个与人类历史运动相呼应的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对特殊性—普遍性的思考本身就是对人类历史辩证的运动过程的思考,表达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最内在的一种结构,即以特殊性为原则来理解现实事物,批判虚幻普遍性,追求真正的普遍性(“特殊性—普遍性”结构)。从这个层面来看,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都各自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和结构,只不过这两种结构相互颠倒,因此他们的辩证法之本质也截然不同。
三、余论:马克思如何“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一直以来人们都围绕着这段话,讨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
我们在前面的阐述本身就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既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普遍性—特殊性”结构,也具体交代了马克思辩证法“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这样,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显得直观了:他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位置“颠倒”过来,使特殊性从被支配的地位转换为第一性和原则性的地位,使普遍性从第一性的位置转变为被批判和否定的位置,并以此指出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方式。这样一种颠倒,解释了马克思是如何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无疑是包含着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的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支配,是绝对精神局限在纯粹的观念世界之中统治着关于特殊事物的观念,形成“普遍的东西对特殊的东西的帝国主义”。①[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第115页。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从特殊性原则,也即区别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事物,揭穿现实虚幻普遍性的特殊性根源,批判“普遍在现状中有害的统治地位”,通过把握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来寻找使得一切特殊性获得解放的真正普遍性。以此,辩证法被黑格尔笼罩上的神秘外壳在马克思那里就无处遁形了。
同时,剥去神秘外壳的过程还是“提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对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的系统化描述。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0页。当我们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原则及其对特殊性的支配力量,确立了特殊性原则后,辩证法的基本关系——如矛盾、否定性、总体和对立统一等——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它们不仅摆脱了曾经笼罩在它们头上的神秘外壳,而且它们自身就包含着对这种神秘外壳的彻底批判,使辩证法从黑格尔面向精神世界的“观念”辩证法转变为面向现实社会历史的历史辩证法。在这里,剥去神秘外壳的过程“提取”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提取合理内核的过程则彻底消除了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这两个过程是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结构的颠倒同时实现的。这样,我们就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阿尔都塞曾经迷惘的“颠倒”“剥去外壳”和“保留内核”三个步骤是如何同时实现的这个问题。③[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8页。
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真正摆正了特殊性和普遍性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位置。他以“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的结构,使我们意识到这两种辩证法可能还存在着诸多我们尚未真正触及的隐蔽张力。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对辩证法的讨论多次涉及特殊性,④[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93-97、214页。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也多次讨论到特殊性,并暗示一种面向特殊的辩证法或“特殊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s Besonderen)的可能,⑤参见[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71、328页。这可以说是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指出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