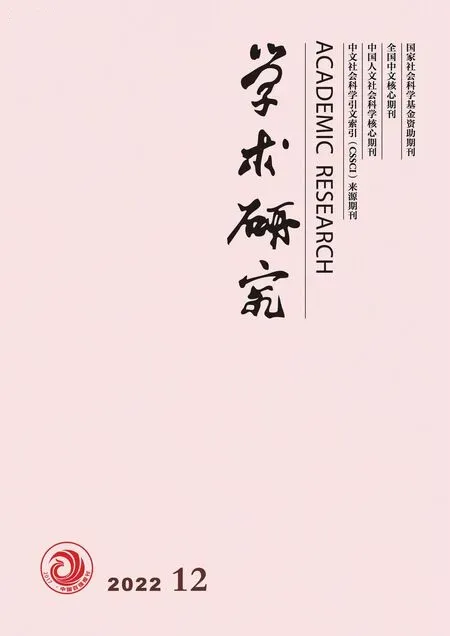“训诂阐释学”构想
张 江
“训诂阐释学”是学科建构方向的新设计。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训诂学与阐释学各自的优势,互为根基,互为支撑,互为动力,为阐释学的发展奠定可靠的中国基础,为训诂学的生长开辟广大的现实空间。如此努力,训诂阐释学将以系统完备的新学科形态,位列人文领域,为文、史、哲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新示范。
一、缘起
训诂学与阐释学,本是两门功能与目标相近的古老学问。前者由古代东周萌芽初长,及至当代已成为与计算机科学深入结合,释读古代典籍的一般方法。后者滥觞于古代希腊,及至当代已成为立足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上的本体论学说。长期以来,两学科各自独立,相互疏离,特别是在中国古代,阐释方法体现为义理方法,两者在各自独立的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一点是,训诂学的阐释能力需要提高,阐释学的训诂约束需要强化,两者洽切会通,训诂阐释循环出新,训诂方法为阐释提供可靠基础,阐释方法为训诂开辟可能空间。由此,两个学科的独立优势可为共同优势,不同的困境皆可纾解。更重要的是,训诂学优势恰是阐释学弱势,阐释学优势恰是训诂学弱势。两者有机融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一加一远大于二。此为设想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出发点。
训诂学的优势是,就文本理解而言,训诂由字词考证入手,识本字本义,得文本之真相。这是一切文本阐释的根基。训诂学立足于此,话语建构的确定性、可靠性强。训诂方法是中国古代经解的基本方法。两千多年的实践,虽有起落,甚至大起大落,但训诂的基本精神贯穿至今,方法不断丰富,特别是由清初至现代,经过乾嘉与章黄学派对训诂理论的改造与提升,训诂学本身有了重大进步。训诂的弱势是,自训诂发生,全力集中并停留于字与词的专门考究,由此而生出释义离散及碎片化倾向。如汉末魏初学者徐干言:“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①[魏]徐干:《中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3页。此言虽有偏颇,但大致不错。至于今天,因时代变化,世情移易,训诂之学虽有进步,但在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当代阐释学理念冲击下,缺失应有的阐释能力,无法挺进人文学科前沿,影响难以扩大。
阐释学的优势是,开放、多元、创意取向积极,随历史与语境演进,集中义理创见,生产超越文本的阔大意义。中国古代的义理之阐,自先秦始,经前汉今文经学再起,至近代康有为、廖平,发扬和发明文本义理,传统浩大,成就非凡。无超越训诂的义理之阐,就无今天面貌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阐释的弱势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轻视和放弃本义之识,放任阐释者生产任意话语,其确证性与可靠性遭致怀疑。就西方阐释学的主流观点说,张扬阐释的主观随意性,认为文本意义由读者决定,文本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强制文本和作者说读者想说的话。譬如,费什坚定地认为,“作品中的一切——其语法,其种种意义,其种种形式单位——都是解释的产物,它们绝不是‘实际上’给定的”,②参见[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意义的产生与否都取决于读者的头脑(思考),并不是在印成的篇页或书页中去寻找”。③[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尤其是文学文本阐释上长期流行的读者中心论,主张作者、文本与阐释无关,一切阐释皆无确定性可言,以阐释者的主观理解为据,任意生产与文本无涉的私人话语,作者死了,文本死了,理论家、批评家却作为读者活着,无边界、无约束的阐释,是阐释的最高形式,是唯一合理与正当的阐释。更进一步,这种以文学为对象的阐释观,与哲学、史学等其他领域的同类话语相杂揉,以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方法解构颠覆历史,否定历史事实的确定性认知,否定对任何哲学思想确当可靠的理解,成为当代阐释学的主流。如此倾向,使当代阐释学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防止和克服无正当约束的阐释,及必然发生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成为阐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读者理论,走得比西方更远。所谓“六经注我”,以本己之意重构经典,史上早有评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版权意识为衡准,断言诸如文本的版权不仅是书写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苏轼直接将杜诗引为己诗,“爱国志士文天祥则不仅赞同这种诗歌文本的产权共享,甚至怀疑原作者享有产权的合法性”。④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如此阐释理念,与训诂精神对立尖锐。
出路在哪里?就克服当代阐释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强化训诂意识,引进训诂方法;就克服古代训诂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强化阐释意识,引进阐释方法。阐释学与训诂学相融相合,择优会通,使训诂成为受到阐释学精神浸润的训诂,阐释成为汲取训诂学精神的阐释,两者浑然一体,为训诂学开拓当代阐释空间,为阐释学扎牢训诂基础。
训诂阐释学基本构想由此而缘起。
二、学科方向
学科建设,首要任务是定位方向。训诂阐释学的发生基点何在,方向和目的何在,这是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要依据训诂与阐释两个学科的各自优势,约束和阻碍其发展的问题,以及会通融合之后的整体功能与作用,确定训诂阐释学的学科方向。我们的设想是,所谓训诂阐释学,其基本路线起点于训诂,通达于阐释,构建于学科。即以训诂为起点和方法,以真理性、可靠性、融贯性为准则,坚持由训而阐,由阐而训,反复循环、螺旋上升的正当路径,最终达致根基牢靠、创造新知的尚意之阐。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统合,建立起学科特色鲜明,具有广泛应用意义的训诂阐释学。由此而区别于以阐释为起点,回归于训诂的阐释训诂学,以及流行于今的各类阐释之学。
训诂不同于阐释,要害在哪里?所谓阐释之阐,《说文》引《易》曰:“阐幽”,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8页。意在明隐幽之理。《玉篇》:“阐,大也。”②[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76页。《易·丰卦·彖》孔颖达正义:“阐者,弘广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种,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阐弘使大。”③[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阐为义理之阐,无大歧义。所谓训诂,孔颖达定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④[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十三经注疏》,第269页。如此定义,明显区别于阐。辨于形貌,通于异辞,足于解释,流于表面,非究义理,非穷大道,此为训诂之要,亦为解释之要。⑤参见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由此看,阐释与训诂的区别是清楚的,无需引经据典,再作常识性的话语堆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训诂与阐释的关系。可集中为三点。
第一,从根基说,训诂为先。训诂本身的性质与功能决定,无论是具体的阐释活动,还是阐释的整体过程,当以训诂为先。训诂是解释。解释的本义是以分析之法,从破解对象细微之节上手,庖丁解牛式地分裂文本,一字一词地说明并实证字词本义,所谓“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就是训诂及训诂学为自己确定的根本任务。孔颖达为什么用解释一词说明训诂,而不用阐释说明训诂?我们可以将其阐发为孔颖达自觉区别解释与阐释的表现。他清醒认知,训诂以解释为宗,赋予训诂以特殊功能和作用。人类的文字运用及辞义理解永无止境。旧词自不必说。尤其是新的字词,譬如,网络上不断产生并流行的新词,如无严谨训诂,如何认知,如何流行,如何进入历史?人类生产言语,进而制造文字,是为了表达、说明,且记录对自我、世界,以及他人的理解,是基本的阐释形式。没有文字词语的确切表达与把握,如何表达自我?阐释如何实现?训诂以文字之形、音、义为标的,为求意、识理、循道,提供基准和前提。训诂信仰言可尽意,重在字词精准。这是人类所以造字、用字的基本精神。此精神由古至今,从岩上简划到甲骨刻痕,从先秦统一文字,到五四白话改革,一以贯之,训诂千年坚守,使阐释成为可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我们都可以认定,不识字无书文,无训诂无阐释。阐释的起始,训诂为先。
第二,从目的说,通达义理。训诂是阐释的基础,是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但阐释绝非训诂一途,不可停留于训诂。训诂方法繁多,基本取向是经典本义。在知识论意义上,是说明和实证已有知识。阐释本图大义,且先不论其真假对错,其核心取向是创造和发明没有的知识,并由此而区别于训诂。皮锡瑞说:“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⑥[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3页。郭象本人也明确,阐释之目的在大义而非小节。注《庄子》鲲鹏之意时便说:“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⑦[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页。如简单以今古文经学比照,古文经学认定“六经皆史”,当以整理古代史料为首要任务,偏重名物训诂,证明孔子是之所是;今文经学认定“六经致用”,当以通经致用为首要任务,偏重微言大义,发明孔子应为所是。两者虽有相互渗透,但阐释以义理发扬为本,非囿于字义训诂和形貌说明。当然,此类尚意之阐,不受阐释对象的束缚,一定会对原有经典之本义有所曲解甚至歪曲,但是,它创造新哲学概念和命题,赋予经典以新的时代性和生命力。义理通达乃阐释最高目的。
第三,从具体操作说,体用兼备。在完备的阐释学体系中,训诂与阐释不可偏废,但就具体的阐释活动而言,阐释主体不必是全面的,每一次的阐释活动更不必求全责备。或偏重训诂,或偏重阐释,以至穷极一生,均无不可。前者如许慎、段玉裁,后者如王弼、康有为,都可为阐释学发展有大贡献。但是,完备的阐释学体系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阐释学已是本体论形态,方法论的追求应该淘汰。此论有失公允。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无需在此讨论。作为完备体系的阐释之学,方法论是必须备有的核心要素。以知识论的观点看,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能够被广泛接受,一要可靠,二要能用。它要有本体论的表达,即此知识所表征的对象为何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如此本源性认知相对清晰,此为可靠。它要与方法论适洽,以方法论所赋予的路径、规则、范式为准,获得更广大的新知识,此为能用。作为完备体系的阐释学,之所以完备且能成其为学,从大的框架说,本体论与方法论当应皆备。古今中外,史上由训诂而义理,由诠释而阐释的成功范例很多。由此路径,为训诂开辟广阔道路,为阐释扎下可靠根基,训诂阐释学的建构意义正当合理,学科方向定位明晰恰切。
三、系统方法
训诂阐释学之为学,应该具备学科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及相对完备的方法体系。阐释立足于训诂,训诂达及阐释,既要有训诂的方法,也要有阐释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两种方法的交叉融合与合理运用。中国古代的训诂方法丰富多样。在字词本义的认证上,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一类的方法早已成熟,至于作为诠释或解释的基本方法,古代学人多有创造,诸如说解、传注、章句、注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文字学、考据学、文献学、金石学等等,为后世所标举。诸多经典体式,譬如“诂训传”体,以毛亨《毛诗诂训传》为代表,后人总结:“《毛诗》在解释体式上,既有‘诂训’二体,可以从文本出发,作语言解释,使整个解释建立在可信可靠的基础上;又有‘传’体,可以从现实出发,作心理解释,使整个解释能阐发出文本所蕴含的义理。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毛诗诂训传》的作者们还努力使‘诂训’体与‘传’体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诂训传’解释体式。”①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总体上说,中国古代训诂或诂训的方法比较丰富和完备,为训诂阐释学奠定了深厚基础。阐释义理的方法总结,似乎比较薄弱,起码未如训诂方法那样多样完整,但实践经验及其累积同样丰富而深厚,为阐释方法的一般概括和提炼,准备了充分条件。从基本理念上说,所谓“诗无达诂”“得意忘言”,为无源头、无标准、无约束的义理阐释提供了强大辩护。在具体方法上,以下几点可资讨论。
第一,立旨为先。义理之阐,立旨在先,寻证为后。旨主其证,证从其旨,亦可谓旨为证之领,证为旨之仆。如此路径,优长在阐释主体有明确、清晰的理论标的,意向坚定,路径简洁,可以作超越文本的广大判断。此为阐释扩张的基本纲领。所谓创造,立旨既是方向,亦为动力。王弼、郭象,二程、朱子,康有为、廖平,皆因此道而独立一方。
第二,不任其辞。阐释非训诂,不拘一辞一句,为求大道,可脱离字辞,“出于其外”,达于至理。此为阐的基本手段。同为《春秋》释本,左丘明以史说经,重在本事。董仲舒志在“大一统”,破《春秋》通辞,从变而移,于定辞之外生出辞句未有之意,“然后可与适道”,②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1页。为义理之阐另辟新途。
第三,弃言悟意。始如《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③[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第82页。再如《庄子》“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④[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五中,第495页。于是,阐释不可尽信于言,弃言悟意,便是正理。至于佛学,“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⑤[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第1286页。由此,抛弃文本,面壁顿悟,便可生意。其意在脱离文字,任从顿悟。
第四,时情交移。理解是时情框架规定的理解。经典文本生于前代,前代世情决定文本为此文本。著者为世情所染而言而文,自有其定向之意。后来者阐释,借文本立旨,将此时情交移于彼时情,将此时情规约之感悟赋予彼时情之生成,并以此为彼时情文本之意,达及阐释目的。用当代语言说,交移时情乃变换语境。文本意义是确定语境下的意义。语境确定,意义确定。变换语境,意义必有改变。文本的广义理解,意义的生成,由语境决定。义理之阐,旧文新理解,皆为语境变换所起,由此新意成为可能。时情交移,是阐可为阐本根之法。
第五,诗史共意。此处称史代表文学以外的其他各科,譬如,经、史、子部,包括以《诗经》证史及尚意。孟子言:“《诗》亡然后《春秋》作。”①[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卷八上,《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于是,诗与史互为表里而利用,史、诗共意,进而以诗史互证,以诗证理,便为正途。以史证诗,为诗的理解与阐释提供历史背景与证据,可视为大的训诂手法。以诗证史则为另途。诗及一般文学文本,与经与史有本质差别。以诗证史,诗歌不再是虚构的文学文本,不复是想象与情感的艺术载体,而被当作真实的历史事实与记录,为史、诗共意开辟新途径。如此,以诗为史,即以想象虚构历史;以诗证理,为义理之阐敞开大门,以至成为传统。著名者有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后妃之德。②[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十三经注疏》,第273页。
上述训诂与义理方法各有长短。训诂阐释学力主将两者之方法系统组织起来,实现两种方法的互补互证。此种取向,历史上多有成绩。经学大师郑玄就是一例。郑玄本于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是为训诂之“诠”;与此同时,他贯通天人古今之道,阐发礼乐文明要义,又是义理之“阐”。郑玄经学的历史价值,源于对训诂与阐释的融会贯通。朱熹既重训诂更重阐释:“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435 页。朱熹强调并践行了二者结合且由训诂而入阐释的正当路径。至于戴震,于此更是大进一步。其言:“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④[清]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页。此论已是方法论层次的总结与提炼,当为训诂阐释学系统方法的可靠参照。
由此看来,训诂阐释学系统方法的建构,首先要全面客观地总结中国古代训诂与义理两者的思想与思维方法,在深厚广大的实践经验中,找到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则或规律。同时,要比较西方古典学、阐释学的经验,学其优长,在比较和借鉴中不断有所成就。主张训诂,不是要简单回到训诂,也不是停留于戴震,而是要推进训诂的现代化及其有效应用,为训诂发展注入活力。
四、学科素养
学科建设,以学科为中心展开研究、培养专业人才,必须注重学科素养的培育和养成。所谓学科素养,是本学科学习和研究者应该综合理解把握的学科主旨与学理品格。有此素养以至素养丰沛,学习和研究方有动力基础和进步可能。训诂阐释学的学科素养,除了包含普通的古代文学、史学、经学,以及必要的哲学和逻辑素质外,我们特别强调此新学科应当具备的三个特殊素养。
第一,训诂精神。训诂是一种精神。其基本构成是,真理性、确证性、创造性的不懈追求。上千年的训诂史,一切进步皆以此为动力,皆因此而有所作为。其一,真理性。此为认识论问题。训诂由求真而起。孔颖达对训与诂的定义,就是求真。所谓“通古今之异辞”,就是寻求异词同义,异形、异音同义相符,与符合论的真理论一致。所谓“辨物之形貌”,就是说解文献中名物词的真实样貌,使人之认识与对象形貌一致,亦为符合论的真理性追求。对古代典籍的诂训,“以意逆志”的指归,求的亦是立言本真。如此真理性追求,在哲学认识论上以可知论为基点,即接受和相信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有能力充分展开自己的理性,实现或趋近对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确当认知。这是训诂之所以有,之所以在的根本。坚持真理性认识,以实事求是而自律,此为训诂精神之第一要义。其二,确定性。此为语言观问题。两种不同的语言观,“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一直对立相抗。训诂者相信,言能尽意,古字异音皆可考证认知,并由此而知字、音之本义。多义之字,在确定语境下,有确定之义,在整体章句中,确定之义的字词,有确定之意。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偏执。但训诂学认为,文字创造本身,其目的和作用皆以确定性可能为基准。我们为什么造字?造字的目的就是要把确定的意义确定地表达出来。因为理性能力限制,原始文字简单粗陋,历史进步了,文字丰富多义,但多义的本质和生成动力,亦是为了确切表现和传达确定的认知。确定性精神,是文字内蕴的本来精神,从于此事业的训诂,当然执着并成就于此。其三,创造精神。一般认为,在意义阐释上,训诂落于本义再现,且常常陷于破碎繁琐,少创造精神。但此仅为一面。整体上衡量,训诂自有其创造,且因为创造,训诂才有今天。回头看训诂历史,训诂的方法不断地有所进步发明。训诂学的萌芽,最早生成于东周。其训诂不过是古代文献中偶然出现的训释形式。而至战国秦汉,可以《尔雅》《说文》为代表,系统的、完整的注释书和训诂专书出现,训诂方法已渐丰富。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及至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将训诂方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理论化、体系化进步明显。20世纪初,章黄学派确定了训诂学以形训、声训、义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框架,训诂学以汉语语义学的面目走进现代。新世纪以来,在训诂及语言学界的努力下,古老的训诂学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对大数据方法的采用,使训诂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创造精神当是训诂精神的重要组成方面,是训诂阐释学应该坚持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训诂精神的养育,是新学科建构与展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第二,公共自觉。阐释是公共的。阐释以实现其公共性为目的和价值标准。训诂是阐释的重要方式,其有效与合理性,同样以公共性实现程度为鹄的。如此,公共自觉当是训诂阐释学的基本学科素养。阐释之公共性内涵丰富而广大。①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从学科建设的意义说,公共自觉重在方法上的相互汲取。其一,就训诂学说,自觉的方法公共,既将训诂方法更广大地推向原有领域以外,为一般的阐释行为所接受,并逐步成为阐释的基本思维方式,又掌握和运用义理方法为训诂所用。义理方法第一条就是“立旨为先”,诸多阐释经常因此而陷入“强制阐释”而难为共识。乾嘉学派对汉学承继与兴盛贡献甚大,其代表人物戴震,训诂考据以“实事求是”为纲。然而胡适却另外指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②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这与立旨为先的义理方法一致。由此启发,自觉方法的公共,就是各种有助于“使人信仰”的方法都要尽力采纳,不应该偏执地独为一统,拒采其他有效方法,对最终达及阐释的训诂而言,此尤为重要。其二,就阐释学说,特别是因当代西方阐释学之影响,阐释对训诂的疏离,阐释落于无根据的概念推演,注重汲取训诂的理念和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清代训诂力求“公论”,主张“不以一己之意为是,而必求诸古今之公论”。③[清]钱大昕:《虞东学诗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59页。在钱大昕及乾嘉学派看来,所谓“公论”与“私意”区别甚大。欲求公意,戴震主张“十分之见”,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④[清]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卷九,第141页。以此而保障其阐释为公共接受。义理或阐释应该汲取和融汇训诂理念和方法,使阐释建立于可靠的训诂基础之上。其三,就训诂阐释学而言,训诂与阐释方法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如何转化?训诂与阐释的循环是转化并促进提高之正途。从起点与终点的关系看,训诂是起点,阐释为终点。清代有人表述为训诂—义理—得道。这只是一个具体阶段的描述。实际的阐释过程,是三者总体相互渗透,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而不前。阐释的循环,是西方阐释学的核心概念。中国古代的训诂循环,由字而辞,由辞而句,由句而章,循环往复,互文互证,已是惯例。扩而张之,由训诂而义理,由义理而得道,同样是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每一次回复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由道看义理,由义理看字辞,新的理解不断生产,阐释不断上升,阐释的公共性得以实现和扩大。重要的是把握循环的本质意义,自觉地推进循环。
第三,范式意识。范式有多种表述。此处就学科共同体一致认可和接受的模型或模式,对训诂阐释学的范式意识作简单讨论。训诂阐释学,作为以方法为主要取向的新学科,范式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针对学科基本建构讲,共同认可的范式,是散漫理论集中为学科的重要标志。没有可靠的范式起点,就没有学科建构的完成。针对学科本身的进步能力讲,可以引导学科以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而少犯路径错误,增强解决学科重大问题的核心能力。进一步的难题是,训诂阐释学既要解决两个学科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科融合以后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新的共同范式,以及从理念到方法的系统建构,就难以发挥新学科的作用,训诂与阐释依然各行其道。学科交叉融合,首先是新范式的建立。其一,基本理念的整合。训诂和阐释均有本学科的习惯理念。训诂偏好于向内集中思考,找到事实证明的确凿点,把握片断本真。阐释倾向于向外发散思考,放弃片断及细节,抓取义理可能的爆发点,扩张精神可能。两者融合一体,共用所长,由此而既有训诂的扩大,又有阐释的可靠,此类理念应为曾经各自远离的学术共同体所一致接受。其二,一般性方法。诸如,前面提到的立旨在先,认证在后的思维与运作方式,胡适定义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前者为义理阐释的上手方式,后者为训诂的中心方法,如此结合,可否成为共同接受的一般方法?同是《春秋》释本,左丘明与董仲舒显著不同,训诂阐释学如何综合与归纳,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模式与方法?其三,核心概念的归纳与证明。学科话语框架以自己完整的概念体系为支撑。这有两个问题。一是,概念的提炼。中国古代训诂与阐释经验丰富,但独立的概念,尤其是义理阐释的概念,总结归纳不多,需要下功夫梳理和再建。二是,古代概念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是,如何以现代汉语无歧义地清晰表达。很多概念,譬如,“坐忘”“虚静”“涵泳”“浃恰”,等等,都是极具当代阐释学价值的概念,但在现代汉语中很少出现,对当代人而言极为陌生,简单用来,很难推广。
训诂阐释学还是一个初步的学科概念,其完整建构与有效应用道路漫长。我们能够把握的一点是: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设想。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是人文学科,即哲学、历史、文学,完型一体的新理念、新方法。分类研究当然重要,但人文研究,其基本理念和方法的交叉、渗透、融合,是当今人文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出路。当代阐释学本身就以此优势为长,与具有传统优势的训诂学相互支撑融合,打造新的训诂阐释学,其合法性可靠,其实践性可能,其成功性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