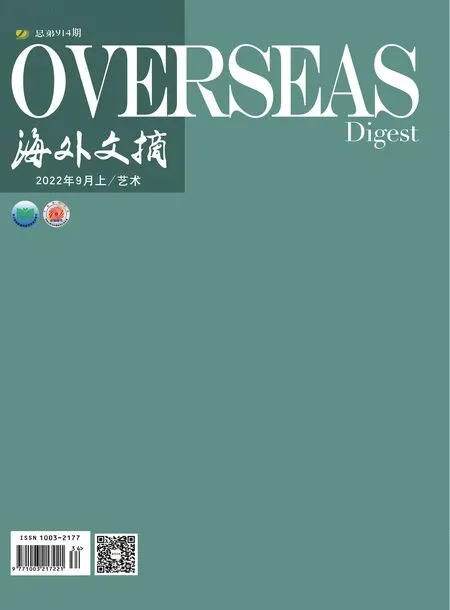塔西佗眼中的日耳曼人
——读《日耳曼尼亚志》
□毛凯华/文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生活在公元55-120年的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制危机致使罗马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成衰落之势,这种衰落的表现深深刺激了塔西佗,于是他将沿途关于日耳曼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日耳曼尼亚志》中,向罗马人展现日耳曼人所谓的“蛮族”形象。那么塔西佗眼中的日耳曼尼亚人是什么样子呢?本文通过解读《日耳曼尼亚志》,进一步分析塔西佗眼中日耳曼人的形象构建及其背后的理性思考。
1 塔西佗与《日耳曼尼亚志》
关于塔西佗的个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从他的作品与朋友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公元61-113年)的十一封信札中可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塔西佗出生于旧贵族家庭,曾就学于著名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公元35-100年),公元79年曾离开罗马在外省做官,期间他可能游历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大致形成了对日耳曼人的初步认知。政界上的塔西佗是一个典型的共和派,向往罗马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贵族“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在帝国时期受到相当的限制和约束。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并常在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对帝国时期的专制流露痛恶[1]。
塔西佗的著作不少流传至今,但在当时他的作品并未获得赞誉,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部分塔西佗的残稿并予以推崇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日耳曼尼亚志》是塔西佗书写的一部最早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不少学者在研究日耳曼人史、德国古代史时都会首先提到《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记载都是极可珍贵的。尽管经过学者的考察,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记述大体正确,有些难免失真,但他从来不掩饰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展现奴隶制帝国走向崩溃的种种症状,使得《日耳曼尼亚志》成为民族志研究的主要蓝本。
而西方学者的争论聚焦于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资料考辨。大致梳理了一下,塔西佗获得关于日耳曼人地理与生活习惯等信息来源无非有三种:(1)当时塔西佗切身走访了日耳曼尼亚地区,与日耳曼人相处,获得了对日耳曼人生活习惯的认知;(2)通过在日耳曼尼亚与罗马边境经商的商人和前线作战士兵朋友获得关于日耳曼人的部分信息;(3)参考其他涉及日耳曼地理与民俗的文学记录。其中赫伯特·W·贝纳里奥(Herbert W. Benario)与阿尔弗雷德·古德曼(Alfred Gudeman)等多个学者坚持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塔西佗曾亲自去过日耳曼尼亚,他在著作中关于日耳曼部落礼仪和习俗的大量详细知识更多出自对文学资料的参考,包括凯撒《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老普林尼《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的相关记载等。
2 塔西佗眼中的日耳曼人
2.1 日耳曼人的起源、构成与性格特点
塔西佗言明他笔下的“日耳曼人”是指生活在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域范围内的日耳曼人原住民。日耳曼尼亚地域环境闭塞,气候严酷,这使得当地原住民很少与外界交往,因此他们大多血统纯正,很少与其他种族混血。可见。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认识最初起源于地域分布,并非基于血缘、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等关于民族特性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塔西佗提到他们以歌谣传述历史,这些歌谣记载了日耳曼人的起源,颂赞着日耳曼族的始祖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奴斯(Mannus)。相传滨海的印盖窝内斯人(Ingaevones),中央部分的厄尔密诺内斯人(Herminones)和余下的伊斯泰窝内斯人(Istaevones)就是因曼奴斯的三个儿子而得名的。因此,可以看出古罗马人对早期日耳曼尼亚各部族的划分和命名主要以地理环境为依据[1][5]。
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居民构成极为复杂,根据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记载,早期日耳曼尼亚人主要包括巴达维人(Batavi)、卡提人(Chatti)、布鲁克特尔人(Bructeri)、卡马维人(Chamavi)、考契人(Chauci)等十余部族。对某些部族的记述甚至带有些许传奇色彩,比如人面兽身的赫路西人(Hellusii)和奥克西奥人(Oxiones)。可见,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居民构成极为复杂,当时的罗马人也无法考察清楚,只能以地域名称来笼统地称呼当地居民。
塔西佗眼中的日耳曼人崇尚武力且骁勇善战,尚武的精神在日耳曼尼亚地区非常盛行。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提到日耳曼人不善耕作与航行,他们只专注战斗。日耳曼人的战斗热情高涨,他们以逃离战场、表现懦弱为耻,甚至把丢失兵器作为一种罪行,给以剥夺参加宗教大会权利等严重惩罚。同时日耳曼社会存在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就是十分尊重妇女。他们认为妇女身上有一种预知未来的力量,所以每逢战斗,妇女袒露胸脯为军队助威,带来胜利。因此在日耳曼社会中,女性地位很高,不会受到侮辱和鄙视,还能参与政事商议。基于对女性的尊重,坚贞也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美好品德,他们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传统,“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欢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但是懒散也成为了日耳曼人的通病,塔西佗记载到,即使是最骁勇善战的勇士在无仗可打时也整天无所事事,将一切生计家务弃之不顾[1][6]。
2.2 风俗习惯与生活特征
日耳曼尼亚地区有很多日耳曼部落,他们的风俗习惯各异,并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王明珂写的《游牧者的抉择》中,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做比较研究时,就笼统的把日耳曼人各部归为游牧民族,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然而,根据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记述,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习俗各异,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将他们笼统地视为游牧民族。
塔西佗笔下部分日耳曼尼亚部族具有游牧民族迁徙性的特征。“他们彼此独立地分散居住,逐泉水、牧场或树林迁徙”“没有房舍、土地以及任何职业,靠四处游荡生活。”也有一些部族以畜牧业为生,“他们以拥有大量的畜群而自豪”,并且牲畜的多寡成为衡量财产的标准,甚至可以作为支付媒介。同时他们饲养马匹并拥有大量骑兵,日耳曼尼亚人中的滕克特尔人一生与马相伴,马甚至作为遗产由英勇的子嗣继承[1][4]。
虽然日耳曼人具有游牧特征,但并不能确定所有日耳曼人都是游牧民族,某些部族还具有农业因素。一些日耳曼部族拥有耕地,以农业为重要生产方式。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对耕地分配:“土地按耕种者数量的比例,由全体耕种者进行分配,以用于耕种;随后他们再按照等级在内部分配,占有土地的广阔程度,使得土地的分配易于进行。他们每年都开垦新的可耕种的土地,即便如此,他们仍有剩余的土地……谷物是他们向土地索取的唯一收获”,其中开垦与分配耕地、种植谷物均体现出日耳曼人具备农耕民族的典型特征。除此之外,部分日耳曼人还表现出农耕民族最基本的定居特征。塔西佗称他们拥有周围有大片空地的固定房舍,“他们甚至没有学会使用石料和砖:只使用未经修剪形状的木材,不加以装饰,外形毫不吸引人;有些部分被仔细涂上亮色的灰泥,闪闪发光,足以作为绘画、壁画的替代品。”除此之外,日耳曼人也有挖掘开放式地窖的习俗,用于冬天避寒或者作为房舍的地基,战争时他们可以躲进地窖以避免敌袭,这些足以说明他们具备定居民族的典型特征[1]。
3 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形象构建与理性思考
塔西佗努力构建日耳曼人善良、淳朴、尚武的蛮族形象,这离不开他对罗马社会形势的反思。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公元前74年的斯巴达奴隶大起义,使罗马奴隶社会发生严重的危机,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裁的形势,由共和制转成帝制。但问题仍旧存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共和主义与帝国体制之间的悖论。罗马帝制下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造成的血腥杀戮迫使塔西佗追寻古老的政治美德,向往古典共和主义。然而帝国治理需要新的道德基础与政治精神,孕育于城邦政治中并以自由和德性为核心的古典共和主义显得无法适应。伴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罗马帝国衰亡的趋势愈加明显。塔西佗看到了走向衰落的罗马,也看到了抛弃淳朴与务实,追逐享乐与奢靡的罗马人,这种与日耳曼蛮族的道德对比,使其不得不为罗马传统道德教育发声。对此,黑格尔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塔西佗曾经心神向往地勾画出一幅日耳曼图画——拿它来反衬出它本人所处世界的腐化和虚伪。”不仅如此,17世纪的《编年史》注疏者特拉伊亚诺·博卡利尼(Traiano boccalini)也表示“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用以在敌视美德的时代通行无阻地传达一种关于政治和人性的学说……[2]”可见,塔西佗是借颂扬日耳曼野蛮人自然、淳朴、勇敢的美德,来反衬罗马人的奢靡与腐化,同时警示罗马人帝国文明的衰落,其中蕴含塔西佗对罗马帝国命运的深深忧患。
塔西佗认为,被罗马人视为敌对与落后的日耳曼人,虽是“蛮族”,但不一定野蛮。书中没有出现认为日耳曼人野蛮的表述,只是指出日耳曼人社会在物质、文化、社会组织等落后于罗马的方面。塔西佗拥有对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较为客观公正的看法,并且赞扬了日耳曼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力量和富于斗争的尚武精神。这就形成了日耳曼族与罗马人社会生活的强烈对比,促使罗马人对现实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思考、反省。
但《日耳曼尼亚志》流传至今,却被犹太裔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列为“史上最危险的书”,而且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度被尊奉为“黄金宝卷”和“日耳曼圣经”,堪称希特勒政权发动的那场日耳曼革命的终极灵感。纳粹用这本书引起民族仇恨,并且发动所谓的日耳曼革命,说其“危险”主要在于对日耳曼人战争德性和残暴精神的鼓吹、歪曲及实践,将日耳曼精神推向极端。可以说,《日耳曼尼亚志》本身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日耳曼尼亚志》的读者们[3]。
如今《日耳曼尼亚》表面的意识形态蒙尘已被拂去,它慢慢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一本写于1世纪本真实性有待商榷的罗马民族志。现代学者更加关心这本著作体现出的拉丁语的语法、塔西佗的写作修辞、文本的勘误、当时罗马人对外族人的态度、与其他考古学资料的相互印证等等。盲目的比附和过度的释读,对于一本书籍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被要求服务于某些政治目的时,它可能从一本普通的古典著作嬗变为“最危险的书”。■
引用
[1] [古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美]里克.塔西佗的教诲——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M].肖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美]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M].荆腾,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4] 赵文君.中古西欧日耳曼人财产观初探[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04):64-68+63.
[5] 宇信潇,宫秀华.试析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Germani”[J].古代文明,2018,12(04):15-24+123.
[6] 柴聪聪.从《日耳曼尼亚志》看日耳曼民族的性格[J].城市地理,2015(4):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