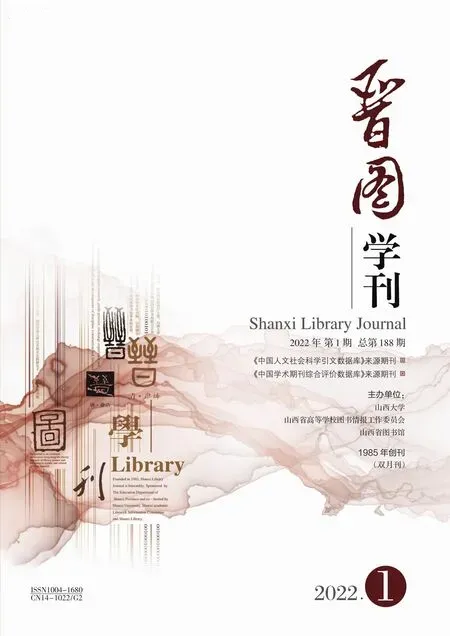古籍书名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考察路径
黄 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0 引言
书名之于书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清钮琇《觚剩续编》卷一“书名”条便云:“著书必先命名。所命之书与所著之书,明简确切,然后可传。”[1]同时,书名还是目录著作不可缺少的项目,“没有书名就没有目录”[2]53。学界很早就已意识到了书名的重要性,余嘉锡《古书通例》[3]、张舜徽《广校雠略》[4]等专著均辟专章探讨书名命名的一般性规律;程千帆[2]54、杜泽逊[5]、曹之[6]等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归纳了书名的命名方式,并探讨了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现象。鉴于书名研究的重要价值,来新夏曾有建立“书名学”的倡议[7]。虽然学界已经意识到古籍书名研究的重要性,但这一研究的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至今无人进行深入探究,更少有人在方法论层面探讨此问题。本文的写作旨意即在于揭示古籍书名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探讨从事该领域研究可兹借鉴的研究理论与可行的研究方法。
1 有利于推动与完善中国书籍史研究
西汉以前,“古书多无大题”,“东汉以后,自别集之外,几无不有书名矣[2]210-217。那么,书名是如何从无到有,成为书籍的必要项的?书名在产生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哪些题写和命名方面的特征?书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都受到了哪些特定历史环境或条件的影响?鉴于书名之于书的重要性,这些疑问实为研究中国典籍制度、书籍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今日书史研究的著作甚多,如钱存训《书于竹帛》[8]、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9]、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10]、陈力《中国图书史》[11]等,诸书研究角度不尽相同,虽均涉及书名问题,但对于上揭古籍书名研究至关重要的问题,均少有讨论。因此,若能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利于拓展中国书籍史问题的研究空间,加深人们对于典籍制度的理解,从而推进中国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从上述研究成果看,古籍书名研究可归纳为书名题写研究与命名研究两大方面,今各举一例以现其对完善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价值。
古籍书名题写方面的例子如:古书“一卷两题”现象。所谓“一卷两题”是指一部书籍或一部书籍的一卷,在开篇与结尾处各题写一个书名的现象。例如:法藏敦煌文献P.3054首、尾题均为“开蒙要训一卷”[12];俄藏敦煌文献Ф072首、尾题均作“瑜伽师地论卷第六”[13]。又如:《中华再造善本》所录北大藏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卷首题与卷尾题中的书名均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中华再造善本》所录国图藏宋庆元六年浔阳郡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首尾题中的书名均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等。
“一卷两题”为卷轴与册页古书标题题写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的起源则可上溯至简帛时期,如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中《八阵》篇题“八阵”分别见于首简(编号336)简背及末简(编号342)正文末;《延气》篇题“延气”亦见于首简(编号389)简背及末简(编号396)正文末[14]。又如:《居延新简》所录文书《三十井侯官始建国天凤亖(四)年亖月尽六月当食者案》与《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亖年七月行塞省兵物录》。前者首题“三十井侯官始建国天凤亖年亖月尽六月当食者案”位于EPT68·195,尾题位于EPT68·207,文字内容与首题同;后者首题“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亖年七月行塞省兵物录”位于EPF22·236,尾题位于EPF22·241,作“省兵物录”[15]。由此可知,作为古书重要构成部分的书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承袭与发展的关系,清晰地描述这种关系,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以及发生转变之致因,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于古书发展历史的认知。
在汉文古籍中,佛、道类典籍的书名在唐代普遍比较繁复,多为长书名。究其原因,一方面当为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因为译经活动为将其他民族的语言译成汉文的过程,翻译势必要以原文献的书名为依据。另一方面,唐代崇尚奢华的风气也体现在了书名中,如为了体现佛教的尊崇地位,译经者往往给书名加上诸多表示尊崇、崇高等含义的修饰词语,这一点在汉文原创佛典中体现尤为突出,因而造成了佛教书名繁复、奢华的特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佛经典籍中书名多有此特征,如英藏S.5475《坛经》,其卷首书目全称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16];法藏P.2382首题作“佛说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17]99;俄藏Ф092首题作“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第七”,其后以双行小字题曰“一名中度那阑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18],正名与异称均为长书名。道教典籍也存在通过书名标榜权威性的现象,因此与佛教典籍一样也存在大量的长书名,如法藏敦煌文献P.2431亦为首残尾全,其尾题作“洞玄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17]358;P.2461首尾完具,首题作“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第四”,尾题作“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19]。
从上引长书名可见,佛、道类典籍书名的这种特点,是刻意叠加多种修饰成份所致。如《坛经》的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南宗顿教”为宗派,“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所说法门内容,“六祖惠能大师”是说者,“于韶州大梵寺”是说经处,“施法坛经”为主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智慧上品大戒”为主名,其前为修饰成分。在古书命名活动中,虽然使用核心词汇加修饰成分来命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像佛、道类书籍为了标榜其权威性,在书名中不仅“人法双举”[20],事无巨细地将诸多信息均罗列在书名中,以至书名变得极为冗长的做法,仍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这与典籍属性以及唐代特定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
此外,书名研究也是推动东西方书籍史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一方面,汉文古籍书名的产生、演变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早在汉唐时期,汉文图书就已流传到今日我国的西藏、新疆、甘肃等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产生了互动;不但如此,汉文图书在此时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地区或国家典籍书名的题写形制、命名方式必然要受汉文古籍的影响,探究这一影响的具体细节,从书名角度考察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地区书籍,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书籍交流史,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题。另一方面,因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书籍之路”[21],“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22],从书名角度做中西方书名的对比研究,同样对比较书籍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古籍书名研究在古籍整理与出土文献定名方面的价值
古籍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无意间产生的讹误,同时也存在故意的篡改行为,当这两种情况发生在书名上时,便造成了书名的讹变。这种现象可能会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困扰,很有必要明确讹变的过程。不但如此,古籍整理的很重要一项工作是尽量恢复古书原貌,因此当整理古籍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时,恢复该书书名的本来面貌就显得非常必要。
例如,据黄永年言,薛居正《旧五代史》本名《五代史》,《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所录均称“《五代史》”。由于宋代时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盛行,薛书到明代传本已稀,入清后遂失传。其后邵晋涵等人从《册府元龟》及《永乐大典》等书中将该书进行重辑整理,于乾隆四十年(1775)进呈。因为要与欧阳修《新五代史》相区别,遂在原书名前冠以“旧”字。欧阳修《新五代史》本名为《五代史记》,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监本的卷端标题书名均作《五代史记》,孝宗淳熙间进《四朝国史》本传,《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亦称《五代史记》,《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名本名为《新五代史记》,不确。该书书名至明代北监本卷端标题始去“记”字作“五代史”。虽“新五代史”之名已见于《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但该名仅是便于和薛史相区别而称,并不见于各雕版本欧阳修书载体之上,直到中华书局标点本该书才径以“新五代史”作为该书的正式书名。[23]
辛德勇承续黄先生的观点,论证了恢复《新五代史》书名本来面貌的必要性。辛先生在《关于所谓“新五代史”的书名问题》一文指出,《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只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俗称,中华书局在1974年点校此书时才正式改为“新五代史”,讹误的时间不过五十年,若有机会重新整理或修订此书,当恢复其本名。因为在花费极大精力、财力并穷尽海内外各种版本,力图勘定一部最符合作者原貌的善本时,在最惹眼的书名上却依后人妄改是不可理解的;从“名从主人”的社会规则来看,整理古籍也应尊重作者本人意见,诸如将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书名改为《汉籍善本考》的出版行为是不可取的。不唯如此,每个书名都带有特定的时代文化烙印,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旦改名这些信息就泯灭了,从此角度看,也应该对本名予以重视[24]93-103。
对于一书多名当如何去取的问题,辛德勇在另一篇文章《由所谓〈新五代史〉的名称论及新印〈二十四史〉的题名形式问题》中提出了解决办法:
今天我们在重新校勘排印古籍的时候,若是能够完整保留旧本固有的卷端(其实还应该包括卷末)题名形式,就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妥善地解决照顾习惯用法与保留古籍原貌之间的矛盾。如欧阳脩(笔者按:“脩”字原文如此。辛先生明确表示“欧阳修”不可写作“欧阳脩”,此处遵从其意见,原文照录。)《五代史记》,在新印洋装本的封皮上,可依从社会习惯,题作“新五代史”,而内文则保持文忠公原书形态,印为“五代史记”。[24]115-120
可见,书名研究对古籍整理与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明确此类问题也可避免研究中可能产生的误解。
除传世文献外,书名研究还将有资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定名工作。今日简帛文献大量出土,散落各国的敦煌文献也不断公布,如何给失名简帛古书或敦煌文献残卷定以合适的书名以便于研究使用,已成为需要学界认真研究并解决的重要课题。对出土古书书名题写与命名特点的考察,将对出土文献定名工作有指导意义。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后附有四篇古逸书,其中第一篇存36行,约2 500字。该篇文字尾部残缺,不见篇题,但从其后《要》《昭力》《缪和》三篇文献的篇题均题写在篇末来看,此篇原当有篇题。张政烺据该篇帛书首句4字为“二三子问”,将其篇名定为《二三子问》;然而,张立文举同附于《周易》后面的《缪和》不题《缪和问》,《昭力》不题《昭力问》之例,认为此篇篇题当定为《二三子》,其说可从[25]。
以上二例正体现了书名研究在古籍整理与出土文献定名工作的价值。
3 古籍书名研究对古籍目录研究及古籍编目的意义
书名为目录编排的必要项,在目录中其重要性超过作者项,为目录书最重要之著录项。精简如尤袤《遂初堂书目》,编撰者、卷数往往省略,唯书名不省。对于这一现象,《四库全书总目·遂初堂书目》提要云:“其例略与史志同。惟一书而兼载数本,以资互考,则与史志小异耳。诸书解题,检马氏《经籍考》无一条引及袤说,知原本如是。惟不载卷数及撰人,则疑传写者所删削,非其原书耳。”[26]730四库馆臣怀疑为传写者所删削而并非尤书原貌,无论《遂初堂书目》省略编撰者、卷数信息的现象是原书如此还是出于后世的删削,此现象已经凸显了书名之于目录的重要地位。类似《遂初堂书目》的情况也存在于《文渊阁书目》中,《四库全书总目·文渊阁书目》提要云:“盖本当时阁中存记册籍,故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橱,若干橱为一号而已。”[26]731《文渊阁书目》可以“不著撰人姓氏”“无卷数”但书名绝不可省,也表明了书名在目录中的重要性。可见,在一部目录中,诸如作者、卷数等著录项均可省略,唯书名不可省,可以说无书名便无目录。
然而,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目录书,书名的著录形式实际是存在差别的。例如:在几部重要的史志目录中,“《汉书·艺文志》没有什么固定的次序;《隋书、旧唐书志》以书名项为主,著者项当做附注;《新唐志、宋志、明志》以著者姓名加在书名之前”[27]。又如:书名在目录著录中有时会因某些因素失去原貌,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录有:“《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28]981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录作:“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四卷。”[29]《直斋书录解题》则录作:“《洞冥记》四卷 东汉光禄大夫郭宪子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30]从作者与书名信息看,以上三处所录当为同一部书,书名繁简不同,为全称与简称的关系。《隋书·经籍志》又录有:“《同姓名录》一卷,梁元帝撰。”[28]978《梁书·元帝纪》录作:“《古今同姓名录》一卷。”[31]《南史·元帝纪》所录与《梁书》同。从书名的繁简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所录书名当为《古今同姓名录》的简称。了解书名在古籍目录中的著录特征与重要性,对图书馆古籍编目将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乔衍琯曾针对当时现代图书馆编目应效仿西方目录编撰规则,将作者项置于书名项前方的意见予以反驳,其立论的主要证据,便来自于对中国古籍书名命名规律与功用的细致考察[27]127-144。
在以往的目录学研究中,对书名的关注往往立足于书名在目录中有无著录,其编排顺序有何特点等方面,从中考察的是学术的兴衰升降,其实际研究对象为书籍本身而非书名。因此,以目录书为依托进行古籍书名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特定目录编撰体例的理解,也将有助于古籍的编目工作。
4 古籍书名研究的材料来源与研究思路
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古籍书名研究无外乎书名题写与书名命名二途,目前的成果实际已涵盖这两方面。然而,在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似乎还缺乏清晰的认知,很有必要加以明确。
其一,在书名题写研究中,当按简帛、卷轴、册页的分期,以各时期典籍实物为主要依据与材料来源,考察书名在不同载体上的题写特征,并考察其致因与影响。具体思路为:从出土文献类型、文献生产时代、保存状况等因素选取简帛文献材料,考察简帛时期古书书名格式;以敦煌文献、传世卷轴古书为主要材料来源,考察魏晋至唐五代时期卷轴古书;以《中华再造善本》《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等所录宋、辽、金、元、明、清版古书为依据,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本图录》《中国版刻图录》等版本图录类著作,考察册页古书书名题写格式。在研究过程中,石刻文献可不作为书名材料的来源,但由于这类文献与书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可运用此类材料辅助论证;文书档案虽不属于书籍,但无论是抄写格式、装帧样式还是典藏方式,均与书籍关系密切,亦可加以甄别后作为论证材料使用。
其二,在书名命名研究中,当以古籍目录书所载书名为主要材料来源,考察书名命名的起源、类型、命名规律,以及书名命名后出现的特殊现象(如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如上所述,书名为古籍目录书著录项中之首要者,精简如《遂初堂书目》仅录书名而无作者、卷书等信息,说明目录中其他项目或可省略,但书名却是必要项,不可省略。与典籍实物之上所题写的书名相比,目录书所录书名虽属于间接材料,但作为考察书名命名的材料来源却有其明显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古籍目录著录书名较为全面。古籍目录或着眼于记录官方实际藏书(如《汉书·艺文志》),或致力于著录个人典藏(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或致力于收录前代所有著述(如郑樵《通志·艺文略》)或反映一代之著述(如《明史·艺文志》),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目录书如同一张张渔网,将古代著述网罗殆尽,可以说,古籍目录是了解我国古代图书著述情况的最佳方式。在早期的目录书中,其中著录的大部分典籍已经亡逸,多数典籍如果不是在目录中留名,后人甚至无从知晓其曾存世。例如,由于兵燹水火、自然淘汰等因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677种、12 994卷图书,流传至今者不过115种,不足原来的六分之一[32],其中所录的《神农》《青史子》等为该书仅见。又如:《隋书·经籍志》录有《后汉书》六家,分别为吴武陵太守谢承、晋少府卿华峤、晋祠部郎谢沈、晋秘书监袁山松、宋太子詹事范晔、梁萧子显,然而此书今天全存于世者仅有范晔的《后汉书》;至于其中著录的六家《晋书》今则全亡,如果不是目录书的著录,我们同样无法了解到这一情况。
其次,古籍目录著录书名较为有序。以古籍目录为书名材料主要来源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这种方法可避免随机选取书名材料进行研究的随意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目录书多以内容为分类与排序首要原则,同类典籍的排序则一般遵照成书的先后顺序排列。这便意味着在目录书中,属性相同或相近的典籍往往被列于一处,且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列。因此,以目录为材料来源,便于以同类相从的方式系统考察书名的命名特点,使研究范围内的书名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排列,在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书名对象的同时,又可兼顾书名具有的时代特征。
再次,古籍目录著录书名信息较为丰富。对某一部具体典籍来说,不同的目录书可能为我们提供该书的异称信息,丰富我们的认识。例如:《世说新语》一书有“世说”“世说新书”等十多种异称,“世说”之名见于《隋书·经籍志》,唐宋古籍称引也多有作“世说”者,而此书传世各版本均不题“世说”之名,所以对《世说新语》书名的考查,须结合古籍目录才可能厘清其演变轨迹[33]。另外,特定的解题式目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包含阐旨、溯源、诠典、释词、正谬、明体、标类等方面书名释义的直接材料[7],极大地方便了参考与研究。
最后,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古籍目录虽可作为考察古籍书名命名问题材料来源之渊薮,但在使用这些目录时应有主次之分。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藏书一般较个人丰富,官方所修目录著录的书名往往更为丰富,从而能反映特定时期的著述大略,因此,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正史目录,以及基于大规模古籍整理的目录成果,如《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应为主要的研究材料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任何目录对其规定范围内书籍的收录均不可能著录无遗,正史目录收书的丰富性虽为私人目录不可比拟,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也会有漏收的情况发生。如《隋书·经籍志》“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28]908的主观刊落行为,或是官方无收藏而民间有传本的客观制约,均会造成官修目录录书的缺失。因此,余嘉锡指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3]188-189,这就需要以私人目录、诸史《文苑传》《儒林传》及史料笔记等记载为辅助材料以补目录之缺,尽可能还原某特定时期著述整体面貌。此方面的材料极为分散,钩稽工作本将极为繁重,幸而前贤所作辑补各史艺文志的工作实质即为此,为以目录为参照进行书名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方面的成果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等[34]。此外,刘琳《北朝艺文志简编》《隋代艺文志简编》[35]、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36]也有新材料的补充,可兹参考。
5 古籍书名研究可兹借鉴的研究理论
无论是写本时代还是刻本时代,各时期的典籍都有其生产规范,版式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模式,而书名格式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若想厘清不同载体、不同生产方式、不同装帧形式的典籍中书名都有何题写特征,其格式规范为何,以及这种规范又是如何被打破并演进至下一阶段的等问题,其中实际涉及到技术规范的形成问题。因此,在书名题写研究中,可借鉴技术规范形成理论,从“生产经验总结—技术形成—示范、模仿、改进—业内普遍技术模式—社会评价—技术规范”[37]这一技术规范形成过程中,考察古籍书名所呈现的诸多题写特征(如古书“一卷两题”现象,古书“大题在下”现象等)。这将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窥见书名格式演变的内在规律与动因。
书名与地名、人名一样,属于专有名词。因此,在书名命名研究中,可尝试借鉴专名指称理论,揭示书名命名内部规律,从而解释书名命名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如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专名有无涵义、如何指称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当代语言哲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为由弗雷格、罗素提出,后由塞尔等人补充的“描述理论”;一为由克里普克、埃文斯等人所主张的“历史的因果指称理论”。前者认为,专名具有涵义,具可描述性意义,它们的实质为一些简化的或伪装的摹状词,或至少与这些特定的摹状词同义;后者则认为,我们给事物命名时,所依据的不是我们对名字意义的了解,而是这个名字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专名无涵义[38]。以上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后续的研究表明,二者不是完全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所谓专名的涵义,指的是专名使用者所理解的该专名所指对象属性的集合。专名的任务是给事物命名并用于指称该物,专名涵义的表达多需借助具描述功能的摹状词,但也不排除通过社会团体中的因果链条在其中的作用[39]。专名的涵义首先应是一个认知概念,它与人的认识能力及关于指称对象的知识和信念有关;同时,涵义还具有社会性,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交际活动有关[40]。书名命名虽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实际反映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书名命名的实质为命名者赋予物质的“书”一个具体称谓的创造性活动。因此,书名研究若能于以上理论有所借鉴,无疑对问题的深入和思路的打开大有裨益。
6 古籍书名研究可深入与拓展的研究方向
如上所述,前人古籍书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书名命名方式归纳,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现象研究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似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书名研究深入发展并拓展研究范围。
其一,研究者不应局限于运用归纳法总结典籍的命名方式,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每种命名方式内部,考察各命名方式生成的细节。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前人通过书名归纳出“与著者有关的书名”这一命名方式,或是再对其细化分出“以人名为书名”“以字为书名”“以郡望为书名”“以官职为书名”等条目,而是应该深入到这些条目的内部,考察每种命名方式出现的时间、背景、原因及影响。由于典籍的命名方式极为丰富,这方面将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其二,对典籍命名进行断代式研究,为书名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典籍的命名具有其时代性,如东汉末年王莽好新,以至当时很多书名都以“新”命书[41],产生了“新苑”“新序”等书名;唐代尊崇道教,官方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若干部道教典籍的书名进行了重命名。如《旧唐书·仪礼志》载:“(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丙申,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42]因此,以时代为依据,考察先秦直至明清各历史时期书名的命名特征是可行的,同样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其三,书名命名特殊现象的研究,为书名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关注最多者为“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现象,实际上,书名命名中尚包括其他有趣的现象。例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十三经”等合称书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为《方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为《心经》等缩略书名;以及书名中托以“黄帝”“神农”“姜太公”等托名现象等。诸如此类现象如何产生,盛行于何时,流行的原因,以及命名者命名心理等问题,都是富有探讨价值的论题,而此类问题目前还少有人关注。
其四,由于书名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解题类目录中往往集中保存了大量的书名释义方面的材料,因此,以某部目录类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书名阐释规律与倾向等,同样是可行的研究方向。黄小玲《〈四库全书总目〉对书名学之贡献》[7],李琳春《〈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整理与研究》[43]是从此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并运用到其他解题类目录的研究中。
其五,据笔者观察,中国古籍书名的命名有鲜明的类别属性,因此对不同部类的古籍书名进行分类研究,也可作为推动书名研究深入发展的可行方向。例如:古代医药书在传统目录中常被归在“数术”或“方技”中,随着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籍的数量不断增加,不同历史时期的医籍书名有其时代特色,分属不同小类的书名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他如戏曲、杂剧、传奇、小说等文学类书籍,佛、道类典籍的书名,以及家谱、地方志类古书书名的命名各有何部类特征,均是值得探讨且有重要价值的论题。李小龙在这方面有较为出色的研究,如他对《红楼梦》《西游记》《子不语》《世说新语》等古典小说书名具体而深入的考察有启发价值[44],可借鉴其研究方法,深入发掘其他类别典籍书名的内涵。
7 结束语
综上可见,鉴于书名之于书的重要性,书名研究可推动与完善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并对古籍整理与出土文献的定名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没有书名就没有目录”,书名研究又可拓展与深化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当遵循以典籍实物所题书名为考察对象,探讨古籍书名的题写问题;以目录学著作所录书名为主要材料来源,考察古籍书名的命名问题。研究时需把书名放在简帛、卷轴、册页这一书籍发展历程中,用共时的眼光,探究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名在题写与命名方面的特征;用历时的眼光,考察中国古籍书名在题写与命名方面的发展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