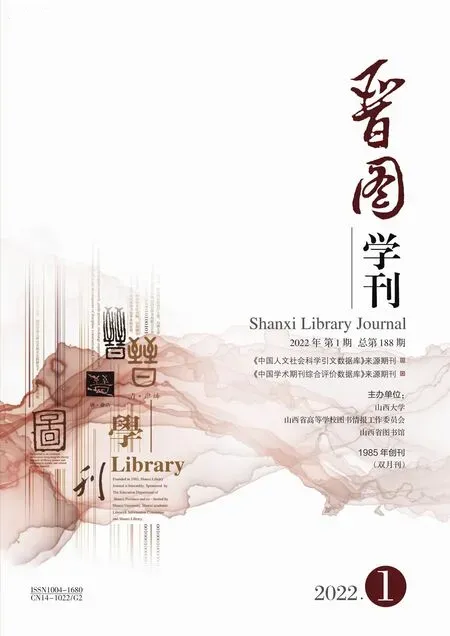唐代官府藏书的生产与传播研究
郭伟玲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前印刷时代,书籍生产方式是人工抄写,抄写、贩卖与偶尔的进献、赏赐行为组成了流通方式,传播途径较为具象,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与权力相结合,被定义为精英媒介,其生产和传播活动被局限于社会的某阶层中,交流空间与边界明晰。唐时雕版印刷技术出现并推广,文献生产方式从书写向印刷过渡,随之文献印本商品属性凸显,文献借助传播范围和规模的扩张,拥有了更大的力量,逐渐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媒介,唐朝成为书史(book history)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图书传播路径改变了以往的直来直去的运行路径,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直线转向网状,其事件过程在内涵与表现上构成新的趋势。
关于唐宋之际的书的历史,学者将其放置在时代、阶层、文化、科技等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各种因素在其中的推动作用,研究深入全面,但不免有一些细微要素未能涉及,文章拟从藏书史的微观视角出发,以唐代官府藏书生产模式的演变为点,追踪“青萍之末”的流通路线,以及所引发的文献交流模式中主体、内容、媒介等诸多因素的相关变化,及其最终的历史价值。
1 唐代官府藏书生产模式演变
中古时期官府藏书的生产方式为机构内官吏的履职性抄写,西汉时“置写书之官”[1],之后成为朝廷常设职官,虽名称各异,如工书人(南朝梁)、内书生(北齐)、弟子(南陈)、令史(西魏)、楷书郎(隋)、楷书手(唐)等,但职责相同,文献生产模式单一。唐代官府藏书制度完备,库内图书有正副贮之分,《唐六典》载:“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2],抄写人员日常任务繁重,机构内人员抄写难以满足典藏需求;另唐廷为快速扩充官藏体量,多次集中组织藏书抄写活动,各时期组织规模、抄写人员、组织方式存在差别,改革了汉魏以来的官府藏书生产方式,文章按照生产地点将其区别为机构内抄写、“机构内+机构外”抄写、“中央+地方”抄写三种文献生产模式。
1.1 机构内抄写
以藏书机构为主导,抄写人员被纳入职官体系,考课入流,在机构内进行图书生产,图书与人员处于某种封闭的状态中,抄写完毕的图书仍旧进入藏书库房,生产与传播物理空间上形成隔绝,机构内藏书生产模式存在时间长,自汉设写书之官到清御用刻工,机构内生产始终是官府藏书复制的主流途径。
唐武德五年,秘书丞令狐德棻奏请“增置楷书,专令缮写”[3],补录藏书;贞观年间唐太宗“令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至高宗处,其功未毕”;魏征“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4],贞观年间增置的抄书岗位和人员规模巨大,宋人周煇《清波别志》言:“(贞观间)秘书省增置百二十员,善书者凡二千人”[5],二千人的数据贞观年间所增置的岗位流动人次,因书手经由八考入流后任他官,书手需要重新选募,唐代墓志文献中记载了两名由秘书省书手入流的官员任职经历,书手李范“弱冠知名,召补兰台书手。……有简帝心,诏授登仕郎”[6];书手王基“年十有四,以贞观十一年擢为兰台书手,……以十八年随碟授岐州岐阳县尉”[6]2345-2346。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机构内模式进一步发展,形成朝廷藏书机构协同抄校,多馆两地同时进行的生产模式。开元五年十二月,“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7],这次秘书省图书抄写与东都乾元殿的图书抄写活动同步分别进行;开元七年,“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文以益阙文。”[4]4362长安洛阳两地多藏书机构相互检校,查漏补缺,协作传抄,时秘书省有楷书手九十人,集贤院御书手一百员,全员满额运作藏书复制,规模巨大,以集贤院为例,“从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3]1119
1.2 “机构内+机构外”抄写
高宗显庆年间,官藏文献生产方法一改贞观年间做法,使用以藏书机构为主导,招募社会书手在家抄写,按工计酬的抄写模式。高宗显庆中,政府删简增设的书手和校雠人员职位,召募社会“工书人”为临时抄写人员,“听书工写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随番刊正”[4]4393。该抄写模式在机构内官吏抄写的基础上,另外招募社会书手进行抄写,藏书文献生产规模扩大,同时也将抄写文献推入了更广阔的流通领域,抄写人员不进入机构,人身自由,文献走出机构,让封闭停滞的库内藏书进入了可传播流通的范围,文献传播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
1.3 “中央+地方”抄写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官府藏书遭遇战乱几次归零,藏书机构的日常抄写杯水车薪,不能及时补充官藏,中央政府却有心无力,地方开始参与藏书事业建设,“中央+地方”图书抄写模式应时而生。
第一阶段,由藏书机构补招书手抄写,地方政府负责纸张、粮食、笔墨等财物支持。
(贞元)三年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元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余钱,请添写史书。”从之。[3]1125
第二阶段,唐文宗时期,中央藏书机构与地方官府共同参与图书抄写。
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8]1336
开成元年七月,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3]1125
“中央+地方”图书抄写模式的出现,第一阶段以中央为主,地方不参与具体的藏书复制,仅提供物资支持,类似于机构内模式运作,文献与人员均可控;第二阶段地方官府直接参与到图书的抄写当中,由于文宗时财政吃紧,官制改革精简胥吏,延长入流年限,藏书机构书手补充困难,藏书抄写任务积压太多无法完成,因此分配由地方官府出人出力进行文献复制,这种模式图书与人员均不可控,官方藏书走出机构走出京城,藏书文献与社会文献之间出现交集。
2 唐代官府藏书的流通特征
不同于社会文献流通的不定向、连续的传播途径,中古时期官府藏书文献的流通是单向终止的,除非遭遇战争、政治等破坏因素,藏书楼就是官府藏书流通路线的终点。静止在书架上的藏书只是一种物品,官府藏书“藏大于用”的本质,导致社会文献进入官藏书库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知识载体的内涵,成为一种陈列与象征,用于政治教化与文化彰显。流通中的文献才能发挥媒介作用,封闭的藏书楼禁锢了载体也禁锢了知识,“一本真正的书包涵了关于这本书为何出现、如何被使用、被何人阅读、被何种机构收藏等等问题”[9],官府藏书文献并非真正的书籍。
唐代官府藏书抄写模式的数次变革,则如一阵风吹入了静止的书库,将藏书从库内移至书库外,从机构内移至机构外,从京城移至地方,抄写模式的嬗变给官府藏书带来了新的变量,人、抄写、流通等,新因素的加入是否使得官藏有了流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从官府藏书的流通者、流通途径来进行验证,进而分析抄写模式的变化如何影响流通者、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流通领域等问题。
2.1 流通者
在写本时代,文献的流通依赖于人,写本文化“表面上是以物质形态的写本为核心,真正的文本创制、知识传播、信仰实践的中心环节,却是书写者与阅读者”[10],其中书写者与阅读者可为一人,也可为不同的人,但他们的抄写与阅读行为均可看作文献的流通,一次文本的抄写复制,一次文本吟诵阅读,都可以算作复本的产生,人的因素与文献流通相结合,成为文献流通者,发起并推动社会文献的流动与传播。
唐代官府藏书抄写模式的数次改易,逐渐使得更多的人、更多身份的人、更多地方的人接触到了朝廷“秘书”。首先是增置的书手岗位,数千人次流动,增加的书手是藏书最合法的接触者,也是最有可能的传抄者。唐代重书政策明晰,抄写任务繁重,对书手的选任与管理逐渐放松,书手不再限定在“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4]36范围,而是面向社会依据书法进行选拔,开元初弘文馆更是允许书手等吏员夜宿馆内,“及写供奉书人、搨书人,愿在内宿者,亦听之”[3]1115,书手成为某些家贫无书士子的上佳选择,贞元年间阳城“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8]3490;唐文宗时期藏书机构将“应抄”图书,分配给诸道地方官府抄写,“应”字应该是为了满足唐朝图书典藏制度而应该抄写的副本、贮本,地方官府应该在获得正本的前提上进行协作抄写,藏书从中央出游地方,经过诸道各地官府书手抄写之后,与副本一起回归书库。多次抄写模式的变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官府藏书,它不再静止在书架上,而成为可观可触可抄的知识载体了。
2.2 流通途径
官方藏书抄写模式的嬗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了藏书,不同的人面对文献的心理和选择不同,而“书籍在不同脉络需求下,有大于‘一’的使用方法”[11],有幸接触到唐代官藏的人,有潜心钻研遍阅藏书者,有私下抄写偷偷带出者,不同的需求所引起的阅读和抄写行为都可算作藏书的复制,不过前者复制在人体中,后者书写在载体上,他们通过两种途径带着藏书文献进入到流通领域。
2.2.1 “记忆本”参与流通
自古以来,人体记忆是信息传播的途径之一,尤其是知识的普遍载体出现之前,人们依赖对文献的记忆来进行文本流通,背诵是中国士子的基本功,如伏生九十尚能诵《尚书》。简帛、纸张载体出现后,文献记忆并没有被取代,反而更加强调记诵能力,尤其在汉唐人物史传中对记忆文献能力的强调,如昭明太子“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记诵文献与抄写文献类似,同样采用字数和纸张来计量,“文献记忆在当时更多地是被从文献而不是记忆的角度来认识的,它的产物作为一种虚拟书籍,与实体书籍并无本质区别”[12],即所谓的“记忆本”,一次阅读就是为书籍制作一个存储在人体中的复本,与抄本相比,记忆本依托人体为载体,完成知识的复制与传播,此类流通方式尤其适合于官府藏书的流通,其原因是显而易见,官府藏书归属于君王,君王是唯一能公开传播藏书文献的身份,官府藏书的流通势必是私下的秘密的,而人的记忆则是最佳承载体。
中唐时期阳城求为集贤院书手,潜心阅读官书六年,无所不通,一举得中进士,后隐居中条山,远近士子慕其才名,在其门下求学,集贤院的藏书经由阳城进行隐形的知识转移,文献通过“记忆体”途径传播。阳城为读书求为藏书机构吏员,被人传为美谈,历史上也有其它“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例子,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始览王充《论衡》”[13],在此之前段成式已然任职秘省,“秘阁书籍,披阅皆遍”[8]2976,后撰成《酉阳杂俎》三十卷,“书名“酉阳”,乃取梁元帝之赋‘访酉阳之逸典’,以示取材秘珍”[14],因此鲁迅先生称其“或录秘书,或叙异事,……所涉既广,遂多珍异”[15],秘阁集贤藏书经历了段成式的“记忆本”而后成为新的文献进行了流通。唐代官藏抄写方式的变化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官方秘藏,他们“充分利用一切接触到书籍的机会——无论是借、蹭、看、听——获得一个记忆本。每一个背诵者都是肉体的书籍、肉体的图书馆,不仅如此,他们还是行走的书簏,通过他们,书籍可以再次传播出去,甚至能传播给无法阅读的人。[12]”需要特别指出,部分藏书接触者选择制作“记忆本”,也是纸笔抄写会受到经济、政治的因素的影响,不便进行。
2.2.2 写本参与流通
官府藏书的建设或许由少数人(君王与上层士大夫)来倡导和完成,但是藏书能参与到社会文献流通领域,应由下层士子来推动,所谓下层,“是政治上的而非文化上的”[16],他们因家世经济等原因,对文献的渴求远远超过官宦子弟,如萧颖士因不愿任职地方而请求韦述:“愿得秘书省一官,登蓬莱,阅典籍,冀三四年内,绝笔之秋,使孟浪之谈,一朝见信。[17]”颜真卿《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公讳沔,字若冲,博陵安平人。……公与江夏李邕友善,为校书郎时,引邕馆于秘阁之下,读书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18]”下层士子还包括基层官员,如藏书机构中校正官员,品秩低微,承担了校雠典藏等藏书事务,也会充任采书使前往地方,社会文献因此聚集也因此扩散,“他们(藏书官员)也会因为其足之所至,传播所持有的一些抄本”[19],另外中唐时期校正官员多在候选时入幕地方,也许会带着利用职位之便获得的藏书抄本一起流动,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宦游者会随身携带自己私藏就任地方,如敦煌文书P.3573《论语疏》残卷后钤有“宣谕使图书印”,学者怀疑该本“为内地写本,宣谕使携至敦煌者”[20],是否有史料明确证明藏书官员夹带私抄上任,不属于本文的关注重点,但不可否认,这是藏书借职官之手进入流通领域的途径之一。
更多身份的人借由大规模抄书活动接触藏书,这其中包括之前的“社会工书人”与非藏书官员,抄书人员可能会因为经济因素、作业条件等原因,无暇制作副本,只有部分有心之士刻意记忆,而非藏书官员会通过抄写,形成写本流通。开元年间秘书监马怀素奏引栎阳尉韦述等人入省校勘图书,“(韦)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8]2156,根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开元二年七月)丙午,昭文馆学士柳冲、太子左庶子刘子玄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上之。[8]116”《姓族系录》成书后直接入库,并未在社会流通,开元五年韦述手抄此书带出秘书省,是该文献的第一次进入流通领域。抄录官府藏书而后偷偷带出的“窃书”行为,韦述之作为可算孤例,而唐朝其他人,如裴孝源、李邕、刘知己等,机缘巧合进入藏书机构,后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知识通过记忆与“再生产”,藏书文献内蕴含的知识通过新的知识集合开始流动,由此说明写本时代,官藏文献的流通途径更多依赖于记忆与创作,而非传抄,这恰巧是写本时期文献传播的基本特点。
3 唐代官藏文献生产模式嬗变的传播意义
“一定的环境因素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影响、规定、制约着人类的传播活动”[21],唐宋之际文献传播特性改变,由精英媒介向大众媒介发展,文化、阶层、技术等诸多环境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在出版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科技进步对出版进步的作用与影响”[22],也需要关注文化领域变化对出版史的推动,其中唐代官府藏书生产模式作为藏书研究的一部分,其模式嬗变对文献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产生了影响。
3.1 官藏生产模式改变影响下的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即从事文献传播活动的机构与个人。汉唐写本时代,文献生产方式是读者自写或雇人抄写,传播模式是点对点的线段状形式,原因在于文献阅读者人数较少且阶层分布集中,社会传播的知识内容有限,手工抄写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图书生产与发行市场尚未完善。虽然六朝时期纸张普及、知识生产丰富、传播途径拓展等因素促进了文献传播主体从上层精英阶层向一般的寒门阶层扩散,如谢灵运的诗作传至京城地方,“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23],但“书籍流通以读者传写为主”[22],书籍的传播主体仍然是读者。
唐代官藏生产模式的改变,将社会工书人、地方官府写手、非藏书职官等不同身份的人引入藏书复制环节,将有限的传播主体扩展为无限,将受到身份限制地域限制的抄书人,逐渐扩展为身份自由地域限定的抄写者,最后发展为地域不限身份多样的书手,藏书生产参与者越来越不可控,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其传播范围也就越来越广阔,使得官方藏书通过生产者身份地域的拓展打破了文献传播的途径限制与空间禁锢。
3.2 文献生产模式改变影响下的传播内容
文献作为一种媒介,所传播的属于知识、信息。写本时代依靠个人力量抄写收集的文献有限,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完成文献最大聚集,隋炀帝对西京藏书三十七万卷挑拣后,尚“得正御本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七千余卷”[24],与之相对应,隋唐私人藏书破万卷者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因此汉唐官府藏书成为社会最大的图书信息源,但这些“图书深藏在宫中,除管理人员和极少数官员能看到外,几乎他人不能问津”[25],不进入社会传播领域,造成了“先圣人之书不传,则后世无以见其迹”[26]的典藏悲剧。虽然史料中不乏入秘阁读书者,但需达官推荐、任职其中、私下进入等方式,官方书库仍然是关闭的,只有在君臣的允许下,才能进行文献抄写与传播,如赐书,“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2]297;如定本颁布,贞观年间,唐太宗诏令抄写《遗教经》传播天下:“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17]41”如国际交流,向新罗、渤海国、吐蕃等政权传播藏书,仅此数种可能性,藏书才可能抄写传播,即使如此,尚有臣子认为藏书应该典藏在书库内,而“弃在夷狄”[3]667或他处,官方藏书并不认同传播,而是重在典藏。
唐代官藏文献生产模式的嬗变,“结构内+机构外”、“中央+地方”两种抄写模式,让藏书走出库房,进入抄写人员的家里,进入地方官府的抄书场所,打破了官藏文本传播的空间禁锢,使得大量的文本进入到社会传播领域,丰富当时社会流通文献的传播内容。
3.3 文献生产模式改变影响下的传播媒介
正所谓“文化之源,系于书契”[27],写本时代文献作为文明延续和文本复制的载体,承担社会遗产传承功能[28],作为书籍传播的作用反而并不凸显,雕版印刷技术普及以后,文献的传播作用和功能得以强调,“书面文化传播时代下的图书不仅是文化传播媒介,且具备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娱乐功能,成为当时的主导媒介。”[29]在这两者之间,唐代官藏生产模式产生转变,而行为之前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朝廷对官府藏书的“秘不示人”观念在摇摆,虽时有政策严格管理,但总体上,人们对于各种形式利用藏书总持有宽容赞赏的态度,甚至写入史书流传后世。“秘藏”观念的淡化,是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引起官府藏书的生产从密闭转向开放,从单一机构职能转变为国家文化事业,从中央走向地方,而这一书籍在空间传播的便利性更深远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时代,图书的媒介空间偏向特性成为主导,使得图书作为一种媒介不仅仅传播了知识、文化,还满足了社会娱乐需求并产生了经济效益,正如白居易诗歌“至於缮写模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盗窃名姓,苟求自售”[30],书籍在流通中逐渐彰显了商品性质,促成了图书贸易的兴盛。
4 唐代官藏图书生产模式嬗变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认为:“书籍的历史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社会等级的历史。”[31]唐代官藏文献生产模式扇动了“蝴蝶的翅膀”,汇入唐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中。在官藏生产模式的转变中,朝廷作为传播活动“把关人”,在生产、制作与传播图书信息与知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逐渐从严格控制到条件输出,将藏书生产过程逐步开放,引入非官方人员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使得官府藏书走入大众传播领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首先书籍的影响继续扩大,社会上可读之书增多,能读之人增多,“当社会上读书的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那种手工抄书的生产方式己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时,人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求一种快速生产书籍的方法,这就促使了印刷术的发明”[32],书籍与阅读者的规模壮大为文学等创作领域奠定了知识生产基础,越来越多的创作主体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其次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公私藏书,宋代馆阁藏书一改之前朝代严格封闭的做法,开始向部分官员及其子弟开放借阅;为私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中后期私人藏书家破万卷者超过20余人,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比五代以前藏书家总数还多,约占历代(先秦至宋)藏书家总数的64%,图书事业“眈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凡国监、官廨、公库、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