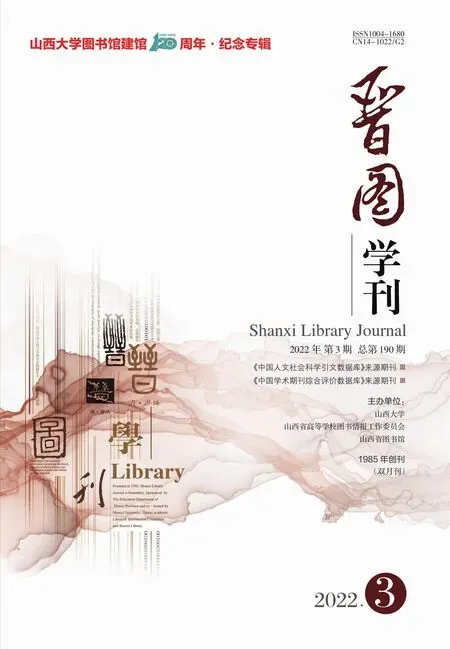“类序”的起源
夏南强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 “类”“序”二字的本义和引申义
“类序”是指书目和类书中对一类具有相同或相近性质意义的文献或知识的“序说”,包括其起源性质的揭示、发展演变的叙述、学术流派的剖析、内容主旨的讲解或评述等等。
追溯“类序”的起源,得从“类”“序”二字的定义说起。
迄今发现的已释读甲骨文、金文中,无“类”字。《说文解字》收入了两个“类”字。卷一“示”部:“禷,以事类祭天神。从示,类声。”卷十“犬”部:“類,种类相似,惟犬为甚,从犬,类声。”两个“类”字,一个从示,一个从犬,哪一个为“类”的本字呢?
查考先秦文献中有关“类”字的记述,《周礼》中较多,且大都在掌管礼仪的《春官》篇章。如: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1]252-257
《肆师》:“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1]321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1]331
《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襘、禜之祝号。”[1]33-34
从这些记述中不难看出,“类”是与祭祀有关的古代礼仪。吕友仁先生认为:“(类)是一种祭祀,因为这种祭祀的礼数比正常之礼略有精简,只是类似于正常之礼,故名。”[1]254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示部“禷”字条引述了钱大昭关于先秦文献中“类祭”之事的归纳讲解:
“类祭之事,见于经典者有五。《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祷祈之类也;《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巡守之类也;《大雅·皇矣》:‘是类是禡’。《释天》:‘禷,师祭也’。行师之类也;《肆师》:‘类造上帝’,战胜之类也;《舜典》:‘肆类于上帝’,摄位之类也。皆非常祭,依正礼而为之,故云以事类祭。”[2]10
上文中,钱大昭引用《周礼》《礼记》《诗经》《尚书》中的例句,说明了“类”是一种依照正礼施行的非常规的祭祀,且能应用于不同的国家行为和场合。桂馥接着还补充了许多文献中的材料,进一步证实了钱氏的观点。
“禷”字本义还可从字形的角度来考察。“禷”字从“示”,“示”字的本义,迄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从“示”之字,大都与祭祀有关,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禷”字右边的义符“米”“犬”“頁”(人头),则为当时社会常用的祭品,“禷”字本身就显示了与祭祀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禷”为“類”的本字,“類(类)”字的本义是国家因事临时依照正礼相关礼仪举行的祭祀天神仪式。“类”字的本义中,就包含有“类似”“相似”的意蕴。
“类”字定义引申为“一组具有相同或相似关系性质、结构性质、行为性质、意义性质的事物”,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我国先民在发明打造汉字的进程中,由最初的描述自然现象、自然物体的“初文”,发展到用“初文”作部首来表达具有某种相同性质的事物(如“日”字孳乳产生的日部,收有“早、时、昧、昭、旭、景、昏、暗、晚、旱”等字);《易·系辞》中“方以类聚,人以群分”[3]5的表述等,都是客观观察事物后对“类”知识的运用和认识。墨子则最先将“类”提高到逻辑的认识高度,为这一定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4]415
杀无罪的人,无论杀的少还是杀的多,是同一性质的错误。杀一个无罪的人就已经错了,何况是杀害众多无罪的人呢!墨子不仅站在道义的立场,更是站在学理的高度指出:公输盘“义不杀少而杀众”,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件事性质方面的错误。他认为,对同类事物的统一认识,就是“知类”,这是概念上的归纳判断。此后,墨子的学生和后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关于“类”概念的逻辑思想,把一类事物的不同个体具有相同的属性称为“类同”,把两事物不具有相同的属性称为“不类”。《墨子·经说上》:“有形同,类同也”。“有不同,不类也”。并且认为,“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发表言辞观点,必须要明晓和把握相同事物的属性,否则,就难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5]。
“序”字亦不见于已释读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序,东西墙也。从广,予声。”[2]6本义是指房屋堂前的东墙和西墙,引申为堂两旁的东西厢房。厢房是古人宴请宾客的处所,由此又引申出“按次序区分,排列”的意义。如《仪礼·乡饮酒礼》:“众宾序升,即席。”[6]99《诗经·大雅·行苇》:“序宾以贤。”[7]632都有“按次序区分,排列”的含义。“序”字被引申作为一种文体来命名,最早见于《易传·序卦》。它叙列了从屯、蒙到既济、未济六十四卦卦名,实即六十四个篇章的名目。《易传·序卦上》: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8]740
很明显,这段“序”文主要是分析论述六十四卦编排次序和其前后相承的缘由。据司马迁记述,“序卦”为孔子所作。后代相承认为,“序卦”为“序”这种文体的始祖。
2 “类序”产生的文化背景
2.1 文字的孳乳且运用于文献记载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注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9]1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肯定了摩尔根的看法,指出处于野蛮时代的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0]25因此,一般都认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时代的标志。“类序”产生的文化背景,当然也一定是以“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为前提的。殷商时期,是汉字大量产生和“繁殖”的时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造字方法都已形成,并用于汉字的“发明创造”。迄今发现的殷商文字有4 500余个之多,这些汉字主要用于占卜的记载。由于占卜所用的材料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文字刻于甲骨之上,故称之为甲骨文。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对诸如上天近日是否会下雨,农作物是否有好收成,打仗能否胜利,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一应事情,几乎都要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愿和事情的吉凶。占卜之后,将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应验情况等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这就产生了批量的有大量文字记载的甲骨文献。自此,中国先民不局限于器物的制造、使用与流传,还有了记载自己喜怒哀乐、言行举止的文献存世。可以说,殷商文字的大量产生和熟练运用,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文献空前涌现的先声,也奠定了中国《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元典形成的基础。
2.2 礼乐制度的制定及《诗》《书》《易》《礼》《乐》元典的形成
西周初期,礼乐制度的制定,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大里程碑。礼的发源极早,最初的礼,可能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6就是殷人率民而事鬼神祈福事实的反映。但西周“制礼”与殷商不同的是,在安排祭祀秩序需要的前提下,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制定了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在寓“义”于“礼”,使“礼”显示出合乎人情道义的同时,从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乐”则是配合各种等级的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都要符合相应的“礼”的规格。“礼”的行为是“别”,即所谓“尊尊”,强调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之区别;“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使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和睦相处。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11]456。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以乐为协调社会秩序的纲纪,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礼乐制度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直接源头,也是儒家尊崇的《诗》《书》《礼》《乐》等元典的催生剂。
现存《诗经》中,至少有三篇《商颂》,是殷人创作的反映祭祀祖宗神的郊庙歌辞,它们是《诗经》中最早的作品。与《商颂》一脉相承,《诗经》中的西周诗歌,大多是为了配合典礼仪式用乐需要而创作的。“它们或者用于敬天祭祖的礼仪,通过歌颂先公先王的功德来祈取福佑,如《周颂·天作》《大雅·绵》等;或用于嗣王的登基奠礼,表达承继祖考之道、敬慎国事的决心,如《周颂·访落》《敬之》。或者用于明君臣之义、洽兄弟之情的燕射仪式,通过渲染宾主和乐的气氛来亲和宗族、抚慰诸侯,如《周颂·我客》《大雅·行苇》。现存于《周颂》中的《武》《赉》《桓》等篇,曾是被视为三代之乐代表作的《大武乐》的配乐歌辞。而《大武乐》,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果,以歌舞的形式重现了周文王、武王开国平天下的历史过程,告功于神明,垂鉴于子孙。无论是典礼仪式中的乐舞还是歌诗,带给观者与听众的,都不是艺术与文学的审美体验,而是典礼仪式所特有的庄严与肃穆。即使是合和宗族、亲洽兄弟的燕射歌乐,给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仍然是温情脉脉、‘和乐且湛’的歌乐背后丝毫不可僭越、违背的礼制规定。”[12]但礼乐文化催生下的王室贵族诗歌,其数量大大增加,类别已经形成,应用场合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诗歌的内容更加多样,表现形式也更加多姿多彩,为《诗经》的早期成书奠定了基础。《史记·周本纪》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征犬戎引“周文公之颂”;同篇芮良夫谏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引《颂》和《大雅》,可见西周时《诗经》已有“颂”“雅”的分类。马银琴先生关于周康王“定乐歌”时出现了以《颂》《雅》分立形式编纂的《诗经》乐歌文本的观点;周宣王时代就有了以《诗》《小雅》《大雅》《颂》分立形式存在的《诗经》诗文本,周平王时期《诗经》结集的观点,应该是可信的[13]135-144,232-238,291-295。
随着礼乐文化制度的制定,国家的政令、帝王的言行记录等文献资料也日渐增多——它们就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资料汇编《书》(后人名为《尚书》)的由来。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为孔子所编纂。《左传》中引用其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并且考定《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文献,《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东周春秋时文献,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时编写的有关古史的文献,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则是编造的伪书(已混编入后代《尚书》)。《尚书》100篇的说法,今已无法印证。但先秦篇章绝对不只二十多篇,已为出土文献所证实。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以下简称为“清华简”),就发现了今本《尚书》未收的《厚父》《封许之命》等六篇佚文,其中《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许国是周代的诸侯国之一。受封的许国第一代国君名为“吕丁”。根据《封许之命》的记载,吕丁在周文王时已经任职,后又参与了伐纣的战事,立有大功,因此获得封地。《封许之命》进一步证明了西周时期有下达册封诸侯文件的传统。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室。周初的分封对象有同姓宗室子弟,有异姓功臣,还有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史传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14]90每一个封君受封的有土地和人口,即所谓“授民授疆土”。封君则要对周王室尽纳贡、守边等义务。现存《尚书·周书》中,类似文献仅存《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二篇。揆之常理,应该还有“鲁、齐、晋、卫……之命”等数十篇“命”类文献曾经存在。又如现存《书》序:“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说命》经秦火不存于世(《伪古文尚书》收《说命》三篇系伪造)。清华简却收有《傅说之命》(即《说命》)三篇,可见《书》序作者的确见过《说命》原文。《尚书》100篇的说法,不一定无根据。其所收各类文献,在两周一定很多,也应该有专门的存放之所。
《易经》成书于西周。传统说法是,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了卦辞和爻辞。但伏羲画卦,乃远古传说,难以置信。“文王拘而演《周易》”,只是司马迁在写给友人书信《报任安书》中的一家之言,现存《尚书·周书》,没有片言只字记载。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里考述了《易经》爻辞中所载史实,认为《易经》成书于周初。[15]996高亨先生也认为:“《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其中无武王以后事,可证此书成于周初矣。至于最后撰人为谁,则不可知。后儒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与此书之内容无所抵触。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16]13但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如宋祚胤先生从《周易》所记载的史实、所运用的术语、所反映的思想等方面辩驳,否定成书周初,认为应该是在“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军不归”(韩愈诗)之后的西周末年[17]15-18。《易经》成书的具体年代,虽难定论,但从卦辞、爻辞本身内容考察,至少在西周末年已成书,学术界则无异议。《易经》非礼乐文化的产物,其实质是一部利用占卜的符号图形体系来阐发思想的哲学著作。以现在的观点言之,其理论前提属唯心主义,但它对经文的解释却是以对客观世界及其变化的观察为依据,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因而包含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它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西周时期,是否就有《礼》《乐》典籍的存在,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现存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原名《周官》,流传无绪,汉初才现于世。刘歆整理典籍,为免与《尚书·周官》篇混淆,故改称《周礼》。今人考证,现存《周礼》大抵成书于战国时期,内容以周代官制为核心,汇编了官制职掌及职责方面的资料。早于《周礼》的《仪礼》,原名《礼》,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唐代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用《仪礼》正式取代原名,沿用至今。南宋郑樵《六经奥论》“仪礼辨”条曰:“古人造士以《礼》《乐》与《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18]348则先秦培养人才所用教材以及儒家推重的六经所说的《礼》,都是指《仪礼》。周人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种仪制,其中除吉礼为事神礼仪外,其它四种均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这五种仪制又被分为“冠、婚、丧、祭、朝、聘、乡饮酒、射”等礼事,各种礼事又各有具体的仪项和繁缛的仪节,这些正是《仪礼》的主要内容。汉代古文经学家说《仪礼》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推重司马迁的记载,认同作者为孔子。沈文倬先生研究认为,《仪礼》是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孔子58岁以前,没有此书。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礼,孔子传授《士丧礼》,《士丧礼》由此成书,是《仪礼》撰写的上限。[19]24-25我们认为,沈氏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也失之偏颇。《周礼》《仪礼》中所载官制礼仪,周时当有相应的文献记载。孔门弟子及后学撰述,必有所本。否则,官制礼仪是无法凭空臆测编造的。前修未备,后出转精。经过孔子及其弟子和后学整理编撰的《周礼》《仪礼》《礼记》流行之后,以前的典籍也就渐渐失去市场,加上秦火和书禁,就失传遗佚或毁灭了。此外,西周时期的“乐”,包括诗、歌、舞三部分内容。《颂》《雅》是诗文本,歌、舞是表现形式,乐器则是演奏工具。歌、舞、乐器演奏,是属于“乐技”的范畴;由“乐技”表演引申出的道德、伦理观念、心灵感受、审美情趣则是“乐”的内涵,也就是“乐义”所在。“乐义”的挖掘和撰述,没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是不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20]1712可见一般的乐官,不可能撰写出被后人尊为经的含有“乐义”的《乐》典。史载汉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师窦公所献《乐书》,却不过是《周礼·大宗伯》中专载音乐典制的“大司乐”篇章而已。《乐》经,是否西周就已经有元典存在?抑或《周礼·大宗伯》中“大司乐”篇章就是西周元典?只能是存疑了。
3 “类序”起源于孔子整理六经与聚徒讲学,《孔子诗论》是创始之作
“类序”的起源,与孔子的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聚徒教学密切相关。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有两次整理六经的活动。第一次是鲁定公五年,“陪臣执国政”,鲁国最大贵族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囚禁主人,季桓子在胁迫下屈服,与之订立盟誓,交出权柄。阳虎执掌鲁国大权,为所欲为。阳虎之外,季桓子等贵族大都骄奢放纵,凌驾于鲁国国君之上。鲁国大夫也纷纷越轨,偏离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第二次是孔子晚年周游列国不遇,鲁哀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绝意仕途,专门从事整理六经和教学活动。《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招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1]2322-2324,2340
上述记载可见,《诗经》《尚书》《礼》《乐》《周易》等文献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取舍与评说,《春秋》则是孔子依据旧有史记而改编。孔子是将传统的贵族教育转向普通民众教育的第一人,也是教学大师。《史记·孔子世家》[16]2322-2324,2340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虽然“弟子三千”不一定能坐实,但学生人数众多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多学生学习,首先就要解决教材的问题。传统的贵族子弟教育教材,也是重视诗、史、礼、乐等典籍教育的。如公元前590年,楚申叔时谈教导太子:“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置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2]485-486可见,传统的贵族子弟教育是多方面的。孔子认为,平民教育,培养人的性格品行、社会交往能力更为重要。而《诗》《书》《乐》《易》《礼》《春秋》在这些方面各有所长: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1]564
因此,整理六经,用六经施教,是最合适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对某类文献的串述、主旨讲解、比较分析——“类序”(后人也称“大序”)和对单篇单部作品内容主题的评述——“小序”,就产生了。虽然,最早的“类序”出自孔子的教学口授,并非孔子撰写的文本,但学生耳提面命受业后的记载成文,自然丝毫不会影响孔子是“类序”这种文体的创造者。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文献,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书证,更证明了孔子评述经典是“类序”的直接源头。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性自命出》是一部儒家佚籍,其中有对《诗》《书》《礼》《乐》的评说文字,也谈到孔子对这几部经典的整理研究和用来施教情况: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宜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23]179
(注:引用时参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性情论》对个别文字作了更改。)
《诗》《书》《礼》《乐》四部经典的产生,都是人的有意创作。孔子分别排比其类别综合论述,考察其先后次序而从逆向和顺向编排整理,体会其意蕴而删节修饰,理解其情感内蕴而出入其中,然后用来施教。教育,是使普通人植根道德于心中的方式和方法——其说是否有据?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回一批楚简,2001年整理出版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收有《性情论》一书,内容文字与《性自命出》大体相同。而上博楚简中的另一书《孔子诗论》,则是《性自命出》所记述孔子整理经典和施教的注脚,也是最早“类序”出自孔子的最好证明。《孔子诗论》现存29简,1 006字。以今天的观念视之,可定义为我国最早的“类序”,殆无疑义:一是有总论《诗》旨以及颂、大雅、小雅、国风各类诗诗旨的论述文字;二是对《诗》中各篇内容主旨的比照分析文字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余篇章也大多是对具体作品主旨的剖析。前者主要集中在前五简。为明晰起见,现删除因文字残缺而文意不全的部分,迻录如下: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讼》,坪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寻,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诗》,其犹旁门欤?残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罴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又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蘖。[24]14-17
(注:引用时参考各家考释略有取舍)
在孔子“诗歌不要隐藏志向,音乐不要隐藏情感,文章不要隐藏意旨”观点的“引领”下,“类序”对《颂》《大雅》《小雅》《国风》四类诗的主旨作了高度的概括:《颂》,歌颂文王武王平成天下之德,多出自文王武王后人之手,其音乐安和而缓慢,其歌声悠扬而绵长,其思绪深邃而远旷;《大雅》,歌颂王公盛德……;《小雅》多歌咏人生苦难,抒发怨愤的情感,反映政治衰败,叹息为政者少德;《国风》普纳风物,可观民情风俗。广泛采集了材料,语言富有文采,音乐优美动听……《诗》,就像四通之门吧?可以周知天下之事。执政者若残民以逞,构怨于民,民众内心会如何呢?《国风》就是民众的反馈。民众劳苦倦极的时候,上下不和的时候,民众的内心是如何呢?那就看看《国风》吧!成功者怎么样呢?《颂》就是歌颂他们的啊!《清庙》,歌颂文王之德,文王之德,是最高的典范。崇敬宗庙的祭祀典礼,作为执政的根本;秉持文王的美德,作为行政的苗芽……
虽然文字的残缺,影响了我们对这段“类序”内容做更深入的挖掘探讨,但其大意还是可以理解的。其对四类诗旨意的高度归纳概括,十分准确到位。
对《诗》中各篇内容主旨的比照分析,集中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简。兹举第八简如下:
《十月》善譬言。《雨亡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24]20
第八简列举了《小雅》中的8篇作品。《十月》《雨亡政》《节南山》都是说执政者德政的衰败。但《十月》善于訾议讽刺之言。《小旻》主旨是批评朝政公卿言不由衷。《小宛》提倡衰政时自保,其言不恶,但缺少仁心。《小弁》《巧言》则都是言谗人害政的作品。8篇作品除《伐木》评述残缺外,其余作品内容是相近的,但各篇诗歌的主旨却又不同。“类序”作者将它们放到一起点评,分析不同的特点,学生便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孔子诗论》是否孔子所作?学术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它是孔子授《诗》的记录。王齐洲先生将《孔子诗论》中评论的作品与传世文献所载孔子所论诗作了比较:如《甘棠》篇,观点完全一致,仅有字句的微小差别。《蓼莪》《节南山》二篇,观点几乎完全相同。《木瓜》《蟋蟀》二篇,只是侧重点不同,论诗基本立场相同,等等。其结论是:全书命名《孔子诗论》是合适的[25]48-53。笔者基本认同他们的看法。将著作权划归孔子,实至名归。首先,竹简中除了多处标明“孔子曰”之外,其余文字也并不一定不是出于孔子之口。通篇文献口语气息十分明显,就像《论语》一样,颇像受业者经过整理后的笔记。其次,据专家论证,《性自命出》《孔子诗论》都是出自战国前期子思学派的作品或传承,二书时代相近。而陈桐生先生根据科学仪器的检测结论和史实推论,郭店楚墓下葬时间应该在在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26]90,如果将《性自命出》《孔子诗论》等典籍的产生定在此前50年,则离孔子在世仅100多年时间。孔子教学,名扬天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弟子和再传弟子众多,孔门师承授受,有绪可寻。早期文献传承,不可能出现断层。虽然《孔子诗论》不会像现代录音机一样,全录自孔子的口头讲授,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们也许要对讲授内容和文字加以润色修饰,甚至增添补充,但主要内容出自孔子,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当然,笔者更赞成参考姜广辉先生的建议[27-29],认为将《孔子诗论》改为《孔子诗序》,更能“名副其实”。
4 “类序”问世的文化意义
4.1 开创了文献研究评论的先河
“类序”产生以前,我国文献的积淀,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载体的不同来看,可分为甲骨档案文献;青铜器物铭文文献;竹简帛书文献,等等。从文献内容区分,则可分为王公贵族的言行记录;历史大事发生、进展、结束过程的记述;官制、典章、礼仪、乐制的记载;歌功颂德、讽刺时政腐败、抒发苦闷、反映民生苦难的诗歌;诸子百家的语录和政论(如《论语》《老子》),等等。它们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见证,也是中国先民社会行为、理性思考、情感抒发的结晶。如何学习这些文献,传承这些文献,利用这些文献,需要专门的深入研究,爬梳剔抉,披沙拣金,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给学生学习指导和研究指引,更要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对单篇文献内涵精髓的发掘不易,对一部著作文献内涵的发掘把握更是难上加难。《孔子诗论》“类序”的问世,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贡献,它开启了我国研究和评论整部文献著述的先例,是中国文献评论的鼻祖。今人研究,《尚书·尧典》成书于战国末期,其中“诗言志,歌咏言”的评论文字,最早也是战国末年纂入的,且并非对整部著作的评论。而《孔子诗论》对《诗经》既有分类作品的研究,也有相近题材不同作品主旨的研究和单篇作品主旨的研究,自成系统。且其研究和评论的方法,也给后人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如按文献内作品分类的不同(颂、大雅、小雅、风)研究概括作品的主旨;按文献内题材相近作品比较研究评论它们的不同主题(第八简);深入分析揭示单篇作品内蕴(如二十六简:“《邶·柏舟》,闷。《谷风》,背。《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闷,指郁闷的心情;背,指忘恩背德;有孝志,指抒发了感恩父母养育的孝亲之情;得而悔之,指抒发了有家室之累者的后悔心情),等等。这些研究分析和评论的方法,时至今天,都是科学实用而可资借鉴的文献评论方法。
4.2 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学术基础
我国目录工作的滥觞,是与殷商时代甲骨文献的产生和批量入藏息息相关的。王重民先生根据殷墟的发掘报告,分析出土的每个窖藏甲骨,都以一定的年代为限。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个帝王在位的时期为断限,只有极少数窖藏是几个帝王在位时期甲骨的混合。从而判断窖藏甲骨的入藏、陈列和参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续。他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甲骨的尾或背上,刻有‘入’‘示’和一些数码,就是主管保藏的人所做的记号,而这些记号和数码,应该都是与另外简单的单据或目录相适应的,这些都表示着目录参考工作的实际意义。”并认为,这“代表着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起源”[30]3,他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符号标示、登记入藏等目录工作,不是一门学问。目录工作不等同于目录学,其目录学产生在奴隶社会时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最早的中国目录学是以文献典籍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是一门研究文献的学问,它包括了对文献的整理排序、文献类别的区分与内容特点的彰显剖析、文献典籍内容主旨的挖掘评述,等等。后代的目录学研究,还包括了对文献作者的稽考介绍、文献中所体现的学术渊源、学术流派的揭示等内容。因此,中国目录学的诞生,是以“类序”的产生为标志的。《孔子诗论》的成书,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目录学的产生,开创了中国目录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可以说,中国目录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指引学习和研究的特点,使其开始就立足于学术的高地,担负有崇高的学术使命,具有实用的功能与功用。
4.3 创立了“序”类文体,对信息情感沟通文献传承流布发挥了重要功用
《汉书·艺文志》载:“《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20]1706孔子作百篇《书》序的说法,已无法证实。但孔子以《书》为教材,一些《书》序文字,出自孔子之口,应该是可信的。今存《尚书》二十多篇“序”,如:
《盘庚》:“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牧誓》:“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
《大禹谟》:“皋陶矢闕谟,禹成闕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康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31]479-534
从序文内容上看,大都是对作品写作背景的揭示,也就是“言其作意”,说明作品产生的由来;从序文内容揭示的方法看,既有对一篇作品写作背景的揭示,也有对多篇作品同一写作背景的揭示(如《大禹谟》《康诰》)。《书》序与《孔子诗论》哪个最早产生呢?我们认为,《孔子诗论》的产生,早于《书》序。《孔子诗论》中“论诗”,除了揭示作品内容外,还体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如:
第二十二简:……之。《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仪一氏”,是“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
第二十三简:……《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兔罝》其用人,则吾取……[24]34-35
第二十二简把《宛丘》等四首诗中的一些诗句拈出来,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喜好。还保留有春秋时期“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意味,或许是对孔子早期论诗的记述。第二十三简则对《鹿鸣》一诗三章主旨分别加以揭示,与全书内容大多是揭示单篇作品主旨不同。它间接说明,《孔子诗论》中的诗论,并非一时之作,是孔子早期说诗到晚期说诗资料的汇辑,其中不乏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修饰甚至补充资料。而《书》序体例整齐划一,大都“言其作意”,只着眼于揭示作品产生的背景,即使出自孔子之手,也一定是其晚期集中时间精力撰写之作。至于另一部“序”类作品——《易》传之一的《序卦》,是否出自孔子,亦难考定。但其论述六十四卦编排次序和其前后相承的意旨的做法,与《孔子诗论》是有些相近的。孔子自己说“晚而喜《易》”,即便为孔子所作,《序卦》也应该晚于《孔子诗论》中的许多说诗内容。抑或“实至名归”,先有此类文体的出现,后以“序”名加之欤?
《孔子诗论》[26]90作为最早面世的“类序”,是将“对一类具有相同或相近性质意义文献的‘序说’”,与对单篇文献内容的揭示结合在一起的。交叉渗透,互为补充。它是单种图书内容品评目录学揭示方法的典范,为后代综合性的私修目录学、史书目录学、官修目录学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借鉴。由此可见,成书于汉代的《毛诗序》;向歆父子私撰的《别录》《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唐代魏征等《隋书经籍志》;清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序”类文体的面世,则为人们评介文献内容、说明创作意图和背景、讲述文献内篇章结构编排次第的缘由,提供了一种可参考使用的“范式”。借助于这种文体,以及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借题发挥,我国历史上众多优秀的作者,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等。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卷中,浓墨重彩,艳丽夺目。对于文献读者来说,几千年来,目录学著述中的“序”类美文和各类著作中的“序”类美文,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许许多多文献作品本身以外的有关作者生平经历、写作背景、情感意趣;作品结构、体例、主旨等方面的信息,帮助了千千万万读者对文献作者和文献内容的深入了解。其对中国文化的信息情感沟通与文献的传承流布功用,也是足可彪炳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