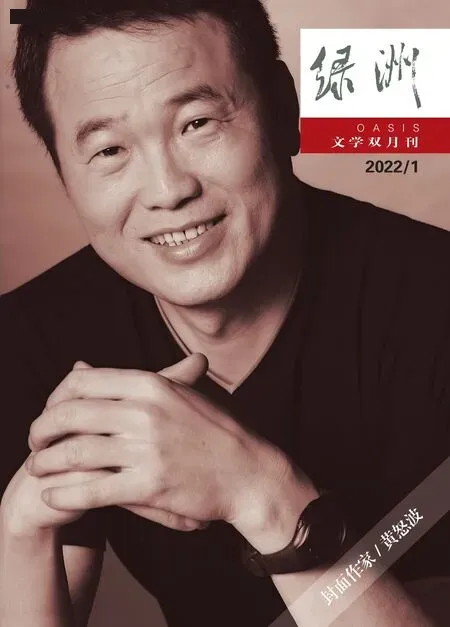蓦然回首
晓寒
1
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穿过广场,向着售票厅走去。头顶,石墨色的秋云一个劲地往下坠,压向火车站那栋矮塌塌的老房子,把墙壁和屋顶弄得灰蒙蒙的,像旧书堆里飘来的一声叹息。
售票廳里没几个人,如同一个冷火秋烟的土地庙。一个臀宽腰粗拖着两条辫子的女人正在买票,她把头挨近窗口,正在小声说着什么。
我快靠近窗前时,女人开始往回走,她走得很快,身子大幅度地晃着,一条辫梢差点甩到我的脸上。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在怪我挡了她的路,我装作没看见,继续往前走。要在以前,我说不定会和她吵起来,甚至动手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别说瞪我一眼,即使再出格一点,我也不会和她计较,我已经不想和任何人计较什么了。
窗口没有第二个人,我递上身份证,说:“往北,最小的终点站,尽快走。”那个脸色蜡黄长着雀斑的女人盯着我足足看了五秒,朝我翻了个白眼,然后低下头,双手在键盘上雨点般敲打起来,不知是要表达她的烦躁还是愤怒。我相信我已经说得够明白,她也听得够清楚了,不过我还是笔直地站着,做好了她问我一点什么的准备,结果她一个字也没问。
这样很好。我不想说多余的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个人一辈子说多少话,是命运决定了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觉得说话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254块5。”
她的声音短促,坚硬,像是刚从冬天的冷水里捞上来的,冒着刀剑般的寒气,不过我不在乎。我没有回话,把钱递过去,她把票和找零从铁栅栏下推到我面前,然后迅速地转过身去,拿起手机当镜子照,似乎想看看脸上是不是又长出了新的雀斑。
我把目光收回到票面上,终点站叫阿达尔火车站。看到这个站名,我几乎有种想欢呼的冲动。冥冥中,我冒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偏远的小站,像是来自我身体的一个声音,一刻不停在召唤着我,只是在此之前我没有在意。
进站台时,我有些紧张,生怕走错了地方。跟着一长串人连走带跑,幸好没出什么岔子。
刚站好把气喘匀,便听到长长的汽笛声飘过站台,很快随着秋风消散在荒凉的天空。
火车准时出发,一上车,我身边的人就忙着往行李架上放箱子和背包,动作干脆利落,像是有人要抢他们的东西似的。我钥匙都没带,唯一的东西就是手机和银行卡,省了这个麻烦。趁他们放东西的档儿,我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房子和昨天没有什么区别,如一些年深月久的集装箱暗沉沉地码在那里,看起来摇摇欲坠,那是打发了我大半辈子时光的地方。
我在那些街街巷巷里,从少年走到青年、中年,再到现在两鬓飞雪。时间是一只闻到了血腥的豹子,铆足了劲往前飞奔,一眨眼就没了影儿,以往那些点点滴滴,像是我昨天晚上梦中的片断。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最后一眼打量这座老城,不过,我的心里很平静,我告诉自己,并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悲伤,有时候,告别只是一场开始。
火车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快得像要飞起来。老城影影绰绰向后退去,一会,就不知被呼啸的风甩到了哪个角落。飞奔而来的是陌生的山峦和村庄,各式各样的房子,我来不及看清它们的面容,就像那些弃我而去的昨天。
困意涌了上来,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三年前,我就这样了。只要一闲下来,困意就会把我整个人攻陷。
有时候,我坐在店子里翻一本书,眼前突然恍惚起来,一会,就不知道身处何处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声音传来,那是一个孩子的声音:“爷爷,这本书多少钱?”我一个激灵醒来,才发觉我正坐在店子里的柜台前。
而夜里两三点的时候,我又没了睡意,往往会突然醒来,然后很久都睡不着。听着外面街道上车子呼啸而过,半大的孩子在唱一首怪腔怪调的歌,醉酒的男人疯狂地咒骂着什么,还有楼下一对年轻夫妻的争吵,“砰”的一声,打碎一个杯子,也可能是一个盆子。这些东西破坏了我积累的经验,原来深夜并非一片死寂。
早晨去店子里的时候,路像是被谁突然拉长了,一双脚虽然不像木头那样坚硬,但总感到没有踩牢、踩实,很别扭。像是农夫突然感到土地不再像昨天那样柔软,又像是一只鸟来到了极寒的冬天,翅膀变得越来越坚硬。
——狗日的,这日子真不像从前了。
记得那时候,雪粒儿总是问我:“爸爸,你怎么不困呢?”
我摸着雪粒儿的头说:“爸爸要给雪粒儿做早餐,洗衣服,傍晚还要来幼儿园接雪粒儿回家,我困了,雪粒儿怎么办呢?”
五岁的雪粒儿不再说话,依偎在我身边,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王雪梦,对于这一点,我从来不敢问她。
王雪梦就是那年离家而去的,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她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她说,要和我一起开家书店,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她还说,等有钱了,要买台房车,和我一起去海边看夕阳,去大草原上看星星,去九寨沟看彩色的水,总之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对她的话,我深信不疑。几经张罗,在杜鹃路租了个门面开了家书店,名字叫闻道书屋。从书店出来,绕过一片草地,就是川城一中的正门,古老的木门,镶嵌在粉红色的墙体上,掩映在树荫里。这是川城最好的中学,有三四千学生,我的一些朋友都说这个地段选得好,是最适宜开书店的地方。
那时,我和王雪梦精心打理着书店,只要哪天卖了三四百块钱的书,就开心得像两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我们都怀揣着一个梦,等着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然后就会有房车,就会看到最美的夕阳和星星。
川城多风多雨。整个春天,都在风雨的统治之下。风雨里,街边的泡桐树开花了,铃铛状的花,似白似蓝,像一盏盏绚烂的灯,照亮了长长的街道。一大早,我和王雪梦穿过花香,踩着湿漉漉的街道去书店。她穿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一件白色的风衣,风掀起她长长的衣摆,露出两条修长的腿。傍晚,雨还没停,我和她共撑一把伞,搂着她柔软的腰,带着嘀嘀嗒嗒的雨声回家。
那段多风多雨的日子,是我人生长河里一朵弥足珍贵的浪花,闪烁着难以描述的光芒,时常开在我午夜的梦里,让我从惆怅和温暖中醒来。我不知道,王雪梦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五年的时间,生意并没有起色,还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期间,雪粒儿出生,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王雪梦的耐心很快被耗光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什么东西都没带,跟着书店对面开花店的那个人跑了。
雪粒儿曾经问过我妈妈去哪里了,我把她抱在膝盖上,告诉她,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赚够很多的钱就会回来,给雪粒儿买漂亮的裙子,好看的娃娃。从表情可以断定,对这样了无新意的谎言,雪粒儿深信不疑——唉,她太小了。面对她清澈的目光,我觉得我不是她的父亲,而是一个可耻的骗子。
或许是雪粒儿看到了我眼角的泪光,她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哭了呀?”我说:“爸爸没哭。爸爸这么大的人,怎么会哭呢?”她伸出小手为我擦了下眼睛,从此再没问过妈妈的事情。
站在我的角度,我理解王雪梦的决定,她想过她还没过上的更好的日子,这没有错,但换到雪粒儿的角度,我永远都无法原谅她。
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被定格,每天要做的就是那么几件事情。早上起来做早餐,守着雪粒儿吃完早餐,把她送到幼儿园。然后去书店,傍晚去幼儿园把雪粒儿接回家,做晚餐,再陪雪粒儿做作业,给她讲故事,哄她睡觉。
我逐渐陷入一个人的沉默。不叹息旧的一天逝去,也不期待新的一天到来。当然,我的天空照旧晴朗,雪粒儿是我唯一的太阳。
火车在穿过一条隧道,霍霍的回声,助长了我的睡意,终于头一歪,睡着了。
2
醒来,已是傍晚,火车停在一片开阔地里。广播里说,这是临时停车。
外面开始下起了小雨,沙沙地响着,两边的油桐叶上悬着一滴滴雨珠,湿漉漉的金黄,寥落,冷寂,仿佛晚秋在宣泄着某种郁结的情绪。
对面的一对情侣紧紧依偎着,男孩把手搭在女孩的肩上,女孩把手揽在男孩的腰上,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长久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像是宣告一场离别即将到来。
我边上坐着个留着长胡子的男人,毛发浓密的腿上放着台索尼相机,上车时就这样放着,看来,那台相机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他从脚下的包里摸出瓶歪脖子的酒,扭开盖子抿了两口,又咂了几下嘴巴,随后递过来,“要不要来两口?”我冲他摇了摇头。
“兄弟,这是个好东西,搞两口,什么瞌睡都没有了。”他哈哈大笑起来,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洞。
见我没有回话,他接着说:“真的,不骗你,我就靠这个提神。”他说完还是这样毫无顾忌地笑着。
原来这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个话唠。一旦被他缠上,就要了我的命了。我道了声谢,转头看向外边。
一棵油桐果啪地掉下来,摔成了几瓣。一只黄鼠狼从那头过来,眼睛嘀溜溜地转了一阵,大约没有找到它要找的东西,嗖地窜到另一边去了。隔这么远,我仿佛又闻到了油桐叶子的气息,温润,潮湿,那段日子,我和雪粒儿经常走过这样的油桐林,有时是清早,有时是夜晚,我骑着电动车,雪粒儿坐在后面,抓着我的衣摆。雪粒儿熟悉钢琴,就像我熟悉油桐林一样。
实际上,我并没想过要送雪粒儿去学钢琴,上一年级时有次带她去图书馆听讲座,中途正好插了半个小时的钢琴演奏。弹琴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白晰的脸庞,头发披着,笑的时候,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最先弹的是《水边的阿迪丽娜》。她修长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琴声像水一样在大厅里潺潺流淌,雪粒儿听得入了迷,直到琴声停下来后,都站着没动。
“爸爸,真好听,我也能弹吗?”雪粒儿小声问我。
能,雪粒儿肯定能。雪粒儿听了,笑起来,脸上也有两个小酒窝。那一刻,我决定带雪粒儿去学钢琴。
后来,这个弹钢琴的女子成了雪粒儿的老师,她姓罗,雪粒儿叫她蕊玲老师,我叫她罗老师。
她住在一所闲置的学校里,那里原先是川城师范,名声大得很,很多初中毕业的孩子为了进那扇大门挤破了脑壳。后来师范停办,改为川城职业学院,不久职业学院搬到省城,房子就一直空在那里,蔓草丛生,一天看不到几个人影,逐渐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如同一个没落的贵族,在备受冷落的时刻,只能用祖先的辉煌来慰藉心头的创痛。那地方偏僻,离我家远,我只好去买了辆电动车,尽管我很讨厌那冷冰冰的玩意。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骑上电动车,载着雪粒儿,沿着门前的清水江拐进正泰路,过立交桥,到达将军广场。广场一侧的苦楝树旁,塑着两匹马,前蹄高举,黄色的马鬃直直地竖起来,似乎在对着天空咴咴嘶鸣。我从马屁股后面被万年青簇拥的小路拐进校门,再往前走三百米,很意外地看到了一片油桐林,这是一片有了年头的林子,上百棵水桶粗的油桐树挺着腰杆,昂着头颅,亮出比巴掌还粗的叶子,在晨风中哗啦啦地唱着歌。树荫把天空遮住,下面阴沉沉的,堆着层厚厚的落叶,落叶上躺着些还没有腐烂的油桐果,经过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潮湿和霉腐的气味。
罗老师已站在宿舍门口等我们,穿着身旗袍,白色的底子,染着蓝色的水仙花,脸上笑盈盈的。身后的红砖墙没有粉刷,石灰线横平竖直,把整面墙分成细细的长条形的格子,干燥的土黄色,衬着油漆剥落的草绿色木窗,仿佛挣脱了时间的桎梏,仍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墙角种了株紫藤,顺着墙爬到了屋檐,花在刀把粗的藤条上横行霸道,像是翻涌着紫色的云朵。
雪粒儿把头凑到我耳边,小声说:“爸爸,真香啊,你闻到了吗?”
我把頭点得像鸡啄米,“是呀,真香,你多闻会儿。”
雪粒儿傻乎乎地笑着,连吸了几口气。
其实,我什么香也没闻到。
罗老师对雪粒儿好得没话说,她总是夸雪粒儿,雪粒儿真乖,雪粒儿弹得真好。雪粒儿好像天生对钢琴有一种感觉,从识谱、节奏、音区学起,几乎没遇上什么麻烦。
有天晚上,猴子打电话来。我看了下时间,已是十一点二十分,雪粒儿早睡了,我正靠在床头翻一本书,这成了我的习惯,我需要借助一本书对付漫漫长夜的荒凉。他的声音很大,放在枕边的手机被震得嗡嗡响。我猜他十有八九是酒喝过量了,似乎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从手机屏幕里飘散出来。
他说:“夫子,赶紧把你那破书店关了,来我这,我包你十万块钱一年。”
他很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想到会突然说起这事,我随口回了句:“你小子不是在说酒话逗我玩吧?”
猴子听了,嘿嘿地笑起来,没多喝,就半斤。那边“哐当”响了一下,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别跟我扯七扯八,给句话,你就说我是不是说酒话逗你的人?”
那时候,我已拿起手机站到了窗前,窗外月色凛冽,洒在街那边的清水江上,反射出雪白的光芒,说话的间隙,能听到涛声拍打着满江的月光。猴子就住在我家后面,小时候,我和他经常偷偷去江里洗冷水澡,江水清如冰棱,水底的温丝草绵密柔软,有些直起了腰杆,有些慑于水流的压力匍匐在河床,成群的鱼虾快如闪电,在水草间不知疲倦地追逐。猴子胆大,水性好,一个猛子扎下去,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对岸的王家洲,那边是大片的菜地和稻田,他跷起腿坐在田埂上,看着我慢吞吞地往对岸游。
上岸后,我们沿着田埂往下走,绕过一座小山,山上长满了樟树,树林中有一栋房子,欧式建筑,两层,尖顶,听老人说是清朝时一个什么传教士建的,最先做学校,后来改为拘留所,再后来就空在那里,成为老鼠和蟑螂的乐园。那地方我们玩腻了,已经失去了兴趣。我们要去山那头的李家湾,那是个河湾,正对着一片菜地,围着竹篱笆,进去的地方用废弃的门板挡着。很多人在河湾里钓鱼,随着钓竿的划动,“扑”的一声闷响,肥嘟嘟的鲤鱼,几尺长的草鱼落在河洲上,拼命地挣扎,弄得一身的枯草和淤泥。钓鱼人把鱼从鱼钩上取下来,随手丢进身边的木桶里,“啪”的一声,溅起高高的水花。清水江涨水的时候,鱼被洪水冲到湾里,不时会浮起头来,附近的人拿着捞网赶来捞鱼,人头攒动,热闹得很。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些打渔的人,站在小船上,撑着竹篙,慢悠悠地过去,船上随意地丢着鱼篓和绿色的丝网。我们最怕碰到一个古怪的老头,这个干瘦的老头,头发花白,颧骨高高突起,眼睛眯成一条线,看不清里面藏着什么。他和别人不一样,喜欢盘着腿坐在船上,将竹篙横搁在船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划着桨,另一只手把水烟筒举到嘴边,咕噜咕噜地吸着。一旦看到小孩子在江里玩水,便把船划过去,非得把那孩子弄上船送到岸边才罢休。
有一次我和猴子就很“不幸”碰上了。这时候,他像变了个人,浑身都是力气,小眼睛猛地睁开,射出两道光,把船飞快地划过来,嘴里骂骂咧咧的:“还不上来,淹死你这两个狗崽子。”见我们嬉皮笑脸,毫不理会,他生气了,操起船上的竹篙,在我们身边拼命地拍打,水花一浪一浪地溅来,弄得我和猴子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只好抓着他的竹篙,任由他像拔萝卜一样将我们扯上船去。他一声不吭地把我们送回岸边,大概怕我们再下水去,便把船停在那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举着那把金黄色的水烟筒,美滋滋地吸着。我们只好乖乖地回家去。
天热得像个火炉,我们躲开热辣辣的太阳,踩着树荫下的淤泥向前走,蝉在头顶执拗地嘶鸣,一声落下,另一声又不知疲惫地奋起。猴子耷拉着脑袋走在我前头,一只青蛙从身边的萱草里蹦到他脚下,他抬起脚恶狠狠地踩下去,“扑”的一声,没踩中,青蛙蹦到水里逃走了。他抹了把脸上的汗,骂了声:“该死的老东西。”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过去,江面上溅起几朵高高的水花。
初二那年夏天,江里涨水了,我和猴子拿着捞网去李家湾捞鱼,一路上满怀着希望,期待也像那些大人一样,能捞到被大水冲得晕头转向的几尺长的草鱼。天还很早,捞鱼的人都还没来,阴沉沉的天空下,浑浊的江水浩浩荡荡,一浪推着一浪,重重叠叠,翻起锯齿状的水花。突然,猴子一脚没踩牢,“扑通”一声掉进了江里,他拼命地挣扎,水流比想象的快多了,他好像突然失去了水性,像是一条绝望的鱼,任由浪涛裹挟着向下游奔去。我吓坏了,情急之中扛起菜地里那块黑漆漆的门板跳进水里,双手拼命划着向猴子游去。最后,我俩靠这块门板游到了铁路桥下的沙洲上。
这时候,我想起那个古怪的老头,觉得他变得慈祥和蔼起来。
猴子躺在沙地上,两只眼睛通红。他说:“夫子,你救了我一命,我不会忘记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发达的。”
我说:“保住了小命就好,把话扯那么远干吗?”
猴子脑子灵泛得很,顽皮,讨厌读书,经常跟我说:“读书有个啥用,还不是为了这个。”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晃了晃,做了个数钱的手势,没皮没脸地笑起来,能弄到这个就行了。
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外面混,先是去了浙江一家制鞋厂,没干两年又去了深圳一家电子厂,后来辗转到贵阳开了个门面,卖摩托车。生意越做越大,都还没有车的时候,他就开上了帕萨特。
我当然知道猴子不会拿酒话逗我,我说:“跟你小子开个玩笑呢。”
“未必我还当真呀。”他打着哈哈,“本来我早想让你来的,没找到机会,现在我刚代理了一个品牌,你自己开门面也可以,帮我做事也可以,保证每年十万。”
我说:“考虑下,明天回话。”
我一夜没有睡好,默默地算了笔账,一年十万,除去开销,最少能剩五万,等到雪粒儿上大学时,我手里就有了五六十万,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啊。我几乎做出关掉书店的决定了。随即,我眼前又浮现出一连串的画面,孤独的雪粒儿,无助的雪粒儿,哭泣的雪粒儿,恐惧的雪粒儿。这些画面,像是电影里的特写,一个劲在我眼前晃动,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
第二天,我給猴子打电话:“兄弟,我现在来不了,等雪粒儿上初中再来。”
猴子有些生气,说:“把雪粒儿放全托,没钱我就打过来。等她上初中,黄花菜都凉了,还赚个屁钱。”
我说:“不用不用,我真来不了。”
沉默了一阵后,猴子说了声那好吧。语气中透着无奈和失望。
雪粒儿学钢琴的第二年,川城一中新建了一个北校区,办了所附属初中,一下增加了两千多个学生。罗老师建议我,可以卖点教辅资料和文具试试,也许生意会好一些。我听了她的话,生意一下子变得红火起来,自然,我也越来越忙了。每次接送雪粒儿都是匆匆忙忙的。
有一次,罗老师说:“你看你现在生意好起来了,忙得没法照顾雪粒儿,要不我去帮你接她吧。”
我说:“这怎么行呢,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的。”
“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反正一个人,闲着没事,孩子跟了他爸爸,他爸爸已有了新家。”她说得很坦然。
我说:“那如果我真忙的时候,就拜托你了。”
罗老师笑起来,脸上那两个酒窝盛满了笑意。“你看你,一件小事情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后来,我忙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让她帮我接雪粒儿。她把雪粒儿接回家,给她做饭,等雪粒儿洗完澡又给她洗衣服。然后,等我晚上去接。雪粒儿很喜欢她,有几天没看到就念叨,“蕊玲老师呢?我好久没看到她了啊。”
到年底,我将五千块钱递给罗老师,我说感谢你帮我接雪粒儿,真是帮了我的大忙。罗老师似乎很生气,一把推了回来,说:“你以为我接雪粒儿,就是为了你这几千块钱吗?”当时,我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她帮我的忙,付出了劳动,我给她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没有影响我和罗老师之间的关系,我照样给她打电话,她照样帮我接雪粒儿。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落,夜已降临,火车开动了,一溜长长的灯火,向着湿漉漉的黑夜掘进。
3
这次,我是从梦中醒来的。
深夜三点,车厢里一片阒寂,昏黄的灯光下,这些萍水相逢的人怀揣着各自的心事进入了梦乡。他们仰着、趴着、歪着,姿势各异,像潮水席卷過后,死在沙滩上的鱼。
窗外一片漆黑,晃过七零八落的灯火。我感觉到外面的空旷和辽阔,像悠扬的蒙古长调。我心里想,大概到平原上了,我懒得去借助手机证实一件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反正火车会把我带去要去的地方,就像死神把每一个人带向最后的归宿。睡意跑得无影无踪,跟我平日里午夜醒来一样。虽然没吃东西,但我并不感到饿,我发觉,吃饭对我来说,似乎也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有时候我忘了吃饭,后来想起来好像又吃过了。不像以前,早餐两个荷包蛋加一海碗的面,呼噜噜吃下去,才勉强把肚子填饱。
梦杂乱无章,都是雪粒儿的事情,像一些不听话的碎片。毕竟时间过去很久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些碎片连起来。
雪粒儿上初中后,我就很少看到罗老师了,去学琴都是雪粒儿自己去。雪粒儿说:“我都这么大了,还送什么呢?”我愿意听雪粒儿的,雪粒儿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还有一件事情,我最终也听了雪粒儿的,那就是她对我的称呼。她不再叫我爸爸,一口一个老范。刚开始我有些不习惯,板着脸批评她没大没小,不懂礼貌。她嘻嘻笑着说:“这不是礼貌的问题好吧,你看我们班好多同学都这样叫,我们家老李,我们家老刘,这样叫显得亲。”雪粒儿笑着,很开心的样子,只要雪粒儿开心,我就随了她。
每次学琴回来,雪粒儿都会跟我讲蕊玲老师说了什么,告诉了她什么。
她说:“老范,蕊玲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去考音乐专业,我觉得她的话有道理。蕊玲老师说,女孩子来了初潮后,就长大了。蕊玲老师还说,我的身体哪些部分是私密的,谁都不许看,不许碰。当然,老范你除外,你是我的大情人。”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非常感激罗老师,她做了王雪梦没有做的事情,让这个年龄的雪粒儿,懂得这么多的东西。
有一次,雪粒儿对我说:“老范,你要不要把蕊玲老师娶回来,我愿意她做我的妈妈。”我说:“雪粒儿,你这玩笑开大了啊。”雪粒儿冲我扮了个鬼脸,“这么好的女人你不娶,总有一天会后悔死的。”
有些事,雪粒儿不会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
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罗老师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她病了。我去看了眼熟睡的雪粒儿,骑上电动车往她那里赶。她靠在床头,头发零乱,手按着腹部,脸上的肌肉扭成一团,像谁正在拧着她的脸。看着她那样子,我的心也揪了起来。我打电话给我家楼下的谭医生,告诉他我一个朋友生病了,想去他诊所里看看。我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在他那儿解决,我相信他会帮我这个忙。他听了后爽快地答应了。
我把罗老师送到诊所,原来是得了急性肠胃炎,需要输液。我守在那里,等她输完液后再把她送回家。
到她家后,雨突然大了起来,拍打着窗玻璃,发出巨大的响声。
这时罗老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笑起来脸上有了两个酒窝。我见她没事了,准备离开,她把我送到门口,一只手突然伸过来,一把揽住我,再呆一会吧。她的声音很轻,用的几乎是乞求的语气。
我压根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一时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她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喃喃着:“从今以后,就让我来照顾雪粒儿,你安心守在店子里,让我来做雪粒儿的妈妈。”
声音越发的轻了,像山顶的薄雾一样向我飘来,我觉得就像置身于一场梦中。我感到身上像着了火一样难受,听到我的血在每一根血管里澎湃。我真想一把将她抱起来,丢在墙角那张宽大的床上,就在下一刻,在幸福的呻吟里,让她做我的女人。
理智终于把我拉回现实中。我轻轻地抱了她一下,罗老师,太晚了,雪粒儿一个人在家,我得回去了。说完,挣脱她的手,转身向楼下奔去,顾不上穿雨衣,跨上电动车冲进了雨中。一路上,雨迷迷蒙蒙,眼前一片混沌,我生怕车子翻了,只得努力睁开眼睛。回到家里以后,脑子里和身上一样,嘀嘀嗒嗒地掉着雨水。
我进房间去看雪粒儿,她蜷缩着身子,睡得像一只慵懒的猫。
胡乱冲了个澡,走出卫生间,我给罗老师发了条短信:对不起,雪粒儿太小了。我想,以她的聪明,不会不知道我的意思。
很快,我收到了她的回复:那我们等雪粒儿长大。
我再没有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城郊的黄岗岭枪毙一个女人,我和一帮同学骑着单车追去看,砰的一声枪响,鲜红的血喷涌而出,那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像条死狗一样倒在荒草丛中,吓得我当时差点尿了裤子,一连几个晚上都做恶梦。那个女人还很年轻,有俏丽的面容,她是个后妈,把六岁的继女按在水缸里淹死了。想到这个,我浑身冰凉,我害怕雪粒儿摊上这样的命运。
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嘀嗒嘀嗒的雨声,我久久睡不着,罗老师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荡。她笑盈盈地望着我和雪粒儿,满脸春风,她帮雪粒儿收拾东西,给雪粒儿扎辫子,教雪粒儿做作业。突然,她变得披头散发,双眼通红,十指叉开,死死地盯着雪粒儿,像个厉鬼。
我相信罗老师不是这样的女人,当然,只是相信。
雪粒儿还小,她还不懂这些事情。等雪粒儿上了高中再说吧。
雪粒儿考上的是川城一中的艺术部,她及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的蕊玲老师。很快,罗老师给我发了条短信:祝贺你,雪粒儿终于长大了。
我寻思了一会,都没想好该如何回复,思来想去,写下了这几个字:风景很好,谁都不知道一条路到底有多长。作为回复,这句话很晦涩,甚至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
手机再没有了动静。我发现我的手心里竟有了汗水,我自己都无法确定,我是愿意听到手机的响声,还是愿意面对它的沉默。
上高中后,雪粒儿再没有时间去学琴了,她上的是艺术高中,练琴的事情都在学校里完成,罗老师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冬天过去,雨季来临,整个川城笼罩在绵绵阴雨里,似乎伸手一握,都能挤出水来。可能是天气的缘故,一天傍晚,我和一个顾客因为一本书的事情吵了一架,心情糟糕到了极点。那个男人,明明是一本正版书,他却硬说是盗版,胡搅蛮缠,在店里大吵大闹,还说要去举报我。我怎么解释都没用。
回家洗过澡,吃饭时破例喝了些酒,酒意上来后,突然想找个人说说话,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想来想去,最后只剩下罗老师。我就是想和她说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
我去了她那里,出乎意料的是门是锁着的,台阶上青草泛滥,覆盖了门槛,窗子上结满了蜘蛛网,那株紫藤正在做着开花的准备,只要再过一两天,墙上就会铺满紫色的云朵。两只鸟在上面喳喳地叫着,声音加剧了周围的冷寂和空荡。
看来,罗老师搬走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窗前徘徊了一阵,直到雨停下来,才满怀失落地往回走。路过那片油桐林时,新叶上的雨珠嘀嘀嗒嗒地往下掉,我仰起头看着那些雨滴,有一滴刚好落在我脸上,无声地往下滑,像是谁的泪划过我的脸庞。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说不上是惆怅还是感伤。我靠在一棵树上连抽了三根烟,风从路的那头过来,捎带着眼前蓝色的烟雾,飘散在黄昏的油桐林里。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罗老师。
有一次,雪粒儿对我说:“老范,我找不到蕊玲老师了,她换了号码,怎么没告诉我呢?”雪粒儿眼里的泪珠挨挨挤挤,正准备夺眶而出。
我心里的线条被雪粒兒一扯,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泪差一点涌出来。我转过身,在心里叹息了一声,对雪粒儿说,可能是有事忘了吧。那一阵子,雪粒儿显得闷闷不乐,我不知道该向雪粒儿说什么。
高中毕业后,雪粒儿如愿考上了四川一所音乐学院。
那时候,我的生意已经很稳定,这些年也积攒了些钱,这些钱都是归雪粒儿的。我每个月定期给雪粒儿一笔钱,我不想雪粒儿为了钱的事分心。
雪粒儿给我打电话:“老范,别总给我转钱,我告诉过你,我每个月有奖学金,平时还在外面教钢琴,我自己的钱花不完的。”这件事我没听雪粒儿的,还是每个月准时给她转钱。
到了年底,雪粒儿把我给她的钱如数还给我,老范,我替你保管了那么久,现在还给你。到了第二年,我依旧每月给她转钱。年底,她又归还给我,在钱这件事上,我和雪粒儿好像两个孩子在做一场机械的游戏。
雪粒儿大学毕业后,破格留校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同时,说:“老范,以后不用每个月给我转钱了,我有自己的工资了。”
我说:“好好,雪粒儿开始长大了。”
雪粒儿哼了一声,“早就长大了好吧。”
有一天,雪粒儿给我转来三千块钱。我跟雪粒儿微信视频,为啥给我转钱?雪粒儿笑着说:“老范,我领了工资呀,在外面教钢琴还有钱,现在我比你富有了,所以呢,给你转点零花钱。”
停了会,她接着说:“我看你把那店子关了吧,没必要开了,太辛苦了。”
我说:“我现在还有的是力气呢,多给你攒点嫁妆钱。”
雪粒儿嘿嘿笑起来,”我不用嫁妆,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嫁妆。“
其实我想的是雪粒儿得买车、买房子,趁我有力气,再赚几年钱,等雪粒儿买了车买了房结了婚成了家,我就可以放心了。
从那以后,雪粒儿每月给我转一笔钱,我把这笔钱用雪粒儿的名字存下来,留着将来给她买房用。
其间,我一再催雪粒儿结婚,雪粒儿说:“老范,你先给我找个妈回来吧,我有妈了就结婚。”
我说:“这是哪跟哪呢?有没有妈跟你结婚有什么关系?”
“老范,关系大着呢。”随后,我听到了雪粒儿有些夸张的笑声。
天渐渐亮了起来,曙色一点点廓清外面的轮廓,像一张大幕向着一边徐徐拉开,露出玉米、白杨、铺满尘土的路、檐低窗窄的房子,还有前方没有尽头的铁轨。
4
离终点站还早,火车正穿过一个山垭。蓝色的天幕拉得很高,上面浮着些乳白的雾般的云彩,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天上的草原。窗外只剩下两种颜色,一种是黄,一种是灰,起起伏伏之间,看不到哪怕像针尖样的一丝绿色,火车像一条绿色的长龙在这灰黄的波浪中爬行。
前面那对情侣终于变换了姿势,在讨论结束这趟旅行之后,下一趟去哪里。女孩说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想去澜沧江边看蝴蝶。男孩好像不太情愿,只是委婉地说敦煌的景色不错,两个人还说了好几个地方。我边上的长胡子男人也给他们建议了几个地方,比如伊犁、腾冲、青海湖,并逐一说了他自己的体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都没有确定。
我很羡慕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到处去走去看。
雪粒儿上大学的那年冬天,王哲打电话给我,说准备组织一些高中同学去三亚旅行,问我愿不愿去。
三亚的美我不是不知道,白色的沙滩,海风中摇曳的椰子树,海水蓝得像蓝宝石闪烁的光芒。尤其是傍晚时分,太阳在海面上欲坠未坠,蓝色的天底下,浮着朵朵金色的云朵,海浪一波一波地涌来,像少女羞涩地吻着沙滩。海鸥在远处循环往复地飞翔。那一刻,我真的心动了,我仿佛正打着赤脚,走在那柔软的沙滩上,我放下了一个已经老去的男人平日里的刻板、腼腆和羞涩,放开嗓子唱着那首喜欢的《外婆的澎湖湾》。
后来,一听到要去二十天,我果断地拒绝了。我暗地里算了笔账,按一天赚三百块钱算,加上去三亚的吃住和车费,一共是二万多块钱,差不多可以买两平米房子。正事还没做好,关键时候,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怎么能把钱花在享乐上呢?
王哲是我们的班长,毕业后去了信访局上班,善于做思想工作。他说:“你女儿都上大学了,也没什么负担了,你手里又不是没钱,就二十天的时间,有什么舍不得呢?”
我说:“雪粒儿还小,我肩上的担子重着呢,等她毕业参加工作结婚了,我就有时间了,你说去哪就去哪,去多久都行。”
王哲听我这样说,没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心里涌上来一阵长长的失落。
那些同学去了三亚后,每天在朋友圈里晒美景和美食,引来很多人点赞。我一一翻看,我在心里哼了一声,“有什么了不起?等雪粒儿结婚了,我去住上个一年半载。”
雪粒儿终于结婚了,就在三个月前。那个叫李天然的男孩是学音乐学的,性格很好,温和,话不多,也是她那所学校的老师,和雪粒儿有共同语言。
第一次见到那个男孩时,我跟他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唯一一点就是你要对雪粒儿好。如果你对他不好,我决不会放过你。”男孩大概被我的话吓到了,一个劲地点头。事实上,所谓不放过,那只是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一场婚姻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就像我和王雪梦。我能为雪粒儿做的,就是这些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雪粒儿自己了。
雪粒儿结婚后,我突然发现我的日子已不再像从前了。我把店子关了,虽然还是有些不舍,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想起我这一生,真是简单啊,一眼就能望穿。除了雪粒儿,就是这个叫做闻道的书店。除了书店,就是雪粒儿。再没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了。
火车接近终点站的时候,我给雪粒儿发了条微信:钥匙放在门边的电表箱里,你回家很快就能找到。我的雪粒儿,你终于长大了。
简单的几行字,我写得很慢,像是用一生写出来的。写完念了几遍,觉得不好,改了几个字,再念,还是觉得不好。改来改去,横竖觉得不对,又没法改了,只好就这样发了过去。
雪粒儿没有回复,也许她正在课堂上。
火车停了下来,终点站到了。
这确实是个小站,典型的日式建筑,两层,下层是花岗岩墙面,像岁月一样斑驳,上层是橘黄色的砖头,让人疑心是用阳光夯成的,透出一種含蓄的温暖。后面有一个草坡,草已经黄了,荡漾着金黄的波浪,草坡尽头,被夕阳染黄的松树莽莽苍苍,向着天边的浮云奔去。正是傍晚,站台上涂抹着金黄的夕照,这温暖明丽的色彩,让人仿佛突然来到了风和日丽的春天。
出站后,我站在铁轨边拿出根烟点燃,不慌不忙地吸着,感受着呼啸而来的风在脸上拍打的畅快。吸完烟,我把烟屁股丢在地上,用右脚踩在上面旋转了几下,从兜里掏出手机,取出手机卡,连同手机一起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我伸了个懒腰,迈着轻快的脚步沿着铁轨向前走去,夕阳渐渐消失在山头,暮色开始涌了过来,朦胧而柔和,在我眼前荡漾着,像是黎明的曙光。
责任编辑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