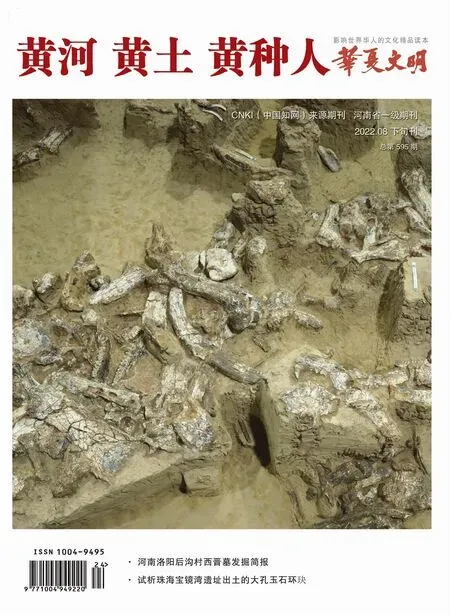商周青铜器中“人兽母题”造型艺术演变原因分析
□杨远 李迪
“人兽母题” 造型艺术主要表现为在一组人与兽共同组成的造型中,两者紧密贴合且处于一种重合或者交叉的状态,其在中、外早期造型艺术中都极为常见,其内涵复杂,形式多样。
依据我国商周时期的发现看,商代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从整体构图上来说,“人”大多处于“兽”口之下或是依附于“兽”。 在具体的形体处理上,动物的脚爪、翅尾、目与牙突出表现,给人以威慑压迫的视觉效果。在人的刻画上虽然人体的五官及各部位的比例都合乎正常,但多数情况下全身都会布满纹饰,有时也会被添加兽角、兽爪,较为神秘。 这种情况到了西周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创作者开始采用高浮雕的写实手法以一种更加简洁、清晰的线条来表现“人兽母题”造型,这些造型多见于器足、器物支架、车马器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也逐渐改变, 人物在整体构图中开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此时,“人兽母题”造型纹饰的神秘性消失。到了东周时期,“人兽母题”造型在构图上基本已经摆脱了商和西周时期的固定模式,写实风格的人兽题材开始涌现,多表现为人驯兽、人驱兽、人抚兽等新型纹饰,此时的“人”已经成为画面主体,而“兽”则起衬托作用。 从威严神秘到华美写实再到生动有趣,商周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其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种造型艺术的内涵极为重要,鉴于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商周青铜器上“人兽母题”造型发生嬗变的原因,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参考。
一、社会观念的不同对“人兽母题”造型的影响
社会观念是艺术创作的主要思想来源,商周不同时期的社会观念的变化对“人兽母题”造型艺术有直接的影响。
商代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与商代人的宗教思想有很大关系。 在商人看来,天地鬼神无所不能,他们具有无边的神力,要想得到他们的护佑,就必须向他们致敬并想方设法取悦和讨好他们。 为了向神鬼及祖先表示恭敬虔诚之心,商人运用不同的方式来举办各类祭祀仪式,并且在祭祀场合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 各种祭器、祭物都是为祭祀神灵祖先服务的。 “人兽母题”造型作为礼器的构成部分,首要的任务也是为“尊鬼重神”服务的,奴隶主统治者或是巫觋为了使祭祀仪式保持一种威严且令人望而生畏的氛围, 会命令工匠在制造青铜器的过程中极力制造出精益求精、近乎完美的“人兽母题”造型,并将它们用于祭祀活动之中。 因此,商代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都呈现出了威严、神秘、诡异的风格特点。 如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图1)和法国塞努斯基博物馆(图2)的两件虎食人卣,这两件作品中,虎的双眼瞪视前方,巨口微张,两只前爪紧紧地将人抱于胸前,胸前的人物则表情镇定,神态安详。 整体造型显得极为神秘怪诞。

图1 商代虎食人卣

图2 商代虎食人卣
到了西周早期, 虽然周王室在政治上翦商伐纣,但在礼制与艺术方面,早期的西周与商代并无太大区别,所以此时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与商代并无太大出入,依旧散发着浓重的神秘主义气息,但是为了使周人的统治地位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周人开始有意将人与神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 此时的天命已经不仅仅是上帝的一种主观意志,它还需要参照一个新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上帝仅授其天命予有德者。 自此之后,西周的统治开始由神治走向了人治,这也使得“人兽母题”的造型、纹饰均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兽母题”纹饰开始趋向呆板与固定化,其形状所表现的宗教式的力量开始逐渐递减,它们的神话性与超自然的魔力则不如商代时期那么明显,开始走向平易写实的风格。
东周时期,王室的政治军事实力逐渐衰微,而异姓氏族的诸侯力量则开始不断增强。 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对旧有的思想体系加以质疑, 并提出了各种新型的文化思想体系。 更重要的是, 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字、科学以及政治哲学不再为宗室所独有,开始深入民间。 因此,在这种争雄争霸的背景下,东周各方面的变化反映在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当中就是结束其作为特定时期政治宗教文化的载体使命,转而向日用摆设等日常装饰方向发展。甚至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尝试对神的至上权威发起挑战,并对各自祖先的功德加以强调和标榜。 从东周时期的神话故事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在不断强调神界对人世上权威的支配力量的减弱, 同时统治者也常常将上帝描述成一个与人为敌的形象。 这种思想动摇了传统宗教思想的基础, 使时人对人自身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人本”的思想意识开始逐渐萌芽。
二、政治制度的演变对“人兽母题”造型的影响
商代实行的宗庙制度与统治阶级的宗法宗族制度相结合,除此之外,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宗法制度之上,因而商代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这时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在视觉表现上深受这种神权政治的熏陶。 因此,此时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充当了沟通神人的媒介。在这种环境中, 商人对于神基本上还处于从属关系,在认识上还是很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天命。 因此,这时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在具体的形体处理上都将动物凌厉的脚爪、尖锐的牙齿、怒睁的眼睛有意地加以突出,以形写神,给人一种威慑压迫的视觉效果。
到了西周时期, 周公对西周以前的礼仪经过一定的整理、改造和规范化之后,为西周确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典章、制度、规矩和仪节,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制礼作乐”,这套制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宗教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礼记》中记载“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由此,可以看出周礼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与礼制息息相关的礼器也受其影响。 尽管周人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形成了一种有伦理观念和严格等级制度的礼仪活动。 这类祭祀活动相对来说有序、有度且理智。 因此, 匠人们在制作青铜礼器的时候也会依据祭祀活动的特点来进行制作。这反映在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 造型纹饰上就会由商代的神秘威严逐渐转化为平易写实,同时,因功能的需要将这种经过演变的威武凶猛的“人兽母题”造型装饰在兵器或车器上。
东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产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周王室日益衰微,虽仍是名义上的“共主”,但早已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统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革新期。诸侯、大夫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代表,他们利用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名义,常“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取代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在这场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诸侯并争的过程中,以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为政体、 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制度逐渐得到确立。 这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得人们对天命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 虽然这时的统治阶级依然相信上天和神明的力量,但是,人们已经可以理智地认为一切天灾不再都是对人的惩罚。 因此,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影响了时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在这一时期反映出该阶段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开始由“神”的艺术转向“人”的艺术,从战国时期的人形青铜灯(图3)、骑驼人擎灯(图4)中可以看出人与自然斗争意识的萌发, 表现出人的进取精神,更彰显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初步确立。

图3 战国人形青铜灯

图4 战国骑驼人擎灯
三、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对“人兽母题”造型的影响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几乎全部出现在青铜礼器上, 兵器目前仅有妇好钺一例,但其功能也是象征着权力的威严。 除此之外, 商代大多数墓葬当中出现的随葬青铜器基本都是以酒器为主要搭配, 这种习俗在整个商代都很流行。 文献中也常记载商人好酒,有时他们还把这种喜好加于诸神身上,认为神也嗜饮,所以酒成为了酬神祭鬼不可缺少的物质,酒器也就作为祭神的礼器用来寄托商人的精神崇拜。 由此可以看出,商人通过一系列较为夸张的表现手法来绘制装饰在青铜礼器上的“人兽母题”造型,使其对参与祭祀的人们造成视觉上和心理上巨大的冲击力,从而增强祭祀环境的庄严和神圣气氛。
到了西周时期, 青铜器开始多用于战争当中。“人兽母题” 造型在青铜礼器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转而在车器以及兵器上出现的次数不断增多。西周时期的兵器完全不具备礼器的祭祀功能,其车器也主要是用于战争, 或作为高级贵族的交通工具。 如《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 这种将虎食人造型铸在战车上的意图明显是看重了虎作为百兽之王的威猛、凶悍、勇往直前的象征。 除此之外,“人兽母题”造型也出现在西周兵器上,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西周早期虎食人铜刀(图5)。 铜刀侧面有两虎张开大口,其中虎口有一人的侧身像。 所以这个时期的“人兽母题”造型在青铜器功能产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定的形变,用一种风格完全不同于商代的虎来提升军队威猛无敌的气势。 由此我们猜测虎口中的人是敌人的形象, 以猛虎食敌来表现军队的威猛无敌、战无不胜,同时也是战功的炫耀[1]。

图5 西周早期虎食人铜刀
东周时期,工匠们在不断完善青铜器实用功能和装饰工艺的同时,各种新型的文化思想和实践经验也为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注入了新的审美理念和精神元素。 此时青铜器中的“人”与“兽”完全摆脱了商代的文化功能, 已经不再具备宗教含义,而只是作为两种题材出现在同一件器物上,变成了以实用为目的的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 也成为了传达时人审美追求和审美理念的艺术品。 这时青铜器中的人兽题材是实用功能与审美意向的完美结合, 反映了东周时期艺术创造和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无论是题材还是造型,其都受到了时人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 趋向于生活化和世俗化,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特性,极富独特的生活气息。 如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图6)及山西博物院收藏的铜牺立人擎盘(图7),都是生活用品和赏玩艺术品的结合。

图6 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

图7 战国铜牺立人擎盘
由此,可以看出商周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随着各个时期青铜器主流功能的改变发生了变化。
四、工艺技术的进步对“人兽母题”造型的影响
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创新,从简单到复杂,由一种工艺到多种工艺相结合,日渐丰富和成熟。 李济先生就曾指出:“铸造技术随时代的演进而演进, 所以一种技术的进步,不但可以表现在制造的程序上,也可以影响到图案的设计。 ”[2]
在商代早期,青铜礼器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其装饰工艺也由简单逐步趋向繁复,普遍运用了合范工艺作为青铜器的主要装饰技术,所以其装饰多呈现出以平面纹样为主的特征。这个时期还采用了分铸铸接工艺,这使得青铜器的装饰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为立体雕塑的装饰提供了技术基础,并且逐渐出现了以平面纹样为主,辅以浮雕、线刻的装饰技法,而这种技法一经出现,就开始流行起来,并为之后的青铜器装饰所继承。 因此,自商代中后期开始,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严密且分工细致。以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和法国塞努斯基博物馆的两件虎食人卣为例, 二者就是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融为一体的佳作。 此外,在小件青铜器上,也开始运用镶嵌绿松石、包金的工艺,个别青铜器还有碟漆、镀锡作为陪衬的现象。
西周时期,由于礼制与艺术方面的延续性,普及于商代的青铜器分铸铸接工艺在西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青铜器的附件被铸成不同形状的艺术形象,而后铸接于器体,既丰富了青铜器的造型,又增强了装饰的艺术效果。 另外, 镶嵌绿松石、镀锡、操漆、包金等工艺在小件青铜器上仍有运用。
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铸造技术不断进步, 越来越多的青铜器铸造装饰技法开始不断涌现。 填漆、错金银、嵌刻等金属细作工艺为青铜器的装饰领域打开了新的视域。 这使得青铜器的色彩变化更为丰富,表现出了对缤纷多彩、华美绚丽的装饰效果的追求。 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在借鉴镶嵌工艺基础上,新出现铸镶红铜的工艺,花纹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有流云纹、变形夔纹、禽兽纹和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画像故事图像, 改变了以往模范法制作花纹的技术,广泛运用模印工艺,新出现刻画花纹技术,所刻花纹主要为反映日常生活的画像故事图像,线条细腻流畅,技法高超。 例如东周时期的嵌赤铜狩猎纹壶(图8),就是以浮雕法在器身上装饰刻画出人兽同器的狩猎纹, 这也是东周时期反映时人日常生活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在以前包金技术基础上,又出现贴金等装饰工艺,常常和其他诸如镶嵌绿松石、 铸镶赤铜等工艺巧妙地综合运用到一件器物上,把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工艺推向了新的高峰。

图8 东周嵌赤铜狩猎纹壶
五、结语
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纹饰由威严神秘到世俗写实,由单一到多样,由对自然的敬畏到对人的自身力量的认可,“人”在“人兽母题”题材中也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配角转换为主角,这些变化实际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生产技术、政治功能等的影响,是其物化体现,这为我们探究商周青铜器中的“人兽母题”造型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