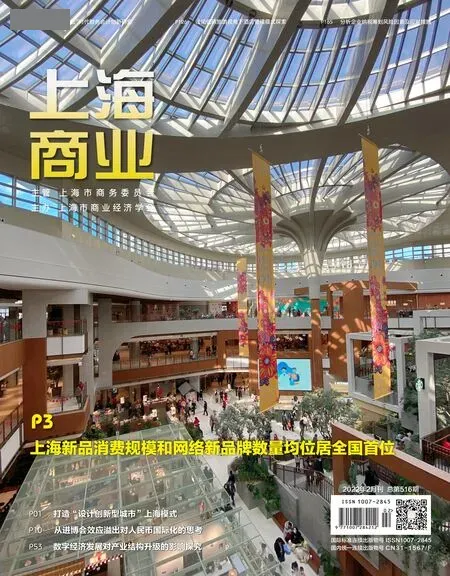不同主体类型下董事责任司法适用的调查研究
吴超琪
随着贝利和米恩斯1932 年提出著名的“两权分离”公司理论和公司治理现代化、跨国公司不断壮大发展,在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中两权愈加独立分离,公司机关分化局面形成,公司经营管理权由股东会过渡到董事会,即公司治理经营从股东会中心主义逐渐转成董事会中心主义。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会(本文不区分股东会与股东大会)是我国公司的权力机构。而在学界,不论是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都认为股东会是公司绝对的最高权力机关。
秉承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与现代商事活动不断发展的公司实践相抵牾,公司法没有摆脱股东会中心主义的陈旧基调,与实践中流行和现实的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运营中心相脱节。基于此,学界也一直主张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应该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在此基础之上,董事责任的立法和研究需要配套相应立法模式的转变,进行董事责任相关的梳理;而目前我国董事责任的承担主要模糊的地方在于董事主体的不明晰和不确定。
一、董事责任概述
1.董事责任之基本概念
依据我国《公司法》,董事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对外代表公司并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的常设机构中的成员。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不论是基于大陆法系委任关系理论,或是普通法系信托关系说,最终在董事上设定的义务却基本一致——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
我国《公司法》对此在148 条和149 条对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法条的基本结构为“构成要件—法律后果”,即主体违反其设定的义务需要承担责任。董事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公司法对其预设的义务,即应承担预设的法律后果。董事责任根据其承担责任的对象主要分为对公司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责任。
2.董事责任追责模糊之主体原因
董事责任的追责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显得模糊,尽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两者存在明显的理论区别,但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商事活动的复杂性和实践中各类行为的纷杂交融,另一方面,裁判文书的篇幅限制和我国的裁判文书中对于论证说理部分历来较为薄弱,导致了董事责任追责的路径往往只用简单的“背离董事忠实义务、注意义务”搭建。加之尽管忠实义务一般以客观标准作为判断,但注意义务之履行难以客观判断,常需要辅之以主观判断,这也导致了董事责任追责的路径模糊。
在中国商事实践中,家族式企业和公司盛行。公司治理的高管在身份上具有多重性,董事的身份不独立,其责任难以论理确定。这让法官在进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难以用翔实、确定的理论和论证去完成精准的法律适用的判断。
3.董事责任厘清之出路
董事责任承担路径的厘清需要理论的精细化,以此来帮助法官精确地进行司法适用和判断。于前所论,董事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委实存在,而且对于法官司法产生了极大的困扰。厘清董事责任须在董事主体上进行精细化的分类和讨论。
董事主体类型的不同在商事实践中暗示说明了其公司地位、权力、收益等各方面的不同。尽管仍然将其称之为董事,并且在违反董事义务,承担董事责任的逻辑圈内进行责任的分配,但是不同的主体之间已然突破对董事的定义边界,甚至与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责任主体角色相交融。故此,在先暂搁厘清董事责任任务的基础上,对董事主体类型的划分和研究对于董事责任整体理论框架构建和司法实践的裁判指引都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二、董事主体类型
1.公司经营中董事之定位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化公司的一大优点也是其特征。但在公司实际的商事运作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往往无法经常召开,原属于股东大会决议之事项往往只限于法律规定之内,未被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之事项应当由董事会行使但董事会又难以召开,这就让股东大会与董事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法律或公司章程均无明文规定应经由董事会决议之事项,似乎也不一定能排上董事会议程,多也是以报告处理。法律有明文规定应当由董事会决议的,例如,《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制定年度财务报表、利润分配方案和提名与解聘经理等,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讨论的议案。通常由控制董事及经理负责提案,按法定要求也都会现提请总经理与董事长批示,因此该二人便成为公司实质中拟定经营政策的核心角色。再当法律与公司章程无明文规定时,公司日常之大小事务均由董事和经理依照职权决定。这也即“董事会”中心主义。
2.董事主体类型分类之必要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行使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的职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公司违反相关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这在成文法上明确了我国法律规定的董事的途径仅限股东会选任,并且违反法定任职资格而选举、委派董事的行为系属无效,也即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但形式主义的董事选任和定义难以涵括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更毋论参照董事责任追究实际控制公司行为者责任。
尽管我国实际的公司商事运作中董事会中心主义盛行,且我国公司治理中股东的高度集权现象明显,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更是通过各种方式操纵董事会及董事,时常使得董事会或董事沦为公司治理中的提线木偶,但《公司法》仍然忽视公司治理需求上的本质差异,将分权控制结构强制嵌套在所有公司权力配置中,造成公司治理规制失当与迟滞缺憾。在公司法与公司治理相脱节的状态下,加之前述我国公司商事实践有其文化背景带来的特殊性,董事责任的追究路径难以完善。故对于董事主体进行类型化有相当之必要:一来促进公司治理的合规化,使前述公司治理的权力架构问题得到处理;二来对公司法修改进行立法建议,解决公司法与我国公司治理需求脱节和强行嵌套的脱节问题;如此还可以指导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法律难以在董事责任上形成逻辑自洽的难题。
三、域外经验与出路
1.董事主体之域外经验
现代商事制度滥觞于西方,因此解决我国公司治理需求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应将目光落到发源处,汲取先行者的经验。西方国家的公司权力配置格局在公司商事实践的发展中表现出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型,但各国公司法实践却演化出不同的董事会角色定位,其中典型便是美国单层制和德国双层制的两种监督角色。
其中,美国单层制下,美国特拉华州1899 年《普通公司法》通过“除非本法或公司设立章程另有规定,公司业务和事务均应在董事会管理或在董事会指导下进行”正式宣告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确立,此后1950 年《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所有公司权力应当由董事会行使或在它的许可下行使,公司业务和事务也应当在它的指导下经营管理,但上述一切均应受公司设立章程明示限制的约束”。明文确立了董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
而在德国公司制度中的董事会则分化为行监事职责的董事与行管理职责的董事,行监视职责董事由行管理职责董事选聘并受其监督,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后者由股东选举产生,行公司经营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经营权。与此形成了董事监督者和管理者的双层角色定位。
总之,虽然美国和德国分别探索出不同的董事会组织形式,但是都保持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大概构架——董事会进行公司日常事务之管理,而股东会仅在法律或章程授权范围内行使其规定的公司权力。
2.司法困境之国内出路
首先,我国在法律的继受上更偏向大陆法系的法典和体系化,在公司法的立法中亦表现出了统一立法的思路。在为保持统一的逻辑和体系上却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治理需求上的重大差异,并且规则间相互妥协,造成尽管上市公司是现代商事活动的主体但其规范却相当分散。其董事责任反而难以形成统一的逻辑和体系,不如将体系化的思维目光聚焦于责任的构建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分别立法,形成大体系架构的公司法典。
其次,在公司法典中全面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其实早已被学者发现成为我国公司权力结构变迁的结果,这也和世界上的公司治理变化潮流相符合。现行公司法所构建的分权控制已然收效甚微,既然董事会中心主义终与我国公司商事实践相契合,因而应当被纳入立法考虑中。
此外,既然董事会中心主义已然被确立,那么董事制度应当重新被构建。主要包括在董事义务的再厘清、董事会制度的梳理,包括:再确定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内涵外延,以此来确定违反义务的董事责任;融造董事责任的体系,包括对董事主体的划分、董事责任的类型化和对相关请求权冲突的法律解释。
在董事责任的构建中,笔者建议在董事责任的主体上进行划分,以此来厘清形式董事和实质董事之责任,在公司治理中明确董事之定位,以董事责任的完全体系化构造和梳理作为公司法立法的立法思路。
四、结语
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争论伴随现代商业的互通、借鉴和全球贸易的不断深入,从公司滥觞的英美蔓延到中国,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我国公司法采取股东会中心主义。但是,从我国公司法的明文规定看,股东会与董事会各自行使公司决策之权力和执行股东会决策之权力,这一模式应该属于职权法定主义。但公司职权法定主义,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产生诸多疑难问题。学界呼吁公司法立法的理论基础和模式从股东会中心主义转为董事会中心主义,以此顺应和解决目前实践中的法律与现实脱节而产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董事责任这一部分中的董事主体类型在汲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从董事的主体类型上厘清董事责任承担的边界问题。但对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为立法基础的未来公司法新法,仍然需要对董事会的职权边界和董事义务进行理论上的讨论,以此完善整个立法逻辑,为公司法内在逻辑的自洽继续在理论上进行完善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