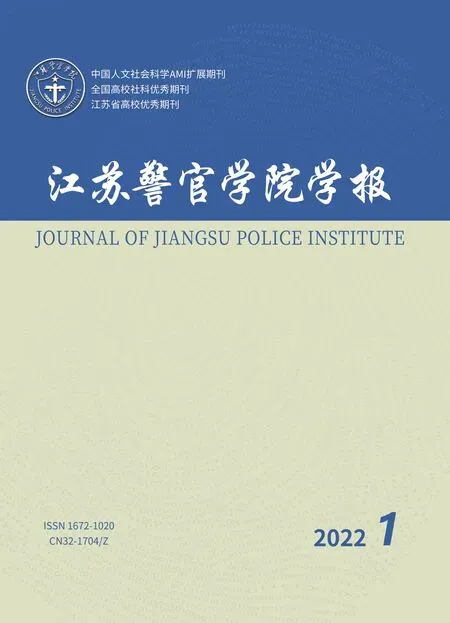从社会排斥到边缘群体:街角青年冲突博弈下的治理与善治
张丽霞 夏鹏飞
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illiam H.Whyte)《街角社会》是研究“街角青年”最具代表性文献,作者通过观察和记录意裔聚居区“Corner ville”青少年的结构方式、现实生活状况、各类不被政府认可的非正式组织及其系统结构、运行模式,并对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进行了论述。“Corner ville”区的最大特征是“割裂”,而这种割裂现象在当今中国一定程度存在,虽不及“贫民窟”极端社会分化程度,但当前就业压力攀升、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不足、各类纠纷增多、环境污染与破坏不减等等,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群体间或多或少存在时代特定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对这一现实问题,应高度重视。
步入新时代,中国在有效实现预防打击犯罪、最大程度化解风险矛盾、创造良好秩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特别是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基层社会治理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全面坚持和发展,有效压缩了社会给街角青年生存所让渡的“合法性空间”,为治理和管控边缘群体冲突提供了保证。
一、现状与问题
街角青年,长期以来被视为城镇、乡村街头的小混混、小地痞,在学校被贴上“差生”、在家庭被贴上“叛逆”标签,他们相似成长经历、不同心路历程,结成了特殊社会群体。目前,我国社会同样存在“时空分异”特征,人员在相对类似时空区域内聚合,文化碰撞导致边缘人——街角青年的产生也无法规避。而由街角青年形成的街角社会,具有独特的规则模式、权威声望和稳定结构,其整体行事方式和生存状态不同于主流社会,否则无法吸引更多同伴。街角青年们在这个“组织”里能够找到依赖和心理认同,试图成为“有头有脸的人”,拥有“街头信誉”。而我国社会和家庭通常要求青少年在各种场域听话、顺从,任何越轨失范行为都会招致家庭、学校、社会的严厉批评。少数青少年则囿于内心深处的失落与压抑、不满和愤恨,无法排泄舒缓而内化了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念,通过采取对抗行为博得关注,以弥补内心匮乏的安全感、归属感、获得感。
近年来我国每年立、侦刑事案件超过百万起,行政案件、调解处理的治安纠纷数量则更大,而其中很多纠纷、轻微违法犯罪系“街角青年”所为。法律层面上,由于行为人年龄和失范行为较轻而难以惩处,尤其是“前科封存制度”进一步完善后,对“街角青年”的防范教育和矫治更显困难。理论层面,国内部分学者对街角社会、街角青年开展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张园等对街角青年的成员构成和特征、类型、形成原因、犯罪类型、冲突模式和回归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①张园:《走近街角社会》,《社会》1997 年第7 期。.;黄海论述了“街角青年”的结构以及心理特征和流动方式等②黄海:《解读“街角青年”》,《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 年第2 期。;何绍辉发现街角青年群体呈现女性化与年轻化的新趋向与新特征③何绍辉:《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中的街角青年》,《中国青年研究》2016 年第7 期。;冯承才针对街角青年冲突模式、易罪错空间、生存现状、涉黑犯罪及治理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研究④冯成才:《街角青年涉黑犯罪研究——基于上海市K 社区“斧头帮”的田野调查》,《青年研究》2020 年第3 期。。这些研究促进了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和家庭给予这一特殊群体更多的关注,伴随着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生活情境的巨大变化,更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对当前街角青年的防控开展进一步研究。
二、概念与分歧
(一)街角青年
“街角青年”术语是一个社会建构范畴,在现实中并未形成一个具有明确定义的、同质的群体或现象。最具历史意义和常用的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给出的定义,即在全球城市中心街道上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人⑤Shorena Sadzaglishvili,“Street-Connected Youth:A Priority for Global HIV Prevention”,Journal of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nd Underserved,2018,29(02):633-644.。具体可分为“街头青年”“街上青年”“街头流浪青年”和“被遗弃青年”。
在新媒体、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泛娱乐化”信息愈发容易获取,对青少年价值观造成一定程度的历史价值观随意化、文化价值观功利化、道德价值观失范化、人生价值观漠视化和审美价值观庸俗化等消极影响⑥欧庭宇:《“泛娱乐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理论导刊》2020 年第4 期。,对街角青年的观念冲击增添了新元素。因此,新“街角青年”又具有了亚犯罪、“泛娱乐化”倾向、社会认同度低的特征,其介于普通友谊网络和帮派性质青年之间,就如《洛城掠夺者》中的“小乡绅”,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撒尿,但肯定知道如何乱来。”⑦J.T.Way,“City Streets in Rural Places:Emerging Cities,Youth Cultures,and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Guatemala”,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019,53(01):76-106.根据笔者2013年在江西某县一社区对12 名青少年(最小1996 年生、最大1992 年生)所进行的街角社会调查,以及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的考证和比较,认为新“街角青年”的年龄,大多数处于15 至20 岁之间,具有低龄化趋势。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是青少年犯罪的易发群体,具有犯罪主观逃避性,易受社会排斥,对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认同度不高,且自身排斥融入正常社会,为寻求归属感而成为街角青年。
(二)边缘群体
上世纪30 年代,Cressey 从种族、文化团体和社会分化角度提出了边缘群体一词⑧Cressey P F.The Anglo-Indians:“A Disorganized Marginal Group”,Social Forces,1935,14(02):263-268.,费孝通则认为,产生边缘人和边缘群体的因素中,社会文化差异乃重要因素之一,即聚集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种群体,必然会产生社会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诚然,政治、经济结构对边缘群体的形成起到更大的影响作用,就街头混混或者其它组织而言,难以用道德语言对其评价。诸多学者认为,边缘群体产自于上世纪80 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原来大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为改变命运寻求财富和体面生活而奔向城市,在赚取微薄工资的同时,还会受到不平等的社会待遇,这就是大量街角青年的父母原型。一些良莠不齐的观点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甩锅给这些边缘社会群体(或偏差青少年),指责他们素质低下,要求他们离开城市,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三)社会冲突
Dahrendorf 认为,权威是划分社会阶级的根本因素,具有权威的统治层和无权威的被统治层构成了强制结合团体,无数的强制结合团体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两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斗争是不间断的社会冲突的来源。Coser 等认为,对社会冲突研究应侧重于社会冲突的起因要素、发展形式以及制约社会冲突的影响因子,其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冲突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巩固等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冲突是个人价值、宗教信仰以及对权利、财富、社会资源等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和争夺,但通过适当允许社会矛盾在可控的情况下被发泄的社会安全阀制度的设定,突出了正向作用,在整合社群内部结构的同时,又能平复社群矛盾,甚至修补和解决某些问题。对我国而言,社会冲突理论最相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即导致阶级产生的最根本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配问题。
三、冲突与博弈
目前全世界仍有1 亿多街头青年,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①Shorena Sadzaglishvili,“Street-Connected Youth:A Priority for Global HIV Prevention”,Journal of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nd Underserved,2018,29(02):633-644.。从上世纪80 年代末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至2020 年全面脱贫,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中国奇迹”“中国力量”成为综合国力增长的代名词,受到了世界关注。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隐于管理对象范围中的“街角青年”也悄然递增,通过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15 年-2016 年涉黑犯罪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看出,涉黑案件虽呈下降趋势,但年轻人涉黑犯罪问题突出,其中18-30 周岁人数占比51.56%,14-18 周岁人数占比3.32%;重庆市 2006 年-2009 年一审判决的涉黑案件显示,584 名涉案人员中14-25 周岁青少年占比达39%。再如符平对访谈的湖南H 镇新街角青年的“江湖闯荡”“吃喝玩乐”“破罐子破摔”,冯成才田野调查的上海市 K 社区斧头帮“涉黑犯罪趋势”,以及前述江西某社区街角青年轻微违法和“劣迹表现”(2012 年-2013 年故意伤害、盗窃等治安案件15 起,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不够行政处罚多起)等等,街角青年所产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及其形成因素,不容怠忽。
(一)政治层面的不安定因素
一是部分地区的城乡基层管理存在软化现象。乡镇政府、社区(村)作为最基层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多,但少数基层组织施政中受到经济或宗族势力等掣肘,极个别基层干部利用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大肆敛财、为非作歹,或成为基层黑恶势力保护伞,弱化软化了基层政府执政能力。而街角青年通常持有不成熟政治观点,缺乏参与政治和活跃社会生活的既定模式,易被“无意识或准意识”所主导。二是街角青年易成为基层涉黑涉恶群体的重要来源。一旦形成群体,他们开始尝试各种“刺激性行为”,城市青年倾向于出没KTV、酒吧夜店等娱乐营业场所,或在虚拟世界中奔波厮杀,或在花天酒地中荒度青春;在农村,这类群体小偷小摸、游手好闲、盗窃等频发,对基层组织的管理形成窒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些街角青年都极易滑向犯罪边缘,如广州市海珠区法院2012 年-2013 年一审案件中,流动青少年犯罪案件占该区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5%,其中90%的流动少年犯来自农村。
(二)经济层面的不公平博弈
街角青年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一些青年难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甚至不得不“拓广渠道”而成为边缘群体。当然情况并非绝对,部分街角青年的家庭条件并不差,却仍热衷于街头小团体活动,此类则肇因于家庭教育等问题。有美国学者认为,经济状况与犯罪率是呈一定的正向关系的,近年来,我们时常会获取到美国警察射杀黑人等新闻报导信息,这些被射杀的黑人中很多都属于街角青年,也就是Whyte 研究中的“社区帮派分子”。
(三)社会层面的多维度冲突
从社会排斥维度分析,一些社会成员因经济贫困,缺乏基本社会生存能力和继续学习的机会,极易被其他社会成员排斥、歧视而进入社会边缘地带,无法参与所谓主流的社会生活。街角青年中大部分属于低收入家庭群体,他们由于缺乏教育、就业以及提升自己经济水平的各种机会,无法掌控自身的生活和生存,难以参加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和政治活动;加之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向上发展的渠道逐渐关闭,导致他们在不同场域和层次上发生多种维度的社会冲突。这些街角青年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团体,在这种看似稳定的组织结构中,他们获得了认同感、自尊感、陪伴感和归属感。
(四)文化层面的价值观碰撞
在全球多元发展和价值观多样化的今天,不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一些来自农村的街角青年因受其家庭、经济、教育等条件制约,在进入城市后从事着脏、累、危险系数高的工作,但又无法获取更多文化层面的资源,易产生不被公平对待的剥夺感和对现状的强烈抱怨,最终形成对抗心理和逆反状态。其次是群体对立和仇视,尤其表现在一线城市的城市青年中,他们鄙视被称为“泥腿子”的农村街角青年;而街角青年因受帮派影响,也不屑或仇视先天拥有社会资源的城市青年;两类群体的道德文化、价值追求、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最终形成群体对立、割裂和冲突。
四、治理与善治
研究表明,社会损害本身与经济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城市化生活的流动和相互冲突的规范对反社会疾病的出现具有更大的影响,一个正常青少年转变为街角青年的原因诸多,为促使更多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个人和家庭、学校和社区、政府和社会对其各类失范、轻微违法等行为进行介入式预防和管理补位尤为重要。
(一)公共管理视角的善治防范
Beck 认为,风险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未知风险,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街角青年问题的背后酝酿着未知的社会危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本单元的社区(村),其治理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对街角青年管理需从综合角度进行考量。譬如受疫情影响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青年就业面临更大压力,一部分青年有可能因生存而转化为街角青年。基层社区治理能力能否应答和解决好街角青年产生的突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区的组织基础,而民众高参与率社区的受害率和犯罪率远低于低参与率社区,我们的社区模式是否具备鼓励更高比率人员参加正式团体和志愿团体的能力呢?因此,基层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重视社区中青少年动态和他们的切实需求。用好社交媒体,改进工作方式和手段,设立综合治理中心的同时,调动更多公共组织参与其中,并结合社区矫正体制改革,拓宽关注管理视野,将社区中的街角青年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帮扶帮教其重回社会正轨。
(二)至善理论范畴的自我矫正
现实社会中,不良行为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并非局限于“街角青年”。Kant 所倡导的“至善”幸福观是构建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虽然自我完善无法完全实现,但这种永恒的进步预示着作为最终目的的彼岸世界—“至善”①李志龙:《论康德的自我完善与至善》,《道德与文明》2020 年第1 期。。而内动力是决定事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街角青年应从四方面自我矫正和完善:一是提升自我修养,树立正确“三观”。清醒认识到自己处于幼稚、颓废、麻木状态,增强榜样意识,主动接近和向身边优秀青年学习,吸纳和学习主流思想文化。二是拓宽知识广度和深度,加强职业技能训练。摒弃对工作及技能的蔑视,明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三是增强法律意识,做知法、懂法、守法者。认知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努力成为正能量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四是增强自尊和自信,寻找正确的释压方式。在成长阶段应多寻求家长、老师帮助,学会倾听、加强沟通,或通过“同伴”教育形式学习交流,合理释放压力,减少产生自卑自弃心理。
(三)社会情境维度的干预机制
调研发现,街角青年实施针对自身或他人的消极行为往往发生在遭受社会排斥后,其经历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异于寻常。而社会情境属于被个体明确意识到的状态,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均能产生反应。因此,基于社会情境维度,可从四个层面预警并建立干预体系。
其一、家庭层面。所有家庭变量中,与母亲沟通不畅和被控制水平较高经历存在显著关联。前述江西某社区12 名街角青年中,4 名来自于单亲家庭,9 名表示不愿意与父母亲交流,或父母亲感情关系不好。因此父母应转变不适当的家庭教育观念,关注子女心理和行为变化,特别是在子女叛逆期;同时加强引导和困惑疏通,多以伙伴式关系进行交流,营造“抱持”的家庭氛围,在孩子发展过程中提供适时的认可和支持,永远以“没有诱惑的深情”爱护他们,确保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成长发展。
其二、学校层面。青少年的转折点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在此期间,其身心方面在社会中最易受到伤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学校应思政引领,围绕“育人”宗旨,让“伪”街角青年认识到,学校没有排斥、放弃、抛弃他们,而是充满冀望。同时提升教师职业素养,展现职业精神、以身作则,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生。
其三、社会层面。被排斥者之所以有亲社会行为,是因其心理驱使,遭排斥后激发了自身与别人友好相处的强烈愿望②张桂平、刘玥:《社会排斥对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9 年第3 期。。因此,政府各部门应强化联动,铁腕整顿,提升监管力,消弭亚文化、“泛娱乐化”行为传播的土壤;工信、文化等部门应净化互联网生态,宣传引导正能量;社会大众则应对街角青年给予宽容和理解,摘除有色眼镜,原谅他们曾经的幼稚、轻狂乃至堕落。
其四、司法救助层面。街角青年实施的许多行为并非完全是对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挑战,反而可能是对社会现象的反映或讽刺。作为政法部门,在管理、防范、打击时应发挥一定干预效能,协助各方指引他们回归主流社会。譬如完善矫正机制,加强事后跟踪教育考察,加强“网格化”社区管理,以及联合社区有意识、有举措的培养专业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参与到问题青少年救助工作中等等。
(四)权益保护角度的治理体系
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显著的反社会、失范行为始于青春期,亦止于青春期。因此,我们应基于对街角青年合法权益保护视角,整合社会各方力量,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街角青年权益维护事业①王建敏:《新中国70 年来青少年权益保护变迁与发展》,《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可从两方面加以建设。
其一、完善法律规范。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厘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法》等法律;制定《校园欺凌法》,严厉打击和惩戒相关校园暴力行为,重点防范校园欺凌、霸凌事件发生;完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预防和干预机制;对教师师德师风不正现象,加大惩处力度,严防学校、教师将偏差青少年推入社会边缘地带成为“街角青年”现象发生;及时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特殊或专门教育、“校园贷”等专项法律规定,规制整改“校园贷”等现象,从而消弭街角青年增多、权益无法得到根本性维护等问题。
其二、建全运行机制。一是建立事前预防型制度和健全各种帮扶、包容、事后救济机制,借助广大社会力量,增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利用多元传播渠道加强丰富多彩的内容宣传,完善舆情疏导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引导和化解因不利舆情带来的社会危机,维护街角青年权益。三是推行建立未成年人的独立刑罚体系。坚持依法治国理念和借鉴域外经验,通过“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权益;试行未成年人分级处理方式,加强对“街角青年”违法犯罪的改造、教育和保护;针对轻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完善少年司法检察制度,推行刑法外处遇或保安处分,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确立少年法庭独立地位等。
五、结语
街角青年作为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的一种较为典型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在与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博弈中,缺乏一定眷注和呵护,对其产生的一些问题缺乏有效的预防管理与善治,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部分青少年会在扭曲价值观的驱使下转化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而另一些却没有?其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有待未来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厘清。无论如何,“街角青年”是客观存在且不能漠视的特殊群体,而预防管理和善治“街角青年”的社会冲突需要社会各层面、各方力量的共同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