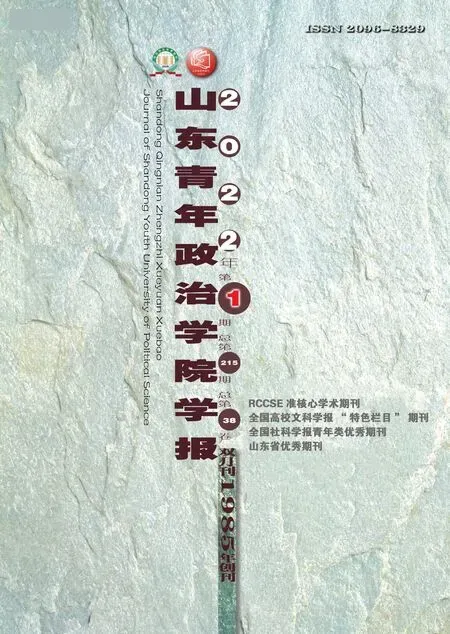复仇精神与革命文化的“落幕”之时:《铸剑》与《左镰》对读
李旭斌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青岛 266100)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关注《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祝福》等文本的启蒙精神和“国民性”批判对当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或是《伤逝》《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反抗绝望”的精神救赎。然而,新时期作家却对《铸剑》的复仇情节和复仇精神情有独钟;不独莫言,残雪也十分钟爱《铸剑》,她读出了小说内含的两种复仇,一种是“表面结构的复仇”,也就是亲情道德内的为父报仇;另一种则是“深不可测的、本质的复仇”,是指向自身的复仇。[1]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无传统”反叛姿态的忧虑,余华的《鲜血梅花》就是对《铸剑》这一前文本的“改写”,是新时期语境下对复仇叙事的“故事新编”,最终指向的是“自我投射”的“虚无”。[2]然而,始终对复仇精神和“打铁”情节念兹在兹的还是莫言,他先后多次谈到阅读《铸剑》的感受,并认为《铸剑》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3]。他每次重读《铸剑》都有新意,从“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4]到“看透了的英雄”[5],再到读出“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6]的“黑色”精神。《铸剑》如同一条河流的源头,沿着文学的脉络发展,流淌到莫言的作品里,莫言早期充满野性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酒国》,后期“大踏步撤退”的《檀香刑》以及“消除”仇恨的《生死疲劳》,都能见出莫言对《铸剑》的接受和改写。2017年,获奖后已经“沉寂”了五年的莫言携带着书写故乡土地和童年回忆的系列小说《故乡人事》①“重返”文坛,在《左镰》中,作者“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7]“打铁”情节背后是莫言从鲁迅那里承继的复仇精神,那么,《左镰》又是如何完成“复仇”叙事的?正在探索“晚期风格”②的莫言,或者说身处革命文化“落幕”的时代中,他在复仇叙事中是否表现了对革命、历史、人性的新态度?同时,《左镰》与《铸剑》在何种意义上产生了对话关系……这些都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复仇精神的原初隐喻:涤荡“旧我”,走向“新我”
莫言对鲁迅的复仇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阐释,《左镰》就是对鲁迅复仇精神的延续,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对话”关系。然而,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更热衷于谈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他对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接受,但是,莫言很早就指出,他读福克纳的小说“顶多10万字”[8],甚至一度“忘记”自己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阅读过马尔克斯。更多的时候,莫言谈论的是中国民间传统和鲁迅对他创作的影响,在谈到《铸剑》时,他认为:“《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这篇小说太丰富了,它所包含的东西,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9]可见,莫言是从《铸剑》中的人物入手,来理解鲁迅的复仇精神。与鲁迅之前的小说相似,《铸剑》的人物并不多但个个典型,眉间尺和黑衣人性格迥异,一个顾虑重重,一个坚毅果断,似乎是人性中相反的两极。1960年代,《铸剑》被编入语文课本,莫言最早从中读到了“冷如钢铁的黑衣人形象”[10],令莫言难以忘怀的是“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11]的外貌和如同“两点磷火”[12]般的眼光,黑衣人就像是为拯救存在性格缺陷的眉间尺而横空出世的“侠”,这黑色形象的描述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与黑衣人复仇精神相通的鲁迅,或者说就是鲁迅的理想甚至是化身,这也是黑衣人给莫言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黑衣人“宴之敖者”③也是鲁迅曾经使用的笔名,1924年,鲁迅编《俟堂砖文杂集》时就署名“宴之敖者”,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丸尾常喜看来,黑衣人的身份可以追溯到鲁迅作品中其他黑色人物系列,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过客》中的“过客”等。如果说眉间尺是子报父仇,那么,黑衣人为什么要复仇呢?为什么莫言认为黑衣人身上体现出了鲁迅的复仇精神?“宴之敖者”这样解释自己复仇的动机: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13]
当黑衣人话音刚落,眉间尺紧接着自断其首,二者的生命和使命实现衔接,我们可以将黑衣人和眉间尺看成是个体生命不同阶段的呈现,黑衣人是复仇的实际执行者,他的内心压抑着深广的忧愤,但他并不是报杀父之仇或血缘之仇,而是向“憎恶了我自己”的“我”复仇。即使这种复仇未必有手刃仇敌的快感,甚至要与仇人同归于尽,但只有通过复仇,才能涤荡令人“憎恶”的“旧我”,实现自我的拯救,也就是走向“新我”。我们认为,鲁迅的复仇精神并不是以牙还牙的生死对抗,而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忧愤和焦虑,由此产生了“人我所加的伤”的“复仇”,要完成这样的复仇,必得经过自我的蜕变。这类从“旧我”走向“新我”的复仇者形象,在莫言创作伊始就得到了继承。《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与《铸剑》的人物形象极为相似。黑孩有着“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14]黑孩就像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结合体,性格矛盾而又复杂。《铸剑》中的眉间尺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莫言也让黑孩以儿童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儿童“只能用一种窥探着的眼光去打量远远超出他们理解能力而他们又必须适应的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透过这样的儿童眼光,自然就有可能避免覆盖在现实生活上的谎言和虚伪。”[15]继而,不论是眉间尺还是黑孩,都会在认清“成人”世界后完成“复仇”的使命;当然,这种复仇不仅是外向的,更多的时候是内在的,也就是从“旧我”走向“新我”的过程。《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尽管遭遇饥饿与孤独的苦难考验,而菊子姑娘的情愫无疑唤醒了他内在的生命欲望和美好的生活感受,红萝卜在他的眼里“晶莹透亮,玲珑剔透”“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16],这个带有性爱暗示的心理意象隐喻了黑孩被激活的生命力,即使未来仍会遇到挫折,但生命主体将会追求超越的存在姿态以反抗绝望。如果说在表现复仇者形象时,鲁迅依托的是一个荒诞化的“理性”世界,那么莫言追求的是充分感觉化的主观世界。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嗅到几年前的气味,看到“晶莹剔透”、流淌着“银色液体”的红萝卜。黑孩的感觉世界占了《透明的红萝卜》中“故事”的大部分,他对苦难迟钝的忍耐力与他对色彩、声音、气味的感受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常感受能力的黑孩儿,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17],在这之后,充分感觉化的复仇者形象贯穿莫言的创作过程,像是《红高粱家族》为中华民族复仇的余占鳌、罗汉大叔,以及《我们的荆轲》中的刺客荆轲。
而《左镰》中的田奎,同样可以纳入从“旧我”走向“新我”的复仇者谱系,这也是小说中复仇精神的原初表现。与《铸剑》相同的是,在《左镰》中,莫言也没有将叙事的重心放在情节的推进和性格的转变上,而是用冷静和节制的态度描述了几个关键性的场景,像是“打铁”的场面、恶作剧的场面、田奎割草的场面。至于“故事”中的一些因果线索则被隐去,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这样的叙事策略是为了更好的凸显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也就是复仇精神。“左镰”在小说中是给田奎“私人定制”的镰刀,因为田奎的右手被父亲砍掉,他只能用左手拿着“左镰”割草。其实,田奎失去右手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情急之下的嫁祸,也是革命文化盛行之时不容辩说的结果。几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的恶作剧,却就此断送了田奎的一生。他不仅变成了残疾,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只能终日在幽森的墓地中收割野草。究竟是谁先喊出的那一声“打啊,挖泥打傻瓜啊”[18]已经无从知晓也无需知晓,因为失去右手的田奎已经默默承担了仇恨的苦果和历史的责任。田奎身体的残缺,本身也成为一种“无言”的诉说和历史的反讽,就像是“十年动乱给人留下精神和肉体创伤的原始见证”[19]。从某种程度上说,“左镰”就是田奎的象征,三个铁匠锻打“左镰”的过程呼应了田奎经历磨难的“复仇”过程。失去右手的田奎或许可以选择强力的反抗,就像《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和戴凤莲那种不顾一切的反叛;也可以就此颓废,变得更加沉沦,进而以自身的荒诞来对抗现实的荒诞;然而,莫言并没有安排田奎选择这两条复仇之路,田奎完成的“复仇”是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漫长而残酷的考验。田奎没有在失去右手后也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他信仰的似乎是民间的生存哲学——打铁还需自身硬,将仇恨和磨难看成是成长成熟前对自我的“锻造”,只有这样,才能让自身成为“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20]利器。而“最冷的和最热的”利器不就象征着莫言所说的“冷得发烫、或热得象寒冰一样的”[21]鲁迅一贯的复仇精神吗?就像三个铁匠“打铁”一样,复仇者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势必要伴随烈火的烘烤和承受巨锤的敲打,只有经受住这一切才能得到成长,田奎也在锻打中完成了指向自我的复仇,就像小说中的“我”好奇田奎是否惧怕坟墓和毒蛇时,他说:“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22]。
二、复仇精神的深度拓展:一出“清爽”的悲剧
《铸剑》凝聚着浓厚的侠义精神,严家炎先生甚至将《铸剑》看成是一部“武侠小说”,在他看来,“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23]。黑衣人的复仇,并非为了消解自身的恨意,他本身并不像眉间尺一样负有道德义务或现实仇恨,他追求的是复仇的本质或本质的复仇。莫言同样认为,眉间尺决然地自刎,并将自己的头颅交给黑衣人,“这种一言既诺,即以头颅相托和以头颅相许的古侠士风貌,读来令人神往”[24]。在莫言对《铸剑》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复从黑衣人出发来理解鲁迅的复仇精神,在他看来,如果说《铸剑》是对“原侠”精神的集中展示,而其中的黑衣人就是鲁迅的化身,黑衣人是鲁迅内在人格凝聚而成的侠士,鲁迅可以通过这个人物来实现指向自身的“复仇”。应该说,莫言对《铸剑》的解读抓住了这个精神实质,他看到了“真正的复仇者应该是鲁迅”[25]。
《左镰》中的田奎也经历了人与铁的锻打之道,在“火”的淬炼中成长起来,然而,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小说的叙事者“我”在文中起到的作用。《左镰》的创作主体莫言又是如何拓展鲁迅的复仇精神的?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小说的叙事者“我”或者叙事者“莫言”与现实中的作家莫言等同起来,但我们认为,作家莫言对鲁迅复仇精神的拓展正是通过叙事者“莫言”完成的,这是对《铸剑》“合于一”的复仇叙事的“改写”,同样也是对莫言此前复仇文本的“新写”。这是因为,在《月光斩》和《生死疲劳》中,复仇主体往往是单一而明确的,叙事者“我”有时不免陷入“操纵”复仇者的漩涡之中。但到了《左镰》中,看似“分散”的复仇主体分别承担不同的复仇要义,但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复仇,比如田奎的复仇是之前论述的涤荡“旧我”、走向“新我”的“锻造”;叙事者“我”的复仇是一种自审的忏悔意识;而作家莫言的“复仇”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26]的主体意识,特别是通过田奎和叙事者“我”,莫言传达的是他既同情“弱者”又同情“强者”的悲悯,他认为强与弱之间没有“定于一”的永恒而是不断辩证的转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铸剑》与《左镰》的“对话”关系。《左镰》中的多个复仇主体指向的是同一的复仇精神,即指向自我的复仇,因此,作家莫言就以一种“轻盈”的方式书写着原本“沉重”的复仇主题,让《左镰》成为一出“清爽”的悲剧。
此外,《左镰》中反复出现的“打铁”情节已经不仅是叙事的情境,还成为展现人物命运的载体,甚至是作家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打铁”是叙事者“我”和作家莫言的复仇叙事展开的契机,“打铁”情节负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铸剑”。鲁迅最早是在1927年4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篇小说:“星期。雨。下午浴。作《眉间赤》迄。”[27]小说首发在这一年的《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的第八、第九期上,题目为《眉间尺》;只不过鲁迅在1932年将其收入《自选集》时才改为了《铸剑》。鲁迅对书写“铸剑”的过程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只用了几笔匆匆带过,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也未见“铸剑”的描写,但鲁迅还是给宝剑赋予了象征的意义,“宝剑在作为侠客文化的代名词之外也是武的象征”[28],这与《铸剑》和黑衣人的侠义精神有关。但到了《左镰》中,“打铁”的场面铺排都是通过叙事者“我”的回忆引出的,“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29];更为重要的是,“我”在回忆“打铁”时,倒叙穿插了“我”当年参与的那次恶作剧,“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30];田奎也就是在这次恶作剧之后失去了右手,只能在墓地里用“左镰”割草。其实,莫言使用的是明、暗两条叙事线索,这两条线索的交汇点就是“左镰”,它一方面是“打铁(镰)”的原因——田奎因为“我”和“我哥哥”为躲避父亲的惩罚而嫁祸于他,从而失去了右手,需要定制特殊的“左镰”;另一方面,它又是“打铁”的结果——田奎在磨砺中得到了成长,同时也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而,每当“我”回忆起“打铁”的场景时,就会联想到是“我”造成了田奎的残疾。那烈日火光下一锤一锤的敲打,不仅造成了田奎的痛苦,也代表了“我”的自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左镰》反复出现“打铁”情景的原因,“打铁”成为了我内心深处对田奎的不安和愧疚得以展现的过程,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我”完成复仇叙事的契机,耳边回想起的“打铁”声是自我反思的流露,这当然是一种指向自身的“复仇”。莫言曾经说过,“知恶方能向善”[31],“我”对自己内心之“恶”的解剖随着一次次“打铁”情节的展开而逐渐深入,到最后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对田奎的敬畏。如果说当年“我”在父亲和刘老三的“凝视”之下迫不得已将田奎作为替罪羊,彼时的“我”暂时摆脱了惩罚,似乎是恶作剧的“胜利者”,田奎作为地主家的孩子,自然没有辩驳的机会,失去右手的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打铁”传来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却是一曲“胜利者”的悲歌,也就是莫言书写的一出“清爽”的悲剧。“我”早已不是什么“胜利者”而是赎罪者,观看“打铁”就是“我”忏悔赎罪的过程。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他的《性史》中曾经指出:“忏悔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特殊的话语方式,即‘话语仪式’。”[32]也就是说,赎罪者的忏悔话语本身蕴含着一种权力关系或者结构,这种结构建立在忏悔主体与忏悔客体不平等的关系上,忏悔话语的背后明显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时代,“我”即使家庭出身再好,也不能高高在上,像当年一样用“话语”权力给田奎造成伤害;相反,“我”和田奎的权力关系此时发生了颠倒,田奎的无辜让我无法逃脱历史和良心的罪责,所以,书写“打铁”情节成为我不断进行忏悔的“话语仪式”。
《左镰》中叙事者“我”的存在,是莫言“把自己当罪人写”的一次实践。莫言安排了“我”自责内心的“恶”,这是作者莫言在复仇精神上对鲁迅的拓展,鲁迅对生命的热爱是与对毁灭生命的“恶”的憎恨相联系的,正如他所说的,“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植于更广的爱”[33]。鲁迅对他者和自我生命的珍爱,让他敢于直面“恶”的人生和人性,《铸剑》以一种狂欢化的形式——三头共葬、民众送葬作为复仇的结束,“鲁迅里面有一些调皮的东西和因素,跟狂欢差不多的”[34],鲁迅在《铸剑》中的笔法充满欢乐和游戏的快感,但他传达的现实却是荒诞的。戏谑的轻快是鲁迅对沉重的现实长期清醒的认知,也是对自我的审思和批判,是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自觉关注,是“向内转”用血凝聚而成的复仇精神。因此,黑衣人不惜牺牲自己来达到复仇的目的,这是毫无保留的自我忏悔,更是对自己毫不留情的批判。莫言所做的是“对鲁迅的气质和个性的呼应”[35],他将自己放置在历史回忆与现实社会中进行灵魂的拷问,与《左镰》一同发表的《地主的眼神》,同样也是因为“我”的无意之举——一篇三年级小学生的作文,却成了“炮打”地主孙敬贤的“大字报”。年少的我,对“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36],可多年之后,当“我”反思自己对孙敬贤造成的伤害时,也难掩自责和懊悔,“我至今也认为孙敬贤不是个心地良善的人,但我那篇以他为原型的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尤其是因为我那篇作文,让他受了很多苦,这是我至今内疚的”[37]。莫言复仇精神中的主体意识在鲁迅的基础上既有延续也有变异,在《晚熟的人》中,最出色的部分已不是他先前小说中对生命意识的歌颂,而是对主体意识的哲理思考以及对人性“隐秘”的探索,同时,在“同情弱者而又同情强者”这一点上也有对鲁迅的致敬。在莫言看来,弱势群体值得同情的背后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缺陷,而仅因为处境的弱势而占据精神的高地是他不想看到的,他一方面意识到弱者的可怜,也意识到强者的不易。他超越善恶的道德评判,有着同鲁迅一样对人性的悲悯,记得鲁迅在翻译《穷人》时,曾在小引中谈到:“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38]
三、复仇精神的主体反思:“虚妄”的救赎与“融合”的默契
王富仁先生认为“剑”的意象涉及到鲁迅的“革命观”与反抗精神,同时也隐括了“立人”思想与革命文学的论证。而我们认为,《铸剑》中鲜明的意象其实带有丰富的文化隐喻——“剑”是权力的隐喻,干将莫邪锻造宝剑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的,而是要献给“王”;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仇行为象征着革命,死亡意味着革命的“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革命与专制权力的同时灭亡,在鲁迅看来,“同归于尽”未必就是复仇(革命)的胜利。这里隐含着鲁迅对复仇精神的主体反思,或者说,是他对革命文化的某种忧虑。《铸剑》充满了复仇的因素,却在仇恨中夹杂着绝望与希望的矛盾,正如顾虑重重的眉间尺一样,面对红头老鼠对家具的咬啮和对睡眠的影响,眉间尺恨,当面对弱小的生命时,眉间尺怜悯;面对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眉间尺恨,当审视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时,眉间尺怀疑……这些犹豫与焦虑都一步步地激化眉间尺心中的“恶”,他除了复仇别无选择,而这注定又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39]。然而,横冲直撞的刀剑相逼在现实的条件下无法实现复仇的计划,他只好迂回地达到复仇的目的,也就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为代价,让黑衣人代替自己复仇,毕竟肉体的消亡在一个只剩仇恨的人眼中不值一提。那么,为何认同“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40]的鲁迅让眉间尺和黑衣人选择了用迂回的方式来完成复仇呢?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铸剑》写于“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创作时间从“1926年10月”[41]到1927年4月,鲁迅在1927年4月3日的日记中提到的《眉间赤》应该是小说发表前的定稿。可见,《铸剑》并非是鲁迅对“清党”的复仇,但鲁迅对复仇精神或革命文化的反思却早已产生。从鲁迅的思想史来看,1926—1927年的鲁迅正处于思想的低潮期,《野草》也是写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野草》来窥见他此时的思想倾向。怀疑的悲观主义贯穿于鲁迅的创作历程中,而在《野草》时期更为显著,他对革命文化产生了怀疑,鲁迅此时的心境变得“分外地寂寞”,甚至是空虚,其实,鲁迅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在经历过一连串的“自欺的希望”和“空虚中的暗夜”之后,此时的他认为,大刀阔斧的“复仇”也许是畅快淋漓的,但是往往只会两败俱伤,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42]《铸剑》的底色是一种对革命“虚妄”救赎的悲凉,因此,小说中的眉间尺最后用牺牲生命的代价换来复仇的胜利,以看客围观的方式作为结尾更具讽刺意味。同样,《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为了养活子女而饱受苦难,甚至做出违背道德的事,但这些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可与同情,反而招致了冷笑与谩骂;但她不再指望“虚妄”的救赎,而是独自走向荒野,“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43],她用这种“无言”的形式倾诉心中的怨恨与诅咒,以完成“复仇”的目的。
《铸剑》其实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鲁迅将铸剑的过程虚化,隐去干将莫邪的名字,只以眉间尺母亲的口吻回顾往事。可以说整个故事是模糊的,并未指向具体的历史,由此,鲁迅的历史观也得到彰显,这是一种同归于尽、不分你我的虚无的终极历史观。《铸剑》所体现出来的献身牺牲的复仇者谱系以及超越个人恩怨的复仇观都和鲁迅的历史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观隐含着对复仇观、创作观乃至人生观的思考,莫言认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并不是以牙还牙的对抗,而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愤恨与憎恶,是对“人我所加的伤”的报仇。“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鲁迅把自己同样放在复仇的对立面,对自己的批判毫不怜惜,由此产生的“内省”和“忏悔”是对黑暗现实深刻的复仇体现,这是革命文化“落幕”之时经鲁迅改造的现代的复仇观。“复仇”绝非为了追名逐利,而是对自身的省思,同样,莫言针对新时期现实生活中追逐名利的现象,或反讽或批判,重新编写荆轲刺秦的复仇故事,完成了《我们的荆轲》这部以复仇为主题的话剧。在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复仇话剧中,没有了血缘的缠绕,复仇指向了其本质,即“向自身的复仇”。然而,与鲁迅对复仇精神的反思不同,在受到仁慈母亲的耳濡目染与民间文化的沁润影响之下,莫言变得温和,形成了“仇必和而解”的复仇观。在莫言看来,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并不能斩断仇恨与恩怨,身负仇恨的人永远不会逃脱自我折磨的阴影,反而容易成为仇恨的傀儡。《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六道轮回”而不能转世投胎就是因为无法摆脱报复的轮回与仇恨的记忆,因此,只有告别过往,与仇恨和解才能解开生活的死结。
与《铸剑》具有相关性的《左镰》也体现了莫言对复仇精神和革命文化的反思,小说虽然没有明确时代背景,但通过人物的对话,我们却可以推测田奎对贫下中农孩子的“人身攻击”,很有可能会在极“左”政治的年代上纲上线为对革命的反动。当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的风向标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处在人为制造的敌意与仇恨的紧张氛围中,似乎每日都在上演“革命”对“反革命”的“复仇”悲喜剧。在《左镰》这篇小说中,身处政治边缘地位的地主阶层,田千亩不想给家族和个人再招惹是非;面对气势汹汹,前来“复仇”的贫下中农,他无法承受想象不到的压力,又不敢将这种压力转向“出身好”的刘老三,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恐惧、愤怒和暴力发泄在无辜的田奎身上。田奎那只缺失的右手,隐喻的是一个阶层的“失语”,是占统治地位的所谓“革命”阶层对“反革命”阶层的规训和惩罚。其实,福柯就认为政治权力话语对人的作用最终要在肉体上表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44]。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明明学习比“我”二哥还优秀的田奎,为何只能早早辍学在家,用“左镰”从事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割草”似乎是对田奎身心自由的限制和约束。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左镰”是莫言对革命文化的反思,现代性的“革命”激发了人性的邪恶,而人性的邪恶却葬送了革命的“现代性”。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时代,田奎本来可以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复仇”,但他默默承担了革命文化加之于他的伤害,以和解的态度对待仇恨的记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发掘出莫言执迷于“打铁”情节的深层原因。他相信“打铁”不仅象征了田奎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仇恨的消弭,“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45]。在小说的结尾,田奎竟然接纳了“仇人”的女儿欢子,这是命运的纠缠和救赎。最后的一个“敢”字,说明仇恨早已消失远去,留下的是温情和感动。
莫言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时代对复仇精神的反思,也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从创作伊始,他书写的便不是史诗性的英雄历史,而是以平民或底层的视角审视历史,用民间化的语言区别于“十七年”文学二元对立的历史“控诉”。他曾经说过:“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46]《月光斩》正文的结尾又变回了书信寄语,整部小说没有涉及复仇、反动、杀戮的过程,只有无奈和无聊的现实,人物只能继续被控制,“月光斩”不再含有敌意仇恨,而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只剩下没有意义的恶作剧。在《左镰》中,莫言对待历史中的仇恨记忆更加宽容,更具有“与历史和解的意味”[47]。由此可见,鲁迅和莫言尽管都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消解,但他们所理解的“传统”并不一致,这也让二人对复仇精神的反思呈现出差异:一种是虚妄的,一种是融合的。虽然他们的历史观有些不同,但“虚妄”与“融合”最后指向的都是仇恨的消弭,只不过方式不同,鲁迅是通过肉体的消亡,而莫言则是一笑泯恩仇,不再执著于复仇行为本身。
莫言曾谈到《铸剑》“跟我的生命经历有某种契合”[48],作为黑衣人的化身,鲁迅自然也和莫言有着关联,而黑衣人“黑得发亮,冷得发烫”[49]的精神也流淌在莫言的文字中,成为莫言创作的一部分。通过《铸剑》与《左镰》的对读,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时代,鲁迅和莫言对复仇精神的认知、应用和反思。莫言将鲁迅的“黑色”精神转变为自身的“和解”态度,从“复仇”起始到仇恨消弭,他们对复仇精神的书写,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符合个性的创造。这两部作品的“对话”,不仅可以彰显鲁迅与莫言的精神通联或是莫言对前人的“变”与“不变”,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五四”新文学精神在今天的延异。
注释:
①《故乡人事》系列首发在2017年5月《收获》创刊60周年的纪念刊上,包括《左镰》《地主的眼神》和《斗士》三个短篇小说。这三篇作品后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中。
②这是王德威对莫言的新近评价,他借用的是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中的理论,但在论述过程中前后矛盾,并混淆了“晚期风格”和“晚熟”状态这两个并不同一的概念;但他认为《晚熟的人》不仅是莫言对前期创作的延续,同时也是新的探索,这一点可以深究。参见王德威.晚期风格的开始——莫言《晚熟的人》[J].南方文坛,2021(02).
③对“宴之敖者”的解释有很多,其中一种是“宴之敖者”生活在“汶汶乡”,“汶汶”指昏黑,昏暗不明。
——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