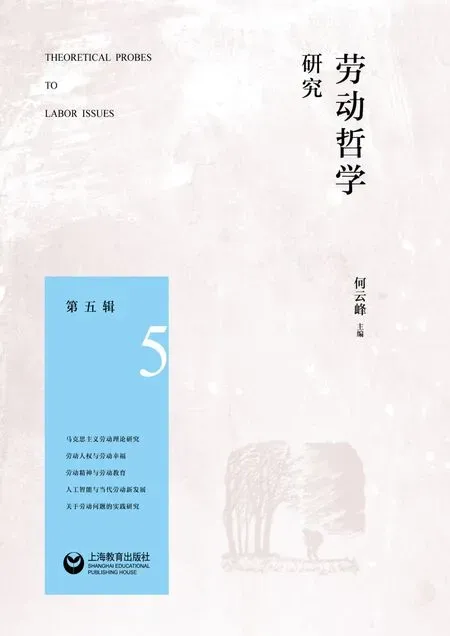日常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论具体劳动的道德情感及情气涵养①
陈 兵,董朵朵
现代汉语“劳动”(labor)一词是舶来词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劳动”内涵则主导了人们对这一词汇的通俗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的考察,分别是从哲学心理学的浪漫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冷静分析两方面综合展开的,这在他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巴黎手稿》《资本论》中可见一斑。马克思使哲学关注具体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实质予以否定性揭露,并就共产主义未来性的“自由劳动”做了预言式的讨论。然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还是“自由劳动”的思想,都不能代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问题讨论,因为“如果没有对中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就不会有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1)叶险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学术界》2019年第2期,第14—15页。。最早反思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中国学者是当代哲学家李泽厚,他在《美学四讲》中提出以审美心理的“情感本体”克服过度技术化导致的存在异化、追寻诗意劳动的观点(2)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8—86页。李泽厚所理解的感性是通过劳动实践其也可以成为涵融理性于其中的积极的、主动的审美情感活动。与马克思不同,李泽厚是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和公有制经济的文化语境中来谈论中国的劳动,把传统的审美心理作用于当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他并未有详论的审美情感与诗意劳动的论断来指明本土语境中的劳动哲学叙事的基本方向和精神。。这一思想创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当代中国的劳动哲学叙事,除了继承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还要积极寻求内在于个体生产活动的情感体验与生命领悟。此意味着,这种针对劳动的内在心性体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个性心理情欲(弗洛姆、马尔库塞)、哲学直观(海德格尔)出发进行否定性批判存在本质区别。劳动的内在心性体认所要思考的问题是“日常劳动幸福如何可能?”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具体劳动中的道德情感塑建和情气涵养,以此呼应时下流行的“劳动幸福论”的先验伦理学目标(3)何云峰:《劳动幸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1页。其第一章第一节题为“劳动幸福论的逻辑假设”,阐述了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的四个核心主张和两个原初假设,毫无疑问采取的是先验预设的理论进路,断言劳动与幸福具有“天然的联系”。但问题在于,劳动与幸福的这种“天然联系”在现实中是如何可能的?。笔者将立足于古典情理圆融的生命学问传统,从情志感发的中正平和视角去揭示个体在具体劳动操作情境中的情气涵养与德性自觉,从而开出有情生命因劳动安身立命的诗意幸福人生。
一、礼乐文化中的情感性劳动
首先,通过反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劳动诗意的论述所植根的启蒙理性立场,可引出本节探讨的主题即礼乐文化中劳动的情感性特征。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劳动,并非纯粹理性的科学活动,而是感性的生命活动。这时的劳动体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形式,由于亲近自然和孕育于家庭的因素,人间温情充斥其间,不可避免地带有田园诗的韵味。在东西方,农业劳动皆偏重情感性而呈现浪漫主义的特征。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古罗马的维吉尔等人的农事赞美诗,古典中国《诗经》中的农事诗和晋人陶潜的农事田园诗都是其明证。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导言中,恩格斯以田园诗的笔调,刻画了宗法家庭关系下农民劳动的平静、祥和、恬淡,并对此种生存样态作了启蒙理性的批判。“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恩格斯认为封建式的农奴劳动的诗意是非人的,缺乏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如果冷静对待启蒙理性立场,似可质疑此种论断而有一个保留的态度,即过着男耕女织、守望相助的农业劳动生活也是“人的生活”,此中自有一定真理,非启蒙理性可完全概括。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要批判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及其农奴制度,以及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各种东方形式,而非“其温情的一面”(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马克思甚至设想,通过合理的所有制以否定封建的生产关系,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关系。。在基督教传统中,农民对劳动有着崇高的解释:土地是上帝的,劳动是为了供奉神,上帝、神和自然界是劳动的主宰。力图确立劳动者主体性的马克思,自然不能容忍宗教化的劳动阐释。“神从来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自然界也不是。况且,在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日益受自己支配的情况下,在工业奇迹使神迹日益变得多余的情况下,如果人竟然为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那岂不是十分矛盾的事情。”(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5页。马克思坚持启蒙理性的目的是强调人在劳动中完全彰显自己的主体性,把神迹祛除殆尽,尽情体验生产的乐趣、享受商品带来的满足。他认为“讨好神恩”与“享受生产乐趣”是互相矛盾的事情,这意味着工业化的机械性劳动只是人的理性和激情运动的产物。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是,启蒙理性过度发展造成的神人区隔,神性作用在劳动生产中的废黜使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神圣基础消失不见,从而造就人的自我膨胀的科学技术的神话。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既理性又温情的情理俱得的劳动实践形态,只能由农业劳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历史扬弃而产生。(7)质言之,劳动主体在摆脱私有制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中才可以积极充分地运用并发展自己的理性和情感。农业劳动缺乏启蒙的理性,雇佣劳动则失于情感的压抑和消极性对抗。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揭示诉诸心理学的体验,但《资本论》中对“劳动”“自然”的哲学本体论阐释,其理论立场和修辞却是客观理性的,并没有贯彻上述情理俱得的生命存在的思想。马克思仅把劳动阐释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性运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页。无论如何,我们从“物质变换的过程”“自然力”“自然物质”等字眼中看不出理性主体关于“温情”的丝毫痕迹。所以,近代西方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以理性化、功利化的劳动将具有神性的自然贬抑为物质世界。马克思承认土地(即自然)作为物质财富“源泉”的地位,他也只是从人类利益的方面去认定,而不是像东方文化那样,把“自然”作为人的道德情感崇拜的“造化之父母”来肯认。劳动不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精神性的、情感性的生命感通。不过,此种精神性的、情感性的生命感通不仅是宗教性的(此一点为启蒙理性的宗教批判所彻底否定),还是世俗人伦性的。
如果进行跨文化的考察,马克思在“情理俱得的劳动”问题上语焉不详,受制于西方天人隔绝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答案只有到中国“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中寻找,古典儒道传统提供了农业劳动寄情自然的生命超越智慧。换言之,在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受动的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激情、热情的感性(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4页。,在儒家看来是可以通过合乎礼乐的生产生活行动,涵养成以亲情为本根的伦理化、审美化的积极主动的感性。此情理俱得的感性,使人从物我对立的对象性追逐中超脱、挺立出来。得益于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古代中国人以礼乐斋戒仪式净化、整齐自身庞杂、汹涌的需要和激情,使感性知觉和感性意识纯粹并升格为光明肃穆的人间亲情,开启了感性合理化和社会化的德气涵养路径,即将自发的喜怒哀悲等具有好恶意向的情气,转化成有秩序条理的伦理性的类型化道德情感。《礼记·乐记》之《乐本篇》便盛言礼乐之道引导喜怒哀乐悲等情气归于性情之正。关于人的感性与理性在行动、实践中的相互转化、融通和一体的道理,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哲学的独特贡献。(11)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续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页。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则不可能,比如康德就认为人只有感性直观而上帝才有理智直观。
那么,将以操纵工具的社会活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放在中国礼乐文化背景中去阐释和理解,其将获得一定的重置、调整。要言之,劳动是人以工具性活动为中介体证“自然”神性的情理交融的生命过程。而劳动生产过程延续着祭祀性特征,劳动者将生产成果归功于天地造化而不据为己有,人不过是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之情。例如在礼乐文化当中,就有严密规定节制各种劳动生产的祭祀,如就有籍田礼、祭祀社稷、报赛礼等各种农祭礼仪庆典,祈求养殖牲畜健肥的裯祭,祈求做工顺利成功的行业工匠祖师爷拜祭,等等。在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劳动涵摄于祭祀之礼当中而不是相反,由于这种特殊的祭祀氛围,劳动成为人们始终面对一切神祇或祖先鬼神的诚敬行动,而劳动产生的物品、财富则为仰仗祖先德业获得的福报。(12)王一胜:《礼仪变迁与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该文指出,在劳动者看来,福报不能只归功于自己的劳力,毋宁还是天地神灵或者祖先鬼神对辛勤专注劳作的恩赐。即使在传统社会的工匠行当中,手艺人给主人家做活并非简单的劳动力的买卖,还意味着高超精湛手艺劳动中的德行肯认与嘉奖,因此工资的支付与收受极为讲究,以免辱没、亏损祖先和行业祖师的荣耀,从而形成手艺人与主人家的衣食父母的关系。李泽厚认为,人类祭祀中具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诚、畏、敬等情感,其依据是经验性的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或“大写的人”),即对具体的时代、社会、民族、集团、阶级等背景和环境下的特定群体的经验利益、幸福的观照和领悟,它可以发展为修齐治平的仁爱道德情感,也可以承接康德先验理性的“绝对律令”。(13)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因而在劳动中前定的这种宗教性情感基础,又蕴含总体理性而体现个体性特征的情感化理性或理性化情感。
劳动的情感奠基包含了人为什么劳动、怎样劳动和劳动如何等全部劳动过程,它将紧扣人的具体内在情感体验去解释,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生产的乐趣和欲望的满足”。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页。。紧接着马克思援引了尼古拉斯·巴尔本的话:“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满足精神的需要。”(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48页。可以看到,马克思肯定了人的部分欲望的正当性,但马克思不加区别地对待精神需要则不可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肯定了“饮食男女”为人之必需与必然,但由于人的欲望无止境,因此强调礼对欲望的节制。(16)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1—153页。由此,我们可以引申,要使商品始终能够正向地满足人的需要,欲望则要节制,而人在劳动中不仅生产着自己的需要,也在节制需要和欲望的劳动中生产着自己的情感。
二、当代语境中的劳动忧患意识
对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情感状态的考察,即日常的劳动幸福体验如何可能,成为劳动哲学叙事不可回避的话题。摆脱了资本束缚的劳动者,不只是出卖自己每日定额的劳动力,还要对自己的工作环境、生产节奏有情感的融入与体会。换言之,劳动者自由地劳动,是介于需要与享受之间的一种既功利又审美的生命活动。与马克思所经历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处于怨恨、对抗状态的情感色调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则在劳动中获得情感的自由舒展,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亲密的而非对抗的,整个生产氛围像团结的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李泽厚说:“我不赞赏现代浪漫派对科技工艺的感伤、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不必去诅咒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而是要去恢复、采寻、发现和展开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中的诗情美意。”(17)李泽厚:《美学四讲》,第85、99页。显然,李泽厚关于劳动的关键阐发在于否认现代生存苦难与科技工艺之间的必然联系,尝试探索工业化劳动操作的审美维度,主张劳动过程中的诗意体验和幸福感受。换言之,李泽厚主张劳动过程中情感的积极性正面表达及超功利的审美升华。当然,劳动者审美情感的自由运用是基于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倾注和美学训练,而个人原始情感冲动充当生产世界诗情美意的催化剂。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关于劳动的诗情画意的哲学预言,终于在二十多年后得到迟来的回应。(18)详见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一书,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关于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的诗歌选集,其非凡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劳动者在现代工业的生产制度中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情理圆融的生命态度,展现了劳动的审美艺术维度。当代劳动者极其艰涩却又富含生机的劳动诗歌,开辟了劳动叙事的新方向。
究其实质,本土语境中的劳动伦理性及其情感奠基,开辟了贴近劳动者本身的关于劳动的内在理解向度。在马克思将劳动客体化为体现时间的“量”的劳动力的外在考察之外,还发掘出一条劳动的情感化的思想脉络。但是,劳动的情感奠基并不直接导致劳动的诗意,而是由对劳动主体生命的尊重和伦理责任去激发对劳动过程中风险性的“筹划”和“戒惧”,从而产生劳动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下面考察劳动的灾难性、分析劳动者“忧患”意识及其情感理性化何以可能的原因。
劳动有时是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肯定性过程,有时也可能是人器俱伤的否定性运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集中于建筑、加工制造、服务等基础性行业,这些行业因劳动强度大、生产安全系数低、环境恶劣等特征,安全事故高发,工人生命遭受伤害甚至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的背后是血泪斑斑的工伤历史。(19)刘开明:《身体的价格:中国工伤索赔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页。尽管研究者们从生产管理、法律救济、文化反思等方面谈论工伤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如此广泛、持续而严峻的社会问题刺激我们反思本土劳动哲学的理论结构与思想指向,即在承认劳动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肯定性方面的基础上,揭示劳动的否定性方面,也就是与创造性相区别的劳动的灾难性,为劳动道德情感的塑造寻找可能性。(20)一般的劳动损伤,如表现为劳动力耗费的工人筋肉、精力的损耗,是劳动过程的正常现象,这个马克思就劳动力的生理极限和道德极限问题已有过论述。工伤作为非正常的劳动损伤,则是由生产资料的严重耗损和生产管理中的人为失误共同作用引发的必然性劳动损伤导致。这里所谈论的劳动的否定性,不是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指挥劳动的“物化”现象,而是指一般劳动过程中由于操作机器的技术失范导致人身心受创伤的工伤遭遇。从本质上看,工伤是人与机器的借重关系向侵夺关系的畸变,是劳动的“自然”向不尊重生产操作规律的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报复。古语有言,人役物的最高境界是物成为人的亲密伙伴,人物各得其宜。役物而不伤物,亦不自伤,即“君子不过乎物”(《礼记·哀公问》);“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劳动安全事故作为一种偶然的必然性,可以通过劳动主体的“忧患意识”杜绝。
劳动的情感奠基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盲目乐观,相反意味着由敬畏情感的反身而形成的对主体操劳自身生命的忧患意识和劳动灾难的风险预感。前面已经提及,劳动成果事先在工人的头脑中“观念地存在”,乃是理性的纯粹运作。劳动的情感奠基,则是要人们在情感认知中直面劳动过程中灾难的可能性,意识到机器“利维坦”的狰狞面目,由此而生敬畏以克服对未知的劳动命运的恐惧、不安情绪,促使人们为正常的劳动准备敏锐的知觉和平稳的情绪状态,保持劳动过程中的精神专注。敬畏之情也是开启劳动者谨慎、规范地操纵机器的前键,把劳动者的身体从血气散漫的休闲状态调整为高度戒备的工作状态,以备随时流畅而迅速地潜入机器的运动节奏中。而程序化的机器操作流程是纯粹的理性化推演,工人的身体行为必须符合这样的机械化的理性过程。这一过程越严密,身体的形态变换和机器的开阖翕辟越一致,人与机器的和谐关系才有一个可能的场域。关于此点,可与人伦中孝子的忧患意识相联系,在儒家的人伦践履中,孝子思父母养育之情,便有很强的忧患自保意识。“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由孝子的这种重孝保身的忧患意识推及劳动生产,我们可以发现劳动者保身的忧患意识不仅来自对亲人的责任,还有他们为“天下”安全地持续生产、服务的先验情感承诺。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只和机器照面,却因为祭祀性情感在生产过程中的渗透使劳动仪式化,实现了和亲人生命的整体性的先验感通。敬畏之情还能激发人类原始而超越的见微知著的察觉能力,这种敏锐的感受力是受理性分析能力锻炼而形成感性直观能力,其往往能超前地感知事物的发展情势、细微端倪。中国古人对事物的初始发展进行极为细腻的辨别,区分事物端倪中消极的可能性,并且趁它们萌芽的脆弱时期进行具体的对治,从而充分掌控事物的发展趋势并作引导。“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昔者荀子以性恶设定来预估人性发展的消极性趋势,以此形成尊师、隆礼和重法的积极防范性教化措施。与此相同,对劳动灾难性的预感和觉知,事实上也是工人进行自我保护的生命策略,而劳动过程将紧紧围绕克服劳动灾难即预防工伤的主题严丝合缝地展开。
然而,工伤之偶然性、灾难性使劳动者不得不洞见到个体生命的脆弱,以明“应物而无伤”的道理。“应物而无伤”是指人在与物的机械性交往中既不浪费物资的功用,又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为外物所奴役、桎梏。具体言之,其指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是一体的血肉联结,此必以人对工具、机器的安全驾驭而规避风险为前提。但人总有侥幸、因疲惫而疏忽之时,所以发生机器伤人的状况,此即为人与机器矛盾斗争的特殊状态。马克思之所以力争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以及强调工人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就在于承认人之体力和精力有特定的生理极限,而必依据此生理极限节制机器的生产节奏以适宜工人的正常劳动,避免劳动伤害的发生。工人的超负荷劳动无异于对人的折磨,并且会使工伤事故易发。“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未开/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产品。手……压烂/中指及无名指/中指二节,无名指一节/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21)谢湘南:《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见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220页。此诗充满着强烈悲愤的工伤抒情性叙事,刻画了女工因过度劳累而违反安全操作程序,手动脱模所遭遇工伤的生存情境。啤机的运行速度飞快才能产生高额利润,但其一合一闭总有停滞、故障之时。女工既已习惯机器的快速飞转,手动违规操作非不知工伤之害,而是异常的工作时长导致身体疲劳,才使她遭遇断指的祸患。由此看来,欲达到劳动的“应物而无伤”的生命自由状态,应当在充分了解机器性能、节律的基础上审慎把握自身劳动的快慢节奏,创立合乎生命自然节律的生产制度和营造体现忧患意识的文化氛围。
三、具体劳动中的情气涵养
不过,工伤的偶然性又决定了主体须有直面劳动灾难的态度,在当下身体的残缺中求心意的端正,避免怨恨、怀疑、懊悔等消极情绪的郁积不化,而持守情气的顺畅平和。人在此遭逢的偶然性中方能体察到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和有限性,体会到生命的可怜和生存的悲剧性。其特殊性在于,个体的切肤之痛、亲人的嫌弃、生活不适、后悔、自责、虚无感、荒诞感等生活的情感性体验如此深切芜杂,这些交织在一起反复汹涌的内在力量完全是个人式的,即便是形成语言、文字也很难为他人所“感同身受”。有此情感体验的特殊性,“残缺”的劳动者被忙碌着的、一般的群体所抛弃而成为游离在生产—社会之外的“天地之弃才”。由于其劳动能力的丧失造成自身社会性(以出卖劳动力为务)的无所附着,开启了个体以总体的一分子重返历史总体的回归运动的契机,即通过对工伤带来的消极性情感体验的条理、涵化和提升而确立恒定的道德情感的生长方向,以实现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挺立。要建立这一向上的道德主体性,必明了生命“栖息”于机器生产的有限性和中介性,以瓦解生命的功利执着而关注于自身的情感与德性,恢复自由活泼的生命本性。理性的执着乃根源于人对自身欲望的无限夸大,人承认理性的有限是觉悟节制欲望的必要。所以如怨恨(对机器、制度、管理人员)、懊悔(对过往的错误的生产行为)、自责(对处于过去状态的不可逆的自我)等外求悬空而无着落的情感欲求,因欲望有节制趋于恒定自持方能裁减或收摄,向内凝聚为在我一身的澄明、平定的情气系统。要言之,人于工伤的消极性的情感体验中为生命的特殊性和有限性所警醒,从而开启个体经由劳动灾难性进至自身情气舒畅化的道德主体性豁显之路,就自然切中了劳动过程向情气涵养的“情境”转化的关键。
尽管劳动作为目的性的活动,因强调理性的密集运用,而持久地形成对情感的贬抑和压制,但情感始终是统摄劳动过程的弥漫性因素,其伴随劳动过程逐渐理性化并形成超越性的道德情感。也就是说,劳动为人的情感的道德性养成提供了充要条件,劳动即是道德践履。
当然,揭示劳动之为道德情感生成的内在省视维度,并非意味着与以人的日常亲情交往乃道德培养之根本的儒学观点相违背,反而是对后者的肯认及批判性考察。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观念,这是本土语境下劳动的现实基础,即劳动成为养生送死并摆脱家庭贫穷的生活方式。但又要注意到,从源头上看传统宗法道德是社会化并不充分的氏族部落生存的情感体验,是包裹着一层巫术礼仪面纱的人文理性。因而前文重提劳动的祭祀性并将其放在道德情感的维度来考察,就是要在劳动这个“情境”,即社会化程度极高和理性充分发展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物(生产原料、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三重关系脉络中分析劳动者的道德情感活动,此亦即李泽厚所说的“内在自然的人化”(22)李泽厚:《哲学纲要》,第5页。。因而我们便获得对“劳动”更为深刻的理解,即在理性化的目的活动中求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我的身心一体。而情气条理化、功与德相称和超然物外则是劳动之为道德践履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劳动创生了人的情感,开启了原始生猛的情气力量的条理化过程。劳动过程在其内容、形式和节奏变化等方面所含有的节律性,会赋予劳动主体的内在情气活动以秩序化的层次和结构。人的混沌、微妙和幽暗的情气活动开始分化、分流和多变,以结构性的动态系统透显于内在心灵世界中,从而形成与具体情境氛围相关联的明晰而准确的情感体验,为人的意象性意识即形象思维所捕捉和确认。这一创造性的活动过程,犹如宋真宗的《送张无梦归天台山》所云“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但其归宿则是突破一切固定形、势窒碍的轻浮流变的自由运动。情气自身的条理是由人的社会化生产活动的具体规律和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例如劳动最初的愉悦感体验就来自人的身体力量在特定方向上的密集输出形成的有效矢量所带来的通透、充盈的轻快感:开启罐头的有力一拧、对烧红的铁块的节律性锻捶、瞄准猎物的命中性的一次投刺等经典性的动作行为。但此处我们不欲对人的喜、怒、哀、悲、忧、愤、惧等多样的情气进行心理学或生理学的研究,也不机械地将其与特定的身体动作联合起来考察,只是就其作为一般的劳动现象做哲学的分析和探讨。但须明白这种建构虽标志人文性,却也是人为创造,以人们生产活动中的身体暴力(狩猎中的击、刺;铁匠的捶、敲等)、机器暴力和技术暴力为支撑,非达到生命之自然。
在儒家传统中,人的喜、怒、哀、悲等感性的情气活动被认为是人的本性,是人生而就有、不学而能的。“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郭店简《性自命出》)但依李泽厚看来,人的感性能力实际上是由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理性生命活动潜移默化而成。此看法的重要性,并非在于喜、怒、哀、悲等情气的形成可以诉诸人类学资料的实证性考察,而在于承认社会化的历史实践对主体的“潜移默化”的物理的或技术的塑造作用,而人的感性能力会随着实践而转移、变化和调整。因此,对于人的喜、怒、哀、悲等情气,既可以做历史的回顾式动态考察,也可立足于特定社会实践的静态分析。儒家以“喜”开情气之端绪,而以“悲”为情气之收束,全副人生践履不脱其养生送死的人伦亲情的乐感精神,并对世俗生命的价值予以正面的肯定,主张个体的健动不息,以此区别于佛家以情为毒为苦、道家无情不仁的思想路线。人有喜、怒、哀、悲四气,如天有春夏秋冬四时,人的情气活动配合着天道节气的规律而行。喜为新婚中心之乐;怒为受外境逼迫而情气盛发难忍;哀为丧亲死别的剧烈疼痛;悲则是直面物逝时变时对生命卑微的感伤。此四气形成人的情气十字打开的骨架,而忧、愤、惧、畏、恐、惊等情境性情绪不过是整体性情气的“大海”与具体情境交感的“浪花”。人的混沌情气在生命践履中有喜、怒、哀、悲等类型的分化,面对吉凶祸福以礼乐的道术引导、促发,使其始终伦类不乱而有节度秩序,体现为一种内蕴身心的体系化的能量团。喜怒哀悲未发之前是一团和气,已发则合乎礼仪度数,能和物宜人从而致福于天地。
在工业化时代转型中,传统的行情之道作为既有的价值规范,也参与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工人的情感系统的建构。这种建构是一种“转化性的创造”,即在工业化的机器生产中安置并生发出具有传统行情之道的中和精神的情感表现图景。历史性的情感传统由血缘宗法的旧有组织形式(区域性的家族)向生产权力关系下的工友组织形式(经济或政治部门性的单位)转变,具备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及其相应的人身自由属性。按照既定的情感传统限制和规定机器化生产劳动的内容、形式,现代化的生产节律又对传统情气感发的规范有所突破和调整,以维护工人的正常劳动与身心和合。以当前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劳动的内容、形式和氛围并不能完全以机器化程度和劳动强度等一般性的指标笼统观之,不同阶层、身份和职业的差异影响了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态度和情感,如体制内产业工人与农民工对劳动、机器的情感,就有着抑或本质性的差别(23)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417—421页。。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下生产资料与工人的对立及其财富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弥漫于社会的“怨恨”是指对自身困窘境遇的无力却又无节制妒羡优越价值的敌意情绪,它是情感脱离常道而走向萎缩与极端的消极性情绪。马克斯·舍勒以此为现代资本主义市民伦理和道德建构的根源,他也认识到怨恨情绪是心灵的自我毒害,其包含了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忌妒和阴毒等负面情绪。(24)马克斯·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罗悌伦、林克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但很显然的是,“怨恨”在中国的情感体认传统中皆处于“仁德”的统摄之下,循礼而发以体现主体内在的道德涵养,并非用来败坏个人德性。其也被用来指认人的非本真生存状态,对治方法不是强行克制而是以诗礼教化、疏导、战胜和升华,最后达到心情“无怨”的安和平静。(25)陈兵:《论君子之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正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如“身有所忿詈则不得其正”(《礼记·大学》)说的是怨恨影响身体回归平常的端正,而“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则意味着人甘于尽己无求而怨恨情绪无所由生。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工业化生产的劳动氛围中,工人的情感亦应该根基于反求诸己、身心平和的传统,不以怨恨等负面情绪毒害身心。(26)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424页。
其次,有必要来审视劳动中的功、德一致问题,即询问劳动者如何更好地劳动而非只是身体血气的锻炼或损耗,针对劳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劳动者都有真切的体认和玩味,从生产琐细中品味劳动的意义、滋味。劳动中只有身体的介入则只是在做功,即生产某种产品而已;而对自身的工具性活动的细节和意义有内在理解和整体领悟,即有得于己、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才算劳动的“德”。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时提到工人身体连同精神的麻木不仁,实际上是在指认一种极不正常的劳动状态即人沦为动物而丧失了一切知觉和精神活动。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工人,可以说只是在劳动中“立功”,即生产了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仅此而已。这种“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人为了获得既定的工资(特定的“利”),其劳动成了低级的生理活动而逃脱不了功利的考虑。单纯功利层面的“劳动”正是身心分离的非本真生存,因为人在劳动中“心不在焉”“不知其味”,既不可能从工业化生产中汲取某种程序性知识和完成理性塑造,也不会有什么情感上的共鸣、变化,劳动完全变成了谋生的空洞手段。在现实中,很多劳动者只是在最低的层次上对待“劳动”,使生命沦落为有功而无德、功德分离的流俗生存。而劳动的“立德”,则意味着劳动者伴随劳动过程有知识的提升、技艺的长进和道德的觉悟等内在理性(实践的或理论的)的建构。换言之,劳动者将劳动体验成一场意义丰富的“学习”活动,其可以是一种体育锻炼,可以是一种技艺比赛、音乐合唱和舞蹈表演,抑或日常的道德涵养工夫。(27)引而申之,劳动本身的意义不仅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地点乃至特定社会环境所决定,还为厕身其中的劳动者(主体)以如何的态度和情感所主宰,人本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成为事物意义的源泉。
当然,劳动的功与德在具体分辨上又有深浅厚薄的差异性,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既能其事又能其心”(28)所谓劳动的“能其心”,意指工人主体在技艺的熟练中能够动心忍性成就沟通神明的积极向上的觉悟,也就是劳动者净化自身的情感而向祭祀性的敬畏情感复归,达到身心虚灵不昧的状态。主体由之鉴照和预知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灾难性,从而做出积极的劳动状态调整。此亦即劳动的“正心诚意”之关键所在。。功力的深浅全靠劳动者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技艺的生熟则依赖心灵的悟性和灵巧;道德的觉悟则需要对整个劳动过程的体悟和思辨。马克思认为通过生产,工人的活劳动以物的方式转移到产品中凝聚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有必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外在的使用价值,商品中灌注的劳动者的道德情感和德性工夫更内在而幽微不显,后者正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叙事严重忽略。也就是说,作为劳动过程及其产品,不仅是某种具体功用的生产,还是劳动者自身道德工夫与德性的展示和感通。千差万别的劳动形式以空间化的时间计量转化成一般的抽象劳动,以作为使用价值的实际承担者,但劳动者自身的道德情感和德性践履却难以被量化的理论视角所把握,其具体而独特的个体化特征只能为审美的、体验的艺术化方法所把握和玩味。劳动道德维度的开辟以及对商品的内在价值(德性凝聚)的发现,将是我们摆脱商品拜物教物化状况的唯一出路,劳动者的内在觉悟与德性也是决定工人命运的现实力量。毋庸讳言,这一关于劳动内在情感的哲学考察,乃是一种强调生命实践的整体性和体验性的新思想形态,其主张从身心合一的角度去内在地生成对劳动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明确劳动中的生命本然面貌及其意义脉络。
最后,因人在劳动中能节制生机淋漓的情气,做精细的涵养工夫,故能有超然物外的气概,所以生起生命的悲悯之情。直奔私欲的劳动,愈是劳动,欲望愈是无穷,难免怨恨丛生,遂于流水线上人心浮浪,疏忽之间酿成事故而工伤连连。人们的仁爱之心日丧而情欲膨胀,对遭遇工伤的劳动者则无动于衷,不知自身为劳动者总体之一分子,沦为机器生产链条上一个麻木不仁的工具。“她们被简化成为一双手指 大腿/她们成为被拧紧的螺丝 被切割的铁片/被压缩的塑料 被弯曲的铝线 被裁剪的布匹/……她们周围是一群观众 数天前 她们是老乡/工友 朋友 或者上下工位的同事/她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四个跪下的女工/她们目睹四个工友被保安拖走……她们眼神里/没有悲伤 没有喜悦……她们目无表情地走进厂房”(29)郑小琼:《跪着的讨薪者》,见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278页。女工们被诗人以“她们”的第三人称复数表象为客体化的集合,确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所指认的那样,“她们”都成了机器动物,同乡、工友之情被这种体系化的机器——资本的力量所摧毁,“她们”亦成为碎片化的物的杂合而对自己同类的不公遭遇麻木不仁。(30)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中流俗的老乡、工友情感,如果得不到劳动工夫的锤炼,即老乡情、工友情不能当即呈现于专门化、部门化的机械劳动中以产生“集体劳动”的共鸣与共情,便只是徒具形式的、无根基的情意。
工具、机器并非僵滞的死物,亦非吃人的怪兽,其根据劳动的道德而有人、器和谐共生的诗意劳动画面。由此可见,人与机器的关系并非主客分立的矛盾征服,而是情气熏习下的和谐共生。人因机器而有机械的理性思维和结构性的力量系统,机器因人的情感灌注而有其“文化的生命”,人机合一以呈现机械性与生命性的情理圆融的生命境界。“锻锤有它豪迈的声音/马达有它优美的赞歌/而电火永远是轻轻地/小声诉说它的快乐……你用奇异的光彩、全部的热/使钢梁用锦缎系腰/让机床开出一束束花朵。”(31)于德成:《电火》,见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361页。此诗描写的是在新中国初期的国营工厂中,工人以其稚嫩的流光溢彩的情感赞美拥有机器生产的高效能生产力,锻锤、马达、钢梁和机床等生产工具在主体火热情感的包裹下,成了有乐感、美感的会开花结果的生命机体。与此相反,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工业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新工人(即拥有土地、农村户籍的农民弃农进城务工群体)来说,机器则是冰冷无情的“管理者”,是限制、侵夺他们人身自由与生命健康的异己的抽象权威。而他们亦以近乎诅咒的情感来表达自身在机器化生产中的劳动苦难,将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视为前现代田园文明的批判对象和养家糊口的无奈之举。(32)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458—459页。如“鸣叫的机台也打着瞌睡/密封的车间贮藏疾病的铁/薪资隐藏在窗帘后面/……工业向他们收缴来不及流出的泪/时辰走过,他们清醒全无/产量压低了年龄,疼痛在日夜加班/还未老去的头晕潜伏生命/皮肤被治具强迫褪去”(33)许立志:《最后的墓地》,见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第356页。。事实上,李泽厚的所谓“诗情画意的工具本体”,不过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积极的“现代化工业田园”的历史叙事在当代哲学美学建构上的“回光返照”。毋庸置疑,生产资料及其生产制度乃至整个生产关系,只有出自劳动者内在德性的安排,体现为道德的、人文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时,人与机器相和谐的本真劳动状态才能呈现。
结 语
一言以蔽之,道德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本根性,而以情气涵养为内在性特征的劳动则是通向这一本根性的唯一道路,此即当代中国劳动哲学叙事的主题。尽管中国极其繁复深广的工业化状况,使数量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很难以确定的称谓缓解内部的分化并达到共同的身份认同,但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作为创造历史(世界的又是中国的)的主要力量对自身的主体性无所自觉:所有打工人皆在以亲情为本根的内在性劳动中安身立命。劳动主体以敬畏谨慎的情感及其道德践履克服劳动的灾难性以实现创造性的自由劳动,这正是当代中国人之为人的即劳动和道德的时代精神的新发展。如果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以道德主体性挺立了人之为人的意义,那么现代中国的劳动者则在劳动这一普遍的生存方式中生长出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如果说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主体性,是特定阶级集团的精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那么当代劳动的情感性道德及主体性,便突破了阶级的局限从而具有强烈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相会通的可能性的持续探索(34)陈兵:《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看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并非如有些人所指出的异化劳动乃是一切社会的普遍本质,中国劳动者在劳动中持守情感的纯正并消除劳动苦难。劳动主体在工业化劳动的生存悲感中生发生命的忧患和满足感,成为面向天地并向其奉献自身的纯粹的人,成为日常劳动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