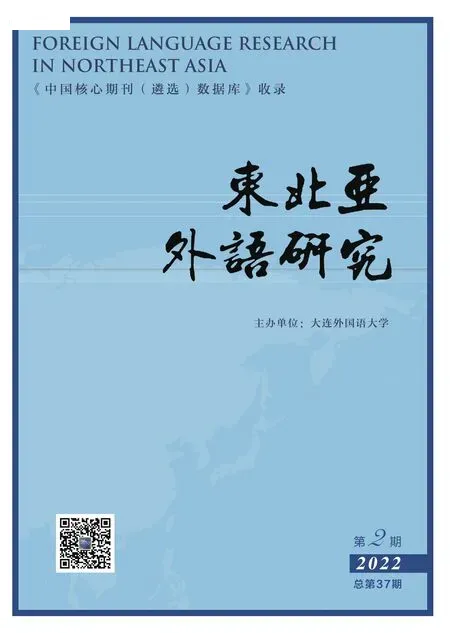俄罗斯汉学家杨申娜的中国神话翻译与研究
——以译著《山海经》和专著《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为例
王 钢 边 晶
(大连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中国东北亚语言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44)
在俄罗斯汉学研究这座百花园里,中国神话是一朵引人注目的奇葩。“神话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王悦,2017:34)。自19世纪末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C.M. Гeopгиeвcкий)的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Mифичecкиe вoззpe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aйцeв»)(C.M. Гeopгиeвcкий,1892)问世至今,俄罗斯的中国神话研究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众多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在中国神话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佐金(H.П. Maцoкин)、杨申娜(Э.M. Яншинa)、李谢维奇(И.C. Лиceвич)、叶夫休科夫(B.B. Eвcюкoв)、李福清(Б.Л. Pифтин)、叶若夫(B.B. Eжoв)、科布泽夫(A.И. Кoбзeв)等。然而,除了李福清之外,这些学者绝大多数仍不被国人熟悉。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神话学界对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及其开创的研究中国神话的俄苏学派一无所知(马昌仪,1988:48)。尽管今天这一情况已有所改观,但是对俄罗斯汉学家关于中国神话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仍然远远不够,应继续努力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优秀成果,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杨申娜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以中国神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但纵览中国学者对俄罗斯中国神话研究的介绍和总结,可以发现,对杨申娜及其重要著作的论述只在个别综述中被只言片语一带而过,并没有更多较为详细的介绍,更遑论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从杨申娜最重要的中国神话研究作品,即俄译本《山海经》(«Кaтaлoг гop и мopeй (Шaнь xaй цзин)»)(Э.M. Яншинa,1977;2004)和神话专著《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Фopмиpoвaниe и paзвитиe дpeвнeкитaйcкoй мифoлoгии»)(Э.M. Яншинa,1984)入手,探寻其中国神话研究的特点,以期稍许补充中国神话的海外译介和研究,为中外神话领域交流对话贡献微薄力量,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一、杨申娜生平简介
杨申娜是当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1924年9月30日出生于文化气息浓厚的萨拉托夫市,194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后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1952年-1960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历史系任教员。自1962年起,杨申娜成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员并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优秀的学术成果。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杨申娜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她成绩最为突出的研究领域。1962年成为研究所成员后,她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古代神话。“曾以《中国古代神话》论文(1965年)获副博士学位,此外还写过《论汉墓浮雕的某些形象(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1961年)、《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题材》(1963年)、《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1974年)等论文”(李明滨,2011:82)。神话译著《山海经》和神话专著《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最能体现其学术成就,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到1959年间杨申娜曾在中国停留,在此期间,她参观了北京、西安、成都、曲阜、郑州等地的博物馆并查阅了很多出版物,目的是收集有关考古发掘的资料,为其学术研究搜集素材、提供佐证。
二、翻译神话经典《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未署名的志怪古籍,“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奇书之一,奇在内容怪异而又不完全失真,形式呆板而又流传久远,经天纬地,不外乎东西南北中”(王丹林,2019:160)。在中国现存古籍中,它保存的神话资料最为丰富,且改动较少,相较于其他文献古籍保留了更加原始的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是了解中国古代神话、民间信仰和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亦是中国科学知识史的宝库,尤其是在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医学、民间医学等方面。在俄罗斯的中国神话研究领域,《山海经》的巨大研究价值早就为汉学家所关注。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最早将《山海经》介绍到俄罗斯的是经济历史学家施泰因(В.M.Штeйн),他在一本介绍古代中国与印度经济和文化关系的专著附录中,翻译了《山海经》的一个小片段(В.M.Штeйн,1960:175)。此后,杨申娜也做过类似的翻译尝试(Э.M. Яншинa,1963:469-471)。1977年,在杨申娜多年的努力下,《山海经》全译本终于问世,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纳塔利斯出版社(Haтaлиc)和里波尔经典文献出版社(Pипoл Клaccик)合作推出了《山海经》全译本修订版,译者仍是杨申娜。通过对副文本和译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杨申娜的《山海经》翻译具有如下特点:
(一)准备工作完善,文献整理全面
纵览《山海经》俄译本,可以感受到杨申娜翻译时所做的准备工作之完善以及她对汉学的精通,这主要体现在前言中对《山海经》成书时间的推测上。杨申娜认为,“任何试图追溯成书时间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推断出该书个别小节以及全书整体的大致形成时间”(Э. M. Яншинa,2004:6)。解决成书时间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取决于学者采用的方式方法和对其性质的理解。因此,在推测《山海经》成书时间时,杨申娜分别从《山海经》作为神话传说、历史地理资料的性质阐述,从不同角度对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证。她首先从神话传说的角度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了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诸多学者著作中《山海经》出现的时间以及关于其产生的传说故事,而后从地理学角度分析《山海经》的创作时间,最后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推测。
从神话传说的角度来看,杨申娜在前言中提到《山海经》的创作时间有如下几种可能:其一,大禹时代说。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以及汉代著作《吴越春秋》的记载,《山海经》是由大禹之臣伯夷镌刻在九鼎之上,用于记载大禹治水时的见闻,这些鼎后来丢失了一段时间,在西汉时期被重新找到(Э. M. Яншинa,2004:9)。《山海经》中的文本就是描写这些鼎上描述的内容,其中的各种奇珍异兽以及奇人画像也是对这些鼎上图像的临摹;其二,前大禹时代说。根据唐代学者啖助所言,《山海经》是在长期口头流传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而这要比大禹伯夷创作《山海经》这一传说早得多(Э. M. Яншинa,2004:11);其三,东周-秦之间说。杨申娜指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是在东周和秦之间的某个时期编写的(Э. M.Яншинa,2004:11),后来被不断补充,因而存在一些汉代地理名称、民族和国家的名字。但是具体是哪些学者,杨申娜没有明确说明;其四,不同时代说。清代学者毕沅认为,《山海经》前五卷是大禹和伯夷所著,第六卷到第十三卷可以追溯到周朝、秦朝这段时间,并且仍以九鼎上的图像为基础,第十四卷到第十七卷是由这本书第一位注释家刘歆所写,是对第十一卷到第十三卷的解释,最后的第十八卷是刘歆对汉代“山海经插图”的描写,是他进行注释时所列(转自Э. M. Яншинa,2004:11)。目前来看,最后一种说法在学界比较流行,著名神话研究学者茅盾(2011)也持此观点。除了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外,杨申娜还将视野投向世界汉学领域。她旁征博引、分析评价了很多西方汉学家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杨申娜还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了考证。除《西山经》第三节、《中山经》第五节和第十节之外,《山经》各节中所反映的地理描述都十分相似且风格一致,这表明其创作之时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神话描写风格,这应与当时的地理学有关。书中所包含的地理学的内容应在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形成,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时期。参考《周礼》中记载的由224人组成专门绘制地图的行政机构的描述,学者们提出《山经》的创作时期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即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杨申娜认为这一推断似乎完全可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山海经》风格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它对海外地区地理资料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机械连接的结果,而应该是后来版本的补充。《山海经》第二部分的内容和风格与第一部分有很大不同,它基于自然哲学和文学传统,主要描述海外国家地区和神话英雄。而这些知识在司马迁时代已为中国人所知,并在《史记》中得以描述。因此,杨申娜推测,奠定《海经》基础的传说形成于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此外,《海经》中存在许多族谱,而汉代随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思想家及其流派终究要接受统治者挑选和排除的命运,各流派为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正统,使自己流派的先祖成为全国的信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杨申娜进而推测,《海经》的创作日期是西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就是诉诸于基层崇拜和民间信仰。在神话材料的选择上,杨申娜发现《山海经》中的神话材料是规范文献中不存在的,尤其是与儒家学派的圣书之一《尚书》存在对立。《尚书》中神话以历史为蓝本,而《山海经》则以与自然神话观有关的情节为主。许多神话人物在两部著作中也都存在类比,因而杨申娜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山海经》是作为《尚书》对立面形成的。基于上述分析,杨申娜最终将《山海经》的整体形成时间溯源至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杨申娜在进行翻译工作之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在全面分析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山海经》形成时间进行科学合理的推测,在这一过程中,她还注意到了《山海经》作为神话汇编之外所具有的其他性质。
(二)剖析原本结构,探索标题深意
翻译《山海经》时,杨申娜为追求译文的科学和真实,结合了三种《山海经》底本,分别是郭璞《山海经十八卷》、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当然,后两部也都是基于《山海经十八卷》进行的审定和注释。杨申娜注意到毕沅和郝懿行版本中注释原则的差异,前者的特点是重理性,广泛借鉴大量地理文献资料,忽视文献神话传说的性质;而后者则使二者得兼,既引用了丰富的地理资料,又注意到该书的神话特性。虽然郝懿行版本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总体而言更加完善,因而杨申娜在其翻译过程中根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为其译本编排了页码,并在其中指出援引郭璞的注释。与此相对,译本的结构按照郭璞的版本进行编排,根据内容和主题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不同的部分。《山经》中的材料按照空间定位原则又排列为五卷,分别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其中每卷中又包含数量不一的小节。《海经》分为独立的十三卷,包括《海外经》(第6-9卷)、《海内经》(第10-13卷)、《大荒经》(第14-17卷)、《海内经》(第18卷)。与《山经》不同,《海经》的内容是根据世界四个方位排列,如《海外经》又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同样的分布顺序也体现在《海内经》中。而在《大荒经》中,分布顺序又有所不同,首先是《大荒东经》,然后是《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顺序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大荒经》属于另一个神话传说。最后一卷《海内经》则是对第10-13卷丢失插图的补充汇编。
在翻译文本时,杨申娜发现几乎每一卷及其各小节的名称都含有“经”字,因而她特别针对“经”这一术语的翻译进行了解释。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关于“经”的含义,杨申娜总结出如下几点:(1)跟“纬”相对的织物的经线以及在这一意义基础上形成的转义——不变的、正确的、正统的原理;(2)教义;(3)经典的、专门的教理书籍;(4)儒教经典的名字——《五经》《十三经》等;(5)在欧洲汉学著作中它被翻译为“经典书籍”(клaccичecкиe книги)、“经典文献”(клaccичecкaя литepaтypa)、“经典著作”(клaccики)、“圣书”(кaнoн)、“书”(книгa)等(Э. M. Яншинa,2004:7)。杨申娜认为《山海经》中“经”主要体现的是山脉、河流、动植物及神话人物等的目录,因此她决定将“经”译为“кaтaлoг”,《山海经》即«Кaтaлoг гop и мopeй»。“经”在文献内部也表示各卷以及卷内各节的名称,为了避免混淆,她将每卷名称中的“经”也译为“кaтaлoг”,如«Кaтaлoг Южныx гop»(《南山经》),而卷内小节中的“经”则被译为“книгa”,如«Bтopaя книгa Кaтaлoгa Южныx гop»(《南山经南次二山》)等。
(三)多种译法结合,再现原本含义
杨申娜研究发现,《山海经》中很多地理事物、植物、动物、矿物等的名称和资料很难确定。很多名称只出现在《山海经》中,其意义可能永远消失,其他的名称即使有对等物,但是至今也没被发现。有些名称可以在一些中世纪的文献中找到踪迹,但是由于朝代更迭、行政区域划分改变、民间与官方名录存在差异、古代和现代科学术语意义范围不同等诸多原因,书中的术语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被揭示,这给翻译带来了一定困难。而在翻译这样一部历史久远、意义重大的文献时,正确传达地理名称的含义尤为重要。因此,在翻译中杨申娜运用了音译、意译与注释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既符合俄语行文规范又能最大程度还原原文含义。
例如,在翻译“山”“河”“湖”等名称时,如果原文为“洛河”(Лoxэ),逐字翻译应为“Лo peкa”,就按照俄语表述习惯,被翻译为“peкa Лo”。有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组成的名称,或由双音节单词组成并使用表示所属关系的助词“之”表示的名称,也是同样如此,如“青丘之山”,译为“Гopa Зeлeный xoлм(Цинцю)”。原文中在提到同一河流、湖泊、山脉时,不同的词汇有时表示相同的地理对象,而有些发音相同的词汇则表达不同的名称,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意义难以理解时在其后括号内加入音译,同时在文后加以注释。如第五卷《中山经》“荆山山系第一座山是景山”,“荆”和“景”的俄语发音高度相似,如果不加以解释就会十分混乱。考虑到古代汉语语音缺乏可靠的重建及其方言的多样性,几乎无法恢复古代的读音,所有音译都是根据现代汉语发音标出的。为便于区别,翻译时译者将所有引用的词语都置于方括号内,而不同的译法、对难以理解之处的解释都置于圆括号内。此外,译本中还使用了许多插图,在每一幅插图下都有相应的解释或注释,所有这些注解都大大降低了读者理解的难度。《山海经》俄译本的问世,“给俄罗斯汉学界莫大的鼓舞,为俄罗斯中国神话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成文艳,2016:19)。
三、出版神话专著《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
杨申娜很早就注意到古代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她认为神话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居住在古代中国领土上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初次艺术概括体验,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文化之一。研究古代中国神话,对于重构统一的整体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非常重要(Э.M. Яншинa, 1984:3)。正如上文所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她就已经着手为这一研究搜集材料。在《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杨申娜基于其所选择的广泛神话资料,对中国神话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重构,从神话起源、促进其他类型文学创作产生的神话元素两个角度分析研究中涉及的神话材料。论述之充分、角度之新颖,无不体现学者极高的学术素养。
(一)综述详尽论述充分
同俄译本《山海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一书的前言部分,杨申娜也进行了全面翔实的综述,内容主要是对各国学者对古代中国神话来源研究的分析和批判。综述首先以评价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和马佐金的神话研究开始,而后按照先中国后西方的顺序分别展开。
与其他国家学者相比,中国学者不是第一批研究中国神话的人,直到20世纪20年代,神话才被纳入研究视域,成为研究对象。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由于考古发掘,人们思想中世代固定下来的崇拜对象被摧毁,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神话传说中所描述的伟大中华帝国不复存在,那段人们信以为真的历史已然瓦解;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掌握现代科学,了解世界文化史,摆脱了把本国文化看作是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领先文化的封闭传统。这就催生了从传统历史中分离神话的过程,它的研究和重建都随之开始。杨申娜将中国神话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30年代后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世纪20年代到30 年代的神话研究,这是神话的发现和神话问题的初步提出阶段,所有成果的特点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还很模糊。杨申娜在肯定其突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这一阶段研究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缺乏对神话与产生神话的社会之间联系的理解,很多神话材料未能得到充分解释。很多学者甚至对神话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由古代历史学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蓄意篡改或伪造的历史;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夸大了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的影响,低估了阶级社会中神话本身存在和消亡的自发性发展过程,以及在新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转化和加工的必然性。
杨申娜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神话来源的研究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批西方研究人员之一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A. Macпepo)的神话研究,他的主要观点在于早期神话资料可以根据后来文献进行修复,这一观点受到了高本汉(Б. Кapлгpeн)的批评(Э.M. Яншинa, 1984:8)。杨申娜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这种重建有一定科学性,但同时也指出其研究的不足,即没有在理论上证明自己的方法。第二部分是与马伯乐同一学派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 Гpaнэ)的神话研究,他提出的目标是基于神话、仪式、传说重建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然而高本汉认为葛兰言对材料不加批判的使用,对它们任意解释,因此在实施这一目标时也遭遇了失败(Э.M. Яншинa, 1984:8)。第三部分杨申娜驳斥了美国汉学家卜德(Д. Бoддe)和艾兰(C. Aллaн)等人提出的关于中国神话贫乏的论调,卜德认为“中国各自独立的神话当然会相遇并形成体系,但我所说的神话体系是指一套高度成熟的神话材料集成,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Д. Бoддe, 1977:367)。而中国神话是否具有成熟的神话体系仅靠个别材料是无法证实的,它与研究深度和修复重构有直接关系。
(二)深刻阐释神话来源
神话来源问题一直是中国神话研究中最迫切、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对某些神话情节和神话实体来源的态度和选择,对它们所蕴含信息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神话的重建。在该书中杨申娜指出了研究中国神话来源的两类材料:一类是具有叙事和铭文特征的古物、考古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造型艺术古迹,如丧葬浮雕、雕塑和雕像等;另一类是具有叙事性质的文字文献,通常没有完整的神话阐述,神话材料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于整体文献之中(Э.M. Яншинa, 1984:13)。
在对神话来源进行分析时,杨申娜发现神话传说的起源和发展受到哲学学派之争的影响。以“禅让传说”的重构为例,尧开创了儒家学派一系列古代英明统治者的先河,舜被认为是主要美德之一的孝的体现,和后来的禹一样被认为是最受尊敬的英雄之一。道家是儒家学派思想一贯的反对者,他们围绕儒家极为重视的孔子的基本道德原则展开论战,负面解释舜的形象,降低了他自身和王位禅让的理想化,通过这种方式破坏了舜和整个“禅让传说”所代表的原则。还有一个版本在《韩非子》这部典籍中可以找到,它属于当时第三大哲学政治流派——法家。法家是新贵族的代表,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者,是强大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在儒家的教义中,“禅让王位”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统治者年老后不将王位传给同姓血亲,而是将王位让给其他有能力的人,法家将其用于截然相反的目的:为了证明在君王面前所有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平等的,君王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从而杜绝任何干涉政府事务的企图。因此,在杨申娜看来,在研究文献的方法中选择一种或两种方案作为神话研究的标尺,而把另一种方案视为“歪曲”是不恰当的。神话以中国古代思想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为基础,在有文字记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形成并发展,具有多阶段性、多变性和矛盾性,所有这些神话的特性都不能被忽略,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解释,再现并表达神话观。
(三)重视考古发掘作用
考古类型学方法来源于考古学,旨在组织考古材料,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归纳、分类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可以追溯遗存器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杨申娜创造性地将这一方法与中国神话研究相结合,指导中国神话研究的实践。正如上文所说,神话材料流传至今,其矛盾性完全可以理解,且不可避免,需要借助适当方法加以再现和表达。这种方法使得在最新形成的神话群中重构某些神话形象以及重建不同阶层的神话观成为可能。矛盾性是神话传说本身固有的,神话在人类发展的漫长道路上形成并流传,虽然人类祖先和早期阶级社会的神话有一些共同规律,但在其他不同阶段却有很大差异,随着社会生活条件、思维发展和社会意识的提高,世界观也发生变化。人类所有创作活动的动态发展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创作和活动再现并表达了神话观。
杨申娜认为,考古发掘材料和书面材料一样,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和汉代的墓葬(Э.M. Яншинa,1984:24)。在1958-1959年停留中国期间,经过多方探索,她发现最有价值的材料是西安附近出土的墓地、常见于中国汉代穷人墓葬中四川的陪葬浮雕、由南京博物馆工作人员挖掘的山东沂南的墓葬以及著名的武氏贵族丧葬群地上祠堂(即所谓的武梁祠)。此外,1978年-1980年山东出土了一些带有浮雕的墓地,这些墓地浮雕的风格和内容与武梁祠十分接近,但是神话主题更加明显。当然,破解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它们的图像上既没有神奇的铭文也没有宗教仪式的记载,只有通过书面文献资料才能对图像进行解释。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包括在商殷都城古墓发掘时发现的文物、占卜铭文“档案”、留有众多人类祭品残余的祭坛群,所有这一切对修正文献材料都极为重要,同时这些考古资料本身也是重建神话的源泉。由此可见,在杨申娜的研究中已经或多或少关注到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即叶舒宪(2006,2011)所谓的“第四重证据”。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两部著作的分析,大体可以窥见杨申娜神话研究的特点:其一,古今并重、东西兼顾。两部著作的前言通过大量详实综述引出论述内容,从古至今、从中至西,内容充实,阐释明了;其二,思考全面、方法得当。无论是对《山海经》译文的处理还是对中国古代神话来源的分析,都没有刻板沿袭之前学者的成见,而是通过自己深刻的思考,综合考虑诸多有利和不利因素后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其三,吐故纳新、勇于探索。一方面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独到见解,从具有叙事和铭文特征的古物、考古材料,以及具有叙事性质的文字文献中探寻中国古代神话起源并对其进行重构,重视“第四重证据”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汉学界无人翻译《山海经》的情况下,克服诸多困难完成俄文全译本,为东方学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尽管译文在某些地方的准确性还值得商榷”(李福清,1987:8),但毋庸置疑,杨申娜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