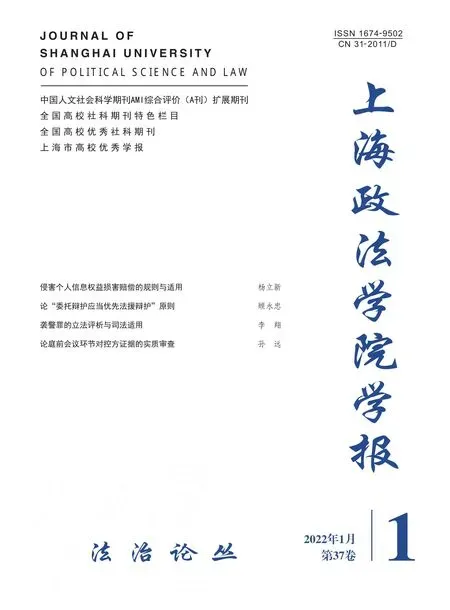纠结的“查阅”同步录音录像: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述评
郭 烁
一、问题的提出
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律师在场权的替代物,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凭借自身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记录的完整全面性和监督审讯的便捷性,在推动侦查(调查)环节公开、防止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解释》”)正式施行。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近10年后,该制度又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修订。本次修订,凸显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据使用的必要性,也再一次激发了学界和实务界对长期存在的律师阅卷权问题的关注。
谈及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有两份绕不开的文件。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于2013年发布的《关于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音录像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2013]刑他字第239号)。该《批复》认为“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你院请示的案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讯问录音录像已经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并已在庭审中播放,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复制有关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应当准许”。也即,该《批复》将所涉案件中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归为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并允许律师的复制要求。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辩护人要求查阅、复制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处理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认为:“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法律规定的辩护人的阅卷范围仅限于案件的案卷材料。对案卷材料以外的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授权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辩护人是否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二、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不是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属于案卷材料之外的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辩护人未经许可,无权查阅、复制。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可以在人民检察院查看(听)相关的录音、录像。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犯罪线索的内容,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讯问录音、录像的相关内容作技术处理或者要求辩护人保密;在人民法院审判阶段,人民法院调取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讯问录音、录像移送人民法院。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录音、录像。但辩护人无权自行查阅、复制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可见,《答复》认为,第一,只有“案卷材料”才能被“查阅、摘抄、复制”;第二,“案卷材料”包括“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而同步录音录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因此也不属于“案卷材料”;第三,在涉及对“讯问活动合法性”的调查时,辩护人才可能“查看(听)”同步录音录像,且要符合保密要求并只字未提能否摘抄、复制,其他情况下辩护人均不能自行查阅、复制同步录音录像。
以上文件以及类似文件效力可以另行具文阐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比上述《批复》和《答复》可以发现,二者在关于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属于“案卷材料”,以及同步录音录像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查阅”,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摘抄、复制”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答复》就同一个问题比《批复》作出时间滞后且内容大相径庭,不得不令人困惑。
本次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又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查阅、摘抄和复制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一规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为数年来存在的分歧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按照起草者自己的话说,本次解释修改在“辩护与代理”部分的亮点之一即为“明确相关录音录像的查阅规则”①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等:《〈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但笔者访谈的诸多刑事辩护律师却一致表示悲观;也有分析者指出,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第一,其没有直接明确地规定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也没有直接规定其可以用来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第二,其没有明确表明同步录音录像应当随案移送;第三,该条限制了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方法,辩护人可以查阅但不能复制。①参见谢小剑:《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发展:从过程证据到结果证据》,《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笔者认为,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实则是对同步录音录像效用和辩护人阅卷权的一种矮化,如果说2013年的《批复》是因为只涉及单个案件的具体做法才无法解决整个制度上的问题,那么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则很难在其实际的效力位阶基础上发挥应有价值。
二、同步录音录像之运行考察
自1977年英国最先开启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探索以来,诸多国家都选择了该制度。其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修复司法公信力和固定案件事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便利作用。②参见李娜:《全部全面全程推进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检察日报》2011年5月16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多年来也对该制度进行了回应与完善,但因为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根本张力,导致其总体发展步调缓慢。从比较法视域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或可以提供参考。
(一)域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运用考察
1.英国:专门性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守则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在讯问中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从制度构建到最终确立经历了20余年。为预防错案,完善司法,英国于1984年出台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并在其执行守则中制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的规则(《守则E》和《守则F》)。③Home Offic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Code E (Revised) & Code F (Revised),London:TSD,20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03813/pace-codes-e-and-f-2018.pdf.其中《守则E》要求对嫌疑人的讯问进行录音,《守则F》则允许同时进行录像,这两项规定为嫌疑人提供了保护措施:防止对讯问中使用的词语以及讯问期间的举止进行不准确的记录,以及针对嫌疑人对警方讯问人员提出的指控,证明讯问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守则E》在历年进行了多次修改,其中2020年更新的《守则E》(草案)④Home Office, “Draft revised PACE Codes 2020 C (Detention) and E (Audio recording of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93328/2020_Covid-CodeE_DraftFinalTracked__2020-06-12.pdf.第3.4条(e)规定,要告诉嫌疑人:如果他们被指控或被告知将被起诉,他们将获得一份录音记录副本,但如果他们没有被指控或被告知将被起诉,他们将只获得一份警方同意或法院命令的副本;讯问结束时,他们将收到一份书面通知,说明他们获得录音副本的权利以及录音将会怎么用。其第3.10条规定,如果在讯问过程中,被讯问人或其辩护人就本守则或任何其他守则的规定提出投诉,或者讯问人注意到该人可能受到了不适当的待遇,则面试官应按照《守则C》第12.9条的规定行事。第3.21条规定,嫌疑人将收到一份通知,说明:录音将如何使用;获取录音的安排;如果他们被指控或被告知将被起诉,将尽快提供录音副本,或在嫌疑人与警方达成协议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提供。在第4节关于使用安全数字录音网络设备进行讯问的场合,其规定和前述第3节中使用可移动记录设备的一些规定。也就是说使用的设备差别不会影响到嫌疑人获取录音副本的相关权利。
《守则F》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在2013年的版本中,①Home Offic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PACE) Code F(Revised)201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06661/2013_PACE_Code_F.pdf.其内容与2018年前的《守则E》在整体结构、具体内容、条文措辞方面都很相似,规定的适用范围都比较广,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在最新的2018年版本中,第2.2条则规定,制作视频记录并不是法律的要求,但是如果《守则E》中所描述的“相关官员”认为应该对第2.1条中提到的任何事项进行视频记录,就应该遵守《守则F》的规定,由此可见,英国对于同步录音和同步录像的要求是有一定差异的,在2020年的《守则E》中,第1.5A条采用的措辞可以体现这一点,对待同步录音其使用的是“require”一词,而同步录像则使用“permit”②“1.5A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which require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to be audio recorded and the provisions of Code F which permit simultaneous visual recording provide safeguards”. Home Office, “Draft revised PACE Codes 2020 C (Detention) and E (Audio recording of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93328/2020_Covid-CodeE_DraftFinalTracked__2020-06-12.pdf., 可见在最新规定中对同步录音的要求更具有强制性。
2.美国:部分州已确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
美国对讯问录音录像呈现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从州警察陆续引入了该制度以后,就得到了一些州审判法院、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以及学界的大力支持,但在1966年的“米兰达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却拒绝采用该制度,此后录音录像制度便受到了冲击。美国许多检察官和警察部门坚持认为,录音要求会妨碍执法并阻止嫌疑人说话,有些支持者则认为记录审讯可以防止虚假供述,增强司法有效管理,并且能改善公众和警察之间的关系。③Roberto Iraola, “The Electronic Recording Of Criminal Interrogations”, 40 U. Rich. L. Rev. 463, 475-476(2006).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④Marjorie A. Shields, “Criminal Defendant's Right to Electronic Recordation of Interrogations and Confessions”, 69 A.L.R.6th 579, 1-118(2011).,保守估计,根据截至2019年5月19日的消息,美国已经有25个州明确要求要进行审讯录音。⑤OKLAHOMA CITY, “Oklahoma becomes 25th State to Require Recording of Interrogations”, (May 14,2019), Innocence Project: https://innocenceproject.org/governor-signs-landmark-laws-for-preventing-wrongful-convictions/. accessed by August 8,2021.
在明确要求进行审讯录音的州,其对进行审讯录音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得克萨斯州Hollis v. State⑥See Hollis v. State, 219 S.W.3d 446 (Tex. App. Austin 2007).一案中,法院认为对被告人不利的口头或手语陈述不可接受,除非被告人放弃了他的米兰达权利,并且对陈述进行了清晰准确的电子记录,保持记录的完整性,并且要及时提供给辩护律师,最后要通过最终判决予以保留。法院指出,这是一项程序性证据规则,在得克萨斯州的另一个Davidson v. State⑦See Davidson v. State, 42 S.W.3d 165 (Tex. App. Fort Worth 2001).案件中,法院指出讯问录音是一种程序性证据规则而不是实质性规则,所以即便录音出现一些错误,只要该错误不影响被告人的实质权利,就可以忽略该错误。而在阿拉斯加州的Stephan v. State⑧See Stephan v. State, 711 P.2d 1156 (Alaska 1985).案件中,其最高法院指出,根据阿拉斯加宪法,无故未能以电子方式在拘留场所进行的拘留审讯侵犯了嫌疑人的正当程序权,由此获得的任何陈述通常不可接受。当讯问发生在拘留场所并且录音是可以实现的,对嫌疑人的讯问进行录音就是正当程序的要求,嫌疑人的权利信息、放弃权利和讯问的信息都应该被记录在录音设备上。并且,虽然大多数执法机构都将使用录音或录像作为保存讯问内容的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手段,但使用替代方法,比如由经过认证的速记记者进行逐字逐句记录以替代电子设备。因此,凡是没有对讯问进行完整录音的,公诉方必须以大量的证据来说服初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录音也可以没有。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1994年的State v. Scales案中也认为,为了确保公正司法的监督权,所有的羁押讯问,包括任何有关权利的信息、放弃权利的信息以及其他讯问内容都应该在可行的情况下以电子方式记录,并且必须在讯问发生时在拘留地点进行记录。如果执法人员不遵守录音要求,嫌疑人在接收审讯时所作的任何陈述都有可能在审判中不被采纳。①See State v. Scales, 518 N.W.2d 587 (Minn. 1994).而在该案之前的案例中,明尼苏达州也只是建议对询问进行电子记录而不是要求其一定要进行记录。
(二)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历史沿革
1.打破秘密审讯之国情选择
在建立起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前,侦查活动因为具有封闭性和秘密性,往往会滋生非法讯问、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辩护职能也因此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为了避免侦查权力被滥用,实现依法文明办案,我国开始建立侦查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律师在场权固然能有助于防止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和夜间突击审讯,但其制度选择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司法观念都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一向对其持审慎的态度。
代表性观点即认为,盲目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就像给本该保密的侦查活动“打开了一扇窗”,会妨碍侦查活动的行使,为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获取和案件的侦破带来消极影响,律师在场制度也不是现代国家的通例。②参见朱孝清:《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之我见》,《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另外,如果要求律师随时准备待命到场参加讯问具有很大的困难,就早前组织的律师在场权试验中,从对56名律师的问卷统计来看,赞成律师在场方式的只有10.8%。③参见樊崇义、顾永忠主编:《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毋庸讳言,刑事诉讼的进化有其必然性,于此番权益保障与侦查权力博弈后,失范性审讯仍然具有极大的操作空间。在舍弃律师在场权制度、刑辩律师不能有效参与侦查活动的情况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其打破了侦查活动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侦查取证行为,客观上给外界深入了解侦查人员审讯活动的过程提供了合理契机。同步录音录像能够保证讯问的合法性,将柔性的自白转变为刚性的可视化内容,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诉讼权益。
2.同步录音录像之立法探索
如前所述,同步录音录像是一项在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制度,直到2012年才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从最早的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确立了“讯问重大案件的被告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录音记录”,到1998年,此规定又增设了用录像方法记录笔录。最开始的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而是通过各种部门规章、项目试验等方式倡导并尝试探索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引入。
2005年12月和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同步录音录像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展开了改革试点并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①包括《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和《人民检察院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建设技术规范(试行)》。首次以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对于职务犯罪案件讯问录音录像的收集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创设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口供,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②参见董坤:《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据调查统计,2006年3月至2007年11月,各地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的录音录像多达4802次,并有效地遏制了被告人翻供。③参见王新友:《凡是讯问全程录音录像 均未发现违法办案》,《检察日报》2007年11月14日。可见当时同步录音录像对于保障有罪供述的可信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007年3月,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中,进一步将同步录音录像扩大到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但该意见只是提出“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尚未确定死刑案件强制性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则。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颁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进一步明确讯问录音录像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同年12月,根据适用“两个规定”的指导意见,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嫌疑人进行讯问全程的录音录像。
然而不仅仅是职务犯罪,随着彼时大量冤假错案浮出水面,学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防止不法讯问导致虚假口供的滋生,正式引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大有裨益。最终,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第1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本条确立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同步录音录像应全程进行,保证其完整性;二是对死刑、无期徒刑、重大犯罪案件讯问的录音录像作出强制性要求。
显然,这一制度可以限制侦查人员非法问供,遏制非任意自白,确保讯问过程合法性,也为法官和辩护人开辟了一条监督侦查人员取证行为和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可靠路径,是维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效措施。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就提到了同步录音录像可以“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这意味着该制度的功能便是用于证明口供的真实,也就是说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并不是法定的口供载体,不能像讯问笔录一样用于证明案件的实体事实。之后的2012年至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性质文件,④包括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看守所设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的通知》,2013年“五部一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的通知》,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扩大了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范围并规范了其操作、管理、监督程序。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 41 条第 2 款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把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明确用于讯问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中,“留存备查”。但对于监察机关调查后的移送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解释仅称“可以同监察机关沟通协商后予以调取”。
2019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同步录音录像明确在检察院的所有自侦案件中。2020年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又将同步录音录像扩大到了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重大犯罪共13类刑事案件。至少近年来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运用成效显著,次数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①参见蔡艺生:《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运用的实证研究——以493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证据科学》2020年第4期。但对于实务界主要关心的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依旧过于笼统宽泛,检法两家也各执一词。
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上述国家虽然都建立起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功能和范围都有所不同。英国走在最先列,讯问录音录像已经可以取代笔录,作为固定刑事被追诉方供述的可信载体;美国主要为保证供述的自愿性,与非法证据排除相结合,考察是否违背刑事被追诉方的意旨,可以作为定案根据。而且,它们都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程序规范和监督审查措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问题之厘清
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复制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对此进行了修改、回应,从中可以解读到立法者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价值肯定和对律师阅卷权的密切关注。值得玩味的是,按照该解释起草小组的说法,新解释本想全盘继承2013年《批复》的内容,即“原本拟吸收上述规定”,但“征求意见过程中,存在不同认识”②喻海松:《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司法适用疑难解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6页。,最终出台了现有文本,使得诸多问题依旧搁置。
(一)证据属性问题悬而未决
新《刑诉法解释》颁布前,虽然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界定的规范文件数量众多,如前所述,包括司法解释性文件、多机关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司法机关出台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但其始终缺乏权威的属性界定,没有比较强的普遍约束力,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倾向于“不给看”。对此问题,有学者认为,案件的真实情况不能用同步录音录像来证明而应该用笔录来证明,同步录音录像只是一种防止嫌疑人翻供、监督讯问的手段,所以没有独立的证据地位。③参见王彪:《讯问录音录像的若干证据法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6年第 2 期。也有学者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只有可以证明程序合法性的过程证据资格,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遏制非法取证。④参见郭志远:《我国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但也有不少学者完全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认为同步录音录像不仅可以用来证明程序性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证明案件的实体性事实。⑤参见王戬:《论同步录音录像扩大适用的证据困惑与障碍破除》,《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期。对于此次立法修改而言,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功能困境依然没有解决。
1.供述合法性证明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既是对贯彻宪法原则的体现,又是更加强调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析,保障合法诉讼权利不受侵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便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制度,逻辑起点显然应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合法为前提,能够帮助更好地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①参见孙远:《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方法》,《当代法学》2021年第5期。同时录音录像也有被用作证明某个证据的取证行为合法的证明,②参见程衍:《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的程序性被告身份》,《当代法学》2019年第3期。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进行印证,同步录音录像都可以帮助遏制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惯性”,③参见郑曦:《刑事诉讼中程序惯性的反思与规制》,《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利用相关自然科学的知识来揭开司法过程的黑箱,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④参见郑飞:《证据科学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我国司法解释性文件已经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明供述合法性功能进行过确认。最早的规定源自上述《批复》,表面上看是辩护律师阅卷权的问题,其实还牵涉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问题。对该《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侦查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属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的视听资料载体,对于案件的作用不是证明案件事实本身而是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如果辩方或法庭没有提出对于有关被告人讯问笔录合法性的质疑,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般是不需要向法院移送或调取该讯问录音录像的”⑤参见王晓东、康瑛:《〈关于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4年第3期。。这一规定明显偏向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过程证据资格。2013年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第2款也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这一条对《批复》形成了完整补充。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项对于同步录音录像材料是否需要随案移送问题的规定,将讨论的焦点复归到侦讯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上。对于《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讯问录音或者录像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防止刑讯逼供,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侦查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主要是用于真实完整地记录讯问过程,在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证明讯问行为的合法性……用于证明讯问合法性的录音录像不作为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据,也就不必要每个案件都随案移送”⑥王尚新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5条第1款第2项也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就可以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这要求在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明程序合法性的证据时,必须要先一步“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辩护人需要先看到同步录音录像,才能判断是否要提出非法证据排除,除此之外辩护人便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形成了“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与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之间的纠结关系,也非常容易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无法应用,并且在实践中也确实是先举证后进行证据合法性调查,对此有学者提出对可能被启动合法性调查的证据,不得在合法性调查前举证和质证,①参见陈实:《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维度与机制探讨》,《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但这在实践中如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帮助是很难操作的。
从以上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来看,讯问录音录像只是被视为“取证合法性的证明材料”,有别于传统的实体性证据材料,而且是要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下,才能随案移送和进行审查。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机关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功能限缩,是将同步录音录像定义为“现代版的卷宗制度”,是为避免审判为中心的架空。②参见佀化强:《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在审判中心主义与避免冤案之间》,《法学论坛》2020年第4期。这其中仅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解决程序争议的作用,对于辩护律师能否查阅、摘抄、复制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对于此,新《刑诉法解释》第74条新增了:“依法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相关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人民检察院未移送,导致不能排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依法排除;导致有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条还是说明讯问录音录像仍然是用于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材料,以及作证笔录真实性的证据材料,其仍然无法涉及案件的事实问题。
2.直接实质性证明
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三项规程”,其中《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22条第4项指出:“讯问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内容,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50条第2款规定 :“法庭应当结合讯问录音录像对讯问笔录进行全面审查。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这是对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进行实体性证明的一些转变,但与上文中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用来作为问供合法性证据的规定是存在冲突的。实践中,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进行记录、总结所制作出的证据材料,往往会注入侦查人员的主观色彩。而同步录音录像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衍生出来的最真实的载体记录,可以对供述的实质内容起到最准确的证明作用。
同时,《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14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前会议中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证据材料进行核实;经控辩双方申请,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该条文明确,讯问录音录像被囊括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性材料范围内。
无疑,同步录音录像也可以作为侦查机关的一种程序控制手段,可以保证其行为以正当程序作为基本准则,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双重价值,①参见张可:《大数据侦查措施程控体系建构:前提、核心与保障》,《东方法学》2019年第6期。但“三项规程”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还意味着讯问录音录像在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作为证明案件实体性事实的独立功能。从一些裁判文书也可以看到,在部分案件中,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讯问笔录和合法性提出质疑,笔录被排除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就作为记载供述、反映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发挥了作为定案根据的实质证据性功能。②例如“常某抢劫案”,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1)冀0529刑初12号刑事判决书。不过相较于讯问录音录像被用于证明证据合法性的案件,这种裁判的数量相对较少。应当说,讯问录音录像能够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能否直接作为证明案件实体性事实的证据问题上在左右摇摆。
(二)律师查阅的权利定位
新《刑诉法解释》虽然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作出了规定,但是该条规定的查阅录音录像的权利范围较为狭窄。其规定律师查阅录音录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作为证据材料”并已经过“移送”;二是仅限于“讯问录音录像”。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于非证据材料、询问的录音录像、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等录音录像,是否具有查阅权,在新《刑诉法解释》中也没有提及。此外,新《刑诉法解释》中也没有对《监察法》录音录像制度的明确衔接,这也会造成辩护律师对于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讯问录音录像的阅卷权利受阻。
1.律师审查的“证据材料”限制
对同步录音录像是否能够作为“证据”的争论由来已久,上文已有提及。《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件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但是同步录音录像能否作为上述规定中的“案件材料”被查阅、摘抄、复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中的表述“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再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7条第2款之规定,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那么对于“不作为证据材料的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诉讼文书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以及“既不作为证据材料也不作为诉讼文书的讯问录音录像”便不能适用第54条规定,是否要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又会因案而异,这对于统一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尺度并无好处。
根据起草小组的说法,“对于移送人民法院的录音录像,无论是否已经在庭审中举证质证,无论是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还是用于证明取证合法性,均应当属于案卷材料的范围”③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等:《〈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其解释道,在公开审理中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录音录像,本来就由于案件可能进行庭审直播的原因导致广泛传播,再以“防止录音录像广泛传播”为由禁止辩护律师查阅则于理不合,对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录音录像,为了方便律师行使辩护权,也应当是可以查阅的,只要遵守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的保密规定即可。这一段肯定了录音录像属于案卷材料,也暗含最高人民法院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呈开放式的态度。笔者认为,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内容,应当可以属于证据无疑。但是实践中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还要通过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确认其与待证事实的关系,以及判断能否会成为裁判者的裁判依据,这样的讯问录音录像能否作为证据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整体来说,“唯有更加全面地收集证据,让更多的证据进入诉讼、进入裁判者的视野,才能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①冯俊伟:《刑事证据分布理论及其运用》,《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律师阅卷以“移送”为前提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解读中指出,“讯问录音录像不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没有必要每个案件都随案移送”②王尚新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理由”。可见,刑事案件一般并不随案移送讯问录音录像,调取需要以判断是否有需要为前提。根据学者统计,裁判文书中载明的讯问录音录像随案移送率仅为4.3%。③参见蔡艺生:《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运用的实证研究——以493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证据科学》2020年第4期。在司法实践中,移送同步录音录像成为了需首要解决的难题。
新《刑诉法解释》第74条规定应当移送讯问录音录像而未移送的,不能排除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要承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后果。此规定看似要求对讯问录音录像要强制移送,实则表述不明。究竟是否移送讯问录音录像,仍然要取决于法院认为有必要移送或调取。新《刑诉法解释》由于设置“移送”的前提条件,很可能会为检察机关拒不移送、法院拒不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找到借口,这大大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3.非讯问录音录像被排除在外
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规定的录音录像只圈定于“讯问”类型中,关于例如询问、查封扣押、辨认、技术侦查、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等过程产生的同步录音录像则只字未提。《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第20条也规定,“询问证人需要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事先征得证人同意。”其与《监察法》第41条第2款所列出的“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的规定,对办案操作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但新《刑诉法解释》对于以上取证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是否需要移送以及是否具有查阅权的规定显然是否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灵活性。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可以起到过程规范与结果规范两个层面的权力规范功能,其客观性较强、记录内容丰富、适应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趋势等优点可以实现包括询问证人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过程在内的权力监督,在上述活动结束后仍然可以用来进行审查,①参见白冰:《搜查、扣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及其实现》,《法学家》2021年第4期。因此不应当将非讯问录音录像排除在外。
4.检察机关录音录像之衔接
关于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的“讯问录音录像”是否包括监察机关收集讯问笔录的录音录像,起草小组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新《刑诉法解释》第74条规定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不限于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也包括监察调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②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等:《〈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如前所述,《监察法》第41条第2款已经规定了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应当同步录音录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说明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并由调查人员或者侦查人员签名。”第76条规定:“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第263条第2款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认为需要调取有关录音、录像的,可以向监察机关调取。”这三条规则结合来看,虽然调查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不随案移送,但在法律上依旧有协商调取的空间,这也得到了《监察法释义》的肯定。③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因此,当作为案卷材料移送给法院后,则应当按照新《刑诉法解释》的规定允许辩护律师查阅。不过,监察调查录音录像的问题目前尚无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解释,如果相关监察调查过程的录音录像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自然不属于可以查阅的范围。通过查阅监察调查录像实现程序争议和人权保障问题,依旧棘手。
(三)律师阅卷权的明确扩张
在新《刑诉法解释》修改前,法院多以讯问录音录像不属于证据法定种类和没有调取的必要性为由来拒绝辩护人提出的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申请。《刑事诉讼法》第50条列举了8种法定证据种类,采用的是封闭式的穷尽列举立法模式。因之前各部门规定不一致,缺少规范统一的上位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属性界定模糊,公检法三机关常以同步录音录像不属于案卷材料和证据为由,不移送或者认为辩护人无权查阅、复制录音录像。又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辩护人对同步录音录像具有查阅权,法院常以没有必要调取为由而不予准许。
本次新《刑诉法解释》的修改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由之前的“查阅、摘抄、复制”删减为仅“查阅”而被众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解读为律师对讯问录音录像阅卷权作出了限制。根据起草小组的理解与适用,“对于查阅申请应当一律准许,但对复制未再作明确要求”④同注②。,这至少说明了对律师申请查阅讯问录音录像的绝对许可,没有对摘抄、复制权进行剥夺。事实上,《刑事诉讼法》第40条也规定了辩护律师对案卷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既然已确认讯问录音录像为案卷材料,新《刑诉法解释》便无权超越上位法律,由此辩护律师应当有权进行摘抄和复制。
(四)查阅方式的范围限缩
1.录音录像泄露及印发舆情之争
之所以未在新《刑诉法解释》中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摘抄、复制权,可能与近几年有律师违反保密义务,把重要案件信息和讯问录音录像视频披露至网络,引发舆情有关。在对新《刑诉法解释》征求意见时,有人认为,讯问录音录像涉及国家秘密、侦查技巧,尤其在有影响力的重大案件中,十分敏感,一旦全面允许复制,传播到网络,舆情可能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对此起草小组认为,对于已经移送人民法院的录音录像,应当属于案卷材料的范围,对诉讼参与人应当是公开的,也不能避免进行庭审直播等活动而被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辩护律师查阅录音录像则不合适,并且即便是允许律师进行查阅,现行法律也有律师必须遵守相关保密要求的规定。 因此,辩护律师是否能够查阅录音录像与辩护律师查阅录音录像应当遵守保密规定两者之间应当独立规定并互为前提,法律完全可以通过对保密制度的完善达到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制的目的。
2.违规泄密应用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规制
笔者认为,第一,移送的证据材料,对诉讼参与人应当是公开的。特别是,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录音录像在内,由于不少案件要进行庭审直播,其本身就会被公开,①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等:《〈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因此不应当限制辩护律师进行查阅。第二,即使讯问录音录像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辩护律师为了行使辩护权,也应当可以查阅,对其保密性可以适用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的规定。
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已对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和泄密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放宽应享有的多种阅卷权利。其规定:“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对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在办案过程中获悉的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不得违反规定泄露、披露,不得用于办案以外的用途。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相关人员出具承诺书。违反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建议给予相应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辩护律师保密信息的范围方面,已由之前《律师法》第38条规定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隐私,扩大到了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和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在惩戒手段方面,不同于《律师法》《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等法律、规范文件的提示性规定,在立法层面上还设置了刑事处罚和刑事责任惩戒措施。
笔者认为,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已对律师不正当泄密作出严厉约束,足以威慑律师履行好保密义务。即使涉及多重秘密,也不足以阻碍律师行使阅卷权利。且不光作为实体性证明的同步录音录像,其他任何案卷材料泄露也可能造成同样的社会风险,限制辩护律师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复制权,恐与其他证据相比存在不平等对待,且也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违规泄密的风险。在实践中,仅仅查阅讯问录音录像不能满足辩护律师的案件需求。法律规定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往往也是重大复杂、人数众多的刑事案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许多动辄数百数千小时,为达到真正的有效辩护,无论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或是证据合法性,单纯在法院查看对于辩护律师都是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这不但影响司法效率的提高,也阻碍了律师辩护权的行使。
四、结 语
同步录音录像实现了固定真相、节约司法资源与证明合法取证的有效结合,英国在此制度上一直走在前列,而美国的各州对此规定不一,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州对其进行了正式规定;与之相比,这一制度的运行在我国依旧任重道远。新《刑诉法解释》第54条对讯问录音录像规定的部分权利不明确,给该制度的价值选择和权益发挥造成了困扰和阻碍,并导致了其可能的操作矮化。
一方面,其对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问题没有明确,目前同步录音录像作为问供合法性的证明已经是共识,但其要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出合法性质疑,甚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之下,才能随案移送和进行审查,这经常给实践当中律师的辩护工作带来尴尬,律师一方面需要初步的证明材料用来提起非法证据排除,一方面又只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被提起之后才能获取同步录音录像——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在同步录音录像能否作为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据方面,第54条对律师权利的规定范围过于狭窄,无论是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在左右摇摆。
另一方面,就律师能够获取录音录像的权利范围而言,其查阅录音录像的前提条件包括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材料”并已经过“移送”,并且录音录像的种类限制在“讯问录音录像”,这需要新《刑诉法解释》与《监察法》进行制度衔接,并且解决录音录像能够作为案卷材料的问题。在查阅的方式上,第54条只写明了律师可以“查阅”,对于能否复制则没有提到,但是无论是从与保密制度的衔接还是从辩护的工作需求上,都需要开放“复制”的权利给辩护人。
其实刑事诉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正式入法以来,跌跌撞撞的10年历程,极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刑事司法于“权力运行”抑或“权利保障”话语之间徘徊的矛盾。新《刑诉法解释》已经生效,可之前的《批复》“三项规程”涉及的相关内容从未被宣布废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能否就此主张权利呢?这些问题都被搁置了。如前文引述的起草小组的“自白”:因为有争议,所以就没写“复制”。从理论上讲,没写明白的权利不代表没有——更何况之前有司法解释性文件“写了”。那么,法官在面对超越“查阅”的权利主张时,能否依据新《刑诉法解释》中白纸黑字的“查阅”权而拒绝该主张呢?
否定掉“复制”权能的意见,完全因循了“可能有弊端所以不能要”的公权力惯性,无论是对于所谓泄露侦查秘密的担忧抑或引发舆情的猜想。如前文所述,在新《刑诉法解释》第55条已经相当严格地规定了相关人员职业操守以及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这种担忧有何正当性可言?笔者再次重申,“复制”权能之于“阅卷权”不可或缺,当然适用于同步录音录像,这一点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法解释得到结论;同时,遗憾地寄希望于下次“解释”能够明确解释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