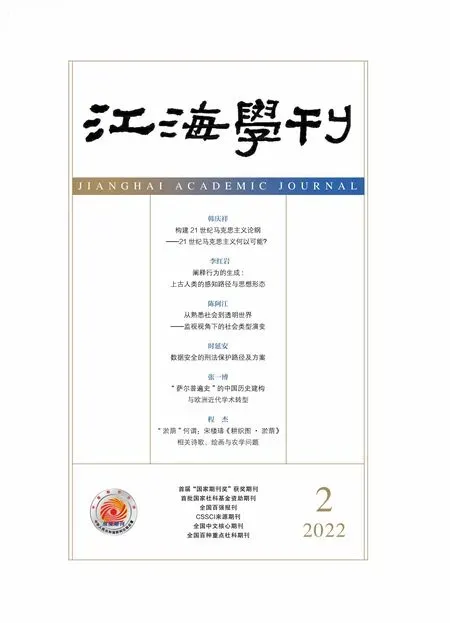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王庆明
引 言
近年来,作为“一种独特研究和书写方法”的口述史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1)左玉河、宋平明:《译者的话》,[美]唐纳德·里奇编:《牛津口述史手册》,宋平明、左玉河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口述史的理解尚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对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似乎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论期待及矛盾:一方面,普通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回想陈述被视为了解历史全貌、洞察“历史真相”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又一直存疑,这不单源自历史学关于“口述能否作为‘标准史料’”的疑问,也源于社会学关于“记忆是根据当下社会框架对过去重构”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从业者不得不面对“记忆悖论”的挑战:一方面,口述史学家认为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得到巩固的长时记忆是稳定而长久的,由此口述资料是可靠的史料;另一方面,口述者在讲述中不断对原始记忆加以重构与创造,从当事人亲历事件发生到讲述呈现的过程中,这些记忆受到神经系统、心理和社会过程的影响。(2)[美]阿利斯泰尔·汤姆森:《口述史中的回忆和记忆》,[美]唐纳德·里奇编:《牛津口述史手册》,宋平明、左玉河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0—81页。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对单位人的口述访谈中,我们也确乎常常会感受到这种张力,但同时也恰恰是这种张力激发我们思考“记忆的社会框架”是如何生成的。
历史当事人的口述以及记忆呈现,不单可以视为一种充满生动细节的历史图示,还可以视为一种缺乏历史连贯性的独特话语模式。作为“企业主人”的单位人,对不同历史时期观察与体验的回忆和讲述,为我们透视单位制变迁这一宏观轨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参照。我们对于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群体的认知,更多依凭的是自上而下的历史记述及宏观叙事。透过这种权威性的历史刻画,我们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波澜壮阔以及工人群体的生产热情。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如果增添新中国工业建设者鲜活的生命体验和个体表达,我们将能更清晰地透视历史变迁的内在纹理和完整脉络。此外,透过工人对单位组织内部生产实践和变革进程中重要事件的回忆和讲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检视理论化的单位人“脸谱”和有关单位运行的规范认识。
主人翁话语背后的身份认知与单位印记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在《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强调,“首先使工人认清自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是企业主人翁的一分子,过去是为日寇、国民党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劳动,现在则为人民大众,为自己而劳动”。(3)《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1948年8月1日),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作为“企业主人翁一分子”的工人不单是公营企业的主人,还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主人翁话语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已萌芽,在边区革命实践中也取得了初步发展。(4)游正林:《主人翁话语的兴起(1930—1949)》,《学海》2020年第1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是企业主人”的主人翁话语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表达是相契合的,前者强调工人是“国营企业主人”,后者强调工人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企业主人翁”的话语是在新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提升工人单位认同度的基础,亦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厂政体和单位体制形成而出现的一种朴素的权利关系的表达。
在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单位组织和单位制度铸造了一种“总体性”的“单位社会”,“单位”是工人群体互动的独特空间。(5)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的单位组织可以细分为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单位三种类型,本文中使用的“单位”若无特殊说明仅指企业单位这一类组织。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工业系统中的单位组织是以“铁饭碗”和全方位的单位福利为制度内核的。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制度文化使单位人的福利配给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与之相关联的是,当时国家针对以“单位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也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集体话语,例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工人老大哥”“以厂为家”等。这套单位人的集体话语构成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在关于工业历史的文字记述中,普通工人往往是被表述的客体,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集体化时代,很多工人的自我体认与集体话语基本上是相契合的,在工人日记、会议记录、工厂厂志、回忆录、单位人口述以及其他档案文本中也可见一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套话语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与单位印记。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人主人翁话语包含着以下三种含义:其一,经济层面,作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单位人不但能获得国家“再分配”的稳定工资和奖金收入,还能获得各类经济补贴和稀缺性单位福利(如免费住房、公费医疗等)。其二,政治层面,社会主义工人作为“领导阶级”不但能直接参与工厂的管理决策,还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表达空间。前者在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中得到了充分彰显,(6)所谓“两参”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鞍钢宪法”的主要内涵是:开展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学习贯彻“鞍钢宪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生产实践环节还是管理决策环节,工人群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在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为重要标准的干部选拔中得以体现。其三,社会层面,“工人是企业主人”不单得到法律认可,还得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认可。全民所有制的单位人身份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地位权”(status rights)。在这个意义上,单位人身份既关乎纵向的社会地位,又关乎横向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总体性的权利束和关系束。(7)王庆明:《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产权结构: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在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鼓舞以及单位日常生活实践的型塑下,企业主人“以厂为家”不单是官方话语的宣传口号,也是工人体现主人翁意识的行动化表达。我们在对鞍钢工人的口述访谈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在“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运动实施的过程中,很多厂长和车间主任会带头把“铺盖卷”搬到车间,住到单位,很多工人也会主动加班。社会主义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成当时集体主义单位文化的重要内涵。在单位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单位人在主人翁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身份产权认知”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单位记忆。只不过在当时并不存在“产权”的概念,在后续国企改革进程中,产权观念与产权话语才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抓大放小、转属改制、兼并重组、破产拍卖等一系列产权变革实践的推进,传统意义上同质性的单位人开始出现分化,单位人统一的组织性身份逐渐消解。既往单位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的视角,(8)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只见制度(组织)不见人的弊端。然而在实践中,单位人的行动逻辑与单位组织的运行机制有时并不一致。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把“单位人”这一个体视角带回单位研究,使单位人口述史成为“后单位时代”推进单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在进行国企工人的口述史调查时发现,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进程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同一行动主体针对单位变革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讲述会因自身个体生命历程的变迁而给出不同版本;另一方面,不同单位人根据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经历,对曾经认同的单位记忆和集体话语展现出反思性的表述。质言之,个体化讲述呈现出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呈现出的社会记忆之间形成一种明显的“记忆裂痕”。此外,同一单位人在回忆同一事件时的不同表述也呈现出一种“记忆的偏差”。由此引发的关键问题是:不同单位人针对同一事件的记忆裂痕,是该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交叉验证”,还是该被视为话语建构的“各抒己见”?而同一单位人针对同一历史事件讲述的“记忆偏差”又如何直面口述历史之“真实性”的方法论诉求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单位人口述和记忆的“裂痕”“偏差”中窥见单位组织变革的微观机制,进而回应口述史的方法论挑战呢?
以上述问题为指引,笔者将从方法论意义上重返单位研究,在回溯既往单位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单位人“脸谱化”的理论面貌,而后结合单位人口述调查来重识单位研究。本研究并不想针对单位研究做一般性的述评,而是试图从问题出发,在考察社会主义工人生命历程的基础上,以单位人口述研究的“田野”经历和经验素材为依据反思单位人口述的方法论问题,努力突破对单位人脸谱化的认知图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回应口述史的方法论挑战。
单位意识与单位人“脸谱”:单位记忆的生成图示
单位体制在我国的产生、延续及变迁有其特定的历史。概括而言,单位制度由战时共产主义的公营企业发展而来,既沿袭了根据地时期的组织管理经验,又参照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历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正式确立。(9)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制度和组织形态,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指出单位体制不仅是中国以往历史和西方社会中不存在的,而且与苏联国营工厂的“一长制”的组织管理结构亦有差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形态。(10)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单位不仅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且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管道,(11)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社会被称为“单位社会”。在集体主义时代,单位是获得一切稀缺性物质资源和政治认可的组织载体,集体认同和单位意识构成单位印记的重要内涵。
单位意识是单位记忆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伴随着部分国企单位的解体和产权变革,学界形成了一套针对单位人“单位意识”的批判话语。这套话语一方面强调市场机制优于单位机制的立场,另一方面则将单位意识视作一种僵化与落后的观念。如果细究“单位意识”的起源和型塑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单位意识是多重文化观念和制度烙印交汇而成的。首先,工厂劳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业主义的协作观念和集体意识;其次,基于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传统而形成的革命主义的服从意识和参与观念;再次,中国家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以单位为家”的传统主义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计划经济前提下积淀而成的集体主义的平均观和依赖性。(12)田毅鹏、王丽丽:《转型期“单位意识”的批判及其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工业主义、革命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四者共同构筑成社会主义工厂内部运行的制度文化基础,进而塑造了一种单位意识。
从产权视角看,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国企单位组织公有产权的建构和型塑过程,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单位组织公有产权的解构和重组过程,“产权型塑”始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线。(13)王庆明:《产权连续谱:中国国企产权型塑过程的一种解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在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前期,主人翁意识和单位福利构成单位体制下产权认知的重要基础;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产权清晰、减员增效、主辅分离和股权多元构成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话语的重要内涵。在单位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单位人的理论形象是标准化和“脸谱化”的。所谓脸谱,是一种传统戏剧演员脸部的绘画艺术,是对戏剧舞台上特定(历史)人物某些基本面貌特征的放大性刻画,例如红脸的关公、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等都是为了凸显历史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曹操的白色脸谱突出了他乱世奸雄的本色,张飞的黑色脸谱彰显了他急躁勇猛的气质。而理论脸谱则是在学术传统和知识脉络下,对事物整体印象和经验感知基础上的概念化提炼和理论化分析。在既往研究中,作为“社会主义工人”主体的“单位人”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脸谱,即“解放”的单位人、“依赖”的单位人和“分化”的单位人,这三种理论脸谱背后展现的是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工人形象”。
首先,作为“解放”的单位人。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公营企业构成单位制传统的重要来源。在“边革命,边生产”的劳动实践中,公营企业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得以锻造和提升。在革命主义劳动伦理的型塑下,主人翁话语逐步演化出两种重要含义:一是关于“企业主人翁”的权利与责任话语,通过工厂管理的民主化以及“完全依靠工人”的群众路线得以强化;二是关于如何使工人阶级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的话语,在进一步推行工人参与管理的实践中,通过切实提升工人主体地位来强化。(14)游正林:《主人翁话语的兴起(1930—1949)》,《学海》2020年第1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通过诉苦、交代和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以实现自上而下建构“新工人”阶级队伍的政治目标。(15)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在这里,作为“解放的单位人”的核心意涵是,企业工人由过去被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底层劳工转变成作为企业主人和国家主人的领导阶级。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产权的政治性重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单位体制逐渐稳固,作为“解放”的单位人逐步演化成作为“依赖”的单位人。
其次,作为“依赖”的单位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的单位体制更加稳固。单位作为国家治理的中介组织,其内部存在着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的依赖性结构。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和对单位的满意度;同时,单位人对获取资源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依赖性行为。(16)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结构性依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特别是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除了工资、奖金、医疗、住房等显性单位福利之外,还存在着诸多隐性的单位福利,单位福利功能内卷化是造成单位人严重依赖单位组织以及国企单位社会成本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17)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85页。基于此,魏昂德(18)关于G.Walder的中文翻译有沃尔德、瓦尔德以及华尔德等,本文引文上尊重其他译者的翻译,在行文中一律使用“魏昂德”。提出了“组织性依附”(organizational dependency)概念,强调“国家—企业(单位)—个人(职工)”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结构。(19)[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8页。单位人除了对单位组织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源性依赖之外,还存在对工厂书记、厂长等主要领导的政治性依赖以及对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直接领导的个人关系上的依赖。这种多重的依赖结构决定了单位人的行动逻辑。“以厂为家”的主人翁意识既是一种朴素的产权认知,也是工人全方位依赖单位企业的体现,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离开单位这个“家”之后就很难生存。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单位体制逐渐松动,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空间逐渐增大,“依赖”的单位人开始向“分化”的单位人转变。
最后,作为“分化”的单位人。在中国单位制改革和市场转型研究中最盛行的分析工具当属倪志伟等人提出的市场转型论。倪志伟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将有利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而相对地不利于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20)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 No.5, 1989, pp.663-681.然而事实上,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一线工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转型红利”,而握有行政权力的“再分配者”也没有变得不利。因此,倪志伟的观点招致了很多批评。边燕杰和罗根(John R. Logan)通过对天津1978年至1993年收入变化的考察指出,中国改革是在两种前提下展开的: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二是城市的单位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各种“单位”仍然是国家的代理人,在这种制度前提下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得以持续。(21)Bian Y. J. &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No.5, 1996,pp.739-758.伴随着市场改革的逐渐深化,同质性的单位人开始出现了明显分化,特别是伴随着企业单位转属改制和下岗分流。“分流”作为“分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使得一部分职工走向市场,另一部分人则继续留在单位。身份不同以及处境不同的单位人对于单位产权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讲述呈现出明显的记忆偏差,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情形。
与这三种脸谱化的单位人形象相关联的是不同的产权话语。“解放”的单位人脸谱强调的是工人的“翻身解放”,由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劳工一跃成为企业的主人,“主人翁”式的产权认知在“工人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认可中逐渐强化。“依赖”的单位人脸谱体现了“国家—单位—职工”三者的独特关系,集体化时代“以厂为家”的主人翁体验既是单位人单位意识的体现,亦是朴素的产权关系的表达。“分化”的单位人脸谱强调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是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而实践中单位人喊出“工人是企业主人”意在突出自身的“终身就业权”。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不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以三种“主人翁”意涵为基础的产权话语对既往研究也构成一定挑战。
既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型塑过程,在时间节点上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主人翁意识的形成和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地位型塑的同步性,(22)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甚至直接将集体主义时代称为“主人翁时代”。(23)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有研究者继续向前追溯,认为主人翁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已经萌芽,在边区公营企业改造时就已出现,特别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改为边区政府后,就意在通过“为革命而生产”的劳动伦理来塑造公营企业工人的主人翁意识。(24)游正林:《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社会》2017年第5期。但这些研究忽略了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主人翁话语会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而发生变化。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在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面对企业产权性质变革、职工下岗以及单位福利消失的压力,一些工人再次喊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口号,意在通过对自身企业“主人”身份的重申,强调他们对于企业组织的身份产权。(25)王庆明:《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这实质上已不是集体化时代的主人翁话语表达,而是职工基于自身处境和利益对就业权和福利权的强调和诉求。由此,问题的关键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政治体制连贯性的双重前提下,如何理解两种不同版本的主人翁话语以及由此构成的单位记忆呢?既然口述历史是个体生命历程独特的再现方式,那么又该怎样弥合记忆的裂痕并透过历史的缝隙拼接出清晰完整的历史呢?
记忆的裂痕与偏差:单位人的反思性讲述
口述史一般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事情的回忆和讲述,研究者通过访谈获得的口述史料,是对文字历史的重要补充,这与讲述者自己并未亲身经历而仅是耳闻的传说故事不同。(26)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换言之,口述史是研究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的方式来透视历史事实和具体情景的方法。很多研究者坚信,口述的意义蕴藏在讲述、记录的过程之中,透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切近地感受历史。然而,实践同时也表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往往只是说其“一家之言”。无论是“有意为之”的话语建构,还是“无意而为”的自我表达,都呈现出当事者对历史的创造或者对历史的“再造”。(27)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通常,话语模式是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表达,也是实际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它揭示了历史演进的独特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就是一种“史观”。国家权力型塑下的主导性话语以及普通人生活世界中的日常性话语是透视完整历史画面的两条线索。
不同时期的产权话语和工人们的单位记忆既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工业化整体历史进程的重要路径,也是透视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视角。在整体性的单位制逐渐解体这一事实前提下,单位人口述成为透视新中国工业历史脉络,窥见制度变迁内在肌理的重要窗口。口述者针对历史的“建构性讲述”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本身的形态和面貌。无论是针对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不同时空条件甚至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亲历者都会产生记忆上的“差异”。这一点在我们对单位人的口述采访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一方面,很多单位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对单位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线索清晰、绘声绘色;另一方面,很多当事人都试图强调个人的作用以及自身的生命历程与这些重要事件的“特殊关联”,有意无意地突出自己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此外,在我们对单位人回访的过程中,同一行动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同一事件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口述者的“记忆偏差”通常会让研究者面临一种悖论式体验:研究者试图通过口述史来了解真实的历史,但口述过程本身可能是偏离历史真相的建构过程,“回忆的真假”叠加着“历史的虚实”让问题更加悬而未决。这种难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似乎并不罕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过去历史”与“现在体验”之间的互动。
通常,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体认,又服务于现在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框架。(28)[英]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页。由此,当我们不得不对口述内容和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作出判断时,我们必然面对“客观真实性”和“主观真实性”两种类型。(29)[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虽然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研究集体表象的重要性,但就知识产生过程而言,集体记忆的社会学和个体记忆的现象学之间很难说孰优孰劣。(30)[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单位人情景化的个体记忆与官方话语构成的制度化的集体记忆各自都有存在的价值。个体记忆有时和集体记忆并不完全一致,二者的分裂恰恰是反思历史逼近真相的可能路径之一。由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单是历史的虚实,而是短暂的个体生命历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是如何彰显自身存在的?或者说普通人和“无名者”的底层记忆如何能在官方话语和主流记述之外留有“一席之地”?这不单关涉如何看待历史的视角问题,亦涉及如何创造历史的行动问题。
虽然记忆的完整图景以及历史真相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一种“虚构”,但我们终究要直面历史。无论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还是我们“绞尽脑汁思索的历史”,(31)[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第1页。都要以完整清晰的记忆为前提。通过单位人对社会主义工厂内部生产实践、劳动过程、管理模式、社会动员以及情感互动模式的体验与回想,我们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历史,即可以捕捉到国企单位产权制度变革这一宏观历史脉络下的微观机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产权的政治性重构,强化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历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改革,针对国企收益权的“利润留成”改革、债权转股权以及职工持股的“股份制”改革、国企资产重新界定的“主辅分离”改革以及当下的“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等,这些变革试图通过产权的清晰界定来提升企业的效率和内在活力。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职工的“身份置换”和“股权置换”是国企产权变革的双向进程。在国有企业的产权重构以及产权关系变革的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产权话语构成产权变革进路的重要表达。在经历了各种产权改革的洗礼后,单位人口述也呈现出一些新的个体化表达和反思性讲述。
集体主义时代的记忆裂痕不单表现在个体行动层面,也表现在国家制度层面。苏联解体之后,原本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对共产主义文明历史的共同经历以及苏东剧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有很大不同。不同国家的记忆规训以及由此产生的记忆裂痕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前的历史有紧密关联,如俄罗斯在经历了相对彻底的产权私有化之后,对社会主义记忆的积极表述更多聚焦于对过去“帝国权威的怀念”以及对集体主义安全的眷恋,而中欧一些国家努力抹掉社会主义印记的意图呈现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32)伊万·塞勒尼:《中文版序言》,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一些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的转型轨迹和发展历程重构共产主义文明的集体记忆,揭示了记忆分裂的主体不单是个人,还可能是企业、国家等组织类型。由此可见,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个体化的回忆与制度化的官方话语为基础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历史缝隙恰恰是透视历史真相的一种可行路径,这也是普通人口述的独特意义所在。
余 论
透过对单位人产权话语与单位记忆的考察,我们发现,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有很大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是企业主人”的话语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表达相契合,“国营企业的主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相统一。“企业主人翁”不单是自上而下贯彻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宣传话语,也是工人朴素的产权认知和单位认同的基础。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不同社会处境的单位人也开始反思主流话语所建构的单位记忆的内涵,这表现为福柯所说的对抗主流叙事整合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过程。这种“反记忆”讲述呈现出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呈现出的社会记忆之间形成一道“记忆裂痕”。此外,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有时也会给出不同版本的回忆内容,这不单是因为时间久远而产生的记忆的模糊化和碎片化,更是讲述者主观建构的“记忆偏差”。透过不同立场的记忆呈现,我们可以窥见市场转型以及产权制度变革这一宏观进程的不同轨迹。
无论是“记忆裂痕”还是“记忆偏差”,都是理解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的重要图示。不同的记忆呈现及由此生成的可供比较的两种历史叙事是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口述历史一直面临着“记忆悖论”的方法论挑战,即历史“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平淡谦卑的“小写历史”,还是未来主义取向的“大写历史”,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都是一种具有内在方向性的运动,是一种有问题意识的“利益”表达,通过建构“真实的过去”来达致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33)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并不存在公认的定义,也不存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规范。但无论是历史学处理记忆的方法还是社会学处理记忆的方法,都要面对一个共通性的问题,即如何将记忆研究中的问题概念化。因为,对记忆的思考冲击了对于历史本身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思考。(34)[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换言之,对记忆的生成、表达以及真实形态的反思直接关涉知识生产过程这一根本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箴言:“要进行回忆,就必须能够进行推理、比较和感知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记忆的完整性。”(3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